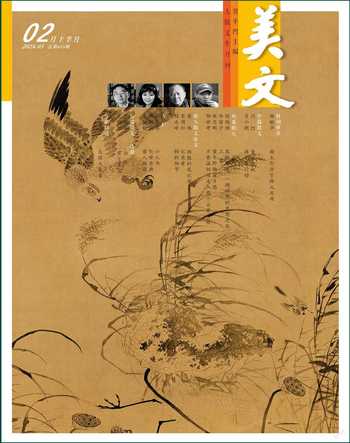童年野趣留乡愁
侯志明
成都的雨
对我这样一个出生并长大在荒漠草原的人来说,成都的雨是别致的。
成都的雨完全不同于家乡的雨,除夏季的极端天气外,一年四季多数时候是润物无声的小雨。
在我的家乡,年降雨量大概在130毫米左右,超过250毫米的年份极少,雨是相对稀缺的资源。一滴雨下下来,无论是经过树梢还是径直穿过空气,都会在泥土中滴出小小的坑,大如纽扣,小似黄豆,好几天不会消失;即使滴在石头上,也要带上泥土的印迹,这是雨的踪迹吧,仿佛在告诉人们:“这次我们下得不少呢!”
成都的雨不是这样的。成都一年中从天上降下来的雨几乎是我家的十倍。没有风尘,每一滴雨都是洁净的,落到地上也不会留下其他痕迹。
我家的雨总是和冷空气裹在一起的,下着下着,雨就会变成冰雹;也总是和风裹在一起的,所谓风雨交加一定说的是我们家的雨。成都偶尔会有疾风暴雨,有时甚至非常狂躁,但不经常。当成都下起这样的少见的雨的时候,我常常辨不清南北东西,更不知身在何处。
我家的雨,也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时候浓云密布电闪雷鸣,看着盼着要下雨了,却滴了一两滴,就随风而去无影无踪了。有时候下着下着就下出了太阳,真的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后来我发现,我家的雨是急就的,成都的雨是充分酝酿的,是要先把云彩一缕一缕地拼块,一块一块地铺开,一层一层地摞起,才开始慢慢地下。因为准备充分,一下就是两天三天或者更长。
“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杨万里的这首诗虽不是写给成都的,可成都的雨与之类似,不分季节。
在成都的雨中漫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成都的雨是十分柔软的,落在身上几近没有感觉。它很温柔,很绵软,即使冬天也没有多少冷意,却总像有一只手在轻轻地轻轻地抚摸。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感受。如果在享受着这种感觉时,还有闲情逸趣留意你的前后左右,你会看到挂在尖尖的青草上的雨滴,那样晶莹剔透,像刚出生的婴儿酣睡在母亲的怀抱里,不用担心风的干扰。你会看到紧紧抓住一朵鲜艳玫瑰或者莲花不松手的一连串的雨滴。落在所有花上的雨滴几乎都是一串不是一滴。不知是花迷住了雨,还是雨迷住了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会忽而出现在你的眼前,忽而出现在你的脑海。
在成都的小巷或者公园,你还会看到,穿着短裙或者旗袍,打着一把伞在雨中缓缓漫步的女子,你一定会把她想象的像这小雨一样柔软、细腻;一定从她轻盈缓慢的步履想象过她的美丽和忧郁。想着想着就会进入民国的文人在我们的心上刻下的那种特有的情调。是的,就是一种情调,附着诗意的情调。此时,就连知了也会痴迷地忘了歌唱,静静地陶醉去了。
小雨,也许是因了自己的细碎和准备充分,下起来就没有要停的意思。老成都的市民,可能都读懂了唐寅的那首“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的词,也可能最知道成都的雨的习性,所以他们从不等待雨停了再走出家门去。他们总要在公园里头、小巷深处撑一把大伞,或者坐在湿不了身的屋檐下,穿个短裤汗衫,趿拉个拖鞋,翘起二郎腿,有一下无一下摇着蒲扇出来品茶、打望、摆龙门阵、掏耳朵。细雨中,密密麻麻的大厦高楼也不像往常那么晕眩,脚打后脑勺的生活节奏也会放慢。你会觉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成都。
所以,成都的人,即使这样的雨连续下个十来八天也并不烦躁。有这样的景致烦躁什么呢?
就连成都的农村也会在细雨中展现出一幅头戴斗笠身着蓑衣点缀在花草中的油画般的美丽。仿佛王建的“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写的就是雨中的成都一景呢!
如无雨中漫步的经历,是无论如何读不懂成都和成都的这种诗意和情调的。这种情调只能生长在类似成都这样的雨中,或者类似这样雨中的成都。很难想象北方能出现这样的情调。
成都说自己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若问为什么?官方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既宜居又宜业;民间会绘声绘色地告诉你。既好吃又好玩。而我却总以为这样的答案太过简单、功利而并不完整,至少还得加一句:有诗意有情调。包括这雨中的诗意和情调。
这也恐怕是自古以来文人的共识。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是写成都写得最好的一句诗,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写成都的花,那就错了,杜甫写的是成都的雨。
成都的雨是恰到好处的,是浸泡在诗画里的,是令人陶醉的!
成都听雪时
我从来不曾听到过雪的声音,在成都这场罕见的“大”雪之前。
这场雪一定给成都人带来不少惊喜、欢乐,也留下了十分闹热的印记。仅从微信被反复的刷屏就足见其受关注的程度。下到成都的雪,受到如此热情的款待,不知他处有过否?也不知是否有点受宠若惊?成都却着实因为这场雪兴奋了一天。
看成都的雪,不, 应该是听成都的雪。成都的雪稍纵即逝很难看到,只能听。听人们的惊喜惊异,听人们的赞美抒情,听人们的小题大做。用一句成都的方言说,一时让人搞不懂是成都闹麻了雪,还是雪闹麻了成都。就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刻,我看到了山西作家、挂职四川的李俊虎先生写的一首打油诗,名曰《蓉城初雪》:“成都初降雪,拥书懒出门。满城雀跃者,不是北方人。”
這首诗我为什么记住了,因为暗合了我当时的心态。由是,想到了塞北的雪、老家的雪。
的确,对于一个北方人,至少在我塞北的老家看来,成都的这场雪,是不能称作“下”的。只能说“飘”了点雪花,或者连“飘”也谈不上,只能说“斗了点清雪”。是的,是“斗”,这个字很准确,有点逗弄、戏弄、逗你玩儿的意思。下,是持续不断的、厚厚实实的、无声无息的、遮天蔽日的、到处弥漫的。我出生在雪域高原上,从大人们的对话中早已懂得了“斗”“飘”“下”的含义。他们经常会说“斗了一下午的清雪,晚上又飘了那么多雪花,夜里要——下——了”。他们会把“下了”两个字的声调拉得很长,那当然是在强调判断的准确。我就会明白,也许只要个把小时,雪就可以把多彩的大地涂成白茫茫一色。
如果连下好几天,大地会被雪厚厚地完全覆盖。没有大风,雪会纹丝不动地趴在地上。只有风来了,雪才会被吹到沟里、墙下、山崖边,或者依托一丛丛相连的荆棘,自己堆积成一座雪山。
雪覆盖了大地后会给所有的动物带来生的困难,但给我们漫长的童年岁月也带来了不少的欢愉和闹热,这种闹热绝不是成都式的。
野兔子是草原上的一种小动物,平时难得一见,但在大雪覆盖了草原后,到处可见。雪停的清早,它们就会急急忙忙地跑出来觅食,就会把自己鲜明的足迹清晰地打印在雪地上。你若跟着雪地上的蹄印走,一定会找到它的老巢,活捉一两只也绝不意外。饿极了,它们会不找自来,悄悄地潜入你家的羊圈牛圈马圈或者柴草垛里。如果你有准备,先把门关了,那一定是瓮中捉兔。肉可以大快朵颐,皮子还可以做成帽子、手套。那时你真会感谢大雪的恩赐了。
树上积雪后,鸟也失去了最后的觅食处。这时,只要你用铁锹铲去了覆盖在地上的雪,露出黑色的土地,哪怕只有一小片,也会白黑分明格外显眼。鸟的眼一定比人的尖,它们会立即发现,等你一离开,马上就一窝蜂地涌来。这时,你只要放上捕鸟的器具,就会有不小的收获。捕鸟都有什么器具呢?说来也简单,只是一块安了套线的木板。这些“器具”谁发明的我没有考证过,但我们用的都是自己做的。随意找一块两尺多长、半尺多宽的木板,铰几根马尾上的长毛(最好是白色的),然后把马尾毛两根并一根,搓成线,做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可以收缩的小圈,用锥子在木板上锥一个半厘米深的眼,把小圈的一头塞到那个眼里,再把一小块蘸了水的棉花填进去,用锥子锥实锥紧,放在外面冰冻,器具就做好了。把做好的器具拿到铲出来的土地上,用土虚掩一下,使鸟们不至于害怕,然后撒一点小米之类的鸟们爱吃的食物,你就可以躲起来了。你会看到一波一波的鸟飞过来,落下来,疯狂夺食。这时,总有鸟会被套住,且越挣扎越紧。这时你就可以冲过去整理你的战利品。往往不是一只,有时候会是两三只。收获了这一波,再等下一波,如是往复,一天下来,最多时可以捕获几十只。我记得那时我们捕获的大多是画眉、麻雀等。也套过野鸡之类的,除了需要更结实的工具,套路是一样的。
这几年,北方的雪也在减少,而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却在增强,曾经的捕鸟野趣也就随着我们这代人童年的消失而消失了——而且也早该消失了。
我们的村东有一条河,冬天会形成厚厚的冰,雪一下,冰面分外得滑。那是孩子们天然的滑冰场。整个寒冷的冬天,孩子们的大多数时间在这里度过,每天几乎要到冻红脸冻痛脚肚子饿才悻悻地走回家。这种玩法在北方至今还能看到。
有一年,雪大,几十只野黄羊从北山上冲下来,在人们的追赶下,有一只跑上了冰面。出乎意料的是,在雪地里、土地上飞奔的黄羊,一踏入结冰的河面,就完全不能自主了,一动就摔倒,摔了几次,或者是摔痛了或者是摔累了,只好一动不动地趴在了冰上。看到这一幕,追逐的几个年轻人激动万分,如获至宝,解下自己的裤腰带,牢牢地拴在羊角上,准备把它拖出冰面,拖回到村里。他们没花多大的力气就把猎物拖出冰面,可哪里料到,这头黄羊一离冰面,就展示了野性的力气和威猛,连冲带突,几下就战胜了几个手提裤子的男人,扬长而去了。这几个男人也因此成为一个笑话,常被村人说起。
雕雪人,也是童年时年年要做的事。我说是雕雪人而不是堆雪人。我们家的雪厚实而粘连,时间长了,会挤压得如冰块。只需用铁锹切割一大块雪,把它立起来,然后用工具精心雕出一个完整的人。完全不似鲁迅说的堆一个上小下大、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的雪人,而且还要谁家的大人来帮忙。我就曾独自做过高达两米多的雪人,找一个旧帽子给它戴到头上,安两粒羊粪当眼睛,安一粒马粪做鼻子,插两个树叶子当耳朵,然后掏一个大大的嘴巴。这件事一般是在腊八前做,腊八的早晨要把红粥喂进它的大嘴里。寓意是什么不知道,但那白的雪人,红的粥,对比分外显眼,如今依然藏在记忆深处。
北方的冬天,下了第一场雪后,家家户户就陆陆续续开始杀猪杀鸡宰羊了。如果不杀,天太冷,所有的动物都会一天天瘦下去,这一点不比四川,要等到春节前才宰杀。那时也没有冰箱冰柜,杀好的鸡羊猪就只能埋进雪里保存,就如南方只能烟熏了保存。这样的事我没少参与过。先在地下铺一层干净的雪,把要埋的肉放进去,再在上面盖一层干净的雪,然后在雪上面澆一些水。这样,一个坚固的冰窖就形成了。没有专业的工具,是无法轻易打开的。所以也从不担心狗之类的食肉动物的侵害。这种天然的雪藏方法怕是如今号称最环保的冰箱也无法比拟吧。
雪,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种独特资源。在赐予资源的同时,也赐予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成都听雪时,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早就跑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地方是雪的故乡。那地方,不似成都,雪是从不稀缺的。而在新年之际,把这种北方独有南方奇缺的东西作为一份礼物赐予了成都,我便觉得大自然对成都的偏爱有点露骨而不含蓄了。
凡是赐予,都须感恩。而成都人的闹热是深切饱含了这样的意蕴和情感的。
雪落无声却有痕,这是在北方,可以看。
雪落有声却无痕,这是在成都,只能听。
瞧吧,2021年这场早来的雪,一定是丰年的吉兆。
成都的春
立春一过,我总要向外地的朋友发出邀请:来成都玩儿,不要错过最美的季节。多少年来一直如此。
是的,在我看来,立春前成都太过寒冷,立夏前后又太过炎热,只有立春过后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冷不热气候宜人,万紫千红景色迷人,是成都最美的季节。
成都的冬天是由立春的到来宣告结束的,此后气温出现明显变化,会从原来的十摄氏度以下,一下子升高到十几摄氏度甚至二十摄氏度,弄得很多还包裹在大衣大氅里的人措手不及。但不是所有人,尽管还有乍暖还寒的日子,一些如春一样蓬勃的少男少女们(也许不完全是少男少女)会相时而动立即换装,短衣短裙短裤、蕾丝长袜,还要将本来就遮不住肚皮的衬衫挽个疙瘩,悬在肚脐眼之上,千方百计亮出更多白嫩的肌肤,充分沐浴春光汲取春的养分。感觉整个城市陡然间因之而青春了很多清爽了很多。
苏轼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城里的春却是少男少女最先知。
立春前的雨没有规律,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立春后的雨多是下在夜里,下得温柔静谧细腻。估计上千年了,一直是这么下的,否则不会有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不知道这雨是不是怕伤到正在含苞待放的花蕾?是不是怕占用了白天的明媚春光?
夜雨驱了雾霾,也把所有的树木、花草清洗了一遍,甚至包括空气,所以春日雨后的清晨是格外清新的。和阴沉沉湿乎乎冷飕飕的冬天比,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走出家门,由不得要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了,这时便懂了沁人心脾的含义。不但沁人心脾,也赏心悦目。如果你留意,总有几滴没有来得及躲起来的雨,还挂在待放的花蕾上、树梢尖,晶莹剔透、恋恋不舍、欲说还休。总有几只早起的小鸟相互拍打嬉戏、叽叽喳喳、飞来飞去。此时,即使你不说出口,也一定会在心里想:春天真美!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这是又一位川籍文豪张栻对春的感叹。
花渐次开放了,最先开的大概要数水仙花、梅花、迎春花。红色艳丽的水仙花除园林家庭外不多见,但梅花、迎春花处处都有。蜡梅花更会在立春前绽放。
立春半个多月后便是雨水,雨水一到,雨量明显增加,加上气温升高,更多的花都会开。如粉红色的樱花、桃花,白色的梨花。
这样明媚的季节、清新的季节、花开的季节、温润的季节,城里人最先待不住了,三三两两地约了去踏春、赏花、品茗、晒太阳、放风筝。很多人恨不得临时安一个“家”在这春天里,于是支起帐篷、铺好气垫、安好炊具、备足食材,还有红酒啤酒,老老少少地集结于这个只属于阳光、花的时光。这种氛围,这种景致,你会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没有忧愁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只有生机的季节。
这个时节,我一定不会待在屋里,无论如何都要走出家门,而且很急迫,因为我知道成都春的矫情和短暂。我可以不去很多地方,但必须到乡村去,去看一种花,一种不会开放很长时间的花。她(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不名不贵,不娇不艳,无人不识,甚至很难称得上花。但我与她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曾因特别的情感为她写过两首蹩脚的打油诗。
其一
春风带雨来,
春神喜徘徊。
遍地金黄色,
此花是谁栽?
其二
春风吹百花,
赤橙蓝紫开。
金黄一怒放,
占尽大舞台。
什么花?油菜花。谁栽的?老百姓。试问哪一种花敢和它较劲儿?那么金黄灿烂、那么耀眼夺目、那么为数众多、那么辽阔无垠。我确实是喜欢油菜花的,喜欢它平凡普通,色彩单纯,不妖不娆,不娇不嗲。无论高山平原,无论悬崖沟壑,都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夺目的色彩。我甚至坚信,成都的春天可以没有许多花,但不能没有油菜花,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我经常会在比我矮不了多少的油菜花间漫步,任凭黄色的花粉沾满我的衣裤。只顾吐纳菜花的醉人香味,静观蝴蝶的上下翻飞,凝视小小的蜜蜂不住地搓着两条细长的腿、撅了屁股、专注于4 只花瓣托举的花蕊。看着看着便想起吴承恩的那首《咏蜂》诗:“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寻香似落星。小小微躯能负重,器器薄翅会乘风。”
我还会折一截鲜嫩的油菜杆儿,剥了皮,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那种略带微辣的清香是独特而可以回味的。我猜想没有人吃过这种东西,因为有一年当我这样做时,几位朋友大吃一惊。而我是打小就把家乡的油菜杆儿当美食当干粮的。
油菜花开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半个月左右吧。一不留神它就走了,会把金黄涂成墨绿。这时在我的心里成都的春天结束了。此时此刻,我会无意识地反复默诵“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的古词。这是黄庭坚的叹惋,春来春又去,年年岁岁,春去春又来,岁岁年年,实在不知道共振了多少人的同频情感。
说成都的春一眨眼就过,有点夸张,也并不过分。
成都的春是短暂了一点,但风姿绰约、生机一片,令人心旌摇荡!
童年野趣留乡愁
有人终其一生要努力挣脱的事,有人会花大量的钱财去追逐;
同一件事,对有的人是无奈,而对有的人则是浪漫。
——题记
所谓乡愁,应该是以童年的记忆为主吧,而记忆的组成一定有野趣、苦涩和艰辛,也一定有快乐!
我出生在乌兰察布草原一个半农半牧的家庭里。荒漠半荒漠的草原禀赋,決定了所有植物动物和所有生命的生长方式及姿态。当它们没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和改变时,它们必须用所有的精力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努力不要被淘汰。
上高中前,也就十五六岁时,我在缓慢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渐渐学会了做农牧民要做的大多数活儿。比如放马放牛,放猪放羊;扶犁耕地,种地收割,骑马驾车;我甚至学会了杀猪宰羊,剥皮剔骨,刮肠子倒肚子。那时还没有拿到初中的文凭。
大约是十一岁时的一个暑假,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姓郝的皮匠手里,希望我能学点儿手艺。在这个偏僻如隐居、封闭如隔世的贫穷地方,也曾读了一点儿书、识得几个字的父亲虽然很重视孩子们的读书,但也不得不做“两手准备”——万一读书不成,好有个谋生的“伎俩”。我大概只待了三天,有一天中午,趁人不备,偷偷用刀在自己的手上划了一个小口子,然后就哭着逃了出来。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改革,还没有包产到户,仍是大集体。所有集体的事,家家有任务,娃娃也不例外。
我逃离了臭烘烘的皮匠坊,却逃不脱摆在面前的种种苦力活儿。贫穷的家庭养不起一张吃闲饭(不干活只吃饭)的嘴,哪怕他才仅仅十来岁。面对这些苦活儿,我唯一能做的是靠自己精瘦的“智慧”在众多的活儿里选择最不苦和好玩的活儿,而且我成功了。今天看来,我实在是“聪明”得很。
每年暑期,正是塞北作物收割的季节,拔麦子、割莜麦、挖土豆都是苦力活儿中的苦力活儿,这时也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为了逃脱这些苦力活儿,同时为了过骑马的瘾、好玩的瘾,我和另一个同伴就去说服生产队长,把放马放牛的活儿给我们,让原来的牛倌马倌去地里干更苦的活儿。队长抠抠脑袋,可能觉得两个娃娃可以顶替两个大人巨划算,也就在疑虑中答应了。所以,从八九岁起,我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放马、放牛、放羊的童年生活。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仅限于暑期。当时的生产队大概只有四五十匹牛马、两百来只羊。
当年的放牛放马,也确实是生产队最俏最轻松的营生。
生产队的牛马,除了冬天之外,平时都圈在两个土坯围起的围墙里。有时候牛马是分开的,有时候又是混在一起的。每天早晨出圈,中午回来饮水休息,下午两点多再出去,太阳落山后回来。
当了牛马倌,第一好处就是自己可以选择确定一匹坐骑,没有坐骑追赶不上其他的牛马。坐骑的背上要捆扎一条羊毛擀的毡子。一是当马鞍用,使骑马的人尽量舒适;二是下雨挡雨,冷冻防寒,穿在身上像斗篷,鋪开的功能大致如今天驴友们的帐篷。还有一件东西,就是一根鞭子,鞭子是由鞭杆和鞭梢组成的。鞭杆大约八十公分长,材质要好,还要打磨光滑。鞭梢是牛皮拧成的,上粗下细,有长有短,长的有四五米吧。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打得响亮、打得疼打得狠,鞭子的末梢还要接上一种更细更结实的“道梢”(当地语)。我八九岁时就会挥动长鞭,不但打得清脆响亮,还打得准,可以在四五米远的地方,准确打死一只小小的蚂蚱。放牧,鞭子摔不响,似乎也压不住阵,因此,每次出场,都要把鞭子摔得震天响。回来也要脆生生地摔几下,让人们知道:我回来了。
骑马对一个内蒙古草原的男人来讲,是必修的科目,我大概在八九岁就可以独自骑马了。我们小孩子骑马是从来不需要什么鞍、韂等装备的,即使有,大人们也不会让我们用,理由是为了安全(当然也有舍不得和怕弄坏的意思)。我们只须有个缰绳,就个高台一跃而上,信马由缰。尤其是几个小伙伴相约比赛,那真是策马扬鞭、四蹄生风、好不威武,真有草原英雄的感觉。因为人小份量轻,腿短夹不住,经常会从马背上摔下来,也因为没有鞍韂等羁绊,人会掉得利索,不会被马拖行而受伤。我是屡掉屡骑,骑到屁股出血,不能坐行,只能躺着。这对一个想学会骑马的人是必须的历练,否则是成不了骑手的。这也是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最大的快乐之一。
在野外,我们有时候会逮一头一岁多的小牛或小马驹来骑,为此,常常会跌得鼻青、脸肿、腿瘸。这是孩子们的常事,大人们也很少过问责怪。
塞北的草原既辽阔而深邃,又遍布山峦沟壑,这其中隐藏着多少秘密,我至今难以说清。
放牧之余,我们经常在草丛里、河沿边、崖缝中寻鸟窝和捡鸟蛋。鸟类虽然不同,但窝大体是一致的,都是安在可以遮风挡雨的石板下、悬崖缝、树木边、蒿草里。窝有大有小,但都是圆形的,外边由较粗的树枝编织,里面是柔而细的草木,有的鸟在细软的草木上还要垫一层羽毛。那时生态好,鸟类多,常有不期之遇。我遇到过的鸟窝最多的有十几枚蛋,最少的也有四枚,而且很少有单数。也遇到过已经出壳的小鸟,待在窝里睡觉,听见响动便会一挺一挺地爬起来,张开红红的嘴,等待食物。也遇到过正在孵化的。而我们寻找的是还没来得及孵化的。怎么辨认孵化没孵化?你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枚鸟蛋,手搭凉棚,冲着太阳,闭一只眼观察。如果里面发黑了,那就一定是孵化有日了。如果是清澈的,那就是没有孵化的,这时我们会摘下帽子,全部拿走。我们在做这些时,总会看到有鸟在身边飞来飞去并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是啊,毕竟鸟的一个窝就像人的一个家,推人及鸟,这种做法也是很残忍的。
进入秋季,牛马的活儿逐渐多了起来。白天,耕地、拉脚、碾场持续进行,牛马吃草的时间基本被“工作”挤占,晚上赶着牛马吃夜草就成了必须。我十岁多一点儿就独自一人在夜间放过牧。有一次,把牛马赶到坡上后下起了雨,我就裹了雨毡在一个地垄里躲起来,没想到太困了,居然睡着了,天快亮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没有一匹牛马。可以想见我急成什么样子。好在先辈的智慧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我渡过难关,他们很早就发明了给爱偷跑的牛马戴上一个铃铛的土法。夜深人静,声音分外响亮。我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便循声找到了我的牛马。但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牛马找回了,却吃了邻村的庄稼,第二天便有人找上门来。好在是乡里乡亲,赔个不是也就拉倒了。
夜间放牧,难免遇到难挨的饿肚子的情况。我们会潜伏进生产队的菜园子偷。其实,那时的菜园子也只有萝卜、白菜、蔓菁、葱、土豆等。土豆是不可以生吃的。我们会捡来干透的牛粪,用火柴点燃,再把偷来的土豆放进去,熟后不但可以充饥,那味道也比今日裹了味精的烧烤好得多。我必须承认,想方设法偷食生产队可食用的东西也几乎伴生了我饥饿的童年。我的两个放牧的小伙伴,为了填饱肚子,就曾以调虎离山的计谋,上演过一出堪称完美的“偷”的恶作剧。那是一个中秋节的下午,他们踩盘了一个看园子的老人的小屋,发现老人正在切肉剁馅准备包饺子。他们很兴奋,就在附近隐藏起来守候着。天色黑净后,老人开始煮饺子,刚刚煮好出锅,外面响起偷东西的声音,于是老人冲了出去,冲着一个人影追过去。结果不但没有追上“小偷”,回到小屋却发现饺子也没了。
在我所有放过的牲口里,猪是最容易放的。赶出村,圈到一个河湾里,最好是有水或潮湿的地方,它们就会拱出一片地,倒头大睡,从不乱跑乱闹。羊最不好放,它们一出群,就从不停歇,一边吃一边走,从早到晚。一个牧羊人一天至少要走上十几公里,没有一个好身板,几乎难以胜任。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着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
这是描写草原最美的歌,是我童年唯一会唱的歌,也是常常把我带入无边想象的一首歌。
在轻风吹拂、绿草如茵、小河蜿蜒、百鸟飞翔的无垠草原上,白日里,我经常躺在草地上,头枕双手,看湛蓝的天空上朵朵白云飘过。看着看着,会把自己想象成孙悟空,威风凛凛作福花果山,腾云驾雾大闹蟠桃园;夜晚间,又总爱靠在大石旁或敖包下,裹紧雨披,托着下巴,盯住月亮,想象嫦娥如何广袖长舒,何时重回人间。
蓝天和大地,虽然人的生命须臾不能离开,但我从来没有像童年时那样亲近过。
放牧其实是孤独和寂寞的,你可能一天也找不到一个说话的对象。而过于孤独寂寞,如果不能把你变成一个傻子,就有可能把你变成一个有“怪癖”的人。就在那些年,我养成了观察蚂蚁劳动的爱好。我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黑蚂蚁、白蚂蚁、红蚂蚁一律称作黑军、白军、红军,看它们如何从洞中用嘴含出一粒粒土,整齐有序地垒在洞口;看它们如何协作,将一只比自己大几十倍的昆虫从很远处搬到“家”门口;看它们如何保护繁衍生命晶莹剔透的、白色的蛋;看它们如何在大雨来临前,将自己的“家门”(洞口)堵得严严实实。看这些仿佛看一部彩色电影,入戏深时甚至亲自参与动手帮忙,痴迷地忘了牛马倌的职责,直至惹出祸来,被人喊醒。
蚯蚓也常常吸引我的注意。一位北京的知青,大概是一位昆虫爱好者,他曾做过我的小学老师,给我们讲过蚯蚓的故事,让我知道蚯蚓不但是少有的雌雄一体的昆虫,而且它非常胆小,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敏感近乎有特异功能,即使小小的地震和地表的震动,也绝对会使它们破土而出来到地面。有很多的鸟类,正是掌握了蚯蚓的这一习性,经常在松软的土壤上啄出或敲出响动,引诱蚯蚓出来,然后当美食把它们干掉。是否确实如此?我至今不得而知,但为印证老师的观点,我在当牛马倌的几个暑期,确曾因痴迷而使用了大量的时间。
我至今不喜欢野营和住帐篷,完全和我从小夜间放牛放马有关。前两年,夫人赶时髦,花了不菲的钱买了一些野外用的帐篷,多次动员我和朋友们野营,我愣是一次没去。夫人曾多次问我原委,我都顾左右而言他,从未回答过。有一次,她“威胁”说,我不去朋友们就有意见了。我才向她坦白:我从小夜间放牛放马,八九岁就裹个雨毡在山坡上、树林里过夜,遇到过蛇,遇到过狐狸,遇到过刺猬,遇到最多的是我十分讨厌的老鼠,担惊受怕的阴影至今折磨着我。我之所以要发奋考大学,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不再到野外过夜,如今好不容易熬出了头,还让我花钱去受“二茬罪”,坚决不干。
妻子听后大笑。
是的,生活已经告诉我们,有人终其一生努力挣脱的事,有人会花大量的钱财和精力去追逐。同一件事,对有的人是无奈,而对有的人则是浪漫。
我受到的最深刻的童年教育就是充满野趣、充满艰辛、充满苦涩的生活。当然也有快乐。这快乐同样来自为了生存的拼搏和挣扎,来自童年的野趣。如果把这快乐比作荒漠草原上稀少而珍贵的雨水,那么童年的艰辛、苦涩就是撒向植物的有机肥,尽管味道不佳,但对植物的茁壮生长大有益处。
童年的野趣留乡愁。留住乡愁,就留住了一份珍贵的记忆,而珍贵的记忆会不知不觉地发酵成一缕光芒和智慧!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