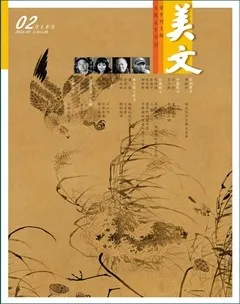南太行方言释义发微(上)
杨献平
整啥唻
露水打湿裤腿,冷风一下就钻到肠子里了。再或者,昨晚的汗水还黏糊糊的。一年四季,人间的气温,和人的感觉总是迥异的。类我们南太行这个地方,四季太过分明,好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某些疆域与壁垒。太阳升起,人们在村路或者田间相互遇到,都会说一句:整啥唻,或者恁整啥唻。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同,都是询问对方去干啥。相当于城市人之间某天初次见面,相互问你好之类的。
人生总是一天一天过的,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时间最公平。黑夜像一群幽灵,被晨曦驱赶之后,余下的,就是光了。人起床,去茅房解决了废物问题,再回来,胡乱洗一把脸,再沾湿了毛巾,把脖子和胳膊等明显处擦一遍。女人开始抱柴火,提水做饭。男人则提着镰刀或扛着锄头下地去。孩子们该上学就上学,背着书包,书包里放着柿子、元枣和炒黄豆、花生之类的小吃。
看到附近路过的人,要是两家没啥仇怨,就会高声说:整啥唻!说这话的人,其实不管,也管不到人家要整啥或者不整啥。这句话,只是一个礼节性的打问。在乡人看来,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都是单独的个体,哪怕亲兄弟姐妹,同族的血亲,只要各自成了家,无论啥事,都只能是某一家人的“内政”了,别人无权干涉。
已成家另过日子的儿女们,如果遇到爹娘,也只能先喊爹娘之后,再问爹或者娘去哪儿呢?怀有孝心的人,都不会直接对爹娘说:你整啥唻。否则,就会笑话为“二八扯”或者“不够数”。爹娘当然不高兴。如果爹娘自行到儿女家里找东西找不到,儿女是可以用“整啥唻”问一下的,但语气要轻,整啥唻,这三个字都必须应当是平声,若是突兀了,有高有低了,爹娘就會以为,儿女在责怪或者嫌弃他们老而无用,抑或对他们有意见。
这是血亲和平素无怨仇的村人之间打招呼的口吻,若是两人或者两家有矛盾,平时见面扭鼻子扯脸,不说话正常,咬牙切齿、怒目相对也算本分,再相互呸一口也不觉得有啥稀奇的。要是两人凑在一起,要开始打架之前,便会相互大声怒斥:你娘的你整啥唻!整啥唻。你整啥唻!另一个也会迎上去说,你整啥唻,操恁娘的你要整啥唻!两人一旦破口大骂,多半会拳脚齐上,相互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嘴歪眼斜。要不是有人拉架,或者一方示弱,赶紧找个空子溜掉,估计会打出活人脑子来。
世上的怨仇名目繁多,也千千万万。有些人脾气暴躁,一言不合,挥拳甩锤。有些人阴暗或者阴毒,不和仇家正面交锋,背后捣鬼。以前是踩坏仇家庄稼,或者砍掉和自家不对付的人家的树苗为基本报复方式。现在手段略高明,用硫酸烧毁别人家的财产,如成年大树,刚栽的经济苗木等,再甚者,还会在大年三十或者初一,趁“仇家”正在“欢乐祥和”之际,自制炸药和雷管,直接在人家房顶上炸响。
这也是过去年代的事情了。时代进步了,报仇和解恨的方式也更新迭代。采取的方式更隐蔽,也文明了。谁家有钱,有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亲戚,或者自己家里有类似的权力,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关系,对待自己讨厌和有怨隙的人,就会采取更彻底、更具有羞辱性的方式。如,一家和另一家人打架,人口少的吃亏了,但没有更大的关系和钱财,不仅满盘皆输,且还会被有关公职人员劈头盖脸训斥一顿,甚至判个没理。想要反抗的话,当然也可以,你可以随便去申诉。而胜者,则听之任之,根本不担心对方会有什么“杀手锏”。
不松活
南太行乡村的山高,石头也多,以前人家盖房子,全部用石头,从打地基一直到覆顶。离开石头,村人就没法遮风避雨,生儿育女。石头多在比较远的山里,还得找可以成块,成片的。成块的,容易凿开,也比较容易搬运;成片的,便于一处就凿够盖房子所用的石料。在众多石头中,不仅需要可以砌地基的,还得要门脸石、门顶石等特殊用途的“石料”。这两块石头,不仅要长,还要宽。其他的石块每块只有几十斤重,门脸石和门顶石至少有三四百斤重。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再威武雄壮的男人,仅凭个人的力量,也奈何不了,就得找人来帮忙。帮忙的人来了,看到这两块石头,基本上都会暗自吸一大口凉气之后,说,哎呀,这家伙,可不松活。
不松活就是很艰难、很吃力的意思。多用在干农活与凿、运石料和大量木料等重体力活儿上,也可以用在人身上,如谁家一口气生了七八个孩子,家境又不好,人见了,或者说起来,就会怜悯地说,哎呀,他们家的日子可不松活!意思是,他们家的日子可不太好过,吃力得很,爹娘得好好干,拼命干,才能把孩子们都养活住。
现在,即便再能生的人家,也不过四个孩子,再多人也不生了。不像从前年代,人想生不想生,只要怀了就生。
现在多数人家也不用石头盖房子了,除了地基,都是红砖。老人们看到,说,这泥烧的东西,哪有石头结实耐用,还冬暖夏凉啊!年轻人说,现在都这样了,红砖盖的房子漂亮好看,再说,现在都时兴这个了。
这是严重的代沟,也是时代特征在乡村的另一种体现。老了的人喜欢结实耐用的,年轻一点的,喜欢外观好看的。正如老人们会经常训斥自己的孩子们说,别整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孩子们则反对说,中用的不如好看的管用!
这两种思维和意识的冲突,最终以老年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当老人生了病,特别是绝症,如各种癌症。倘若儿女们家境好,人不觉得有什么,若是老人自己和儿女们经济条件都一般,甚至中等偏下,家里老人得了绝症,其他人说起来,也会用“不松活”来形容他们家的经济负担重,生活得不易的现实情境。
这话还可以用来形容病人病情、缴纳彩礼钱、盖新房困难等。
但也有人说,“不松活”是人一辈子的常态,无论做啥,都是“不松活”的,尤其是老人们常说,人活这一辈子,凡事都难,可不松活唻!此外,这句话还可以用于男人对女人的某种判断,如某女太胖或者体格过于健壮,而其夫又看起来相对不够孔武有力,其他人在开玩笑的时候,就会用“不松活”来形容其夫在某些隐秘时候的吃力情境。当然,这肯定是戏谑之言。
死气马趴
山岭或沟壑之间,那在缓慢移动的,看不到人。但都知道,这是人背着这些柴火在移动。背的工具,当地人就称之为柴架子,形状如大写的“H”,又像一个“井”字,两边分别有两个襻带,挎在双肩上,主要承重,后面是空的,但可以用绳子将柴火捆住,放在柴架子上,再竖起来,就可以背动了。
不仅柴火,还有玉米和玉米秸秆、谷子、土豆、黄豆、麦子和麦子秸秆等,都可以这样背,小的东西,加一个黄荆条编织的篮子或者篓子就可以了。尤其是冬天,人在背柴火的时候,那种躬身哈腰,在山上挪动,或者从山上向沟底行走的样子,我们南太行乡村人就会想起“死气马趴”这个词。它的主要意思,用来形容人在劳作时候的可怜样子,更可以表达苦难生活情境。比如,父母在教育、鼓励孩子争气、上进的时候,会说:“俺死气马趴地干活,这都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咱家日子好过点!”
多年前的南太行乡村,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幅情景:大风吹袭的山岭,人间酷寒,只剩下了穷山瘦水,以及残留在树枝上的红柿子残骸,以及挂在长刺密集的树枝上的酸枣,除此之外,都是空的。一个人这样在山里打柴和背柴的样子,让不知人间此苦的知识分子能瞬间悲悯全人类。往往是天色将暮之时,冬天太阳下沉,几乎是眨眼间的事儿。背柴的人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到家,否则,山里的路乱石横陈,还有些石头是倒三角形的,人体碰上去,非死即伤。
我少年时代,也死气马趴过,但当时没有想到苦,只是觉得累,大冬天的,还出一身臭汗。另外,就是想着早点到家,放下柴架子和柴火,赶紧坐下来休息,再吃饭。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无论我们,无论他们,无论城市和乡村,也无论非洲和亚洲,欧洲和大洋洲。可现在看来,这样的生活,也唯有山里的人们才这样,平原地带的用农用车,或者用架子车 ,还比较省力气。
关于“死气马趴”这个方言,大致是我们南太行乡村先祖生造的,在很多的地方,我没有听到,也没有在相关的书本上看到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个词是原汁原味的南太行乡村方言,它所表示和形容的人事,或者人生活的艰难情境,似乎也具备了专属性和唯一性。
方言“死气马趴”,在很多时候,也用来形容人挣钱的艰难程度,比如那些只能在山上摘酸枣、捡板栗和割黄荆编织各种用品卖钱,才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人们的劳作与生存情境等。
得劲儿
“你那边儿得劲儿不?”“得劲儿!”“你那边唻?”“得劲儿!”这样的对话,一般出现在两个人或几个人共同劳动的时候,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搭伙人。比如,两个人合着抬起一块大石头,目的地又远,需要走几步、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两人抬起来,用肩膀,或直接用手,抬的过程中,两人都会相互问下得劲儿不。意思是,(你觉得)合适不合适,行不行,有问题没?主要是问对方抬得称手不称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比如,手没使上劲儿,或者放得偏了一点,用不上力等。
这在我们南太行乡村很普遍,特别是干重活的时候。如抬石头、抬大木头和其他大型物质,需要两个以上的人一起完成的,相互之间才会这么打问。一是保证安全,别谁抬得不到位,不舒服,突然松手了,出了偏差,砸到了自己手脚,同时也会殃及其他人。二是相互之间表示关心,用這种方式,提高合作的有效性与密切性。这时候,用得劲儿和不得劲儿来进行问答,很经常,也最有意思。
但这个词儿更多地却用于男女之间。当然夫妻最多。它的意思,主要是舒服和不舒服的意思。当然,这个事儿比较私密,属于夫妇之间的交流,与其他人无关。当然,也还有情人之间。
得劲儿不得劲儿,有时候也会用于农具用得顺手不顺手,干活时候,是不是心情好甚至愿意干等方面。还可以用于个人身体,坐的位置和屁股下的垫子、椅子、凳子等。比如人觉得自己病体恢复了,就会说,现在觉得得劲儿了!再比如,买了一张新床,或者一张新家具,坐上去,感觉一下,也会说得劲儿、不得劲儿。但是,在南太行乡域,得劲儿的这个“得”不能叫“de”,正确发音应当是“dei”。
够喝一壶了
那小子,够他喝一壶了。
这句话包括了“吃力”“危险”“艰难”三方面意思,通常,可以用同情的口吻,也可以是幸灾乐祸的。比如,一个人做错了什么后果严重的事情,同情的人会说,哎哟,这下可够他喝一壶了。哎呀,你得好好整(或好好对付、处理等)。要是存心落井下石的人,则会笑着说,这下,够他小子喝一壶了!娘的,活该,真活该!
春天,人们不仅忙着翻松土地,点种种子,还忙着栽树。这些年来,板栗树又成了南太行乡野的新宠,此前是苹果树和核桃树。为了多挣点钱,人们纷纷把分给自己的荒坡斩草除根、扒皮抽筋之后,再栽上板栗树苗。大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南太行乡村每年都很干旱,尤其春天,有时候连一点雨都不下。村里唯有的小河没水了,人们就开始掘井,用水泵抽水浇树苗和其他庄稼。
村里的张四起虽然手里不缺钱,可还是很爱惜自己那点山坡,也学着其他人,种了不少板栗树。头一天下午,张四起和自己老板优哉游哉地种了二十多棵板栗树苗,累得腰酸背痛,但心里还是喜滋滋的。第二天一大早,怀着喜不自禁的心情,张四起背着双手,哼着豫剧《打金枝》,迎着东边的朝阳,来到了自己家的荒坡。一看,哎呀, 昨天栽的树苗竟然不翼而飞。
张四起愣了一下,脑袋同时轰的一声。然后张开老迈的喉咙,对着全村人骂说,哪个操他娘的干的这缺德事儿啊,把俺的树苗薅了不说,还给俺全都折断了啊!
张四起觉得,这事就是村里人干的。自从他的儿子调进市政府当了科长,他们家的日子彻底发生了变化,每天来看望他们两口子的,也不知道都哪里的人,来到家里,放下东西就走,有的自报姓名,有的连名字都不说。
村里人找他办事的也多了起来,其中几个,是他女婿的亲戚,因为村里的宅基地纠纷和其他人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就没怎么费劲儿,几年十几年没搞定的事儿,几句话就解决了,个个欢天喜地。这世上的事儿都是相对的,有人乐不可支,肯定有人气不打一处来。
有人加官晋爵,就有人告老还乡。看起来是帮了人,其实也害了人。这样一来,有人不满意,明着不敢和他硬碰硬,只有阴着来。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张四起骂了半天,口干舌燥;老婆再接着骂。可无论他们怎么骂,就是没人搭腔。女儿女婿闻讯而来,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张大有干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原本属于张大有的一块地,在他人的强力干预下,划给了和他有争议的人家。这张大有独门独户,又是地道的农民,两个孩子还小。和人缠斗,实在没那个能力。阴着来泄愤,这太有可能了。
张四起老婆暴脾气,家人刚一商量完,她就跳到张大有的院子里,一边骂张大有是王八羔子狗操的,一边拿着石头,使劲丢出去,只听一阵脆响,张大有家的窗玻璃哗哗碎了,纷纷掉落。正是半夜,张大有一家人正在呼呼大睡,突然被人骂醒不说,因为床铺挨着窗户,碎玻璃掉下来,差那么一点没把他老婆的脸给割破了。
张大有本来心里有气,一听又是张四起老婆,还砸了他们家的玻璃,一骨碌爬起来,裤子也没穿,猛地跳下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南太行乡村人家也都睡床了,只有上了年纪的人,还喜欢睡土炕),光着脚追上张四起老婆,上去踹了一脚,又在她年老的屁股上狠狠地跺了两下。
全村人午夜惊梦。
当众人知道了事情原委,同情张大有的会悄悄说,这下,可够他张大有喝一壶了!不看人家现在在哪根树枝上唻!(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生好比一棵树,占据高枝的,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觉得张大有过分的人,会说,哼,够他小子喝一壶了,等着赔钱吧。对张大有不满的,甚至恨他的,也会说,呵呵,这下好了,不用咱收拾他,这一次,怎么也够他狗日的喝上一壶了。
(贝+青)受
这个词好像很文雅,也很书面化,意思是儿子继承父母的遗产。这没什么。在我们南太行乡村,出嫁的闺女是不可受亲生父母遗产的,即使终身不嫁,一辈子都窝在娘家的闺女,也没这个权利。受,只有儿子们可以。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常常被村人们相互之间作为恶毒诅咒的代名词。比如两家人吵架,一家人骂另一家人赶紧死,全家死绝死光;另一家人则会反击说,俺死了,操恁娘的你想受俺啊?!
如此吵架干仗,在我们南太行乡村,隔个三五八天,就会有那么一场。受了人家的遗产,那就是人家的儿子了,这也是变着法子骂人的意思。
邻村一户人家,兄妹五个。爹先没了,几年后,娘也去世了。两口子生前,为两个儿子盖了新房子,娶了媳妇。三个闺女有的嫁得远,有的嫁得近。娘去世第五天,兄弟俩开始分家产,为了公平,得有个见证人,叫了舅舅和姐姐姐夫们来。在我们那里,姥娘舅舅是家族里最有权威的,特别对于外孙和外甥子们来说。
这就是受,而且是天经地义的。可分到最后,就剩下一只粗瓷大碗。老大也要,老二也要。兄弟俩争了起来。理由是,给爹娘养老送终,这一路钱都是平摊的,东西也都应当平分。他的大姐夫为人老实,看着两个小舅子为了一只碗争执不下,一着急,拿起那只碗,往院子里使劲一摔,哐当一声,瓷碗顿时粉身碎骨。回过头,大姐夫看着两个小舅子说,这下好了,谁也不要要了!
众人默然。
另一个村里有一个老太太,只生了一个闺女,还是哑巴。丈夫死得也早。自己一个人过活,按照风俗,她百年之后,闺女和女婿是没办法受她的任何财产的,只有委托给自己的侄子(如果侄子多,可以任選一个)。老太太去世后,她的闺女虽然一直在伺候和孝敬自己的亲娘,但娘的遗产一分都不能拿,全部给了堂哥,也就是她父母的亲侄子。
与之雷同的还有一例。一对膝下无儿夫妻,早些年收养了一个儿子,给他起房盖屋娶媳妇,生了孙子,但因为闹矛盾,养子不赡养他们。闺女和女婿只好照顾他们晚年。尽管如此,把爹娘先后埋葬之后,闺女不要一分遗产,全部给了养子。为的是,自己娘家还有人,她自己和丈夫过世时,还有后代到家里披麻戴孝,去主持丧事。这不仅关系到出嫁妇女的出处问题,还关系到夫家的颜面。要是她和老伴去世了,娘家没人去,那也是一件极不光彩,丢人败兴的事儿。
败兴
败兴这个词,还兼有对某个人的人品批判的意思在内,如:败兴哎你。就是形容某个人做不了啥体面事儿,全是丢人的。更多的时候,这个词用在对某人的指责上。比如,两个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喝酒聊天,笑得嘴都咧到地上了,忽然一人进来,佯装发生啥大事一样,咋咋呼呼,然后神情庄严甚至有些悲壮与害怕地说了事情原委,但他说的事儿,却在其他人心里根本不算个事儿,反而扰了人家正酣的酒兴……这样的,就会被说成败兴。
张思水家境算是我们那一带比较殷实的,朋友也多,喝酒就成了常事。不论何时,只要有人来他们家,猜拳行令之声就会响彻四野。一般而言,这类的场合,一般人是不适合去凑热闹的,可偏偏有人不懂得。其中最经常的,就是和张思水同村的张建水。这张建水生下来就是个智力有缺陷的,半傻不苶,会说话,也认得人,更知道吃喝拉撒娶老婆好,但对于人情礼道,特别是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他不是搞不懂,是压根就不知道。
这不,张思水家来了客人,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正在秋天,人都在忙,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张思水家虽然有儿媳,也有闺女女婿帮忙,可连炒菜带做饭,忙得人喊马叫。张建水晃着一颗大脑袋,迈着高低不平的大步子,一抬脚,就进了张思水家的大门。
张思水赶紧说,哥,来抽根烟。张建水点着。张思水的意思是,给你一根烟抽,你赶紧走,别在这搅和了。张建水哪里懂得?抽着烟,不但不走,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张思水的沙发上。沙发的旁边,就是张思水的外地朋友们。那些人都衣着光鲜,个个都是生意场上的。这张建水一身灰土,身上还冒着阵阵汗臭,张思水的客人,就都起身往院子里去了。
张建水兀自坐在沙发上,继续抽烟,而且自己拿了水果,往嘴里塞。这一下,张思水的老婆进门就说,你坐在这儿做啥啊,不去割玉茭,到俺这儿丢人败兴啊!娘儿们这么一呵斥,张建水才回过神来,起身出了张思水的家门。诸如此类,多少有些不对等。天下哪有同样的人呢?另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自家孩子不争气,老是调皮捣蛋,或者作奸犯科之类的,就会被父母斥为丢人败兴。再比如,亲戚和亲戚之间,有些家境好的,也会嫌弃家境差的。好的不愿意和差的攀亲,甚至连话都不想说,原因就是,怕亲戚给自己丢人败兴。
装蒜
南太行乡村人,包括冀南平原甚至京津等地,人们大都喜欢吃生蒜,尤其是吃饺子和面条时,不吃几瓣生蒜,好像过意不去。我幼年时候,父母告诫我们说,不要把蒜放在衣兜里,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才懂得,装蒜一词是骂人的。意思主要有三个,一是自己没有能耐,反而在人前总是鼻子插葱,装象,把自己弄得神五神六的。二是喜欢说大话,吹大牛,但又落不到实处的。三是直接用以骂人。
曹建平和曹建军两人素来有怨隙,偶尔遇到一起,气都不打一处来,两人先是谁也不理谁,斜着眼睛或者昂着脸,轻蔑对方。要是接上火了,一个喝骂说:装啥蒜啊你!另一个也怒声回应说:你装啥蒜啊!这么一来二去,不消第三回,就甩开膀子,扭打在一起了。有些时候,两个冤家碰头,都会用装蒜你,或者你装啥蒜来表示轻蔑,甚至直接为了挑起两人之间的正面冲突。
我在老家长到十八岁,似乎还没对哪个乡亲说过这样的话 ,也没和谁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冲突。有几次回去,在村子里,目击了几个男女之间互相骂对方装蒜,然后厮打的现场剧。我想拉架,但被告知,这类的架是不能拉的,拉谁都不对。比如,先拉了这一家的某人,正巧这时候,他的对手趁机打了他一拳,或踢了他一脚。他要是还回去了还好,要是没还回去,这人一准骂我拉偏架。
人在很多时候的矛盾和邪恶,其实来自内部。但乡里人不知道,他们只看眼前的,也只在乎伸手可及的,至于其他的,他们没空去想,也不会去想。
混账
这是人尽皆知的一个词儿,落在具体乡域,意思又不尽相同。幼年时候去舅舅家,一个表哥名字就叫会账。他的父亲和我舅舅是叔伯兄弟,也是近亲,拜年的时候,我和弟弟也会去他们家。平时在村里见到,我也会叫会账哥。但每次心里都打个嗝儿,觉得这个名字实在不好,主要是和混账的读音相同。
混账这个词,在我们南太行乡村,多数意思是不懂事、糊涂、油泼不进等,用来形容人想不开事儿,凡事都很糊涂,一根筋。比如,村里有一个老人,性格很犟,明摆着一件事很简单,可他就是想不开,梗着脖子和人理论,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人们就会说,这人简直是个混账疙瘩蛋。
村里有一个妇女,常年和婆婆闹事。
主要原因,是她持之以恒地嫌弃和责怪公婆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不如其他人家的公婆之类的。亲戚们好言劝她说,公婆都老了,也都是一辈子农民,能把七八个孩子拉扯大,就已经很不易了,还能给孩子们创造啥财富呢?可她不听,就是以为公婆没有尽心尽力,以至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更不如别人家。
另外一个,自己的女婿其实也不错,有一年,他自己不小心摔断了腿,找女婿要钱治病,女婿当时也困难,没有拿多少钱给他。等后来女婿的生活条件好了,隔三差五地给他钱花,还给他买烟酒衣服啥的。可每次女婿上门来看望,他不搭理人家,心里还是怪罪女婿那一次没有拿钱出来给他治病。别人也劝他说,女婿当时有困难,又不是不给,现在人家手里有钱了,也没忘了你,时不时地给你送东送西,这多好,还记那个陈年老账做啥呢?无论怎么劝,他的耳朵都被磨出老茧了,可他还是不原谅。人就说,这老家伙,也是一个混账疙瘩蛋。
膈谅
应是这两个字:膈谅。在我们南太行乡村,是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主要用来表达内心的歉意。当然,人都会说假话,说膈谅的人,未必都是真的膈谅。膈谅的意思里面,包含了愧疚、不安、怀想和感恩等意思。
比如,我爷爷在一个中午猝死,很多年后,我心里一直很“膈谅”,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幼年时候,爷爷是对我最好的人之一。他时常把家里的饼干、糖块、面包等好吃的东西偷偷给我吃。在我十二岁之前,他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包括我们村子的各种往事和人事,算是我的文化启蒙人。他的猝死,留给我的遗憾实在太多了,那时我才十七岁,完全不懂得人世冷暖和悲欢。
另一个人是我的大舅,他为人很好,一辈子无儿无女。要了一个养子,一个女儿,都抚养成人了。养子很有出息,对他的兄弟和妹妹、大舅都很照顾,凡事都替别人着想,委屈和艰难自己咽下。有一年,我们家盖房子,要买覆顶的石板,大舅一个人跑到了武安市的一个农村,为我们买了石板,又付了钱,又帮着装车,颠簸了几个小时,夜里到家,才知道他饿了一天。
他也是猝死的。在一个冬天,六十几岁的他一个人到房顶上拿东西,不小心滑到了后巷道,好半天才被人发现。再一个是我大姨妈,她受了一辈子苦,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她也跟着我母亲和小姨、两个舅舅训斥我,但她也是对我最好的人。小时候,我是跟着她的几个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表姐一起长大的。更重要的是,两个舅舅和大姨、母亲、小姨几个兄妹关系一直很好,但凡谁家有事,都是尽心地帮。
大姨死得更惨。2007 年秋天,大姨和几个孙子孙女去给四表哥摘玉米,三表哥的大儿子驾驶着三轮车,因为毛糙,三轮车车况也差,在山路上跑得快,一下子翻了,表姐和她唯一的儿子当场死了,大姨被撞破了头,昏迷了几个月,最后也死了。其他几个孙子孙女虽然也都受了伤,可保住了性命。
无论我在哪里,老家还是外地,只要想起他们,我心里就膈谅得很。从前,他们都对我那么好,我该报答他们,可那时候我还没相应的经济能力,现在有点了,可他们却都不在了。还有我的奶奶和父亲,他们都没有沾上我的光,我也没有尽到应当的孝心,他们也都走了。这种膈谅是錐心刺骨的。
膈谅这个词,在我们南太行乡村,是感恩的代名词,是对逝者最深切的感念。在一般情况下,生者很少对逝者说假话。因此,凡对某位逝者使用膈谅这个词的人,其心都是真诚的。
毁烂
要过年了,外出打工的人,上班的人,做生意的,等等,都回来了。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年货。这年货,除了花钱买的,有些还得自己做。或者,人都觉得买的不好吃,还是自己亲手做的好。比如豆腐、粉条、馒头、包子、疙瘩(饺子)之类的。李长林就是这样。他对老婆赵秀花说,咱们家里也有黄豆,还有红薯,买的不好吃,咱们自己做着吃吧。
赵秀花说,你是当家的,你说了算。两人开始泡黄豆,洗红薯。
越是临近春节,天气越冷,天空蓝得干净,远山一片苍黛,近处的小河和大水库都结了冰。磨坊是别人家开的,两口子就挑了黄豆和红薯,一前一后地往磨坊走。村子里的路都是小路,公路倒是有,可远。正走着,扁担嘎的一声断了,正在下坡路上,两只桶当的两声掉在地上,然后顺着斜坡滚下去了,黄豆撒了半坡。李长林说,毁烂,这下可毁烂!
赵秀花一看,心里有些不高兴,黑着脸说,可不毁烂咋的了!
毁烂的意思,就是突然坏事了。相当于四川人说的“哦豁”,北京人的“哎呀”。其中的意思是,突然之间一件事出了差错,而且挽不回的。再比如,赵家的老三在某个工地上干活儿,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工友闹了矛盾,两人打架,赵家老三把人打死了,传信的人也会说,毁烂,这下可毁烂!出了人命事儿,不死也得坐牢。再比如,某人在山上锯木头,或者放羊等,不小心摔断了胳膊或者腿,或者滚下悬崖碰死了。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老婆也会高声哭着说,可毁烂了啊!俺家的顶梁柱没了!
毁烂也可以用来开玩笑。某人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突然一个人跑进去大声说,哎呀呀,可毁烂了啊,某某某,您家的老母猪被人偷了!正在打牌的人信以为真,收拾了赌金就往自家跑。回去一看,自家老母猪还躺在圈里哼哼叫着,瞪着两只大黑眼睛冲他要吃的。这才知道,那小子是开玩笑的。等他再回到牌桌,开玩笑的那个人已经坐在了他的位置,东风、五条地打起了麻将。
当然,这词语也可以用于夫妻之间。其意思,大致是用来增强情趣的。但这个话,不怎么好说出口。具体的情境,也因人而异。
如果遇到什么大事,牵动各方的,那么,听说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说,毁烂,这下可毁烂!也难怪,人们只对自己和牵扯到自身利益的事情感兴趣。多数情况下,所谓的毁烂的事情通常出在一人一户,而不是全体人。因此,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语气和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因为这里面还涉及一个远近亲疏的问题。对于亲近的,“毁烂”的口气中就有了惋惜和悲悯;要是和自己关系差的,“毁烂”就显得轻描淡写;若是仇家,则会充满幸灾乐祸的意味。
汉语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无论在书面还是方言当中,都有着真切的表现。
搌闲
在家挣不到钱,闲坐了一年,一家人山穷水尽。朱老三憋闷得很,先去开矿的妹妹家一趟,回到家,顷刻精神抖擞,找到村里的暴发户朱有才说,哎呀,才哥,现在包矿很赚啊!朱有才爱答不理地说,包矿?这近面处(近处的意思)的矿都被其他的人包完了,好的人家舍不得转让,赖的根本赚不到钱,说不定还赔本,包个鸟啊包!朱老三就说,这一回,俺去了我妹夫的矿上,俺一连看了他们好几天,那真个儿干得好,这一年下来,怎么说也整他个百八十万。俺妹夫说,他的矿旁边还有一个矿,出铁可以,要不是出事,死了七个人,那老板还不想转手。俺听说,哪个人要是有挣钱的命的话,怎么着都行,天不怕地不怕的。你才哥这么能抓钱,包上肯定没问题。
朱有才又斜了朱老三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不搌闲,不搌闲!那出过事故的矿谁还敢包?朱老三说,搌闲,搌闲,只要下面有铁,有东西,就能赚钱。朱老三不耐烦了,大声说,不搌闲,不搌闲,就是不搌闲,你去找别人吧!朱老三这才悻悻地低着脑袋,起身出了朱有才的家门。
搌闲的意思是能行,可以,很好,有出息。不搌闲,就是不行,行不通,做不了,不可以,不能行,不中,没出息,没发展前途等。
在南太行乡村方言里,搌闲也可以用来夸人,比如某家的小子聪明伶俐,不仅能干活,还能赚到钱,人就夸搌闲。谁家的小子好吃懒做,正事不干,人就会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说,这小子,不搌闲,不搌闲。夸人的时候,还可以用搌闲得很来说。损人或者贬低别人的时候,可以用不搌闲得很。这个方言,到了冀南平原的邢台、南和、内丘、隆尧等地,便省略为“搌”和“不搌”。意思与我们南太行乡村基本相同。其中的“搌”字,有黏合之意,和“闲”字组合,就是黏合不住,就是闲的意思。
膈应
“膈应得慌嗯。”付盖群说了一句,脸上一副嫌弃和唯恐避之不及的厌恶、无奈等复杂表情。去年,她婆婆生病了,癌症。婆婆八十六岁,人都说,能活到这个年纪,也算是够本了,即使死了,也是喜丧。老天从来就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生命,无论是谁,老了,都得死,可有的人死得痛快一些,嘎嘣一下,就没了,有的人死得慢一点,还特别痛苦。
这不,婆婆病倒了,屎尿都在炕上。几个儿媳妇和两个闺女轮流支应(伺候、照顾的意思)。付盖群是大儿媳妇,轮到她伺候了,心里虽然不情愿,但也得去。婆婆已经不能下炕了,还能吃点东西,这倒是好事,可吃了還得尿和拉。每次替婆婆收拾那些便溺的时候,付盖群就扭着脸说,哎呀,膈应的,膈应的,受不了,受不了。
这个“膈应”就是脏的意思,其中还带有嫌弃、鄙视、不想做必须做等意思。主要用在人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体排泄物的厌恶情绪上。遇到人,付盖群也会呱唧说。别人问她,伺候你家老娘子(婆婆)咋样。付盖群说,其他的吧好说,就是替她收拾那些东西(屎尿)的时候,膈应的,想哾(呕吐),可膈应人了!人就会怜惜地看着她说,唉,这也没办法,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这样儿,没办法。意思是,人老了,生病了,躺在炕上了,大致都是这个样子。
如此情况,还体现在父母对新生儿女便溺的态度上。有的男人,见到孩子屎尿也会觉得膈应,不上前忙着收拾,都是媳妇来做的。对于老人,普遍的反应,就是膈应。毕竟是老年人。人到了老年,基本上都脏,尤其是躺到炕上了,病了,更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懂事的人会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子。得提前给自己的那些儿女们做个榜样,以便于自己也这样的时候,孩子们尽管觉得很“膈应”,很不情愿,但还是能够尽心地支应自己。
同时,膈应还可以用于评价人品,如:某某某,是一个膈应人。或者说,哎呀,某某某,别提了,太膈应人了!如此等等。人都是有功利心的,对此,佛家说是因果,儒家说是人伦,道家说是善心。但民间也有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也是事实。人们只欢喜新生的儿女,对于生养自己的人,却没有足够的耐心,也觉得老人膈应。从这个方面看,人生是一场悲剧,但悲剧的结局,大抵是更深的悲剧。悲剧往返,一代代的人,就这么生活着,悲剧着,却也喜怒哀乐,油盐酱醋,生老病死。
夜儿个
五月的早上,风还是有些凉。人们穿着短袖或者长袖,拿着家伙什儿往田里走。在地边或者路上遇到了其他人,都会打招呼,说恁整啥唻。然后再扯一些闲话。比如,赵思妮和张海兰俩娘儿们(专指已婚妇女)只要遇到一块儿,就会扯闲话。赵思妮凑近张海兰,一脸神秘地说,咳,你知道不?夜儿个黑夜,曹建明又去那个李艳梅家了。张海兰也一脸神秘,干笑了一声,然后一脸淫荡地说,哎呀,还真是的啊!这两个人,骚狗一对儿!赵思妮后撤一步,然后说,可不,这无风不起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其中的“夜儿个”,就是昨天的意思,要是说“夜儿个黑夜”,那就是“昨天晚上”的意思。这个方言很奇怪,与之相同的,还有把太阳叫“老夜”或者“老烨”,这可能和古老的阴阳理论有关。昼为阳,夜为阴。太阳升起,即早上六点到九点之前,大致是少阴,到中午,太阳的光亮和温度便开始衰弱,至傍晚,成为老阳。南太行人可能不是太懂,祖传下来的口语,就是把太阳称之为老夜。
“夜儿个”这个方言里面,也包含了一个夜晚过去,或者过去的那个黑夜的意思。我们南太行的方言当中,既有“晋语”,也有“豫语”的成分,总体上属于北方语系。但各个村子的方言又不尽相同,有些方言,在我们村里可能是褒义词,夸奖人的,若换了另一个村子,则可能以为是骂人的。如“固执”的意思是说某个人的性格倔强,不轻易听人劝。到了另外一个村子,“固执”就成了死脑筋,做人做事没有分寸的意思。
出串
过了正月十五,日光一下子就暖起来了,河沟山间,似乎都有热气蒸腾,蛰伏了一冬的动植物纷纷翻身, 整个乡野充满了新生的欲望,以至于整个人间,都有了一种蓬勃的气象。
这个时节,村人们都会去翻松土地,晾了一冬的田地表层,嫩草已经冒尖,尤其是去年秋天堆放的玉米秸秆和谷子秸秆下面,嫩黄的植物像是顽皮的孩子,一个个歪着脑袋,从缝隙中打探外面的世界。
翻松土地的农具叫䦆头,还有板镢。其实这是同一种农具,但用途不尽相同。䦆头的面比较窄,但头部较为尖利,用以刨石头蛋子比较多的土地和山坡,板镢的面比较宽,也比较短,适合刨松软的沙土地。
扛着䦆头和板䦆到自家田地边儿上,人先看看,男的抽根烟,女的四处走走,然后才抡起䦆头或者板镢,开始翻松。一䦆头下去,新土外翻,其中有很多的出串,在泥土中扭动着红色的身子,像是地蛇,样子可爱又很可怕。
这“出串”其实就是蚯蚓,是有益于土地的虫子,替庄稼翻松板结的泥土,利于庄稼扎根、吸水和成长。村人也知道,但在翻松土地的时候,免不了会把出串拦腰斩断,或者把人家的头或者尾巴给切下来。这其实很残忍。
有一年,我跟着奶奶去刨地的时候,斩断了好几条蚯蚓,奶奶看到了,说,不怕,这出串自己能把自己接上,有本事着呢!我不信,可也无从验证。等到第二年再刨地,还是能看到很多的“出串”,在泥土里翻滚。
拱门儿
星星很亮,也很多,地面却是黑的。这不怕,有手电。村里不比城里,有路灯。没有路灯的乡野大地,手电是必备品,家家户户都有,而且不止一只。尤其在冬天,要是没有月亮,整个人间,好像沦陷的地狱,到处黑黢黢的,白天看起来好走的道路,一下子就变成了布满陷阱的歧路末途。
顾明初早早吃了晚饭,收拾了和他一样经年累月形单影只的碗筷,回身锁了房门,走到院子,再走上院子左边的小山头,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到村子里去。所谓村子,大都是一座一座的自然村,分别散落在附近的山坳里,有的近点,有些稍微远些。但最远的也不过三五里路,一个大男人,甩开大脚片子,不消半个小时,就走到了。
顾明初这个名字实在好听,给他起名字的人,一定是有文化的,而且是大文化人。他的曾祖父顾闻道就是清末的一个秀才,虽然一辈子没有当官,但肚子里四书五经和各种学问不少,而且还是一个懂阴阳术数的人。顾明初出生那年,也是他曾祖父顾闻道去世的那一年。顾明初的娘怀孕的时候,顾闻道得知之后,一阵默念和掐算之后,对着顾明初的爹叹息一声,说,这个孩子,不成器不说,将来还是一个光棍。尽管顾闻道想通过起名给他改运,无奈,人算不如天算。
爹娘先后辞世,这个时候,顾明初也快五十岁的人了。自己一个人,进门一根,出门一条。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最难熬的便是,一个男人的生理问题。要说这么些年来,顾明初也厮混了几个妇女,都是别人家的。可这事儿,毕竟偷偷摸摸,不可能长期。隔了几年后,又遇到了一个对上眼的。这不,顾明初早早吃了晚饭,蹚着寒冷的北风出门,在夜晚的村庄游荡,所为的当然是一时之乐。
对这样的事儿,我们南太行乡村叫做“拱门儿”,这個词很形象,意思是,男人像猪拱圈或者骡子跳厩一样,去做那样的事儿。和“拱门”这个名词有着天壤之别。即使各家各户有拱门,但也不叫拱门,叫大门。绝对不能叫“拱门儿”。这是一个禁忌。外地人不知道其中意思,说出来之后,主人家以不吱声回应。
类似顾明初这样的单身汉,在乡村尽管占极少数,可也是一个群体。由他们而引发的桃色新闻几乎没有中断过。而被“拱门儿”的,多数是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或者工作的娘儿们。但为数极少。但再少的人,也是人。是人,就得有人的欲望和想法,也会做人人要做的事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在乡村,这样的人事比较多,但大都秘而不宣,不小心让人知道了,这“拱门儿”的和“被拱门儿”的关系,通常会快刀斩乱麻,自此变成陌路人。当然,“被拱门儿”的多数是有所图,极少数的,才是心甘情愿或者心有灵犀。
修德
肯定是这两个字,也只有这两个字,才符合本意。一个娘儿们见到另一个娘儿们。她们都是该做婆婆的人了,也大致在五十岁左右。在路上遇到,一个娘儿们会问另一个娘儿们:恁家老大去年过的事儿啊?另一个说,可不是哎!这个娘儿们继续问,“修德”有了(怀孕)没?另一个娘儿们则说,好像有了。
这里所说的“修德”,就是媳妇儿。这两个字,大致取自《易经》中的坤卦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就是“修德”,也专指做媳妇的是一家之福,要时刻注意“修养自己的德行”。在我们南太行乡村,“修德”就用来专指别人的媳妇。比如,曹建花是朱福林的“修德”。当然,朱福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曹建花是俺“修德”。曹建花也可以对其他人说,俺是朱福林的“修德”。
这个称谓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启用的,也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带来的方言。据说,我们南太行乡村一带的人,大多是明朝时期由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迁徙来的。这些人,各自携带着故土的方言与风习,聚集在新的地方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融合,方言也就很快一致了。可万事都是有变化的,如果谁家的男人很年轻就不在人世了的话,年轻“修德”肯定会再次嫁给别人,但无论怎么嫁,乡亲们见了,也都会说这娘儿们是谁谁谁的“修德”,而这个谁谁谁正是这娘儿们平生嫁的第一个男人的名字。
娘儿们
张海林要娶媳妇了,头天晚上,附近村里的幾个人商量,要去送点贺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大致是几个人一起凑钱,买个被子面、床单、暖瓶之类的。新娘子过门的前一晚,先派一两个人送过去。次日晚上,新娘子过门了,所有送贺礼的人,都要再去一次,目的是吃喝,再就是去给人家凑热闹。这也正常,毕竟,结婚是喜事,凑热闹的人越多,主人家越高兴,也越有面子。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南太行乡村的风俗有所改变,以前送东西,现在也都开始送钱了。十块、五十,最多给一百。也如此这般去吃喝,凑热闹。娶媳妇的人家,晚上不仅要好好招待,而且还要请放电影的来,放映两部有意思的影片,为的是助兴。
新娘子一过门儿,哪怕是第三天就离婚了,人再见到她,都会说,这个娘儿们,再也不会说她是闺女了。这个意思就是,嫁为人妇,不管有没有夫妻之实,只要明媒正娶地嫁出去了,这女的,就再也不是闺女了,只能是娘儿们了。即使到了七八十岁,人也只会在娘儿们前面加一个老字,叫老娘儿们了。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过。先是小娘儿们,再是娘儿们,再就是老娘儿们。
要是有人不知道这娘儿们是谁家的,丈夫叫啥,就会这样问说:这娘儿们是谁的“修德”?知情的人会如实告诉。至于这娘儿们的人品如何,包括能力大小,会不会持家带孩子,其他人说起来,都会说,谁谁谁家的娘儿们如何如何。这种称谓,多少还有些重男轻女色彩,但村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千百年来,人们就这样说着叫着。直到现在,很多风俗都变得似是而非了,可这个称谓,仍旧牢固如初。只要在我们南太行乡村,任谁,都会随时听到娘儿们、娘儿们的称谓,以及她们各个不同的秉性和“故事”。
汉儿们
意思和娘儿们一样,只有娶了媳妇的男人,才叫汉儿们。他的娘儿们也可以说:俺家那个汉儿们,也算是有本事,以前啥也不会干,这不,去学了个修手机,现在还行了!汉儿们的另一个名称,在我们南太行乡村,还有一个说法是:俺那口子,恁那口子。孩子他爹,她公公、他爷爷、他姑父、他舅舅之类的,都可以。
“汉儿们”是一个统称。
最有趣的,便是娘儿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说自己汉儿们的各个方面,能挣钱的,就是香饽饽,谁家的娘儿们都会夸,见到那男的娘儿们,就用羡慕嫉妒恨的口吻说,哎呀,恁家的汉儿们顶事儿,看人家一年挣多少钱!另一些也会附和说,可不就是咋的!恁这辈子哪儿修来的福气,嫁了这么好的一个汉儿们!如此等等。要是谁家的汉儿们不行,挣不到钱,好吃懒做,或者有赌博、喝酒的毛病,其他娘儿们见到以后,叹气说,哎呀,恁家那口子最近还喝酒不了?
这个话,一般娘儿们不敢问,要是遇到脾气乖张的娘儿们,一准顶回来,而且说的话叫对方没法回嘴。比如,南街村的朱启明喜欢喝酒,家里条件不好,也不出去打工,孩子大人的日子过得稀汤寡水,缺吃少穿。人都说朱启明是一个懒汉,不是一个好汉儿们。可是他娘儿们赵连秀却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男人不好。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大嘴娘儿们见到赵连秀,开口就说,哎呀,连秀,你就不能把你家的汉儿们好好管管,让他出去干个活儿挣个钱啥的?
赵连秀哼了一声,脸色下沉,乌云还没落到鼻子上,就回怼大嘴娘儿们说,俺家的汉儿们挣不挣钱,干不干活儿,关你屁事,你闲得蛋疼,没事找事!大嘴娘儿们本来是一颗好心,结果被骂了一通,只好低着头,红着脸,扭头走开。
过事儿
至少两个月前,朱秀的家人就放出风来,说朱秀腊月二十那天“过事儿”,熟悉的人会当面说,这是好事,迟早得过,早过早“歇心”(即不用再为这件事上愁、着急和各种操劳操心的意思)。曹美的家人也这样说。人知道了,与之有关的,比如亲戚,心里就想,要记住这个日子,到时候得去,还得准备相应礼品。与自己无关的,知道不碍自己事儿,听说就算听说了,也不当作耳旁风,至少知道,这朱秀和曹美,马上就要单过(另立门户)了。
婚期确定,朱秀家里开始置办各种必需的东西,但主要是新房和洞房。新房是早就盖好了的,洞房,当然是要现布置的。
这所谓的“过事儿”,在男方家叫娶“修德”(媳妇),在女方家说“嫁闺女”。这一对亲家所为的,是这一对新人。我的儿子你的闺女,你的闺女我的儿子。这么一凑,原先是不咸不淡的乡亲,现在是儿女亲家。人生角色的转换,看起来突然,但仔细想想,倒也很自然和平常。
腊月二十那天,朱秀家人雇了十几台轿车,再加两台中巴车,连新娘子曹美和她的亲戚们、一个村子里的,都拉到了朱秀家。上轿礼、下轿钱之类的,大致不算多,即使多一点点,人也能够接受。既然做了亲家,又成了夫妻,一般人是不会在这一天故意给对方弄难看的(故意刁难)。
来送亲的人,所为的只是好好吃一顿,然后各回各家。朱秀这边,村里男女老少都来帮忙,主要是伺候来送曹美的人,即女方的亲戚和族人们。有路过的人看到这一场景,心里就知道,这人家在“过事儿”呢!至于为啥叫“过事儿”,据南太行乡村的老人说,人生有几件大事:生孩子、盖房子、娶“修德”,打发老人(为爹娘丈人丈母娘养老,再送到坟墓里)。
日惑
赵盖贤在屋里转了一大圈,又转了一大圈,带着一脸的蒙,又出门来了。老人的双脚走到门槛下面,自言自语说,哎呀,俺这是找啥啊?忘了!哎呀,这日惑得不行了。“日惑”的意思,就是糊涂、健忘、忘事,也有不懂人情礼道、脑袋不够数的意思。同时,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人的脑袋不够用,缺一根筋,还有明明知道自己要干啥,刹那间忘了,不知道做啥等情况。
日惑,是一个中性词。
赵家庄村有一个特点,代代出傻子。有些半傻不傻,说他聪明,可有些事儿,他完全不懂得;说他正常,有很多事儿他做不来,也说不来。这种人,叫傻子有些过分,通常都叫他们日惑蛋,意思是脑子不够用,不会做事,不懂事。赵家庄的赵建平就是这样,他能够认得所有人,而且记忆力很好,可就是日惑。
比如,有人请他帮个忙,去商店买香烟,指定买什么牌子的,多少钱的,他去了,结果那牌子的香烟没了,有同样价格的,他就不买,把钱送回来。人就说,那个也行啊,他才又跑一趟。再比如,一户人家正在忙活,人来人往的,赵建平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人家家里往沙发上一坐,自己动手拿烟抽,还吃东西。主人家说他吧,不好意思,都乡里乡亲的,不说他一句,他自己不知道。对这样的人和事儿,南太行乡村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没眼色”。
“眼色”的意思,就是人的灵性,就像一首诗的灵气,看不到摸不到,但可以明显感觉出来。人都知道赵建平生下来就是一个“日惑蛋”,也不责怪。人们都知道,和一个日惑蛋说事儿,相当于撞南墙,自己找罪受。赵建平怎么做,只要不过分,一般没人当场指责他。
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人上了岁数,经常丢三落四,就会自己说自己,老了,日惑了,不中用了。然后是深深的叹息。所以,日惑这个词,也指人的记忆力退化,对其他事物无法掌控,做事颠三倒四,自己力不从心的意思。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