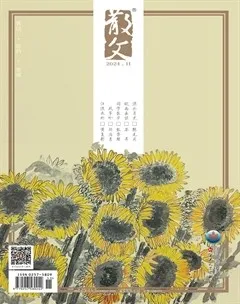落木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写于代宗大历二年(767)秋日夔州的七律《登高》,从内容到形式几乎达到了挑不出任何瑕疵的地步, 在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视为七律巅峰之作,素享古今七律之冠的盛誉。这一年,杜甫已经五十六岁。明代诗歌批评家胡应麟在《诗薮》中十分肯定地给出结论:
作诗大法,唯在格律精严,词调稳惬,使句意高远,纵字字可剪,何害其工? 骨体卑陋,虽一字莫移,何补其拙? 如老杜“风急天高”乃唐七言律第一首。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深沉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首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重要题材,登高,算得上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古老母题(尤其是后来与九日登高风俗结合在一起以后),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在《魏风·陟岵》这首最早的登高诗中,民间的歌者已将登高与另一怀人母题息息相关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登高行为赋予忧伤的色彩。登高怀人, 通常的情形都是身处故乡的人怀念远方的人。《陟岵》却进行了反向写作,不是故乡人在登高怀想,而是远方的征人,在登高怀想同样怀想着他的故乡亲人。
实际上,杜甫那首写于青年时代的《望岳》, 尽管诗人最终并没有登上泰山顶,仍然可以视为一首登高诗。晚年的杜甫虽然身体不太好, 还是不断地登高不断地写登高诗。如作于大历元年(766)的《九日诸人集于林》,其诗题中的“九日”,一作“登高”:
九日明朝是,相要旧俗非。
老翁难早出,贤客幸知归。
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
漫看年少乐,忍泪已沾衣。
此前四年,杜甫写过一首登高诗,名叫《九日》,其时诗人还在四川梓州一带避难:
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
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
这首诗和《登高》诗在情绪上颇有些相似,同样出现了“白发”“路难”(“艰难”)和“酒”。
不过,若说堪与《登高》比肩者,唯有杜甫写于成都的《登楼》可以当之,《登楼》与《登高》,可以视作七律诗史上对峙的双峰: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这首思古伤今、关怀时代命运的《登楼》,同《登高》一样,也是杜甫七律中的压卷级存在。王嗣奭《杜臆》指出:
此诗妙在突然而起, 情理反常,令人错愕;而伤之故,至末始尽发之,时竟不使人知, 此作诗者之苦心也。首联写登临所见,意极愤懑,词犹未露,此亦急来缓受,文法固应如是。言锦江春水与天地俱来,而玉垒云浮与古今俱变,俯视宏阔,气笼宇宙,可称奇杰。而佳不在是,止借作过脉起下。云“北极朝廷”如锦江水源远流长,终不为改;而“西山寇盗”如“玉垒浮云”,倏起倏灭,莫来相侵。“终”“莫”二字有微意在。
这段话,除了对“锦江”与“玉垒”有些过分的符号化解读之外, 其余都说得相当好。王嗣奭在清代杜甫研究中,常能言人所未言,可谓老杜的异代知音了。
如果说《登楼》的起句突兀,那么《登高》的起笔则堪称“陡峭”,如同天风海雨袭来,不给读者留有任何延宕和喘息的机会:“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心理学认为, 人的情绪常常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环境呈现某种极端状态时,会更加剧个体的心理反应。杜甫此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与天高气爽的日常秋景不同,峡中的秋天自有其动人魂魄之所在。这是由三峡的峡谷地势所造成的: 壁立千仞的峡谷两岸剧烈地挤压着气流, 穿行其中的风势远远强劲于平坦开阔之地的风力。同时,峡谷虽狭窄,抬头却可以仰望苍穹,在空间对比之下,天空变得格外的高远,格外的不可触及。风急与天高,意味着外部世界的强烈变化和广阔无垠, 使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 感到对未知不可控力量的敬畏。接着,诗人由触觉(风急)与视觉(天高)直接切入听觉———猿啸哀。 猿的哀鸣,既是一种自然现象, 又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借助拟人化的手法,诗人将自身的哀伤情绪投射到了自然之中, 形成了一种物我共鸣的效果。
古代的三峡一带多见猿类———《水经注》中就记载了流行于当地的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的夔州诗中亦多次说到这种令人神伤的动物:“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耳聋》)“雁矫衔芦内,猿啼失木间。”(《远游》)“有猿挥泪尽,无犬送书频。”(《雨晴》)
或许是诗人觉得这样的风景太过惊骇,于是在次句写下了比较温情的画面,感觉也由听觉再次回到视觉, 尤其是青绿与雪白的色彩。随着飞鸟的影子不断扩散,生命的气息弥漫开来, 如同宣纸上洇开的彩墨。但是,温情背后仍然是寂寥和空虚的感觉,鸟儿飞回,飞回了巢中,而诗人真正的家在哪里呢?
楼台之上, 视野自然比在平地开阔得多:“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同《登楼》诗颔联“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一样,《登高》的颔联写得惊天动地。前者之苍凉后者之壮丽,前者之秋色后者之春光,前者之迷茫后者之透明,将汉语的表现力推向了无人能及的纵深。无边落木、不尽长江,上句写岸边,下句写江水,都在以自身的节律变动不息;锦江春色、玉垒浮云,上句写江水(锦江),下句写山峰(玉垒),江水是动的,但在更为广大的春色笼罩之下,似乎又具有一种宁静之美,其“来”不是奔腾汹涌, 而是如爱情一般不知不觉间便浸染了万物。山峰是静止的,但由于有浮云聚散,便充满了动感。空间之美与时间之美在此融合,在此化生,在此永驻———这是什么样的气象! 这是什么样的笔力!
一般来说,落木就是落叶的意思,不过我觉得既然叫“落木”,也不排除有落枝落条的意思。明初的刘基在《杂诗》中就说:“叶落枝亦尽,愁闻蜻蛚吟。”以“萧萧”状落木的漫落,仿佛是广角的慢镜头,不仅呈现了落木的落姿, 还隐括了落木的声音。以“滚滚”写长江的奔流,亦同样具有声色之美。清人王士禛提醒人们不要轻轻放过这两个叠字,杜甫早已窥破汉语的秘密,将叠字用得出神入化:
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如杜子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是也。
落木用“无边”,说的是上下空间的持续状态,是仰望;长江“不尽”,说的是西东方向的瞬息涌动,是俯视。无边的落木,不仅从树上、壁上和天上落下, 也从屈原的《九歌》中落下, 从湘夫人的忧伤中落下———“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滚滚的江水和无边的落木,无不寄意事物的悄然流逝: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流逝,美的流逝。在此物象的暗示下,诗人清晰地感受到个体生命是多么短促。
不知“落木”一语最早始于何时,不过我想一定和前面引述的《九歌》有关。我们在堪称杜甫偶像的北周诗人庾信的《自古圣帝名贤画赞》中看见了落木:
治身紫府,问政青丘。
龙湖鼎没,丹灶珠流。
兴云即雨,落木先秋。
至道须极,长生可求。
又在南朝张正见的《赋得秋蝉喝》中看见:
秋雁写遥天,园柳集惊蝉。
竞噪长枝里,争飞落木前。
风高知响急,树近觉声连。
长杨流喝尽,讵识蔡邕弦。
杜甫在《秦州杂诗》中也曾写过落木,冬天的落木:
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
塞风寒落木,客舍雨连山。
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
东柯遂疏放,休镊鬓毛斑。
《刈稻了咏怀》写于夔州,其中再次出现落木:
稻穫空云水,川平对石门。
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
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
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在诗中经常使用“万里”一词,通常都是以此广阔无垠的背景托喻自身的细微与悲情:“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寄杨五桂州谭》)“中原有兄弟, 万里正含情。”(《村夜》)长时间地远离故土和亲人,让杜甫感到越来越孤苦, 仿佛天地间就只有他一个人。《江月》中也出现了“作客”一词:
江月光如水,高楼思杀人。
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
玉露团清影,银河没半轮。
谁家挑锦字,灭烛翠眉嚬。
“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所写情景与《登高》甚为接近,就是太过凄凉,不如“万里悲秋常作客”,悲中有壮,哀中有力。这个“客”,和《登楼》诗中的那个“客”,是同一个人,只是景况更加不堪。
每一首好诗, 都应该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性。清人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注意到了《登高》的脉络:
远客悲秋,又以老病止酒,其无聊可知。千绪万端,无首无尾,使人无处捉摸,此等诗如何可学?“风急天高猿啸哀”,发端已藏“独”字。“潦倒新停浊酒杯”,顶“百年多病”。结凄壮,止益登高之悲,不见九日之乐也。前半先写“登高”所见,第五插出“万里作客”,呼起“艰难”,然后点出“登台”,在第六句中,见排奡纵横。
杜甫在夔州写过一组《九日五首》,现仅存其四(一首七律、三首五律),那么第五首去哪儿了呢?赵次公认为,这一首不是被弄丢,而是被移了出来,变成了《登高》。为什么要移出呢? 是因为这一首写得太好太突出,其光芒完全湮没了另外四首,所以编纂杜集的人才将其从组诗中抽出。这种可能性理论上是存在的,理由也充分:一则写作时间地点完全一致,二则诗歌情绪连贯。譬如《九日五首》中同为七律的第一首: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独登江上台。
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
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
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
这一首确实和《登高》一脉相承,甚至韵脚都一样。此诗若放在别人的集子中,绝对是好诗:竹叶无分,菊花不开,日落玄猿,霜前白雁,多好! 然而若与《登高》摆在一起,气力也好气象也罢,就分明显得衰飒了些。也有一种可能是:杜甫先写出这一首,觉得不太满意,于是又写下《登高》,随后又写出另外三首五律———通常, 杜甫组诗的形式都是一致的,不会一首七律一首五律。若果真如此,那么将《登高》移出来的人,很可能不是别人,而正是诗人自己。只是《登高》被移出之后, 总的标题却未及相应改动。
九日登高, 赏秋览胜, 心情应该是好的。孰料杜甫登高远眺,却酿成一场浩大的痛苦而孤独的体验。全诗最后由造化复归个体身心, 从浩荡天地回到了一杯浊酒———“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就如一通响鼓,最后的收音却很轻,很准,也很扎心。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