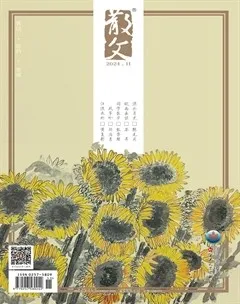陆城粮仓记
这些年有过好几次机会, 却一直不曾到一座粮仓里面去过。这一次到陆城却是不期而遇,从粮仓入口一直进到它的腹腔,像一粒稻米那样停在里面。接着又像那些看守粮食的人一样走上粮仓高处的栈道,从粮食们的天空走过。
小时候倒是去过生产队的保管室。那里头除了稻谷, 还有棉花油料农具化肥和农药之类。就因为里头住着粮食,保管室的房子是全生产队最好的。人住的地方屋顶可以漏水, 墙上可以有裂缝, 地板可以上潮,粮食住的地方就不行。爷爷的说法是,吃过白米饭就知道,粮食比人金贵,生产队没了谁都行,谁没了粮都不行。
一个人在农村长大种过田, 也就跟庄稼一起生长过, 就知道种子会在泥里头翻身扎下根长出叶瓣来, 知道禾本植物会分蘖,一粒稻种可以抽出几根稻穗,每一根穗条又可以排出好些稻粒来。知道因为有了这些禾本植物,才有了余粮有了粮仓,从而也就有了大型号的人类社会。
陆城地处长江中游的丘峦与平畴地带,是天然的粮仓。陆城之为陆城,据说是因为三国时候东吴的陆逊, 说他当年以此为据点囤积粮草。看着是陆逊造就了陆城,掉过头一看, 又似乎是这块地方的水土粮草成就了陆逊。不管怎样,陆城打一开始就与粮食有关是实。现在的陆城粮库始建于1952 年,两栋苏式仓库外加一栋粮油供应站,建筑面积一千三百平方米。它们与之后陆续建起的几栋粮仓一起, 成为湘鄂交界的一处规模较大的集中储备和中转仓库。如今,两栋苏式仓库已不再存储粮食,云溪区已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偌大的房子空荡荡的, 一个人填进去就感觉自己像一颗细小的谷粒, 只觉得世界很大人很小。想要说点什么,声音从嘴边开始旅行有些到不了边。七十年的粮仓,不知道有多少粮食从入口进来,在这里停留,又被运了出去。就想起“沧海一粟”这个词。海里头不是水吗? 为什么不说沧海里的一滴水,而要把粮食扯过来呢?大概因为无论水滴还是沙子,都不及粮食离人那么近。那个里边藏着一点点生命的细小颗粒, 简直就是人自己。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的骨肉里,哪一处不是粮食? 把一粒粮食放进无边的空阔与漫长的时间里, 人一下就有了切身的感受。
我收割过稻子。稻秆在往上长的时候是那样挺拔,足以把抽出的稻穗举起,把一生的事业撑持下去。等到上面的谷粒渐渐成熟, 它们也像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弯起了腰身。那些中空的秸秆,好像从还是种子起就已经懂得,它们之所以长出来,只是要把来自泥土的水分和养料送往谷粒那里,而留给自己的,刚好够它们完成这些。谷粒熟了,它们的身子也就软了。接下来的一切就像赴约似的, 那些前来收割它们的镰刀恰好弯成新月的形状, 那些拿着镰刀的人同样弯下了腰身。再往后,天与地在稻子身上达成的那份果实, 就带着那一年的阳光和雨水进入粮仓,进入人的血肉之中。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去半坡遗址, 一眼看到泥地上储存粮食的窖穴圆溜溜地窝成一种呵护的样子, 人与粮食之间的那份亲情,仿佛全都在那圆溜处。后来又在博物馆看到那时候留下来的已经炭化的粟米,还有陶罐陶盆小口尖底瓶与石器。六千多年过去,人早已化入尘土,在半坡人的身后,出来代表他们的,是粮仓和粟米,还有他们用过的那些器具。
阅读粮仓,阅读一颗稻粱的生命行程,也就是在阅读我们自己。我们这些身上装着稻粱在地面行走的人,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顶着各式的帽子揣着各样的名片,要么叫作这个要么叫作那个, 就像有的稻粱叫作糍粑有的叫过桥米线, 有的或许还成了爆米花。可是最基质的部分还是那样,粮食还是粮食,一如我们也还是要吃粮的人。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