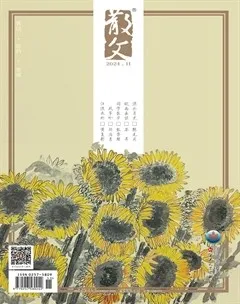今夜何处宿
一
是万不得已才让儿子留守H城的。人们总说“留守儿童”,孩子们“留守”的多是自己家乡的农村。可我们来自安徽家乡的农村,携儿带女到外省漂泊,脚跟未稳,又要去向下一站另一个外地, 把孩子仍留在上一站暂居。生计难以维持, 决定离开苏北,去苏南“觅食”,那儿女怎么办? 起先想让我娘来照料,做奶奶的也答应了,后来说家里走不开,上有老下有小。我只好告诉儿子:奶奶说她还有更小的孙子需要照顾,另外还有你的曾祖母老太太,奶奶说她两难,没得法子啊。儿子说哦哦, 仿佛懂事地应着。那就让十四岁半的他,远在七百里外独自生存吧。
那天晚上给儿子送铺盖去, 初七八的月亮大大的,又亮亮的,半圆不圆的她,将柔柔光辉如水一般漫洒在校园里, 给人一种可堪托付的安谧感。教室里亮着的灯光与月光相得益彰,宿舍一带却是漆黑一团。生活老师给我们开了门,又开了灯,让我们为儿子选择寝室和床铺。寝室蛮宽大,先儿子而来的同学未洗的袜子、乱堆的球鞋、散放的书本,还有随手扔的毛巾、废纸等,把冬日的空气搞得有些糟。男生宿舍,一股青春男孩的脚丫子气息直往鼻孔里钻。
天哪! 这怎么能住人啊。妻子惊呆。
环境能改造人,人也能改造环境。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妻子和我撸起袖子,分工合作,找来脸盆笤帚拖把和抹布,开始连夜大扫除。整理毛巾和盆桶,收拾桌子与茶缸,归整鞋子袜子,不消一会儿,整个寝室明亮整洁了许多。接着为儿子铺床。带来的海绵垫子过宽,铺上去不能就位,又没带剪刀, 只好取下我钥匙串上的小水果刀,一块一块地切削;怕五厘米海绵太薄,又垫上条毛毯, 那是我们当年结婚时用的老毛毯,就让它代替我们夜夜拥抱儿子,也被儿子拥抱吧。
不久我先到苏南, 他妈仍留在H 城,清理店货与尾账, 也是要看看儿子能否安处。儿子住进校舍头几个晚上,做妈的放心不下,近十一点,掐算着晚自习刚下课,骑车潜到寝室的楼下,像个小偷一样,去关注儿子就寝前的一举一动。妻子对我说,如实在不能适应,她愿意做儿子的“宿管”和“陪读”。夜深,风冷,灯多,又不想被人看见,楼角里的她有些瑟瑟, 但一直坚守着直到寝室关灯。有次被正下楼打开水的儿子迎面撞上, 后者一怔, 接着便是推搡着要她离开。儿子生气:你干吗跑到我学校来? 快点走! 一句“我学校”,是拒斥和排外的。做妈的嘴上说就走就走, 手却上来帮他整理凌乱衣领。那头小牛犊犟了起来,相当痛苦地跺起小牛蹄,发出低吼:你再这样我不住校了! 你丢我面子知道吗?
二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话筒里咝咝电流的声音, 像一条小蛇在伸缩着舌头。蛇在跑,话费也在跑。电话电话,电催人要不停地说话。我无话找话地问:哦,小子你今晚住在什么地方呢? 那边不语, 我又问了一遍。半天,听儿子吞吞吐吐着回答:我,我,今晚还真不知道住哪儿呢……小子作老人般叹息,说发愁着呢。牵挂,思念,心疼或伤感,就在那一刻带着质感袭了过来,仿佛儿子脸上密集的青春痘一样。
儿子是从女儿同学家里打的电话。他每个星期天下午先打过来, 见号码我们回拨过去,为的是不让同学家付电话费。儿女都留在H 城,女儿大些,就寄居在同学媛家。做弟弟的呢,偶尔也去蹭蹭,把那里当作姐弟的会师地,稍能落脚的地方。媛的父母单位老房窄且破旧,号称的“两室一厅”,其实统共不过有钱人家的厅房大小。我们走时把家具啥的赠予媛家, 媛的妈妈都给堆在屋里。女儿与媛一间,媛的父母一间,客厅摆张饭桌便抵了厕所的门。儿子平时住校,只在周日下午去那里休整一下,理理发,洗洗澡,换换衣。方便成了最大的不方便,儿子说,媛的父母方便时不怎么关门令孩子们脸红。可是,当天毕竟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是年底的12月31日, 翌日就是元旦。儿子告诉我,学校放假三天,所有住校生都被“赶”出了校门———回家过新年。
回家啊回家,我们的家呢,我们和儿女的家呢? 家是啥,啥又是家? 是拥有栖身的房子才算有家吗?在故里安徽,两三间破落未坍的土坯老屋, 那里面烟熏火燎地蜗居着我娘和我的祖母, 近七十岁和不到九十岁的两位老人, 她们在那里平凡勇敢地坚守着,也在那里孤独无助地遥望着。许多年前她们各自从娘家嫁到了婆家, 农村女子的人生,一世就活在那里,不出意外也将死在那里。漂泊苏省的北与南, 儿女没法上学,就带点小礼把户口挂靠H 城城郊一农民家里。然而仍是没有能力置房呀,风吹浪打和雨雪风霜里, 我们一家四口就像是一小撮聚散漂荡的浮萍。H城肮脏的某某路后面,有一套我们赁居了N年的“好房”,那房子破到比媛家的还差两三倍, 可那是父母所能给自己儿女唯一的一个家了。生活如果是根鞭子,我们就是那被鞭的陀螺吗,被抽得满世界地乱转? 我和妻子“转”到了这里,我们在这里,儿女在那里,我们在江南,孩子在淮左,这里离孩子那里好近,又好远啊。
我和妻子幸与不幸地赶上了改革开放,以农民身份漂进城里打工做小买卖,纳税缴费时被叫作了“个体户”。个体,一般是指一个生物,或一个群体中的特定单独体。因为我们是单独一个的生物个体, 孩子们今夜就将注定无家可归吗?
在新年钟声将敲响的夜晚, 妻子呆坐床边又在默默流泪了。她怀里抱着的家庭影集,成了她每晚必看的心灵圣经。翻阅着也是回忆着,看儿女们一天天地成长,她的眼泪流得一塌糊涂。顺着看,儿子从小往大里长, 嫩芽幼苗渐渐变得玉树临风; 逆着翻, 儿子从瘦高的一米七, 再回到她的怀抱,回到她的乳房和肚子里。怎么看怎么心疼。儿子一岁时在油菜花丛里受惊时的哭泣,儿子三四岁在就要离开的山村前,沉着脸,小手反叉着腰,还有一张儿子已坐上城里马桶时出恭流汗的痛苦表情……
很少看到儿子开怀大笑, 连微笑的表情都少。我们常感到不解,小小少年这是怎么了? 不是都说面部表情是人生经历的刻记与写照吗? 那一张很生动,极难忘,在瑟瑟秋风里, 拍摄者抓拍了一张儿子挨冻的窘态。刚刚一岁半的“小模特”为了一块总也够不着的大白兔奶糖,被使坏的老爸哄着脱光了身子,赤条条的,光溜溜的。小家伙一丝不挂,瘪着嘴想哭,却终于又没能哭出来。
三
H城中学的前三名分别是:一淮中、二清中、三洲中。第三名的洲中因总被前二者抢去生源,便每年最先组织考试,带摸底性质,也带着“掐尖”的目的。洲中的那场考试儿子在全市两千六百人中名列第二十五,只要我们同意,将稳稳被洲中录取,并且校方已承诺进“快班”。老乡中的C,C的儿子名次在儿子后面的一百名以外。接着淮中、清中市里安排在同一天考试,C 直接给儿子报淮中,我儿子自己报了清中。我心里不服气,便劝儿子改变主意,夜以继日地劝,实际上是勒逼儿子“向一流冲击”———考淮中。儿子噘嘴不肯,因为他觉得自己走清中这条路最有把握和自信。
记得是6月30日临出发考试的早上,儿子仍流着泪说要考清中,我开始骂他,什么“燕雀之志”“鼠目寸光”等。妻子也来劝,他们母子感情好, 但妻子关键时刻又劝又逼着儿子听我的主意。儿子不得不让步跟我去参加了淮中考试。一周后放榜,老天洒下湿淋淋的梅季小雨, 我恐怕毕生也忘不了在雨中为儿子看榜的情形。那打印张贴着的录取名单里, 从前往后看, 五十名以内,没有儿子的名字,再看一百名以内,仍没有。我慌了,就从后往前看,目光犁过两三遍,终于确认没有儿子的名字。被遗忘了吗?被搞错了吗?贤郎名落孙山外,而那“孙山” 正是老乡C的儿子。那孩子上的淮附小,学过英语,儿子上的繁小,压根没教英格里希。差距就在这儿!然而这就是人生抉择的生死时刻,儿子已经被秒杀。儿子淮中落榜,同时与清中失之交臂,而此前洲中的录取通知书已被我们倒炒鱿鱼, 过期作废了。我们落得的结局,便成了清淮皆不要,洲也不肯收, 儿子成了个刚刚小学毕业就无学可上的少年……雨, 夏日丝丝点点凉爽的好雨,你浇灭了火苗,打疼了希望,湮灭了未来。我淋着雨向妻子报告消息,全家泪雨。
三年后的初中升高中, 儿子争气地被清中录取了。而我竟又打起了不服气的主意,三年前在淮中输惨,我要儿子和我一起“再攀高峰”。那张英语奖状至今还能在儿子当年的学习资料里找到, 而我也许再没有勇气拿出看一眼了。儿子在第四五流的某某路初中就读, 竟凭苦干拿到了全国级英语竞赛第一名, 整个H 城不过五人中选,而儿子是光荣的佼佼者之一。那张奖状被认为是“扔水里鱼都跳”,我就带着这投名状先行登门去找淮中领导, 他们看后做了登记, 给出承诺:“你这小孩我们一定要了。”但旋即又加上一句:要看全市统一考试成绩。结果全市统考儿子的分数与淮中差了近十分。我再去找淮中兑现前言,却被答复:请缴择校费。此时,C家买房了,C的儿子录取了淮中。
正在赌气想为孩子们买个蜗居的我,哪舍得出三万两千五百元的择校费? 儿子最终成为清中的学子,但是不满一年,竟又被我易地“移栽”了……
四
翻阅十几年前的家庭记录, 一股难言的滋味堆在心头。那时候做父母的我们念儿子,盼儿子,渴望团聚,可今时今日,儿子连同他的孩子都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块儿。你让我说实话吗?对于儿子我已感到厌烦, 儿子之于我们, 恐怕也同样是这感觉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同在一屋檐下,反而生疏,厌腻隔膜,人变得像乌眼鸡对乌眼鸡一般。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背诵着伟人的这首诗,我在少年失怙的十五岁那年,就走出家乡,过长江去贵池挑鱼花池,在冰碴淹没大腿的泥淖里冻坏了身体, 最后到山里“驮料”挣回家的路费。十六岁上江西彭泽红光砂场拉砂, 遭遇一场砂暴雪崩差点埋在里面, 我写信给娘, 那信封背面的“诗”据说现在还在村里流传。十七岁上庐山学瓦工手艺, 冬夜凌晨洗水刷石从六层楼失足掉落, 一路胡乱抓摸在四层楼上抱住了一根脚手架毛竹竿……每一次都在又恰恰荡回的边缘徘徊人世, 否则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妻子和儿女。
我娘在家乡风闻“庐山有小孩摔死了”,就摸爬着行程千里上了山。看到我又吐着血能上工了, 工头问要不要带下山去治疗,我娘忍着两泡眼泪点点头,我却牙咬嘴唇把头摇了摇。山脚下的县城里居住着我的三个舅舅, 舅舅家的表兄弟妹们过的是城里人生活, 在我这年纪正是求学的黄金时期, 我怕自己一看到他们就捺不下心来学徒打工了。我坚持上工,没钱就医就买几颗黑跌打丸, 就着工地洗石子的黑胶皮管里的水生吞。到腊月里回乡塘里挑窑泥,一担窑泥不止一百五十斤, 我甩上肩走一截嘴里冒甜腥味,又一口一口地吐血,娘带我到乡村医院去看病, 拎回家大包小包中药却生怕邻人看见, 怕人家说这小伙子有病将来讨不到亲。这背伤一直拖到今时,梅雨冬九还出来喧嚣作痛。“信儿如鸟飞江北,千言万语寄儿心。儿今身受苦中苦,日后方为人上人。”我终于忆起当年写在家书背面的寄语,想到的是我娘,想到的是她的“大胆”、她的“放心”,用今天的话讲———她的心可真大啊! 她宁愿忍受着每日每夜的思念与牵挂, 也胆敢把长子鹰一样地放出去飞,因为她知道,守着窝的鸟,永不会有大出息。往深里想,这种感情里,恐怕也包含对自己儿子的肯定和信任, 于是敢于把更大的舞台和天空,全都给予他。而这里面当然也有无奈,娘她又能怎么办呢?史铁生在《我与地坛》写到他的母亲时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那么作为娘的儿子,我之于我的儿子呢?在育儿教子这件事上,我比我娘这个农村妇女的境界与胸襟,是不是差了“蓬山一万重”呢?
生怕儿子吃一点点的苦受一点点的罪,生怕他饿了渴了凉了热了,生怕儿子有一些些的委屈与不如意, 稍有一丝丝风吹草动,我和妻子就要冲上前为之“排雷”。是的, 我们把他当成了易碎品和温室中的花蕾,我们承受不起时空分离的考验。我们团聚,小聚即安就像农民小富即安。那年,就是儿子在清中就读的第二学年, 我竟连他的学籍也不顾了, 硬生生地把这株小树苗移栽到苏南来了———花费两万元, 做了个“借读生”。这边公布成绩,儿子的名字和分数,作个体“单列”。在提出批评或表扬时,可爱的老师总来上一句:某某同学,我们并没有另眼看待你哦,虽然你是个借读生。后来高考,儿子回到学籍地H城参加考试,惨遭滑铁卢,便只好复读,再复读。
五
要是时光能够倒流, 要是青春可以重来……人们是否能够承认, 爱子往往也正是害子? 床替他铺好了,饭替他盛好了,连如厕,儿子的妈都要隔门问上一句“可擦干净了”。啥都替儿子想和做了,殊不知,这并不是把儿子当儿子,而是把儿子不当儿子。那时的我们还没学会做父母, 现在感到懊悔和惭愧。“古来成败难描摸,而今却悔当时错”,可是还来得及吗? 张爱玲家大人怕她熬夜辛苦了, 大年初一早上让她多睡一会儿, 谁知她醒来时发现新年的鞭炮已经放过了,“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是啊,那稍纵即逝的风景已然错过,就算穿上新鞋子使劲再去赶,又能赶得上吗?许多年后, 儿子的人生已定型, 他有自己的孩子,也为人父了。而我们呢,也让他有了个小弟了……亡羊而补牢, 现在的我们是否学会了一点什么, 让自己和孩子可以避免重蹈前车之覆辙?
那一幕又浮上心头。
天已经黑了, 时间已经晚了, 拿起电话,想再拨过去询问儿子今晚的下落,手僵在了半途。他妈摇摇头,又摇摇头。不能再扰,不敢再扰了。白天至少已往媛家打过五六遍电话了,人家会不会嫌烦?一烦会不会就不让姐姐暂住她家了? 今后会不会不给姐弟好脸色? 还是撑着吧,我和妻子,就那么面对面地撑着,呆鹅一样……
时间的脚步声嘀嗒作响, 带着那一年最后的欢歌笑语一路飞奔。邻家的电视声传入耳来,欢呼与鞭炮一同炸响,伴随而来的还有祈福的新年钟声。礼花升入夜空,主持人和热情的观众开始跨年读秒: 十,九,八……
悠悠钟声新年到,万家齐欢笑。儿子,今夜的远方,有没有你就寝的床铺?夜无瞌睡,失眠背诗,总把两句串烧在了一起:“不知今夜何处宿,一夜征人尽望乡。”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