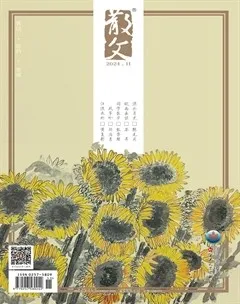江流天外
宣城差旅几日,归途急雨敲窗。车行一处,司机像是摸透了我的心思,南向一拐,进入一条国道, 不一刻, 那座西班牙人1872 年建造的大钟亭映入眼目———这是2020 年7 月,大雨滂沱,我再次回到古名澜溪的故乡大通。
江南的梅雨季节,站在龙头岩上,鹊江对面的和悦洲漂浮在那无边的浑黄中,越发的碧绿轻盈,如一片巨大的荷叶。在我的脚下,灰褐色的瓦连绵一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此刻,这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被满灌的江水切成了一条条、一块块。
七十五年前, 我降生在鹊江对岸和悦洲的一条街上, 八岁时举家迁居澜溪共和街六十四号,一直到父母相继离世。现在,我成了一个外乡人,有时候回到澜溪,却再难得见一个熟悉的人。偶然大街上遇到儿时的伙伴,也俱已鬓发苍苍,表情都是淡淡的,绝没有之前想象的激动。而我也为不再能讲好纯正的家乡话而尽量寡语, 免得人说我洋不洋、土不土。
接到电话的张利民为我们带来几把雨伞,还有一艘不小的木船。几年前,长江禁渔,有人要一把火烧掉沿河所有的渔船,远在深圳的郭熙志联络我们几个乡友共同发起倡议, 希望能为澜溪渔民留下最后一点记忆。被我们保护下来的渔船,现在又担负起为我们服务的义务———世界上的事情,原就是因因果果循环往复,说是说不清的。
江岸沙滩的累年淤积, 加速了江河的改道, 发达的空中和陆地现代交通取代了老式的马车和轮船, 这座曾经有过“小上海”之称的古镇,早已繁华不再,就像一个老人,渐渐地被人忘却,受人冷落。
兴于水而衰于水, 这也许就是故乡的命运。
大约一百五十多年前, 湘军首领曾国藩站在甲板上四下巡望, 远处一片白亮的沙洲引起他的注意。近了,只见枫叶荻花,秋风瑟瑟,又几点灰白,一两处村庄,二三十户人家,男耕女织,一派祥和。在发现长江上这片白沙孤岛的一刻, 曾国藩兴奋地对着天空大叫:天助我也,我行于天! 他让部将彭玉麟镇守这一片水域, 以抵挡即将从南京打过来的陈玉成军。又给这片荷叶般漂浮在江面上的孤岛易名和悦洲, 赋予其一道儒学的光润。从此,孤岛不再冷落,各路商家纷至沓来。洲上有了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有了清字巷、洄字巷、浩字巷等共计十三条通江的巷子。为了控扼水上命脉, 曾国藩又在对岸那个早被宋代文人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写进诗里的古镇澜溪设立盐务招商局。曾文正比谁都明白,当下的世界,谁掌控了盐,谁就能上控武汉,下夺南京,进而所向披靡。
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
须风那敢望,下水更劳牵。
芦荻偏留缆,渔罾最碍船。
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
有人说,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大通镇》是故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首秀”。其实,早在此前近百年的北宋时期,诗人黄庭坚就曾在这一带滞留,留下诗作,且不止一首———
提壶归去意甚真,柳暗花浓亦半春。
北风几日铜官县,欲过五松无主人。
(《阻水泊舟竹山下》)
元祐九年(1094),黄庭坚五十岁,知宣州(今宣城县),正去知鄂州(今湖北省武昌县)路上,却因《神宗实录》一书被一道圣命阻于路途,以听候国史院的查证。七月,《神宗实录》一事似乎并没有多少进展,黄庭坚趁机去看望同他一样犯了“讥刺朝廷”罪的东坡先生, 这一对几乎一生都在贬谪路上风雨颠簸的难兄难弟相遇于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尽诉衷肠,何其痛快淋漓。三日后,二人洒泪而别,竟成永诀。也是在此间,黄庭坚顺道经过铜官(今铜陵),见风高浪急,得诗一首,诗中有“顿舟古铜官,昼夜风雨黑”以及“北风几日铜官县,欲过五松无主人”之句。铜官、五松,均是现时铜陵的别名,曾以古铜都著名。恰这时,提壶鸟在耳边叫着:“不如归去也,不如归去也。”这如同人语般的鸟啼,听得山谷先生五内俱焚。是的,是该归去了,像前辈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又过了九十多年,杨万里也来了。与前辈诗人不同, 杨万里的时代, 正值宋金媾和,小朝廷偏安江南,冤死风波亭的岳飞也得以昭雪。偏安一隅的南宋依然地大物博,依靠着土地的丰肥和人口红利, 权贵们依然和歌而乐,纸醉金迷。
1162 年,杨万里在零陵丞任,七月,踌躇满志的他焚烧了青年时代的一千多首诗歌,表示与过去告别。杨万里所告别的,不仅是自己青春期时带些稚气的“江西体”,也是自金人入侵以来社会动荡给人民以及自己所带来的动荡与不安。1163 年,孝宗皇帝与名臣胡铨谈及当代诗人的一些情况,表达了朝廷亟须一批青年才俊的愿望。胡铨举荐了一批年轻新锐,杨万里亦在册。杨万里开始关心农事, 在他的诗歌中抒写家国情怀,他所独创的“诚斋体”,使他在后人眼中往往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 这样的评价应该是足够高了。在从政的道路上,杨万里虽然屡遭挫折, 但比起前辈的苏轼和黄庭坚,他算是幸运得多了。
绍熙二年(1191),花甲之岁的杨万里一度成为朝廷重臣, 六月,“奉诏决狱于江西上饶”。这一次,他自安徽宣城、宁国等地入江西浮梁,案毕,又过鄱阳湖,循长江经彭泽、湖口、舒州、池阳、铜陵、芜湖、和州归建康,历时二月。正是这一次的循江而下,因一场风雨的阻遏,杨万里有了《舟过大通镇》。
南京行船慢悠悠,采石弯弯对荷洲。
芜湖螺秆山上峡,羊山矶对和悦洲。
(大通行舟谣)
大通位于鹊江南岸, 在其下游两三公里处,有羊山矶立于潮头,其水有不可测之深,遍布险石暗礁,水流湍急。鹊江平缓的江水顺流而下,遇到羊山矶湍急的漩涡,便形成“江拐弯,海掉头”的独特水势。遇到这种情况,去往下游的船不得不大江掉头,返回鹊江岸边的小镇大通歇息, 静待风平浪静。黄庭坚如此,陆游如此,杨万里也如此。留住黄庭坚、陆游以及杨万里这些诗名显赫的大佬的不是大通风光的旖旎, 也不是大通之于南宋王朝战略上的优势, 而仅仅是风浪的阻遏。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是故乡澜溪大通的幸运。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 坐于江南的大通镇因其水路的“大道通衢,融达八方”,至明清后,崛起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 并迅速与上游安庆、下游芜湖以及淮北的蚌埠并称为皖省四大商埠。历史吊诡,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却加速了故乡迈入现代化的步伐。那时候,歌星周璇的《夜上海》《四季歌》刚刚在上海大世界唱响,很快就传到了大通澜溪,南京路上刚挂出的时髦西服, 一星期不到就穿到了澜溪人的身上。现代的人无法想象,弹丸之地的大通澜溪,居然有人口二十几万之众,大通总商会下注册的招牌多达一千二百余家。有地方报纸, 有专设的红灯区, 有电灯公司,有现代化的水运码头。轮船靠岸后,平整的大街上黄包车往来穿梭, 车上的铜铃一遍遍地响过,洄字巷里灯红酒绿,勾栏瓦肆,纸醉金迷,外地人见证了小地方的大格局,于是故乡便有了“小上海”之称。
物极必反, 大通澜溪的盛世又是短暂的。淞沪抗战,下游告急,大佬们早早地撤走,驻守和悦洲要塞的川军眼看抵挡不住,临撤退前, 偶然在一堵坍塌的墙缝中发现了大户人家私藏的银圆, 于是一间间房屋被推倒,甚至索性以“焦土抗战”为名,一把火点燃。“大火持续三周”,留给日本人的,果然就是一片焦土。“小上海”元气大伤,从此衰落。
扳罾、起罾
扳个鲤鱼十八斤
大鱼留着卖
小鱼留着自家吃
虾子螺嗦送隔壁
(大通童谣)
似乎是在不久前,我们还经历着“鱼蟹不论钱”的时代。少年时,我们用四根竹竿撑起一只鱼罾,蹲守在江岸上,不消一个时辰便能满载而归。九月鱼汛期,青通河上鱼罾遮天蔽日, 河岸两旁同样是一张张鱼罾依次排列。夜里, 我们将一盏马灯放在江边,呆笨的江蟹顺着灯光爬上来,趴在江滩上纹丝不动,就等着我们伸手去捉。鱼汛到来时,从上游突然传来的欢呼声风暴一样从河岸两旁迅猛卷过, 那是渔人的歌唱,是对天地日月的祈颂,是对丰收时节的礼赞。
大通澜溪有渔村, 河南嘴是江南平原伸向长江的一片沙洲,二三十户人家,一半在水,一半在岸。境况好的人家,水上捕捞,家在岸上;一般的人家,一只乌篷船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船板被桐油油过,在日光下泛着古铜的光亮。很多年前,他们是大通的“贱民”,被人称为“鱼花子”。不知何时始,鱼蟹又开始论价了,尤其是冬天。能把躲在江底石缝中的鲤鱼鲫鱼逗到鱼市的渔人,自然也被另眼看待了, 岸上人家甚至开始与渔船上的人家通婚。
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章贤贤就娶了我同班同学周愿喜的姐姐,老师变成了姐夫,学生变成小舅子。章贤贤不仅数学教得好,还会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他一边拉琴,一边教我们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就唱“我的家在青通河小渔船上”。周愿喜数学成绩一般,语文成绩不错。小学五年级时, 语文老师方来和让我们用一句话表达自己将来的理想, 周愿喜说:“我的理想是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从此不再看这人世间的苦难。”
成年后,我爱上了文学,有时候,我会踩着青通河松软的沙滩在江岸慢慢地散步,并开始主动与渔民搭讪。得到允许,我会小心地踏着窄窄的跳板,爬上一只渔船,像他们一样盘着腿坐在船舱里, 亲戚一样喝茶。我坐在那里,看船妇用一双灵巧的手一边快速地编织一张尼龙丝网, 一边熟练地往缸灶里塞着柴火。饭熟了,船主留饭,我也不客气,一碟蒸干鱼、一碗乌黑的霉干菜烧肉,与船主喝上两杯酒,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聊江上日月,聊婚丧嫁娶,聊古今传奇,其中的“淌捐”一事,后来被我写到了一部小说里。
他说他曾祖父原只有一条小渔船,鱼蟹不值钱的年代, 他曾祖父决心干一票大的,这一干,就歇不下手了。他曾祖父的船越来越大, 吨数越来越重, 后来就开始了“淌捐”。清政府在大通设立了水事局,过往的船只都得按吨位纳税。官府有苛捐杂税,船家也自会有偷税漏税的行为。最狠的,是除夕夜里的“淌捐”。每年除夕,大通水上督察局连同税卡照例会关闭一夜, 官员回家过年,船家便有了一夜“淌捐”的机会———任船顺江而淌,免去官税。侥幸漏过一次官税算不得什么,那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祖父后来说,从英国偷运来的大烟土,是北方豪族烟榻上的至宝;《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中的蒙汗药, 黑道白道都很紧俏;法国俄国的枪支弹药,自是上海滩上青洪帮拉杆起事者的抢手货。只要有胆量,淌一次捐,干一票大的,就够吃上半生了。
光绪三年(1877)除夕之夜,上千艘船只满载着“货物”隐蔽在洲头的芦苇荡里。那天晚上, 他的祖父与曾祖父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天将黑时,不远处的芦苇荡里一群鹭鸶贴着水面惊恐地飞过, 明明已经大年三十,天气却热得像三伏天。只听得一声骤响, 那一片大铁锚起出水面时的响声惊天动地。刹那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他祖父本已经将大锚起出水面, 却听到他曾祖父大喝一声:下锚,吃年饭!他祖父说:老头你疯了吗,可不就等着这一刻吗,一年的盼头啊! 他曾祖父说:你是老子还我是老子? 他祖父急了, 回骂: 这舱里的货你留着生吃吗?说话间,芦苇荡里就只剩下他们这一条船了,他曾祖父神色严峻,将一杆撑篙递给儿子,又指着自己的胸膛说:狗日的,老子不想死后连个送葬的都没有,你先做了我,再淌捐去吧。看着曾祖父铁青的面孔,他祖父不敢再说什么, 将那只大锚狠狠地砸进水里。
第二天上午, 从大通羊山矶传来的消息让他祖父惊出了一身冷汗。那一片江面上,到处是块块被撞碎的船板,还有具具变形的尸体。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羊山矶一带究竟发生了什么。此后,他曾祖父变卖大船,置了一条渔划子,开始在青通河上捕鱼为生。老人家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临死前说:记着,天道难违。
北风起,盐船开
盐船儿郎送钱来
洄巷妹子迎人笑
安乐窝里乐开怀
(大通民谣)
自幼生活在江岸, 我写过不少江上往来人的文章, 也读过不少江上往来人的故事:唐人笔记、明清小说、地方志、高僧传、黄姓家谱、剑侠恩仇、江湖传奇、男欢女爱、精怪鬼魅。近读明史学者章宪法传来清初许奉恩的笔记小说《里乘·俞寿霍》一篇,感觉颇有意思———
俞寿霍昼寝,见一皂隶来,出铁索系予颈,拘至一处,俨如官署。堂上坐一官,叱曰:汝家累世受国豢养,奈何勾贼屠毒生灵? 罪应炮烙。俞寿霍急,大声哀呼曰:未曾有此事,小人冤枉。官乃扔下案册于地,册上书:“极凶鬼犯余寿鹤,南直隶铜陵人,顺治二年夏,左师次九江,勾其部曲扰劫沿江一带居民,除淫掳不计外,共杀老幼男女六万八千四百三十五人,罪应炮烙同等次数。”俞寿霍急辩曰:小人乃桐城俞寿霍,而非铜陵余寿鹤。
官署阴司,皂隶勾魂,听来是故事,闻到的却是人世间的烟火味道。往事越千年,仅清初以前沿江一带的乱世劫, 见诸地方志的就有二十余次。
从宋人杨万里的“鱼蟹不论钱”到曾经的鲥鱼白鳊价比千金, 这是一个水上历史的圆周。似乎又在一眨眼间,历史像翻了个个儿,江水混沌,包括白豚在内的一大批水中珍稀相继功能性灭绝。白豚、黑豚、鲥鱼、刀鱼,说没就没了,在地球上活了一亿多年的长江白鲟, 如今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的变幻,常常比翻书还快。
十年禁渔, 世代打鱼为生的渔民们上岸的第一夜怎么都睡不着觉, 他们的耳边只有江水拍打在船舷上玄妙的声响, 只有丝网被拉出水面的一刻白鳊欢腾扑跳的场面, 而九月鱼汛期青通河岸边风暴一般从上游传来的欢呼声, 仍一浪一浪地在他耳边回荡。这一切,依水而居、以渔为生的渔人们啊,又怎能丢舍? 听到否? 那从亘古传唱的歌谣:“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维其嘉矣! 物其旨矣,维其偕矣! ”
渔民出身的大通民俗学会会长张利民是我的朋友,他弃船上岸,不经商,不开店。长年的水上生活, 早就为他积累了他与家人一生的衣食。他丢弃了一切关于鱼蟹的研究,在大通后街创办了一家民俗博物馆。他有一身过硬的水上功夫。每年端午的龙舟活动,他赤裸着上身,穿一条短裤,在船尾的一根竹竿上表演水上芭蕾。他在那竹竿上接连地翻着筋斗, 或一只脚勾在竹竿上来一个倒挂,引得岸上阵阵喝彩。
这几年,大通的居民越来越少了,张利民说:我生是大通人,死是大通鬼,你不听歌谣里这样唱嘛———
一舍不得和悦洲上的花花世界
二舍不得关门口的鲜鱼小菜
三舍不得“生源”茶干一个铜钱一块
四舍不得“万春”瓜子一嗑两开
五舍不得“芝兰宝”的包子和烧卖
六舍不得“洄字巷”的姑娘拉拉拽拽
七舍不得八帮大会上的千奇百怪
八舍不得五月端午的龙舟竞赛
九舍不得鸦片烟馆的殷勤招待
十舍不得长龙山上的黄土一块
责任编辑:沙爽
——上汽大通D90……虞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