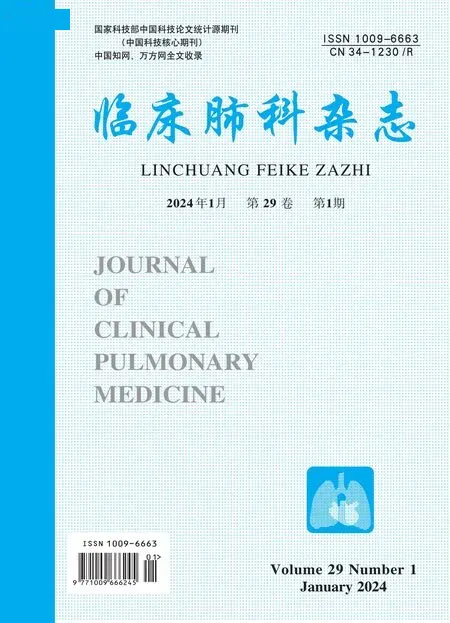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在特发性肺纤维化中的研究进展
陈凤 李龙 王洁 刘胜菲
由于病因不明,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RAGE)是免疫球蛋白受体超家族的成员,在肺脏中表达最多,有助于维持肺组织的动态稳定。其参与糖尿病肾纤维化和肝纤维化已有证明,多项研究也表明,RAGE与IPF有关。本文就RAGE与IPF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为IPF的治疗提供一思路。
一、RAGE的简介
RAGE最早于1992年从牛肺中分离出来,首次被发现是因为其结合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的能力,促进糖尿病的炎症和血管并发症。编码人类RAGE的基因位于Ⅲ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的6p21染色体区域。RAGE是一种由404个氨基酸组成的35kD多配体跨膜蛋白,由胞质区、细胞外区及跨膜区三个主要区域组成[1]。RAGE的细胞外段是配体结合位点,由三个免疫球蛋白结构域组成,包括一个可变(V)免疫球蛋白(Ig)结构域和两个恒定的C(C1和C2)组成,V-C1结构域的分子表面被疏水腔覆盖,并含有许多带高正电荷的Arg和Lys残基,多个RAGE的配体含有带高负电荷的区域,可以与带正电荷的V-C1结构域结合,以发挥其特异性作用[2, 3]。胞质结构域可与各种下游信号效应分子,如Toll-白细胞介素1受体结构域衔接蛋白(TIRAP)、透明相关福尔马因-1(DIAPH1)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和2(ERK1/2)进行关键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 protein kinase,MAPK)途径的激活[2, 3]。RAGE在体内以两种主要形式存在:膜结合RAGE (mRAGE)和可溶性RAGE (sRAGE)。mRAGE有三个结构域:识别和结合RAGE配体的细胞外结构域、疏水跨膜结构域和在细胞内信号传递中起作用的带电细胞质结构域[2, 3]。sRAGE是选择性剪接事件或ADAM10或基质金属蛋白酶对mRAGE蛋白水解的产物,其包括内源性分泌性RAGE(esRAGE)和外域脱落形式的RAGE。因缺乏跨膜和细胞内C末端结构域,只包含细胞外结构域,虽能与RAGE竞争同一配体的结合,但却不能在细胞内转导信号,是一种诱骗受体,通过隔离RAGE配体,从而阻断RAGE信号向细胞内转导。
二、RAGE在肺中的表达
RAGE在肺组织中高度表达,是多种肺病理的重要媒介,如IPF、肺癌、哮喘、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和囊性纤维化(cysticfibrosis,CF)[2, 4]。RAGE在肺中的多种细胞类型中都有不同水平的表达,包括肺泡巨噬细胞、肺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气道上皮细胞和气道平滑肌细胞[5]。而在Ⅰ型肺泡上皮细胞(type 1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AT1)中表达最为丰富[6]。通过细胞外基质跨膜区直接分泌到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参与维持肺泡结构、AT1的生存发育和分化[7]。
三、RAGE与间质性肺疾病
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是一类广泛的弥漫性肺实质疾病,其特征是不同程度的肺纤维化和炎症,IPF是一种常见且原因不明的进行性ILD。RAGE被认为在肺中起稳态作用,因为RAGE敲除小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为肺纤维化。据报道,IPF患者肺组织中的RAGE分布降低[8]。在多个肺纤维化试验模型中(包括博来霉素、石棉和二氧化硅所致),小鼠肺内RAGE表达显著下降。但在这些模型中,对RAGE的意义仍存在着分歧。RAGE缺失对石棉引起的纤维化作用最强,对博来霉素引起的纤维化也有一定防护功能,但对二氧化硅引起的纤维化则没有作用。在不同肺纤维化模型中,RAGE作用不同的原因仍未可知。RAGE对细胞是具有保护作用还是有害作用可能取决于细胞暴露的损伤类型[9]。RAGE在AT1中高度表达,但RAGE后信号的增加导致上皮损伤和EMT导致RAGE表达减少[10]。总之,在小鼠动物模型及肺纤维化患者中,RAGE的表达水平都有所降低。
1. RAGE与DNA损伤修复
肺大量暴露在高氧张力和活性氧(ROS)中,氧化应激易导致DNA损伤,进而发展为IPF,因此需要一个有效的DNA修复系统来对抗活性氧增加的后果。有缺陷的DNA修复潜力导致细胞衰老,促炎性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促进促炎因子(如IL-6)和成纤维介质(如TGF-β)的分泌,并最终导致纤维化及推动纤维化的进展[6]。RAGE的缺失可导致细胞衰老的增加,这是由于缺乏足够的DNA损伤修复,促进了老年RAGE-null小鼠的SASP和随后的肺纤维化[11]。
Kumar等人[12]通过WT和RAGE-/-小鼠模型发现,RAGE的缺失与小鼠肺纤维化组织的堆积和衰老病变有关。在RAGE-/-小鼠的其他组织中也观察到衰老病变的积累。RAGE-/-小鼠的肺显示出更为扭曲、松散的肺泡和肺泡周围区域。并发现衰老相关细胞特性的标记物IL-6、H2AX、53BP1和pATM均增加,表明存在持续的DNA损伤信号。而缺乏充分和及时的DNA修复可能会导致突变的积累,最终导致癌症。还证实了RAGE的重建有效地恢复了DNA损伤并逆转了病理异常,RAGE可以被转运到细胞核,在细胞核中它被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激酶的Ser376和Ser389磷酸化,磷酸化将RAGE招募到DNA双链断裂区域,在那里它增强内切酶活性,促进DNA损伤修复[12]。因此可知,RAGE与DNA修复之间的联系对纤维化的进展,甚至癌症的发生具有一定作用。
2. RAGE与2型免疫反应
2型免疫是对抗寄生虫感染的关键性防御机制,当调节失调时,它会导致不良的免疫反应,不仅导致过敏性哮喘和特应性皮炎(AD),还会导致组织纤维化[6]。在这种反应中,IL-4和IL-13由Th2细胞、肥大细胞和ILC产生[6]。促炎和促纤维化细胞因子,如IL-4和IL-13在IPF患者中升高。IL-13是一种多效性2型细胞因子,可促进炎症,细胞增殖和纤维化[6]。有研究发现[5],RAGE在2型炎症驱动哮喘的实验模型中起着核心作用,在哮喘进展的多个步骤中需要RAGE,包括响应过敏原释放IL-33,以及rIL-33诱导ILC2在肺部的积累。持续IL-13诱导的Stat6激活和随后的Stat6诱导基因(例如Clca1和Ccl11)的上调需要RAGE,这些基因驱动粘液产生和炎症[5]。有文献报道,ILC2s参与肺纤维化[13]。RAGE还促进ILC2的活化和积累以响应外源性IL-33[5]。RAGE在哮喘模型中直接或通过ILC2调节IL-13信号传导的关键作用表明RAGE也可能在调节IL-13介导的肺纤维化。
3. RAGE与巨噬细胞极化
M1巨噬细胞(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具有抗肺纤维化或是致肺纤维化作用还有待考究。极化巨噬细胞表现出可塑性,因为它们可以去极化为M0巨噬细胞或通过复极化表现出相反的表型,这取决于特定的微环境[14]。说明M1巨噬细胞可转向M2巨噬细胞的极化。M2巨噬细胞产生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精氨酸酶1(argininase,Arg1)以促进纤维化过程,还可产生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诱导成纤维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源自M2巨噬细胞的IL-4和IL-10的过表达也有助于肺纤维化[15, 16]。肺部间充质干细胞(LR-MSC)对肺纤维化中成纤维细胞的活化具有积极作用,M2型巨噬细胞可促进LR-MSC的成纤维细胞分化及α-SMA的表达[17]。Li Zhuang等人[18]研究发现,HMG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有助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M1样极化,RAGE在TAM中充当HMGB1的受体,并通过RAGE-NF-κB-NLRP3炎症小体途径,HMGB1增强了TAM的M1样极化。在巨噬细胞中,HMGB1通过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1/2)的磷酸化激活RAGE,然后激活NF-κB和细胞因子产生。已有研究表明,MAPK和NF-κB可能在巨噬细胞M1样极化中起关键作用[19]。He等人[20]研究表明,用RAGE抑制剂对巨噬细胞培养物进行预处理,可抑制MAPK-p38信号通路的激活,促进巨噬细胞的M1极化。此外,HMGB1与RAGE的结合与HMGB1的释放增加和RAGE的表达之间建立了正反馈机制,导致M1巨噬细胞极化的增强。说明,在巨噬细胞中,HMGB1可通过RAGE/NF-κB信号通路诱导M1巨噬细胞的极化。所以,深入研究RAGE在巨噬细胞极化中的作用可能对IPF的治疗带来一定帮助。
4. RAGE与其相关配体
RAGE被认为是一种模式识别受体(PRR),在单体状态下,RAGE对几种配体只有弱亲和力,而多聚化是配体结合所必需的。RAGE对配体的识别主要是通过细胞膜上的3种结构域实现,其结合的配体又与其他受体结合, 构成复杂的RAGE配体轴。IPF患者中,RAGE的主要相关配体,包括SI00蛋白、AGEs和HGMB1等升高。RAGE与配体结合被激活后,促进各种细胞过程,包括炎症、迁移和增殖,导致多种疾病,如糖尿病、肿瘤和器官纤维化等。
在IPF中,S100A9激活肺成纤维细胞增殖,并通过RAGE信号激活NF-κB通路,诱导α平滑肌肌动蛋白(Acta2)、胶原1A1 (Col1a1)、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和RAGE的表达并诱导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参与纤维化[6]。
有文献报道,当HMGB1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时,通过与几种跨膜受体(如RAGE和Toll样受体)相互作用,激活多种细胞内信号通路,包括MAPK、ERK1/2、NF-κB和PI3K通路及其下游靶标AKT[21]。MAPK信号传导对成纤维细胞分化和成纤维细胞活化至关重要,导致基质产生和积累增加,而肌成纤维细胞持续活化为IPF重要“核心效应细胞”。IPF的发生及恶化与肺部持续炎症有关[22]。PI3K/AKT通路介导下游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例如TNF-α和白细胞介素,最终诱导炎症和组织损伤[23]。NF-κB途径在HMGB1-RAGE相互作用时也可被激活,释放多种炎症因子如TNF-α、IL-6和IL-1β等炎症因子过表达[24],导致肌成纤维细胞聚集合成成纤维细胞灶,最终形成肺纤维化。有文献报道,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IPF有关[25]。血管紧张素Ⅱ 1型受体(AT1R)能与 RAGE形成异构复合物,Ang Ⅱ诱导的AT1R 激活反式激活RAGE细胞质尾部的跨式激活和NF-κB驱动的促炎基因表达。当RAGE被删除或其胞质尾部的转导被抑制时,由AT1受体激活诱导的不良促炎信号传导事件被减弱[26]。
HMGB1与RAGE结合后,RAGE的细胞质尾部可通过募集Dia-1,来活化小GTP酶Rac1/Cdc42, 从而增加细胞的迁移、调节细胞骨架的重塑、细胞运动、神经轴突生长和肿瘤生长等,最终发生IPF。在AGE-RAGE相互作用期间也可激活小GTP酶Cdc42/Rac[1]。同时,当细胞处于炎症状态时,AGEs与RAGE相互作用,持续激活许多与炎症机制(粘附分子的表达,细胞因子的产生)相关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包括MAPK、p38-MAPK和p-p38MAP[27]。AGEs/RAGE轴激活也可促进TGF-β1的表达。有研究证实,RAGE通过阻断TGF-β诱导的Smad2、ERK和JNK信号激活,抑制EMT进程[1, 7]。
综上,RAGE与配体结合被激活后,通过众多途径参与肺纤维化。可知,靶向配体/RAGE轴可能对IPF的治疗和预防有积极作用。
四、治疗
1. RAGE抑制剂
(1)RAGE抑制剂阻断RAGE信号转导或与配体结合
RAGE抑制剂可阻断相关配体与RAGE结构域的结合,从而抑制RAGE下游信号转导。通常用于抑制RAGE在动物实验中的作用。现已发现的RAGE抑制剂有很多,如FPS-ZM1、生物碱和曲尼司特等。
FPS-ZM1是一种高效RAGE抑制剂,已在动物模型中各种炎症的治疗中进行了测试。Nam等人[28]用FPS-ZM1处理小鼠晶状体上皮细胞,证实其显著抑制了TGF-β2诱导的α-SMA表达,Smad2磷酸化比对照明显降低,抑制了纤维化的发展。另有研究表明,用FPS-ZM1治疗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可抑制NF-κB的活化并降低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降低肾脏AngII水平,可减轻肾脏的氧化应激,进而减少肾小管间质纤维化[29]。说明FPS-ZMI可能对IPF的治疗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该化合物仍需进一步的体内研究,证明其在实际临床研究中的适用性,从而证明其是否可用于IPF的治疗。
生物碱是RC的主要药理成分,包括小檗碱(BBR)和罂粟碱等。Xiao等人[30]利用db/db小鼠证实,BBR下调了肾组织中AGEs-RAGE-TGF-β/Smad2和PI3K-Akt通路中相关蛋白的表达,缓解了db/db小鼠的结构异常和肾纤维化。有报道发现,BBR通过减少ACES的产生来抑制RAGE的表达,还抑制TGF-β/Smad3诱导的肾纤维化和NF-κB介导的肾脏炎症[31]。表明生物碱可作为先导分子,用于开发新型有效的RAGE拮抗剂,可以是IPF有前途的候选药物。
曲尼司特是一种常用的抗过敏药物,具有抗纤维化作用[32]。可通过阻断S100A11与RAGEV结构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细胞增殖[33]。
现已发现,他汀类药物、替米沙坦被用于抑制RAGE。二甲双胍也能抑制AGE诱导的MCF-7细胞RAGE和VEGF mRNA水平的上调[34]。这可能对于IPF合并高血脂、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是一重大进展。
(2)可在细胞内结合的RAGE小分子抑制剂
RAGE的细胞内结构域对各种类型的RAGE信号和下游效应起着关键作用。Manigrasso等人[35]在一组58000个分子中鉴定出13个最佳的小分子(化合物11-23),这些小分子可以与RAGE的细胞质结构域结合,抑制RAGE和DIAPH1的结合。在AGEs-BSA刺激的Ager小鼠巨噬细胞模型中,用ctRAGE/Diaph1抑制剂(化合物11,inhRAGE)处理显著但部分抑制AGEs-BSA-RAGE介导的NF-κB活化[36]。可知,阻断RAGE和DIAPH1之间的相互作用对IPF的治疗有积极作用。
综上可知,RAGE抑制剂可能是IPF治疗的新型策略,目前该类药物在IPF治疗中的研究甚少,还需对其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进而为IPF的治疗提供更广阔的前景。
2. sRAGE
sRAGE是一种强大的保护分子,在IPF患者中,sRAGE的循环水平降低,且sRAGE水平较低与AE-IPF发病较早且预后不良有关[10]。sRAGE的保护作用已在临床前模型中得到证实,sRAGE给药可减少由RAGE刺激引发的不同有害损伤。体内直接施用sRAGE已被证明可以逆转RAGE介导的病理状况[37]。表明sRAGE在IPF的治疗中具有积极作用,其可能为未来IPF的治疗新前景。他汀类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罗格列酮和维生素D被用于增加sRAGE水平,这可能作为RAGE介导途径的调节剂。
3. siRNA
siRNA具有转染效果、效力和特异性高及免疫反应低等特点,是最适合RNAi疗法的药物。Gross 等人[38]在实验中发现可用siRNA转染HCE细胞来对抗RAGE。表明siRNA在RAGE介导的疾病中具有治疗潜力。可能是IPF未来治疗的新领域。
五、小结与展望
抗纤维化药物的使用对IPF的生存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下降,故需早期发现新的治疗方法。RAGE通过多种机制参与IPF的发生及发展,进一步探究RAGE的作用,将会对IPF的临床治疗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且鉴于这一靶点在多种疾病中的重要性,RAGE药物化学的未来发展可能为新一代新型疗法的发展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