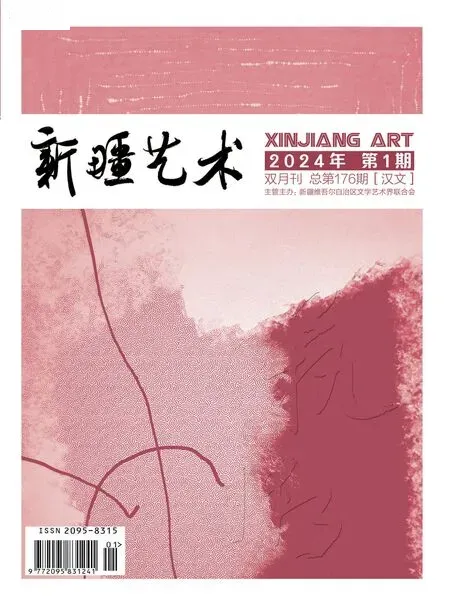论刘亮程小说《本巴》中的主体重塑
□ 杨钦增

作家刘亮程
《本巴》是刘亮程基于史诗《江格尔》再创造的一部当代文学作品,在文化的真实与瑰丽的想象之间,勾勒出一个沟通传统与现代、弥合主体与客体、传递文化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艺术世界。目前学界对《本巴》的研究侧重于作品的文本解读和叙事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季进通过对小说梦境的分析,揭示作品寻找人类失落的故乡的文学主题,阐释了刘亮程作为一名“全球在地化”作家,“世界性的叙事方式”的文学创作[1]。学者刘大先从《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的角度,关注到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讨论小说史诗思维在世俗时代的现实意义,彰显了作品的当代性[2]。学者李敬泽认为《本巴》是一个景观式的存在,包含着当代作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遗产的认同和珍视,包含着我们这代各民族作家要承担起来的共同责任”[3]。可以发现,《本巴》是一部兼具当代性和世界性的小说。一方面,作品具有珍视文化传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小说也在叙事方式和价值指向上有一定的世界性意义。但是,小说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理解作品的时代特征与其传达的世界性意义之间的关系?能否在这些问题之间找到一个具体的、鲜活的呈现载体?
人是文化的真正载体,人物是小说中一定程度承载作家精神风貌、文化信仰和价值指向的文学形象。笔者以《本巴》中人物身心的发展路径为中心,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处于现代生存困境的存在主体的重塑作用。《本巴》中赫兰、洪古尔、哈日王、阿盖等人物身上,一面有着死亡恐惧、自我迷失、意义虚无等现代性焦虑,一面有着赤诚、仁义、担当、和谐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沉淀在中华儿女精神深处的文化传统从史诗维度原初的“本巴”的展示,到象征现代各族儿女,甚至全人类的“本巴”的抵达中发挥了作用,潜藏在中华儿女血脉与精神中的文化因子在其现代性的生存困境中被激发、被唤醒,支撑起现代主体的现实生存与精神皈依。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影响的“关系性”的现代主体,即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生态整体也指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个更大的整体,现代主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
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视域下的主体重塑的研究,是对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主体的心路历程的一次剖析及照见,对塑造现代人具有文化意识和整体性的现代人格,增强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作用。
一、现代性与主体性:文明发展中的主体离散
西方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解放,强调主体的优先地位和自由、平等的权利,促进了现代人的觉醒。现代主体逐渐走向独立、自由、理性,追求形而下的物欲满足,其间伴随着人与自然、社会、心灵、文明的矛盾冲突,导致了现代文明发展中主体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疏离。现代主体深陷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断裂、自我认同的危机、形而上世界塌陷的泥沼。刘亮程始终密切关注文明发展对现代人身心的冲击,于创作中一边体现现代主体与他者的疏离和自我意义世界的陷落,一边守候着内心的文化家园,探寻现代人的精神出路。
刘亮程注重对人物自身主体与客体疏离的心理体验的描写,隐喻了现代主体个体化、碎片化的生存现状和其现代生存中产生的孤独感、虚无感的心理真实。刘亮程第一部小说《虚土》便以直观、错乱的写作方式,将现代主体与自我、自我与他人的疏离描写出来。《虚土》中写“我”一出生便认为自己与现实无关,询问母亲“是否有一个人已经过完我的一生?恋爱、婚姻、生老病死,全是他的”[4],现实中的婚姻、恋爱、生老病死都跟“我”没关系。“我”感知到的“现在”是被悬置的、不被信任的现在,代表历史的过去和尚未进行的未来同样处于缺席状态。可以发现,现代时间的断裂,现代性中矢量的时间观冲击了传统循环的时间观,进而造成人对现代与传统、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等关系,产生割裂、混乱的心理感知。“割裂”一方面指现代人生存经验的断裂,“我”一出生就感觉一生已被别人过掉,主体没有可以参照的过去生存经验的积累,也丧失了可将生命延展至将来的力量;另一方面指社会生产与分工使人成为社会中一个“断片”,人与人心灵的隔阂加剧。“我”与那个从未看得清的父亲、桃树下长大的妹妹的相遇,彼此并没有实质性的交流和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不过与陌生人的相遇一般。“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5],二者的相遇并不产生情绪、情感的联系,也不会产生诱发共同记忆产生、共鸣、留存的影响因素。
在《凿空》中,作家表现了处于传统生存的主体与现代文明的疏离。阿不旦村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人与万物共生的村庄。当村民得知“西气东输”工程要途经阿不旦村时,村民欣喜地去翻新、打造手里的坎土曼,准备大干一场,祖祖辈辈就是靠坎土曼吃饭的。然而,这一工程却在挖掘机等现代机械的挖掘下,在村民的不知情中悄然开动了。随着工程而来的地面硬化、轰鸣的卡车等也扰乱了村庄原来的生态环境和村民的生活方式,三轮车代替了驴车,现代工具取代了坎土曼。“凿空”不仅是石油开采凿空脚下的大地,也是现代文明对乡土传统的“凿空”,意味着作为人们精神情感寄托的乡土世界的塌陷。仍处于习惯性的、乡土的传统生存的主体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主体的情感与精神却隔离在现代文明之外,一定程度上造成主体与现代生存脱节,成为精神世界在现代文明中的漂泊者。
现代主体的离散还指向人们意义世界的陷落,体现在主体对生命的情感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刘亮程小说《本巴》中的人物形象多处于对生与死有着无限恐惧的生存情态中,草原上的儿童有不愿出生、成长的恐惧,成年人有不愿变老、死亡的恐惧。主体生命在普遍的存在恐惧中停滞、涣散。儿童洪古尔在拉玛国与本巴国的战争中被莽古斯掳走,用铁链锁在车轮上,从此便不愿意长大。不愿长大的原因不是长大意味着被杀掉,草原上不杀没有车轮高的孩子,而是他真正害怕的“没长出来的恐惧”,“他似乎看见自己青年、中年和老年,模糊地静候在虚空里”[6]。赫兰是草原上不愿出生的儿童,因救哥哥洪古尔来到世间,他不吃奶水和粮食,不愿被现实沾染,决心在救出哥哥后再回到母腹。显然,赫兰身上有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子,在现实中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处。但在他为救哥哥把拉玛国的人都带入捉迷藏的游戏中时,自己也身陷其中,在人们隐蔽地找和自身无处可藏之间,陷入无家可归的孤独处境。此外,本巴国的成年人有着不愿变老的生存恐惧,他们只愿意停留在最富力量和激情的二十五岁的幻梦中,在一场接一场的筵席和美酒中过掉一生的时间。但是,当本巴国与拉玛国发生战争时,面对拉玛国有无限力量的未出生的孩子,本巴国的成人选择让儿童洪古尔和未出生的赫兰出战,成人们迷醉在筵席与礼赞中。这是小说中最为吊诡的一幕,儿童成为战争的主力,成人退居其后。这显然是不符合常态和常理的。但从小说的叙事逻辑出发,这样的设计又是合理而巧妙的。合理的地方是,小说架构了陌生的、未知的、虚无的、强大的叙事逻辑,一定意义上未出生的孩子比成年人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本巴草原上可看到过去未来九十九年凶吉的谋士策吉,当他面对所能看到的限度之外的场景时,也总是浑身一怵,模糊与陌生的恐惧感席卷全身。巧妙的地方是,小说借现代人对未知生存的恐惧映射了现代生存的多变性、不确定性、虚无性。主体意义世界的陷落,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人的社会身份和价值属性,战争也略为戏谑地演变为孩子之间的一场“闹剧”。

冬日里的木垒书院
因而,《本巴》中反映了意义世界陷落及现代主体精神性的“死亡”,主体随着成长而变老的死亡恐惧只是其恐惧的浅层表现,深层次的是现实世界的虚无性、不确定性,其导致了现代人意义世界的幻灭。本巴人滞留在二十五岁的一触即溃的幻梦中,岌岌可危,生命在此刻的无意义中按下了暂停键。主体“心中的恐惧,其根源大部分在外在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具有真正的威胁性”[7]。现代社会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社会,“一百年前‘成为现代’意指追求‘最终的完美状态’——现在却是指永无休止的改进,既没有‘终极状态’也别无所求”[8]。急切地、强制地、无止境地现代化致使了现代人生存的无知和无力,产生了精神信仰的虚无、身份认同的危机等。
可以发现,现代社会发展中主体的离散,与人所处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生存困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不管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疏离,还是主体自我意义世界的陷落,都涉及自我主体性的丧失,每个“关系”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主体性的“我是谁”的价值诉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现代主体的身份重构自然要回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过程中对这一矛盾的化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来。
二、情感感召与人性自觉:传统文化转化下的自我重塑
《本巴》中的人物还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9],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早已内化于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中,塑造了中华儿女精神意志和主体人格。刘亮程传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在对传统史诗的现代小说改造中,将文化植入人物品格,既对现代性的虚无与迷失给予疏解,又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容,使其产生新的思想内容、新的价值传达和新的可能性。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中国传统文化自产生起就体现着一种整体性思维,将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视为一个整体。现代主体的重塑包含了真诚、纯良的主体人格,仁义、担当的社会人格,自然、和谐的生态人格三个方面的和谐与完善。
首先,在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中,小说《本巴》重塑了现代主体真诚、纯良的主体人格,即自我保持一颗童心,坚守纯真的心灵,培养崇高的德行,避免在物欲横流和无端消耗的现代社会中沉沦。赫兰在小说《本巴》中是一个不愿被世俗沾染、性情纯良的儿童,他有着露珠般的心灵,可以附在一朵蒲公英种子上飞到想要去的地方。他用“搬家家”游戏的方式,把自由、轻松的生命体验带给本巴草原上的每一个人。最后从史诗说唱人的口中得知所有人的故事,他从那段亦真亦幻的故事中走出,顺着清风、夕阳、人们的念想回到“本巴”。因此,赫兰经历了“出走本巴—在游戏中迷失—在讲述中达到现代—回到本巴”的探寻历程,返回“本巴”有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意味。但这一过程中不变的是赫兰“回到本巴”的初心。在史诗世代的讲述中,赫兰的故事历时性地在一代代说唱人的讲述中“复活”。史诗中草原人民原初的精神品质和现代人内心深处建立起共时性的联系,真诚、纯良的主体人格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共振中愈加丰富而醇厚。
赫兰、洪古尔、哈日王等人的儿童视角,在小说《本巴》中被大量使用,这是刘亮程为透视社会现实或增强叙事自由度而选取的“合适视角”,包含了作家对现代社会及主体一定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儿童的世界由现实和幻想构筑,有着自由、轻灵、多变等特点,更加贴合“流动的现代性”求新求变的社会特点。通过儿童的眼光透视现代人的生存现状,有利于打破现代人固有的思维认知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儿童视角是以感性的生命体验为主,较多新鲜而奇特的感性体验是对现代人生冷的理性体验的丰富。如地上的羊粪蛋是羊,马粪蛋是马,草叶是搭起又拆散的家,“搬家家”游戏就是建立在人们对事物感性的感知上。拉玛国的人从原本草原转场的沉重中脱身,进入游戏世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渐渐变成天真的孩子。“游戏性的史诗世界之轻,使人从真实世界的沉重里暂时脱离出来,拥有更超越的目光,提示着人类有限视角之上的另一种可能。”[10]从沉重、不变的传统生活到轻松、自由的现代生活的转变,是现代对传统的超越,但这一超越仍建立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真诚、纯良的主体人格上。以感性体验为主的真诚的主体人格在促进现代人生活观念的转变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其自身的内容也得以更新与发展。真诚纯良的主体人格是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关系等一切关系的“中心点”,既是在处理主体与自我关系中保持“真我”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初心、坚定方向的精神品质。李贽的《童心说》中提到,“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11]。童心是人心灵的本源,心灵之真是体现人完整人格的重要对象。

刘亮程的乡村生活
其次,在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中,小说《本巴》重塑了现代主体仁义、担当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指受同一文化体系影响的同一种群体中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和价值倾向。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儿女仁义、担当、悲悯、责任等的社会人格,在《本巴》中主要表现在主体对他人的仁爱之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上。一方面,《本巴》人物身上体现着仁爱之心,主体对他人有着较强的悲悯意识。小说中不仅描写了血缘关系中自我与他人的仁爱关系,如赫兰与洪古尔之间的兄弟情谊,两兄弟与母亲的母子之情等,还书写了自我对其他社会个体普遍的仁爱。面对从草原沉重转场生活中脱离,如孩子般玩搬家家、捉迷藏游戏的牧民,赫兰感叹道,他们在那不变的生活中活得太久了,传达了他对牧民长久不变的、枯燥单一的游牧生活的深度同情。书中的阿盖夫人在考虑,大人全都变成了孩子,谁来养活的生存问题。哈日王的母亲看着遍地的孩子,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这些曾经是她的士兵、牧人和随从的男男女女,如今都变成孩子,她疼爱地摸着这些孩子的头。可以发现,主体对他人既有一种内心深处的悲悯意识,还有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血缘之爱,士兵、牧人、随从等都视为母子关系中的孩子。学者李泽厚将传统儒家思想模式“仁”的内在结构划分为: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格个体[12]。宗族血缘是“仁”思想的现实社会基础。孟子有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13]。由“仁”到“义”,“仁爱”的对象也由血缘关系的人延伸到无血缘关系的四海之内的人,达到“泛爱众”的仁爱境界,这一种爱超越了人物的身份、阶层,达到生命与生命之间情感心理的深度共鸣。
另一方面,《本巴》人物身上有一种责任意识。赫兰、洪古尔两位少年英雄在本巴草原遭遇灾难之际挺身而出,拯救草原人民,小小的年纪反而承担起了民族的重任。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着对古代知识分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责任体系,以个体的道德素养为基础,通过家庭的和睦、国家的治理,实现家国同构、社会和谐的目标。小说人物身上的责任意识正是根植于中国儒家传统这一责任体系。小说中传唱人“齐”承担起对史诗故事世代传承延续的历史责任。“齐”是世代负责向人们说唱史诗故事,延续文化传统的说唱人名字,只要有讲述的人和听众,史诗故事就一直存在。刘亮程基于史诗《江格尔》而创作了《本巴》,本质上也是承担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其注入现代活力的历史责任,正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不断的传承与创新,才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仁义、担当的社会人格是现代主体人性自觉和社会价值的体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14]组织社会的制度和伦理的“分”和自身的道德修养的“仁义”,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亦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5],从宗族血缘为纽带的“亲亲”之情到自我与他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6]的普遍情感,是人性的第二次觉醒,代表了普遍的“民吾同胞”人性本体的生成。既持守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人性关怀,又有着社会性的责任意识,是现代主体理想的社会人格的体现,对人格内在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小说《本巴》重塑了现代主体自然、和谐的生态人格。“本巴”草原上的人们逐水草而居,随着季节的变换转场放牧,将肥美的牛羊、甘甜的美酒等看作上天的恩赐,有鲜明的游牧文化色彩。一方面,小说《本巴》中用诗性语言还原出生动、盎然的草原生态,传达了游牧文化中人对自然的敬畏。“雪消到哪儿,羊的嘴跟到哪儿。大雪埋藏了一冬的干草,是留给羊在泥泞春天的路上吃的。羊啃几口草,喝一口汪在牛蹄窝的雪水。牛蹄窝是羊喝水的碗,把最早消融的雪水接住,把最后消融的雪水留住。羊蹄窝又是更多小动物的水碗。当羊群走远,汪过水的牛蹄窝羊蹄窝里,长出一窝一窝的嫩草,等待秋天转场的牛羊回来。”[17]好的语言读起来会像呼吸一样自然、舒畅,这百十余字,将草原上大雪、牛羊、嫩草、雨水等诸多事物间的生态关系以及自然时间的变换,不动声色地描绘出来,绘声绘色、生机盎然,给予读者自然而灵动的生态审美感受。作家还描写了本巴人民对草原的敬畏之情。班布来宫的筵席上,每位勇士如数家珍般轮番为草原上的酥油草、牛羊、虫子、蒲公英等敬酒,献给万物以祝福。草原脆弱而恶劣的生态环境,使牧民与草原及草原上熟悉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另一方面,作家以现代生态思想为指导对传统的游牧生活做出现代改造,给人们提供更加自然、绿色、轻松、环保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体验。传统草原重复、沉重的转场生活,让牧民愈加乏味与疲惫。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加快了人们开发资源、开垦土地的步伐,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作家于传统草原生存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处,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游戏是消融人与自然对立关系,深化主体对自然生态体验的媒介。赫兰用“搬家家”游戏代替牧民沉重的转场生活,使其变成孩子沉浸在游戏的愉快体验中。游戏的最大特征是自由,它无关功利和日常需要,它是一种“假装”,但又需要人们全身心的投入。因此,《本巴》的游戏中,人们和万物都以自由的姿态投身游戏中,二者同为“主体”,消融了西方近代以来提出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当转场停止,少数牛羊在牧道上带人游玩起的“牧游”游戏,更具现实感地、直接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白天,游客跟着羊走走羊道;夜晚,人跟羊一起在山谷中过夜。夜间的温度使人与羊紧紧贴在一起。游客还把自己金玉宝石收起来,佩戴上黑亮的羊粪蛋项链,金黄的骆驼粪蛋挂坠。走入自然,体验自然,融入自然,对于生存已经模式化、形式化了的现代人而言是一次感觉的更新,一次生命的涅槃。
总之,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之基。潜隐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在现代文明的精神困境中被唤醒,成为指引现代主体价值判断、促进身份认同、重塑自我的重要养料。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塑了现代主体的整体人格,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为“同心圆”的整体结构。这一主体契合了后现代文化中对“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性的、生态性的理解”[18]的看法,人的本质是关系性的存在。
三、主体存在与精神展望:关系整体中的意义生成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塑了现代主体的整体人格,在文化的精神世界中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主体的离散,并给予自我一个丰富、广博的意义指涉。“真正重要的是,设想的身份建设和重建的必要性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它如何被内心认识、理解和感受,它如何被经历和度过。”[19]学者刘大先从《本巴》篇章结构论述了小说内部呈现的史诗的原初本真性层面、本真性瓦解和存在链断裂层面,以及经验融合后返璞归真层面[20]。“本巴”是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人们原初的、文化的精神家园,那里有人们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显然,重返“本巴”既有中国传统道家复归于朴的“道”的境界,也有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意味。但是从这一角度上看文化作用于主体的方式,并不清晰,所以可以将视角聚焦于内容的承载主体——人物上。小说主要人物赫兰身上呈现了“出走本巴—在游戏中迷失—在讲述中达到现代—回到本巴”的探寻历程。再结合小说的叙事时间,可以发现,“出走本巴”发生在传统的史诗时间中,“讲述”发生在现代时间,“迷失”承担起史诗时间和现代时间的过渡。“回到本巴”则发生在史诗经验和现代经验的弥合处,无法给它一个时间上的定义,却可以将其看作主体抵达的一种存在境界,主体有了一种由传统到现代,时间情感化的生命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时间情感化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被积淀、被感知、被理解的。

刘亮程的乡村生活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以时间情感化的方式内化于主体的情感深处,成为明确自我身份、建立情感沟通的本体力量。刘亮程曾说,“在写作过程中,你一定会慢慢明白,你的气息跟前人的气息连接在一起了,你能接着他的思考去思考,你能接着他的想象去想象。你在传承一颗古老心灵的温度。这就是传统。”[21]这便是文化在时间的情感之流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被想象、感知的生动呈现。小说中洪古尔独自走向老年,坦然地在远离人群的草滩上搭起一顶小毡房,他给老马修理蹄子、梳理毛发,拿拾来的牛羊毛给自己织毛衣,他对死亡的恐惧在变老的那一刻就消失掉了。巧妙的是,他从未做过这些活,一上手却熟练无比,仿佛他父亲、母亲的手艺,转眼间传到他手上,他在这些手艺间看见父母的身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存。同样,当草原上的女性在阿盖夫人对老年的渴望声中一起变老时,她们从自己衰老的脸上,认出早已不在的母亲的脸,在自己的唠叨里又听见母亲早年的叮嘱,皱纹在她们欢乐的微笑中生长。可以发现,人物对于熟悉的亲人的情感在时间中沉淀下来,温存的情感体验使其克服了死亡的恐惧,快乐地面对衰老。“只有期待(未来)、状态(现在)、记忆(过去)集于一身的情感的时间,才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22],主体的生命在一次次的情感回味中变得鲜活、丰富、深刻。从史诗《江格尔》中的“本巴”到这部小说中再度重构的“本巴”,在传统到现代的时间中沉淀下来的,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对“本巴”情感的累积。在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带有文化内涵的情感积累是延续在中华儿女潜意识中的精神品质和情感标识,在多义、混乱、迷茫的现代处境中,给人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连续的意义框架。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意识,在塑造现代主体的整体性人格中起着凝聚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尚书·尧典》中写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3]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崇高的德行,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后再推己及人,促进各个家族团结、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后再促进各个邦国的和谐关系。“协和万邦”引申到今天,即世界各个国家平等互信、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意思。小说中草原人民向往的“本巴”,“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24],隐喻了一个由共同的生活追求或文化理想维系的,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构成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首先指向中华各民族构成的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民族是我国的一个特色,历史的演进中,各民族在广阔的中华版图上交错分布,相亲相依,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族儿女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刘亮程也关注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问题,“两千多年来,中华农耕文化一直在跟西域边疆的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相互碰撞……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个主体文化。”[25]因此,“本巴”即一个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儿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引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凝聚精神力量,这正是现代主体需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发挥的价值与作用。
一个由共同的生活追求或文化理想而维系的,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构成的“共同体”,同样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特征和价值设定。学者季进认为,刘亮程对世界的关注中包含着对“传统性与先锋性、史诗性与抒情性、社会性与生态性、全球性与本土性”反复辩证的思考,用一种“世界性的叙事方式”向世界传达中国故事、新疆故事。显然,刘亮程不仅仅在叙事方式上有世界性的体现,在创作内容上也已经触及世界变革中“先锋与传统,社会与生态,本土与世界”等重大内容。“本巴”隐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它传达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生态美好,人民幸福的理想图景,符合世界人民的生活需要和情感诉求,是一个世界人民认同的理想境界。

刘亮程庭院中的猫
结语
从小说《虚土》到《本巴》,刘亮程曾坦言,“《虚土》中属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荒野,在《本巴》中无边无际地敞开了。”[26]可以看出,《虚土》中的时间是“一个人”的,个体性的时间,主体呈现出自我与他者疏离,以及虚无、孤独的生存样态,自我被悬置在现代生存之外。《本巴》中的“敞开”建立在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上。作家在存在主体的现代生存困境中,一方面重新唤醒、审视、创造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在中华传统文化时间之流的情感积淀中重塑现代主体的整体人格。现代主体在传统与现代连续的文化情感结构中获得了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现代主体首先是有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主体,这是人的身份标识和情感归属,其次是有责任意识的“共同体”中的主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一定贡献,为向世界展现可信、可靠、诚信、担当的中国形象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