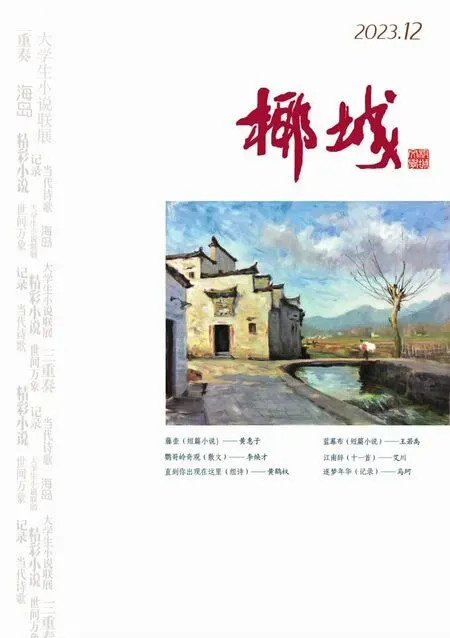蓝幕布(短篇小说)
◎王若禹
一
程季时唱了十几年戏,但是,他最熟悉的是戏台子,不是戏。
戏台子修过好几回了。木做的戏台子,也粗糙也结实。每过得几年,四周的围栏就破败了,“欻欻”地掉皮子。团长会喊他们给刷层漆,程季时就老帮着干这样的活。新的漆,旧的漆,他弄不均匀,弄得像木栏杆上的补丁。
戏台子是团里的戏台子,程季时打小就住团里,团里是他家,戏台子是家里最好看的那间屋。程季时觉得,不演出的时候,家里破破烂烂的。每回演出,家就新了,台上拉起帘幕,道具上的布也是极鲜艳的。这些是消耗品,常换。演出时的台子像过年一样亮堂,程季时的心情也跟着亮堂。隔天的演出把他弄得一会儿喜一会儿悲的,像刚换上新衣裳,马上又脱掉似的。这样的情绪时常出现在他的少年时期,如今就少了。程季时天天做着拉幕布的活,他们团台上的幕布,还没换成自动的。
这活也无聊也磨人,日复一日的总也停不下。从师父手上接过这件事的那天起,这活就归了程季时。有时候,他前边跑着龙套,后边还管着整场戏的幕布,开开合合,换个场的工夫都休息不成。他的一整天,就这么被占满了。程季时过得很充实。
“老乔东,来帮我吊一段琴呗。”程季时对着远处那个人喊道。今天台上没戏,老琴师也就相对清闲。乔东六十多岁了,团里干了大半辈子,谁都不敢请他退休,他也不肯走。所有的年轻琴师都由他带着。
“怎么,今天突然来求我,”老乔东坐椅子上抬了头,“十几年没主动请我给你吊胡琴了。你晨功出了吗?”
“出了,现在都要晚上了。你怎么比我师父还会磨叽我!”
“我管你十几年了,孩子啊,”老乔东的声音既爽朗又透出水到渠成的自然,“再说,你师父离开团里之后,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师父已经回来了。”程季时说。
“什么,他还回来唱戏?几时来,几时走?”
“我师父他病了。”
“严重不?他住哪儿?”
“住他家里呀,”程季时笑嘻嘻地说,“我师父这次回来,可走不了了。”
“莫瞎说啊,莫瞎说,你也是个没心肺的。”
“所以,我求你帮我练练,多少年没正经唱过了,我怕师父一会儿又考我。”
“好吧。”老乔东说着,就开始调琴。调琴的声没有调子,但是很润。“你要唱哪段,要不先吊下嗓子,你今天唱过了吗?”他问。
“我不知道。”
“那么,先试试二黄的调子?也别太高了。一轮明月照窗前还会不?”
“会啊,怎么不会?”
“《洪羊洞》里为国家那一段呢?”
“当然会,会十几年了。”
“好罢,你要先唱哪段?”
“先唱,短一点的。”
于是他开始唱:“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程季时一人立着唱,就是规矩地立着,他的手上没有动作,头也不跟着晃动,只有眉毛在兴奋地挑。
“情绪还是不对,”老乔东说,“操心劳碌的角色哪有像你这样的?你唱戏吧,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多少年都没全改过来。”
“我扮上,情绪就对了。”
“哪儿行?你啥时候都得对。”
“那,下次不了。”
“但你的嗓子还是亮,练练要更好听。”老乔东夸他又说他,“你就是唱得少。”
“我每天干活呢,干那么多的活,再加唱,可不得累死。而且,我师父和师哥,他们嗓子才好。”程季时说。
“对了,你师哥呢,没跟你师父一块回来?”
“师哥有戏唱,他为什么回来?”程季时说,“三年了,师哥好容易熬出头,他终于肯把师父还给我了。我可不要他回来。”
老乔东摇摇头,他眼看着程季时一路跑着走了。程季时跑得很快,总是跑到双脚悬空,跑得喜气洋洋的,就差往前,再翻一串跟头。
二
“季时啊,”王梦得喊他,“把李玉给我叫来,帮师父忙。”
“做什么?”
“拉幕布。”
“为啥不叫我,为啥要我去叫师哥?”
“你还小呢。”王梦得说。
“师哥只比我大,嗯,不到两岁!”程季时抗议。
“是,你师哥要多磨一磨性子,你呢,要多磨一磨戏。”
“什么意思,师父?”
“你不懂的。”王梦得说。那时候,程季时十二,李玉十四,他们俩在团里好几年了。程季时的个子,也就是在那几年疯长,长得快要和师哥齐平。听师父这么说,他就一溜烟跑了,嘴里喊着师哥师哥,喊得清清亮亮的。
“老乔啊你看看,”王梦得望着那孩子的背影道,“我这两个徒弟,将来会怎样?会出名不?”
“天分么,那都是挺好,毕竟是你选出来的孩子。出名可不敢说。”乔东比王梦得还大上几岁,团里一众演员有个什么事,都爱问他做个参谋。
“天分,天分?你看我怎样,”王梦得苦笑,“师父还没唱出来,却指望着徒弟先唱出来,这也是很好笑的。”
“你看看你现在,还不是过挺好?”乔东也冲他呵呵笑,“带着徒弟,生活无忧,人要知足。话说回来,你也不想趁现在多带几个孩子,带几个不是带?更何况团里缺人,你知道的。”
“这俩孩子,嗓子好。”王梦得眼望着前方,仿佛还能捕捉到刚才那个孩子的影子。
“怎么,条件不够的你就不带了?那一辈子台上翻跟头的孩子,也都是唱戏出来的。”
“嗓子不好,就别学戏。”王梦得的语调变得不是很顺畅。乔东后面拍了他一肩膀,他猛一回头,又松口气笑了:“我要是带十个……老乔啊,我不要那几个钱。十个孩子,肯定有九个不聪明的,带不出来,我这心情上根本过不去。我没那么多工夫,又不可能不对他们负责。说实话,对于自己的戏,我还是免不了有的时候,痴心妄想。”
“妄想那是可以有的,没人能够阻你。”已经五十岁的乔东说。
程季时到底把李玉给拽来了,两个孩子肩并肩站着。
“你刚才在干啥?”王梦得走到李玉跟前。
“练功。”
“练的啥,练嗓子么?”
“师父昨天教的,枪花,一个人打打。”
“也不要太用功了,孩子,欲速则不达,”乔东从后边走过来,到他面前,又指指一旁的程季时,“没事的时候,也跟你师弟学学,玩一玩儿罢。”
“是。”李玉点头。
王梦得往戏台子上面走去,他们也都从后边跟上他。虽说是白天,戏台子上没有戏,便是极黯淡的。这黯淡不似黑夜里的黯淡,而是朴素的黑白照片一般,有亮光的黯淡。幕布,好几层错开的幕布敞开在一侧,幕布是灰蓝色的。
“你们看,”王梦得说,“师父今年四十岁,除了演戏,还是天天守着这个。这是很重要的活,是师父的师父交给我的,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
“师父,幕布为啥都是灰蓝色的?”李玉说。
“为啥都是灰蓝的,我们的幕布?嗯?师父?”程季时说。
“师父也不知道,蓝色朴素,用得多。”
“其它团里也这样吗?”
“也这样。”
“不会,北京的团里的幕布,肯定有很多颜色的。”程季时用手拽住身后幕布的一角。他的手摇晃来摇晃去,幕布由下而上地震颤,像湖面上的波涛。
“是啊,也有黄的,也有红的,蓝色用得多些,”乔东回了他的话,“以后啊,你们如果去北京演戏看到了漂亮的布景,也来个电话说给我听。”
程季时乐了,他停下手中的动作:“好噢,我们跟师父去北京唱戏,什么时候?”
三
“最后面的是大幕,开场时要拉开。”王梦得边走边说,“这里是二道幕,管换场,这幕动得最勤。然后,最前边是天幕,前边也用不着动它。整场戏演完了,演员也谢完幕了,才把它闭上。”
李玉跟着师父,前台后台地走。程季时拽住师哥的衣角跟着他们,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地看,看他们团里的戏台子。戏台子宽敞,又高又空。程季时仰起头,望着灰蓝色的,有几个他那么高的,窗帘子一般的幕布,他想:紫禁城里的围墙是不是也有这么高,让人眼晕的、生畏的高?师父给他们讲过。但紫禁城里的围墙是大红的,他们团里的幕布是灰蓝的。紫禁城里也唱戏,那他们那群人用的幕布是什么颜色呢?他的思绪很飘忽很跳脱,所以手上一直不敢松开师哥的衣服,他怕,只几步路就把师父跟丢了。那,师父真会板着脸说他。
“师父讲得清楚么?你们能听明白么?你们知道,拉幕人,师父平时还在做什么工作了吗?”师父的声音突然又响起来。
“知道了师父。”李玉说。程季时的思绪,也跟着师哥回来。
“那,今天的幕,师父先交给你。”王梦得拍着李玉,“今晚上师父的戏,其实只有两折子,《空城计》连着《斩马谡》,幕布上的事情不会太难,你能不能做?”
“我大概知道了,师父。”李玉说。
“没事,下午还有工夫,我给你仔细说。”
“我会,师父为什么不交给我?”程季时抗议。
“你今晚台上有角色,演诸葛亮身边的琴童,你又忘完啦?”
“师哥他也有角色!”
“到那场,师父会找人替他,”王梦得打断他,“你要多磨一磨戏,师父说过,别着急考虑戏以外的事情。”
“那,以后,两年以后,师父和师哥会交给我吗?”
王梦得笑笑,他把身子转回去,背对着他们:“你要是只图个新鲜劲,就算了,你不会做好的。没有人会喜欢做这件事,你还是不明白。”
“所以,你们打算永远不交给我了?”程季时抓住重点。
“行了,眼看着不早了,你们先去吃中饭吧,吃饭重要。”但是师父说。
“师父你呢?”
“师父和乔师傅待会儿过去。”
于是两个孩子就跑走了,王梦得回身看向他们:程季时猛跑一阵又停住望师哥一阵,李玉先是快步走,被师弟招呼之后改成跳一步走一步,他有些笨拙的忙乱,像跳格子的兔子。
“梦得你看这俩孩子,还是听话的,”乔东背着手踱步,“季时要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正常,才十一二岁的小孩。你看看他今年,终于开始窜个子。”
“他们是听话,听我话。其实,也不小了,心里该有动静了。”
“都是苦出身的孩子啊,梦得。你一定听我话,就别严厉得过分,孩子要像孩子那么长大才好。”
“苦出身的孩子多着呢,更何况,”王梦得笑出声来,“老乔啊你对我这个偏见!你自己问他们去,师父是不是个好师父?”
“那,行了,咱们也走吧!”乔东不想理他,径直就往前走。
“老乔你先等等,”王梦得又说,“少跟年轻孩子抢饭。我这,已经开始担心件事,季时过了年就开始窜个子,我估摸着他将来,还能长得挺高,那练功就有苦头吃了。”
“嗐,你这个人心眼子太多,担心这那的,难为你能长到现在这个高度。唱戏的孩子嘛,最重要的是踏实肯干。有空你多琢磨琢磨季时的性子,将来能不能稳住。”
“性子么,我倒不担心季时,”王梦得叹口气,“他是挺天真的,挺好。我担心李玉,他有一点像我。所以,我这么早,就塞这活给他。”
四
下午,王梦得坐在台边,给李玉还有程季时讲,几张幕布什么时候拉开,什么时候闭上。李玉和程季时也随师父坐在台子边,他们的脚都规矩地点着地面,不似刚来的时候,两条腿晃里晃荡。
“听起来是不难的,”师父说,“做起来也不难,但真个天天做起来,方寸就容易乱了。戏你们是天天听,若是又要演又要兼着拉幕人的角色,得足够熟练才行。”
“我记住了师父。”李玉说。
“要记住啊,师父说第三遍了,师父唱到这句,再有两句念白,这一折子戏才算结束。但你听到这句就要开始准备,到念白就迟了。迟了就容易忘了。”
“我记住了,师父。”
“你们过来看,”王梦得说,“拉幕布的时候,不能够猛地拽住跑,你的人形隔着帘子被观众看得清楚,就不对了。”
“好,我知道,我会慢着跑。”李玉点头。
“知道就好,师父盼着你们,永远不出错,或者少出错。好不好?”师父拍拍程季时的脑袋。
“师父,你刚才说的哪句?”程季时的思绪还没跟上,“你要唱一遍我才知道。你演一遍,我拉幕布。我们真的演一遍行不行?”
王梦得已经演过三遍了,但他没有说不行。
李玉和程季时,来自吴镇的戏校,他们是王梦得亲自选进团里的学生。吴镇不大不小,有城区,也有城郊有乡下。戏校处于城郊相对偏远的位置,隔壁有一所大学,一所职高,连接着一所职大。戏校很空阔,硬件软件留有数十年前的气质,寒天里冻人。它临着吴镇最有文化的地方,又很孤独,因为里头的房子没有亮色,至少从外观是这样。里头的孩子由六岁到十六岁,多数乡下上来的,兄弟姊妹多。有意思的是,孩子们对亲生的兄弟姐妹,反倒没有师兄弟姐妹那么亲近。
刚进团里,李玉十岁,程季时八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命运中细微的变化。师哥仍是师哥,师弟还是师弟。只是,李玉身边一起练功的孩子,由五六个,变作只剩程季时;程季时身边一起练功的孩子,由与他同岁的,变作大两岁的李玉。适应这样的变化于他们,只需要短短两天。团里当然也有其他师父选来的其他孩子,与这两个孩子一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更早地清晰了人生的路。
“师弟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像师父那样,台上唱老生?”
程季时见李玉的第一面,就叫师哥,他是个外向的人。李玉机械地叫了师弟一声,他觉得“师弟”还没有“程季时”这个词出口来得容易。所以,李玉常常等着师弟叫他,练功也好吃饭也好。他完成了一件事,就原地停住,等着师弟也完成,又能意识到他的动静。程季时的性子却用不着师哥等候,就一叠声地叫了,多费些嗓子于他是件开心事,算不得吃亏。但是日子久了,叫“师弟”的机会不由得多起来,李玉也逐渐习惯了“师弟”,“程季时”这个称呼,反倒忽而陌生了。
“我们到师父那个时候,已经变作师父的样子,那么老。当然就能够像师父一样,台子上唱老生。”程季时漫不经心地说。
“那么以后呢,你猜我们会干啥?”
“唱戏呗,唱成师父的样子!”
程季时和李玉两个关系很好,这也是王梦得最欢喜看到的。平时,他也会特意花心思,培养他们两个的关系。比如早上练功,就让他们背对着把腿绑在一处。一旦一个偷懒另一个就会疼。
“梦得啊,上午你还没说,李玉还这么小的年纪,咋就让他碰幕布的事了,不是你干着吗?”乔东问王梦得。
“是我师父,我挺年轻他就让我做了,你知道,我师父在磨我性子。”
乔东呵呵大笑:“磨成啥样了?”
“就现在你看到这个样,毛里毛燥,眼高手低。”王梦得眼珠子上翻。
“那,磨得啥性子嘛,你师父!你骗不了我,你拉帘幕那会儿都二十了,已经不是他们的孩子样儿。”
“你不懂,”王梦得说,“我那是太迟了,纠正不过来。你哪儿懂他们,李玉这孩子,我说过他有点像我。”
“哪儿像?”
“他心高,又没脾气,不吭气。我怕他将来没那么好运气,就跟我现在似的。”
“好运气,那是千分之一的机遇。”
“但是,我怕他受不了。”
五
“师哥,累吗?”
“不累。”
“那,好玩吗?”
“也不好玩。”
“我不信,你换我试试!”
“师父他……”
“师父他又不知道,”程季时说,“这样吧师哥,你不给我,我陪你,这样的话到点还能给你提个醒。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玩意头!”李玉笑了。
往后的十年,只要王梦得台上演戏,幕布就交托在李玉手中。师父演戏没个定数,因为团里的票卖得没个定数。有时候一周演六回,有时候两周演一两回。李玉呆在戏台子的时间多了起来,程季时也是。演员们排练,他们在台底下看着,以便记住更多的东西,而不误换场中,幕布的开与闭。
“师哥,你要是累了,今天就换我。”程季时说。
“好吧。”李玉坐在台侧,下意识地回了声。他们没跟师父说过,就开始实行轮班制了。李玉总觉得师父可能知道,又仿佛完全不知道,他有些心虚。程季时完全不心虚,因为老乔东知道这事。他觉得老乔东既知道,师父就一定知道,且认可,他一个转身就坐到师哥边上去了。
“师弟,你还觉得好玩儿吗,这活?你小时候老跟我抢,我挨到第几年才答应的?”李玉掰着指头数年头。
“你不是不答应,你早就想答应了,你怕师父怪你……你怕师父。”程季时捏住幕布的一个角往上晃荡,上边传来轻飘飘的“刷啦刷啦”,把他的最后一句声遮住。其实现在,台上很黯淡,没别人,师哥不是那个“别人”。
“你别打岔。我是问你,这活好玩儿吗?”
“还可以,我习惯了。”程季时说。
“我也习惯了。”
台子上很黑,往观众席上看也是什么都没有。李玉站起来,把台边的第一道幕拉上。距离晚上的戏,还有五六个钟头。演员们上午排完一遍,下午都在修整,所以没人在这。师父也不在,今晚的戏没有师父。事实上这一周师父都没在团里,走前他说,去省京剧院,顶他师哥几天戏,他师哥摔了。
“他严重吗?啥时候能好?”李玉说。
“我师哥要是摔了,我也顶他的班儿。”程季时说。
走前师父只交待了老乔东,没交待两个徒弟。年轻的,也是成熟的龙套演员,生活上已经十分规律,用不着特殊的交待。师父走了就不成事的徒弟,不是他王梦得的徒弟。
李玉躺倒在台上,程季时把最后一道大幕拉开,然后跟着躺下。最后一道大幕后边是两面墙,一面布景,一面承重。承重墙很高很高的地方开着两扇小窗户,少有人清楚这个,但他们清楚。因为,屋外的一点光顺着窗子进来,照亮了两面墙之间的窄道。背景墙的两侧便也透出光来,台子上就拥有了一点泛黄的光。这光传不到很远,偶尔往幕布上活动,原本的黑会掺入一段又一段紫色的调子。
“台子上嘛,确实比床上还要踏实舒服。”程季时说。
“今晚上的幕布,还是交给我,”李玉对着师弟言道,“你的韧带前两天是不是伤了,我看着今天走路的样子,回去歇着吧。”
“我不歇着。”
“你台上又没角色。”
“那,我后台歇着,结束了再回。”
当天晚上,是李玉这些年来唯一一次出错。他睡着了,因为台上没有角色。因为师父不在,师弟伤了,所以他台上没有角色。
程季时比师哥更早地睡着,他坐在地上,两手扒住一张木头椅子,李玉把他往边上挪挪,他也不醒。李玉看看台上台下的缤纷的,凌乱的颜色,他感到有些累。是师父突然走了一阵,生活突然空了一段的累。李玉感到自十岁起,往后的生活就被定下了。他不知道师弟是否这么想过,能够去更好的地方学习,师弟与他的水平差不多。有时他也羡慕程季时,师弟真是开朗而正直地长大了,本分唱戏,本分干活,与师父的教诲完全一致。他没有师弟活得坦然,所以,他也不能够在后台坦然地睡着。这段日子是奇怪的,李玉的心中有一种奇怪的疲惫与兴奋。
于是他睡着了,直到换场的一刻,使命般地惊醒,那是他现在的工作。他睁眼就知道迟了,师父说过迟了。然后,他看到老乔东从他的面前经过,把二道幕合上。戏的进程,一秒钟都没有被耽搁。
然后,他弹起来,程季时也跟着从地上起身。老乔东什么话都没说,他坐回去,拿起胡琴。幸好那场戏,他只是琴师中的B 角。
六
王梦得突然就火了,那年他四十九岁。火是一场机缘,来自他受了伤的师哥,与在省京剧院演戏的两个星期。命运总是十分有意思的,不知道会在哪一天给个蜜枣,又在哪一天使个绊子。王梦得的二十、三十多岁无风无浪,甚至称得上艰苦。他不信什么大器晚成,却在给师哥帮忙的时候,以B 角的使命被众多的人认识。他得到了一个省京剧院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他没有立刻让吴镇的团里知道。团里只知道,王梦得火了,团里也知道,火了就也该走了。去省城,或者去京城,这个团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将在王梦得的身上发生。
李玉和程季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么些,他们听说师父唱火了,高兴得很。李玉想着,师父真算得见了大世面,那是值得庆贺和羡慕的。而程季时的脑子里,完全是另一桩子事。他知道师父过两天要回来,就开始担心,自己和师哥头先犯下的错会不会被师父知道,知道那可就完了。于是他拽着师哥去找乔东。
“老乔东,你说我师父会不会知道?”
“知道啥?”
“我和师哥犯错了。”
老乔东想了好一阵,才想起来。
“你说我师父会不会知道?”程季时问。
“你说,谁会告诉你师父!”他反问他。
“你!那我和师哥求你,别给我师父说。”
“算个啥嘛你们的事,我保过的人太多了,就你们师父,我都保过。”
“我师父咋了?”程季时立刻对新的事来了兴趣。
“不知道,不说。”老乔东摆摆手要走,但想想又补上一句:“你们都是团里的孩子嘛,犯错是有限的,往后肯定越来越少了。就像,你们师父年轻那会儿吃过次亏,就再没犯过。”
王梦得回来后,乔东确实没提过这事。但就算提了,他也不会罚他们。事实上,他遇到了一件,他从良心上难以抉择的事情。程季时和李玉的命运,可能就这么定了。他可以推荐一个人,入省京剧院青年团。但是只有一个,也许,几年后他唱出更大名堂,就能推荐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几年过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王梦得想起好几十年前,他师哥进省京剧院,那情形与现在不同。因为只有师哥到了年龄,就只有师哥能进去。后来,他师哥确实出了名,王梦得却从没想过请师哥帮一把。他并不是极好面子的人,就是没想过。他是直性子,想的不多,但是今天,他不得不去考虑所有的后果。然后,他清醒过来。就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难的,他只担心另一个人的命运。命运不可怕,命运的落差才可怕。
于是他找到李玉还有程季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话:“师父要带一个人走,过两年再接另一个。你们先商量,好了告诉我。”说完他就走了,没给两个徒弟留下回答的机会。这时候王梦得已经完全清楚,他会带李玉,再怎么考虑都是带李玉啊,他是师哥,他个性要强,也更踏实。可是,程季时怎么办?
“师哥你走呗。”程季时说。
“为什么?”
“师父说了啊,先带你,两年后我再跟去。”
师父没有说,但他们都明白师父话里的意思。事情已经定下了。
李玉没有师弟那么单纯,他隐约地感觉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不只是把他与师弟分开那么简单。他无疑会更好,但这种好会不会带来其它变化。师弟一人留在吴镇的团里,又会怎样?再往深处想,他却也想不清变数。于是他说:“我走了,团里的幕布咋办?”
“你交给我呀!”
“只有师父交给徒弟,却没有师哥交给师弟的。”
“这有什么难的,让师父再交给我一次不就得了,正好,我把你单干的那几年补上。”
“不行。”李玉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难不成我过去?不可能的,师哥,我没你唱得好。”程季时拍着李玉。
当天晚上,程季时坚决地把师哥赶回房里收拾,然后留在后台干起一个人拉幕布的活儿。他让王梦得看到,也让老乔东看到。于是,王梦得也明白了,他了解师父的决定,他没意见。
七
“季时啊你来,”老乔东喊他,“你师父怎样了,给我说说。”
“还好啊,”程季时说,“我师父他挺好。”
“他脾气怎样,最近?”
“也还好。”
王梦得离开扬城的第三个年头上,嗓子出了问题,是多年累出来的。王梦得在省城,呆得并不糟心,也不十分顺心。人就是这样,几乎要实现梦想的时候,就突然累了。逢年过节,每个省城的演员们收到邀请,会各处串着唱,最后,还去京城搞个联欢。王梦得出事前,已经收到了来自京城的邀请。他是个大器晚成的、执着的人,当然自身带着热度,若是留得下一两篇的小报导,对谁都是件好事。李玉已经在省青年团跑了三年的龙套,还没等来一个机会。他告诉师弟,省城的幕布是自动升降,自动开合,用不着人力。省城的幕布,确实有其它颜色,但仍是蓝色更多。
“那,我不过去了师哥,”程季时笑道,“过去可要失业了!”
“哪儿能?师哥我也天天翻跟头,翻得比家里还累。”
“师哥,你可别荒废了唱啊。”
“有师父盯着呢,是你,别荒废了。”
“我又没戏唱。”
王梦得的声带上需要动个手术,往后就算要唱,也得半年后。他心里知道,嗓子恐怕回不去了。他最终决定回吴镇休养,走前把手头上唯一一个去北京比赛的名额让给李玉,原该是他去。师父病了,徒弟替上,没人会说什么。王梦得突然觉得,这是他能够为徒弟做的最后一件事。李玉能不能唱出来,他不知道,程季时能不能唱出来,他不敢想。
“你师父,改不掉的暴脾气,”老乔东说,“没人治的住。”
“你说我师父啊,但我不怕他,我师哥才怕他。”
“瞎说。你真不怕他?刚找我帮你吊嗓子。”
“是真的,”程季时说,“而且,师父现在,嗓子还没好,他没法子骂我。”
老乔东拍拍戏台子上的木板,让他坐下。“老乔东没有跟你说笑,孩子,”他说,“你是个聪明孩子,你师父,他没你活得通透。他年轻那会儿,爱戏爱得疯了。”
“那有啥的,他给我说过。我师哥也爱戏,我也爱。”
“但他一定没给你们说过,他想成角儿,做梦都想。他从来不说,是不是?怕把你们带偏了。”
“我比你们师父大十岁,你师父进团的时候,我已是个青年琴师。那批学生里,你师父的确是最有天分的一个。他一心想去台中间唱个正经角色,也难怪,他托生得不好。我们这个地方,唱主角完全靠年纪,熬不到那个时候,他既唱不了,也出不去。他啥也不懂,只知道狠练。他师父见苗头不对,马上给安排了个管幕布的活。这活累啊,排戏的时候干,演戏的时候干。这日子满了,人就老实了。
但,他不知道累似的,过去练多久,只加不减。没人理他他又发狠,跑龙套的时候不化妆了,过两天又不带道具,就是不敢少翻跟头。他说翻跟头也是练功,练武戏。没人管他,看戏的谁在乎他是谁,团里也不在乎,因为看戏的不在乎。
后来他真的出了件让他们在乎的事。那天演的什么戏我忘了,总之是个夫妻对唱,《四郎探母》 《武家坡》这类,爱听戏的没人不懂。他那天昏了头,换场的时候早了一个点,硬生生地把台上的夫妻俩隔开。场子全乱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救。还记得你师哥那次么,那样的场子,老乔东救得多了。我只好急着让旁边的鼓师加了一段,让台上吊着的演员赶紧下场。
这事之后,团里幕也不让他弄,龙套也不让他跑了,我拼命保的他。我资历老,说得上话。我说,团里培养个人多不容易,哪能一棍子打死!再说,年轻人里本来没几个能唱的,再不把梦得培养起来,这帮老的退了怎么办?到底把他给保下了。你师父,是又感谢我,又气愤我。他脾气有多差,就这样还说呢,我对他们年轻演员老带偏见。他的脾气,是带了你们两个才算好点,他没成家。有徒弟了,也清醒了,才不会老想着成角儿。”
“我师哥的梦想,可能也是成角儿吧。”程季时悄声说。
八
李玉的比赛比得不错,他不像师父那般火得突然,但再不是个籍籍无名的人,固定的演出有了,去北京的机会也有了。
师父若是一直不得恢复,他在京剧中留下的,可能只有那一两篇没人在意的报导,和几场没有录像的演出了。程季时想,师哥若是能够一路顺着往前走,可真好。有人少年成名,有人一炮而红,但是,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是程季时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师父可惜了,师父好不容易成名的。如果师父不可惜,师哥就要可惜了,总是要可惜一个。那么,那个很可惜的人,会不会是程季时?
王梦得这么想过,李玉也这么想过。
“师弟,我那几场比赛,你们别看。还有,比赛后又有演出,别给师父看吧。”李玉说。
“啥玩意儿嘛师哥,我们看着,你在那边就紧张了?”
“不是。师父不是病着?”
“就因为病着,才要看你的演出,高兴嘛。师父要是介意,还是师父吗?”
“不止这个,”李玉说,“他们弄了个采访,我感谢了师父,也感谢了你,他们都给删了。留下些官话,师父不喜欢。”
“你放心吧,我有数。”
“师弟你说,师父的嗓子还能好吗?”
“难。医生说的。”
下午,团里没戏。程季时便去师父家。师父现在刚出院,他手术住院的那几天,也正是李玉比赛的那几天。
“师父,要不你去床上休息?”
“不休息,哪儿有那么累?师父要问你的戏。”
“又被我说中了,我师父。”程季时嘟囔。
“那,过两天再考你?”王梦得看上去心情不错。
“过两天?过两天师父你都好了,又回省里去,那我可没人管了。”
王梦得不说话,他用手拍拍程季时的脑袋,就像从前那样。程季时看着师父坐在沙发上,坐得很板正。师父打开电视,“看你师哥。”他说。
电视的屏幕随着师父的动作一下一下地闪烁,闪到一闪而过的,师哥的影子。调过了,但程季时不敢说话,他看着师父再一下一下地调回来。然后,师父把电视关了。
“季时啊,”师父说,“你过了年,是二十五岁了?”
“当然。师父,你想让我结婚还是干啥的?师哥都还没结婚呢。”
“不是啊,”王梦得说,“你二十五岁了……”
“想啥呢,师父?”程季时说着,又把电视打开,“我们看师哥演出吧,师哥演得挺好的。”
程季时看见,师父看一会儿屏幕,又回头看一会儿他,终是看他的时间长些。师父的眼里,说不清是喜是悲。程季时和李玉,其实,天分上差不多。“师父,”他说,“你看,北京戏台子上的幕布,也是灰蓝色的。”
他没有告诉师父,师哥的每一场戏还有比赛,他都从电视上录下来,看过了很多遍。
学戏的孩子,可能都想过,成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