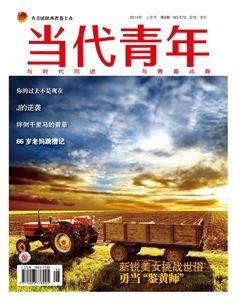大师哥
沈星
认识大师哥的时候,我是18岁的大一女生,面容羞涩,心无芥蒂。
记得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好有安全感。我常想,是不是他很高的原因呢?一米九的个子,我站在他旁边,只是到他肩头而已。我仰头看他,一脸崇拜的样子。最要命的是,他还很帅,坦诚爽朗的笑容。
那次是学校的元旦晚会,我是大一新生代表,要表演节目,他是校广播台的台长,负责这个活动。晚自习结束后,他来找我商量,披着厚厚的棉军绿大衣,英气逼人。我俩在宿舍前说话。冬天的夜晚,站一会儿就彻骨的冷,他看了我一眼,把大衣脱了递给我。鼻头冻得红彤彤的我乖乖穿上,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偷偷喜欢他。
在我念书的那个年代,加入校广播电台是很牛的一件事。开学不久,广播台便有招募新人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不亚于高考地认真准备。一轮轮下来,我成为最后两个被留下来的同学之一。从此我就顺理成章地待在那个大操场边的绿阴小楼里,时时出现在大师哥面前。多么美好,我这样想。
课余时间我都待在小楼里,可是,就这样也并不是总有机会见到大师哥,他是学生社团的风云人物,总是来去匆匆大步流星。偶尔碰面,也会聊聊,指点我的发音位置不对,态度友善。如果哪天正碰到开饭时间,他就会说:“走,请你去尝尝我们理科的饭好吃不。”
跟在大师哥身后去食堂打饭,再端着饭盒在校园里漫步,是我最愿意的事情。一路上,会收到很多女生羡慕的目光。可是,这样的机会不是常常有,大师哥不是每天都有空的。
他还是校篮球队的主力,在他有集训的下午,我总是主动承担寝室打开水的任务,不厌其烦地往返于那条通往开水房的小路,只因为小路的那边就是大师哥训练的篮球场。是不是很傻?而当年懵懂如我却浑不自知,乐在其中。
直到有一次,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二个冬天,周日我照例到广播台玩耍,他不在。屋外的水龙头边有一盆泡著准备洗的脏衣服,一看便知是他的牛仔裤。自然,我走过去,蹲在那儿,开始搓洗。
北方的冬天很冷,洗衣粉在水里化不开像沙粒一样咯着手,这时候大师哥回来了,正好看到狼狈的我,他愣住了,一把捧起我的手,不停呵暖气,还数落说:“你怎么这么傻,谁让你洗的,手冻成这样长冻疮了怎么办?”
那一刻,我只觉得我的手被大师哥握住好暖和啊。晚上,大师哥来找我。我抬头看着他,他却回避我的目光,告诉我,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从高中时就在一起了。他还告诉我,在他心里我就像个小妹妹。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远处,不看我。
回到寝室,我在上铺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清晨起来,豁然开朗。其实,我喜欢大师哥,并没有奢望大师哥也喜欢我,我喜欢他就好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大师哥之间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一如往常。
我们结伴出游,三五成群,他待我如自家小妹,处处相让。我在学校碰到的所有鸡毛蒜皮的问题,都会跑去找他,他甚至还帮我写过一篇中国革命史的期末作业,我塞给他一袋大白兔奶糖算是贿赂。
大师哥高我两届,第二年的暑假,他要毕业了。七月的校园,弥漫着桂花的甜香和小豆冰棍的清凉。我帮他整理行李,他也不再阻拦。我送他走,一路无言,大门口我俩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想,也许,他能拉拉我的手吧,也许,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吧,我静静地等着。大师哥却用格外轻快的语气说:“小妹儿笑一个。”他逗我,我气极,抬脸望他,深深一眼,不发一语转身离去,他在身后唤我,我也不理,反倒脚步越走越快。
待我停下,驻足回望,校门外,却早已人海茫茫,一时间,我泪流满腮……
接着在学校的两年,大师哥也常常回去,逢年过节我们也会不由分说地下一顿馆子。只不过在我心里,他只是我的大师哥了。
后来,我毕业离开,再后来,大师哥结婚成家,正直如他,自然生活得顺意美满。那个我生活了四年的城市,直至今日也没有机会回去。
而今我早已失去了当年毫不掩饰的勇气,甚至还会故作老成和超然,不过我晓得,在我心深处,依然相信和期待,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爱情这样东西的存在。
●责编/安然(anran01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