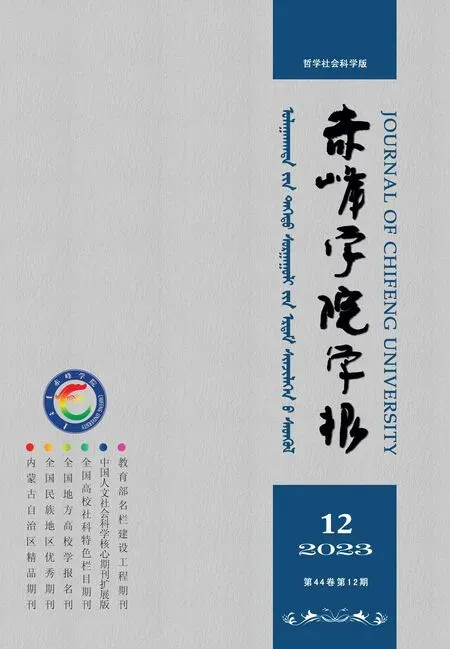以辽庆州白塔为视角论辽代民族融合
于升江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辽代疆域辽阔,涵盖了蒙古高原、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地区,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内。境内民族众多,以其统治中枢所在地——今天赤峰地区为中心,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不断接受来自西域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澶渊之盟后,随着辽宋的和平交往,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加速北进,深刻影响了辽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庆州及庆州城
庆州城作为奉陵邑,建于辽兴宗景福元年(公元1031 年)。此地建州则要早于此,“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1]。建城之初,除了番汉守陵军三千户,庆州辖统三县:立德县(景福元年,括落帐人户,从便居之,户六千)、孝安县和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由此可见,庆州当时是诸民族混居之地,多民族杂居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客观基础。
庆州城建筑风格深受南方汉地建筑文化影响。沈括《熙宁使虏图抄》中提到“庆州塔庙廛庐,略似燕中”[2],足以见证在辽代中晚期庆州城的繁华程度。与庆州同为奉陵邑、建州更早的祖州城,城邑布局上,采用了上京的格局,城分南北,取向东西,特别突出了城邑的民族风格。而相比之下,庆州采用了中京大定府(辽中京是仿北宋汴京而建)的格局,内外城相套,坐北朝南,注重城市的环境美化与人文园林景观,以佛教建筑为主体。地理位置上,庆州城与上京和祖州城距离更近,且庆州隶属于上京道,但是其城市布局风格却借鉴了更远的中京风格。
庆州城既是捺钵要地,辽代皇帝夏秋捺钵经常巡幸于此,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城邑。辽政权属国向西延伸到丝绸之路沿线,包括党项建立的西夏,以及西域地区的于阗等。当年清理庆州白塔天宫时发现了一件墨绿色玻璃舍利瓶,瓶高3.3cm,口径0.8cm,腹径3.3cm,内装舍利子若干。该瓶色泽墨绿透明,器表光滑无饰,呈蒜头状,小口圆腹圆底[3]。此类不远万里随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玻璃制品,在辽代文物中多有发现,也反映了当时草原丝绸之路的繁盛。
二、辽庆州白塔建筑形制及营建制度
(一)建筑形制
庆州白塔由章圣皇太后(辽兴宗生母、史称钦哀后)敕令特建,属于皇家营建,也是现存辽塔中品级最高的一座。
辽庆州白塔的建筑形制是契丹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在建筑领域高度融合的见证。辽代佛塔比照中原建筑样式,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唐代式样,收分合理,宽高比例得当,砖构仿木斗拱以辽代大木为据,制作一丝不苟。辽塔大多为砖塔,却模仿木构结构殿宇,并形成一整套标准建筑式样,用砖筑材料显示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庆州白塔是辽代楼阁式建筑的代表之作,以体现辽代佛教信仰为主题,在塔身的部分设置了浮雕金刚力士,经幢等佛教装饰被用作塔身的雕塑装饰,宋式楼阁塔少有这样设计[4],塔内部没有按照中原楼阁式塔采用筒形,而是每层砌成蒙古包形层层相叠,体现了契丹佛塔对汉式佛塔的借鉴和吸收,使佛塔内部体现出马背民族的风格[5]。辽塔的抗震性也得到历史的验证。庆州白塔在维修施工时发现,此塔沿塔壁每层都设置了木制“圈梁”,这种木圈梁呈八边形,深深嵌固于塔壁砌体之中,而且在八角形的八个结点处设拉梁分别与塔心柱拉接。这种放射形的木拉梁在宋塔中未有发现,当是辽塔的一个创新[6]。应该说,庆州白塔,从建筑风格与形制来看,是承袭唐代建筑风格、运用宋代建造技术、融合了契丹民族自身特点。
(二)营建制度
从出土的螭首建塔碑、圆首建塔碑来看,由玄宁军节度使等军队官员“奉宣提点勾当”营建,负责“勾当钱帛”“勾当工匠”等事务,当时的佛教高僧也参与修建,碑文中共提及三位“赐紫”高僧,其中参与营建的“庆州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朝阳北塔石函题记》中有“都提点前上京管内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此处的蕴珪与庆州白塔建塔碑铭中的题名蕴珪可能为同一人,由此有学者推测,宣演大师极有可能是参与辽代塔寺营建的重要僧侣。“塔匠都作头、副作头”主持修建工程,“贡物库副使、盐铁司度支、塔下行遣人”等配合并监督。诸多工种“匠作头、小作头、常行人”等具体执行。上京归化军、中京归化军、彭栅军等军丁“奉宣建塔下功役”。从这一营造组织体制分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在军事管制下,组织完善、配合严密、诸作齐全、分工细致的营造组织模式,整个营建的过程中存在严格监控之下的服役性强制劳动。这一模式应是辽代皇家直属营造制度的反映[7]。在中国古代官制中,营造工程一般由“将作监”掌管。辽代也设有这一机构官职,但是庆州白塔的营建显然不是由将作监所为。
三、辽庆州白塔是辽代宗教信仰融合的反映
辽庆州白塔是宗教信仰融合、辽代佛教兴盛的见证。契丹人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崇拜日月山川等自然景物或现象,以青牛白马传说为族群起源,推崇白色,尤其是在祭祀中,《辽史·礼志》所述:“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8]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回鹘社会中流传甚广的摩尼教对契丹人也有较大影响,认为太祖阿保机的出生传说大都源自摩尼降生和受启神话[9],摩尼教也以白色服饰为一大特征。辽释迦佛舍利塔塔身为白色,与大多数辽塔一样,是契丹人崇尚白色的体现,白色本身在佛教中也象征着纯洁、清静解脱。无论塔身颜色源于何种宗教信仰,庆州白塔之“白”都是宗教信仰融合的体现之一。
辽庆州白塔的螭首建塔碑文第一句即为“南阎浮提大契丹国章圣皇太后特建”。按佛教在地理方位上的划分,世界有四大部洲,中国属于南瞻(赡)部洲,唐宋石刻中常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契丹人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可见汉文化影响之深。这一点庆陵出土的哀册中也可以证明,辽圣宗的皇后萧菩萨哥《仁德皇后哀册》中道“秦汉已还,隋唐而下,我国迭隆”,辽道宗耶律洪基哀册也写到“一统正朔,六合臣妾”“化流广夏,福庇群氓”,从中不难看出,至少是在圣宗朝以后,辽经常以中国正统自居。
从建筑形式上看,此塔并没有登临揽胜、瞭望敌情的功用,是辽代统治者将契丹皇族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的重要体现。
辽庆州白塔也是西域、南方宋地和契丹本土佛教文化融合的体现,同时塔身浮雕、图像亦是辽代政治社会的写照。在上文中提到塔身浮雕内容十分丰富,有中国传统图样的蟠龙、不同样式的二龙戏珠、牡丹、飞天、迦陵频伽、天王、胡人牵狮献宝、胡人引象献宝、胡人舞乐宴戏等图像。一层壶门内残留一座汉白玉观音浮雕,雕功精湛,虽然不能看全貌,但是从人体形象和衣着看,可以断定是一位女性观音形象,女性观音形象是宋代流行起来的,随着佛教信仰的深入和时代变化,观音形象从信仰偶像渐渐转变为更接近生活的具体人物形象,这可以作为辽代佛教人物形象由南向北传播的实证之一。
塔身浮雕中众多胡人形象,均以长宽飘带作为装饰的砖雕人物,第一层东南侧窗棂之下,绘有西域胡人驯象场景。画面中共三位西域胡人,位于画像前方者,一手持彩带挥舞于头上,一手抱两个柱状短棒;单腿直立腾空,一腿作曲膝舞蹈状。象身正中者一手置于胸前伸作行进状,头裹帛巾,身着短裙。象后站立一西域胡人,手持长板负于肩上,一手托一桃形贡品。亦见有胡人驯狮题材的砖雕,驯狮人卷须,深目高鼻,反映了辽人对于驯狮表演的喜爱以及对西域文化的认同。许多拱眼壁内都浮雕了大量胡人欢歌乐舞的场面。“辽代壁画中的汉人和契丹人从未发现过这样的装饰品,此飘带长而拖地,加之身前飘带容易缠足绊脚,不会是日常服装所用饰品,我们推测可能是西域胡人舞蹈服的装饰品。”[10]另外,庆州白塔每一层拱门门楣上均有二龙戏珠的浮雕,南门与北门的龙纹一致,前后皆为四爪,典型的唐代龙纹样式,且造型饱满生动,体型健硕丰腴,充满生活气息。东门与西门的龙纹一致,为汉代常见的螭龙纹,左右对称,刻于塔门门楣上,造型流畅,形态优美。塔身上的浮雕一般采用对称的图样,但也不束缚于对称之美,同时兼具灵动、流畅的视觉效果。比如迦陵频伽的浮雕形象,有对称雕刻的,也有单体迦陵频伽与双头迦陵频伽分别在假窗之上。
四、辽庆州白塔出土文物是民族融合的见证
(一)文字、纸张
白塔作为庆陵奉陵邑城中之塔,与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略有不同,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均为契丹文字与汉字书写而成,能够看出契丹统治阶层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在皇陵中使用汉字记事。从庆州白塔修缮过程中出土的两块建塔碑(螭首建塔碑、圆首建塔碑)题记均用汉文书写而成,塔体上发现的辽代题记内容,均为汉字书写。出土经咒如《银本功能法》、银本鎏金錾刻梵文《相轮橖中陀罗尼咒》、纸本雕版印刷《根本陀罗尼咒》、纸本红木封装墨书《佛说摩利支天经》等[11]的写本、雕本均为汉文书写,体现了辽代汉字使用的普遍性。即使在辽代皇室兴建的佛塔上,也出现用汉文直书题记的现象,从碑铭中所记各样工匠等,从侧面反映出汉文化在契丹腹地流行,汉族工匠、居民深入契丹腹地生产生活的情况,堪称辽代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写照。佛经用纸的造纸方法与中原地区相似,属于北方造纸体系,是一种质量一般的书写印刷用纸,反映出辽代中期造纸工艺及水平状况虽不及北宋,但也发展得较为成熟完善,是辽代手工业借鉴宋代技术的体现。
(二)丝织绣品
庆州白塔共出土辽代中晚期丝织品276 件,工艺精细程度较宋代有差距,但兼具唐宋契丹的风格。主要分为织染绣三大类,品种有罗、绫、绢、绵、染缬、刺绣等,纹饰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人物故事等,以云雁纹最为普遍,反映出游牧文化特征[12]。辽代设有专门的织造机构,有契丹本土和来自汉、渤海国的织工,因此丝织品融合各地特点,具有独特的风格。以橙地联珠云龙纹绣巾为例,刺绣的主题是龙与祥云,中心为四窠联珠团龙,团窠由白色联珠圈成底处绣对称行龙各一条,空隙处点缀灵芝云纹。这件绣品中龙的形象与宋代流行的龙(纹)形象几乎一致,宋代的龙纹较汉唐以来发生很大变化,恢复到汉代以前的蛇蟒身,身体修长,可以盘足起伏。宋代的龙多是素身的,即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他们的腿比较长,尤其是后腿,很是细长,总体给人一种纤细文弱的感觉。此件绣巾中龙的形象与庆州白塔塔身浮雕中一处龙的形象相同,后腿细长的特征十分明显。团窠样式的使用,主要是继承于唐代,是唐代织绣品中一种常见的形式,庆州白塔出土的团窠样式织绣有四件。联珠纹一般认为是从西亚萨珊波斯王朝经由新疆传入中原地区,在中国大致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唐代达到兴盛,并与中国本土装饰纹样相互融合,在唐代织绵中,联珠纹取代了卷云和各种鸟兽横贯全幅、前后连续的布局方式,以联珠圈分隔成各个独立的花纹单元[13]。就辽代的联珠纹来讲,可能是从唐代承继的样式,也可能是从西域各国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东进到契丹腹地,也有可能是二者兼有。
(三)中药材、香料
庆州白塔出土了多种药材和香料,经鉴定有公丁香、母丁香、乳香、沉香、白檀香、槟榔、肉豆蔻七种。这些药材大部分具有防虫蛀、防潮湿功效,五室中凡置放药材之处,遗物保存大多完好,似与药物功效有关[14]。说明当时人们对此类药物的功效已经了解得相对透彻。辽地的医药具有较为浓厚的汉文化背景,且用途广泛[15]。辽塔中埋葬香药除了宗教意义外,还向我们提供了辽与周边外界关系的信息。而上述香药绝大部分为南方热带亚热带所产植物,有些甚至是南沙群岛、阿拉伯半岛及非洲特产。辽塔中的香药可能是通过与各国进行贸易、国朝贡等方式间接得到的。辽与中亚西亚关系密切,伊斯兰学者马尔瓦兹记载伊斯兰世界向辽输入的物品有:“象牙、胡椒、阿魏、玻璃、青金石等。”《契丹国志》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遗使约四百人,至契丹开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契丹回赐至少不下四十万贯。”[16]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繁盛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辽代各民族融合发展。
五、结语
作为个体的契丹民族已经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契丹民族的基因却融入中华民族中,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庆州白塔屹立于内蒙古高原的秀丽丘陵之中,在近千年的时光流转中,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过往,既保留游牧传统,又能因俗而治。庆州白塔恰恰是辽代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写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