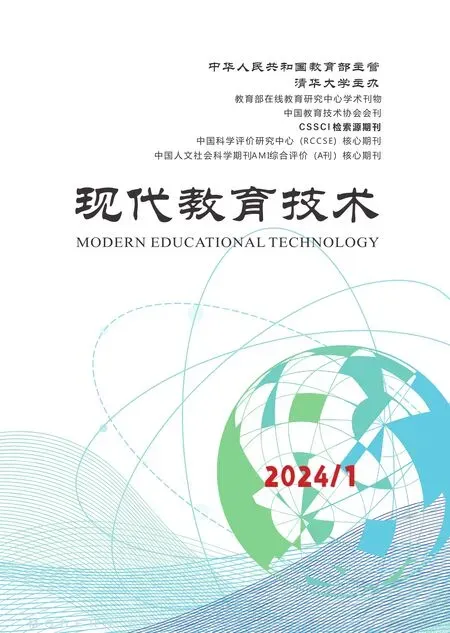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知识观的再审视*——兼论两个经典知识之问的当代回应
杜 华 孙艳超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知识观的再审视*——兼论两个经典知识之问的当代回应
杜 华 孙艳超[通讯作者]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浙江金华 321004)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基于先进算法、强大算力和海量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新定义知识、重塑知识传播方式,促使知识生产模式进阶到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IV”,开启了一场知识生产力革命。在此背景下,需以当代视角回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两个经典知识之问。考虑到“最有价值”隐含绝对主义价值判断,故“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什么知识更有价值”表述更为妥当。对于“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不能仅将目光凝聚于抽象人类群体,而应关注更广泛的社会节点,阐释智能时代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知识与权力关系,人机协同共创的知识更有价值。而对于“什么知识更有价值”,应考虑知识的未来适应性,应对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意识、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阶思维、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综合能力、构建正向可信“人机共善”图景所需的伦理道德更有价值。文章可为分析、研判并主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带来的挑战奠定基础,并为构建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图景提供重要视角。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观;创造性破坏;经典之问
引言
当下,人类社会正经历“六千年从未有过之大变局”,“智能之光”照亮整个沉睡的宇宙[1]——这束光正是来自以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是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目前已升级至第四代GPT-4,未来仍会不断迭代升级。ChatGPT的技术机理,是以先进的算法、强大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为支撑,构筑在“巨无霸”式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之上,采用“预训练+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技术,依托Azuer AI超算平台,具有突出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持续的人机对话互动能力和惊人的原创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ChatGPT的横空出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引导着世界人工智能产业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赛道,被认为是“继计算机图形操作界面以来最伟大的发明”[2]、“AI领域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甚至是“AI时代的二次复兴”、人类告别弱人工智能时代迈向强智能时代的重要拐点[4]。
“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5]。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代表着一种新型生产力工具[6],“将重新定义人类知识,加速我们现实构造的变化,并重组政治和社会”[7]。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非人类要素“身份”与人类平起平坐地介入知识生产过程,使知识生产进一步走向智能化、自主化、高质化、仿真化、个性化,并重构时代的知识秩序,触发知识社会转型,一场静悄悄的知识生产力革命正在发生。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尝试分析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用于知识观嬗变的创造性破坏表征,在此基础上以当代视角回应“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什么知识更有价值”这两个经典知识之问。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用于知识观嬗变的创造性破坏表征
“创造性破坏”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被美籍奥地利学者Schumpeter[8]进一步定义并发展为理论,之后广泛流行于社会科学领域。创造性破坏是人类进步的常态,而技术是创造性破坏的风暴,突破性技术往往会引发系统性生产关系变革。知识观属于知识的思想观念形态,知识观转变不是独立于其他因素的单一思想转变,而是知识范式或知识形态的转变或颠覆;同样,知识观变革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具备社会推动力的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过程。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突破性技术[9],犹如一场创造性破坏风暴,蕴含着广泛的影响力乃至实质性的破坏力,带来了巨大的创造性破坏效应——这种创造性破坏不是真的破坏,其更多地表征为对旧有体系进行吸纳和改造形成更高效率的新体系,或者打破旧有格局建立新格局。因此,这种“破坏”最终带来的不是真的破坏,而是一个全新的景象。
1 重新定义知识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经典问题[10]。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到柏拉图的“知识是证实的真信念”论断,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名言,再到Young[11]的“把知识带回来”口号,都展现了人们对于知识问题的关注。“知识本身与创造及再生产知识的文化、社会、环境和体制背景密不可分”[12]。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来袭,需要重新审视知识,以更好地适应当下及未来的社会环境,并更准确地描述智能时代的知识实践、更快地适应智能时代的语境。
知识是一个蕴含多层涵义的复杂概念[13],其内涵扑朔迷离。“关于知识的文献提供了各种对知识的不同理解——有明确的定义,有含蓄的暗指,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定义,尤其在数千年来对知识的哲学思考之后,居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知识定义”[14]。例如,有研究者认为知识是客观的、自主的、独立于人的存在,是“加工过的信息”[15],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产生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16];也有研究者认为知识是主观的,存在于人的心智中,是附属于个体的东西,是发生在个体层面上的认知现象等[17]。这些关于知识的看法虽有不同,但关涉范围都限于人类。
知识不是脱离情境且亘古不变的逻辑体系或“真理”表征体系,而是根植于社会情境之中,有其适用的特定时空场域或条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生成对抗网络(GAN)、变分自编码器(VAE)、转换器(Transformer)等算法,创建或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可以“写故事,给予生活建议,写诗和编写计算机程序”[18]、撰写文献综述[19]、辅助完成问卷编码[20]、完成医学报告[21],已达到无法与人类生成内容相区分的水平。也就是说,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机器凭借自我学习能力感知外部刺激信息、模拟人的知识处理行为、实现自主性推理与决策、完成知识生产与创造的闭环。由于机器的参与,知识仅关涉人类范围的这一重要界限被改变:人类的知识不再只是人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成果,还包括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的结果,以及人借助技术从数据中获取的认知成果[22]。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改变知识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写了知识的定义,延伸了知识概念的外延。所谓外延,在逻辑学上指一个概念所指向的对象的范围,如“人”这一概念的外延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知识的外延应该关涉一切知识,当然也包括机器知识和人机协同产生的知识,因此知识将被重新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指出,可以将知识“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和态度”[2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人、机器或者人与机器协同,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态度等均是知识。
2 重塑知识传播方式
知识传播是知识通过载体进行扩散并被知识需求者所获得的过程。人类在远古时代通过口耳相传,传播关于采集、狩猎、种植、工具等方面的经验性知识。在之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和文字成为知识传播方式的重要里程碑,人类藉由语言和文字进行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接着,纸张和印刷术为人类知识承载提供了绝佳的物质载体,使知识得以大范围地保存和传播;后来,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更为丰富的资源与环境,人类借助媒体技术提供的声、色、形等多途径进行知识传播;再后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知识以数字形式存储于网络空间,且可以被无限复制、随时随地获取。上述知识储存与传播方式的巨大改变,促使知识传播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由地域性演变成全球性,知识可以于瞬息间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进行一场知识传播方式的再升级,这将从根本上颠覆知识先生产后传播的流水模式,代之以生产与传播同步的人机交互模式。
①高密度知识生成拓展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ChatGPT使用基于GPT-4的大型语言模型,应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指令微调(Instruction Tuning)等技术实现对人类认知机制的深度模拟,其功能以聊天和文本创作为主。由于有大量的人类偏好知识注入,ChatGPT能够有效学习人类认知与表达的惯习。此外,ChatGPT能够实现连续性人机协同,即可与人类进行长时间的连续对话,并基于给定的主题或在多轮对话过程中识别的上下文信息,高密度生成符合逻辑的、富有启发和创意的连贯性回复,因此其可以称作是“全年无休、无所不知的巨无霸信息检索和答案生成大师”[24]。这些生成的连贯性内容不仅可以成为人类的创作素材,还可以在思维广度上给人类以启发,从而拓展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②对话式知识生成提升了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个性化。ChatGPT是“革命性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以为复杂问题提供长篇回答。它经过训练,可以理解人类提出问题的意图,所生成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提示(Prompt)”[25]。人类用自然语言对话的方式向ChatGPT提出问题,所给的问题提示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会不同。这主要是因为ChatGPT在与人类对话的过程中,会不断对人类的个性化要素进行识别、学习和整合,并对输出要素进行结构化处理,最终以贴近人类的方式进行个性化呈现,完成对人类对话方式的深度模拟。因此,知识传播能满足人类直接的、个性化的知识需求,具有实时互动性。在人机对话过程中,知识并非单向传播,而是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可以实现人机双向赋智。
③类人式知识生成增强了知识传播的情感体验。ChatGPT可以基于人类的提问,生成顺畅、自然的语言表达,在处理语言交互任务时更加准确,还能根据人类的反馈来调整自己的回答,故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同时,ChatGPT在语言感知力、认知力等方面已取得突破性发展,其精准的理解、流畅的应答、清晰的逻辑、礼貌的拒绝等类人特性,使人们在接受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有了更丰富、更真实的体验,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情感交流。
3 升级知识生产模式
1994年,英国学者、科学哲学家Gibbons等[26]提出“知识生产模式”(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的概念,用来指知识产生和创造出来的方式,这既是一种解释知识形成和发展的模式,也是人类在知识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于知识生产及其变化的认知。
人类之所以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站到文明金字塔的顶端,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通过不断生产、积累、迭代大量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就是人类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知识生产模式也相应发生了变迁,如表1所示。

表1 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
具体来说,在农业社会,人类主要通过个体感知、思考、创造等方式产生知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可称为“模式0”。进入工业时代,人类认识到个体知识生产往往受个体经验、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于是个体趋向融合,逐渐产生依托于国家的专业社会组织。自此,知识生产成为一种专门活动,主要由某一学科领域的少数精英学者或学术共同体开展,且大多分布在大学与科研院所,倾向于开展认识论层面的“形而上”探究,具有权威性、集中化的特征,这种知识生产模式被Gibbons称为“模式I”[27]。20世纪中叶,大学、政府、产业组成知识生产共同体,“知识生产模式II”应运而生[28]——这是一种相对大众化、具有普及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扩展了科学研究、知识创新的参与主体和空间边界。此时,大学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机构,政府、产业也成为知识生产建构和发展的参与者,大大提升了知识的系统化和应用性。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的普遍应用和Web 2.0的广泛传播,出现了用户群体智慧汇聚生成新知识的方式,被Carayannis等称为“知识生产模式III”[29]。此时,知识生产的主体进一步拓展,不仅包含大学、政府、产业,甚至还涉及整个公民社会;知识生产和知识进化都在分布式协作网络中完成,协作关系成为知识创新的动力。
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知识生产环境的迅速变化,开启了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智能知识生产模式,亦可称为“知识生产模式IV”。知识生产原是人类所独有的智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打破了这种局面,重塑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使算法驱动的智能主体开始嵌入知识生产框架中,带来了突破性AI技术赋能知识生产主体与方式的结构性变革。此时,知识是在人机动态交互过程中联合创生的,人机协同的新形态颠覆了人类知识生产所依据的先决条件,知识生产主体、工作模式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人类和ChatGPT以彼此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合作,重塑了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原本是“人类的创造物”,但现已成为人类的协作者,这打破了人类的知识生产垄断性地位,而呈现出人机二元智能体协同进行知识生产的新图景。
综上可知,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知识生产模式已迭代升级至智能知识生产模式,且这种模式的社会影响正越来越广泛,重构了时代的知识秩序,倒逼人们不得不思考:教育者究竟该教什么?学习者究竟该学什么?这些问题既是教育的逻辑起点,也是教育教学中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需要站在全局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思考。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并解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等振聋发聩的问题,这既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起点和关键,也是数字化转型极为特别且重要的学术议题。
二 “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人与机器协同共生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振聋发聩的问题,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阿普尔[30]于1976年提出,他将知识放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政治文化语境加以考量。这一问题包含知识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勾连的内在关系,为知识价值提供了“人的尺度”[31],彰显了知识主体对于知识价值的意义,肯定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人们在肯定此问题之价值的同时,也发现其有一定的局限性:①“最”在汉语中有“终极的”“绝对的”“无比的”“第一的”等含义,故“最有价值”隐含绝对主义价值判断。绝对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从来如此且永远如此,只承认其绝对性,而否认其相对性。照此绝对主义逻辑做出绝对性判断或得出绝对性结论,终究逃不过被批判的命运。因此,“谁的知识更有价值”表述更为妥当。②过于肯定人的主体性,在学理上暗含着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界限,未能摆脱主体与结构、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使知识价值成为某种客观结构或主体的赋予之物。③存在“泛意识形态”“泛政治化”趋向[32],仅揭示知识背后隐藏着“归属”于人类某些群体的权力,反映的是一种相对宏观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并不总是被握在统治阶级、利益群体手上,而是弥散地存在于社会每个节点之中并制约着个体的行动。我们从理论上强调权力时,其实是在论述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
尝试以当代视角回应“谁的知识更有价值”,既有挑战又具现实意义。在哲学层面,价值是事物因为生命需要而产生,能满足生命存在、延续或发展进化等其中某一种需要的属性。在此话语逻辑下探讨“谁的知识更有价值”,实则是回答“谁的知识更能满足人类生命存在、延续或发展进化的需要”这一问题。随着知识范围延展到机器,关于知识价值的讨论不再局限于人类范围——知识价值不仅限于促进人类个体与群体发展,机器及其发展也成为人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33]。Kurzweil[34]在《奇点临近》一书中预测:下一阶段智能发展将是人类与机器的联合,即嵌入人类大脑中的智慧将与容量更大、运算更快的机器智能相结合,在不同层次给社会生产制造带来范式增长,人类与机器成为同事正在变为现实,人机协同共生将成为常态。人类赋予机器智能、智能机器反哺人类,将推动人类智能进一步发展。人类智能在感知、推理、归纳、学习等方面具有机器智能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机器智能在搜索、计算、存储、优化等方面领先于人类智能,可见这两种智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互相取长补短,将形成一种新的“1+1>2”增强型智能——融合智能。因此,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将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对相生相克的统一体,从而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机融合智能时代。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人类群体,而应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到更广泛的社会节点,阐释智能时代人类与机器相互敞开、彼此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关系。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掀起了一场智能化新浪潮,需深度匹配“分布式社会”所带来的权力弥散与更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与机器在内容创新、知识生产中拥有了更多的平等机会和权利,这将促成知识生态的深刻变革。因此,“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中的“谁”,既不是一个边界分明的群体,也不一定是一个完全具有自主能力的“谁”,而是人与机器协同共生。
三 “什么知识更有价值”:为未来而学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1859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斯宾塞[35]提出的振聋发聩的问题,他给出了“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回答。这一观点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引领欧美乃至世界各国将课程改革的价值指向“科学”,表达了对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强烈认同。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导致传统知识体系的坍塌,“课程”这一传统的知识体系外显形式,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也值得进一步讨论[36]。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判断知识价值的标准:到底什么知识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究竟该学习什么?什么才是对他们未来成长和发展真正有帮助、有价值的东西?显然,“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回答已不适合当今的情境。斯宾塞的理论基点是客观主义知识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受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范式的影响,知识普遍被认为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具有客观规律性——而发展到今天,知识观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他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人文知识的价值——而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分离的结果,使现代人要么成为只懂技术但灵魂苍白的“机器人”,要么成为高谈人文但技术文盲的“边缘人”。
同样,由于“最有价值”隐含绝对主义价值判断,故“什么知识更有价值”表述更为妥当。而回答“什么知识更有价值”,需要审思教育的真正目的。对于教育目的的探讨,Whitehead[37]表示教育应当让学生体会到各种思想的力与美、能从整体上把握各类知识的结构,并能让学生深入了解某类与未来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知识;Durkheim[38]从高度工具主义的思想出发,认为教育目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历史场合的社会需要;Dewey[39]主张教育目的源于教育活动本身;而Taylor[40]提出了“社会意象”,认为社会意象是一个社会中普通人共有的思维方式,是指导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共同文化,教育目的便存在于社会意象中——对教育目的的分析,除了检验各种相应的政策与项目,还应当考查赋予该教育目的以意义与合法性的社会背景。这些观点表明,为学习而学习的方式存在不足,教育不应服务于这样的功利化目的——实际上,教育目的是工具性的,是为了发展人力资本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以当代视角回应“什么知识更有价值”这一经典之问,答案是:为未来而学、能够适应未来的知识更有价值。
1 应对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意识更有价值
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浪潮,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学会与之共存,并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复杂性、扩展性、不可控性、不可预知性等特点,故这一新兴技术浪潮可能会引发诸多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对此,我们要做好风险预估和防范工作,以规范人工智能研发、生产和应用的秩序,所以应对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意识更有价值。
实际上,掌握多少事实性知识和理论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能理解世界的社会关系,站在全球视野、未来发展的高度,将复杂关联的真实世界作为学生的“教科书”。以知识积累和传递为主旨的课程教学模式将无以为继,未来社会发展需要教育打破既定的知识框架,通过切实的谋划和行动回应社会转型期更为广泛的现实需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人类要站在更高的意识维度思考和学习,提前布局,做到“升维思考,降维行动”,增强应对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意识,具体包括对不可预见性的理解、对风险的预估和积极准备[41]、不确定状态下采取行动的意识[42]、对失败的接纳和包容[43]、稳定积极的心态等,以达到一种高意识的状态。高意识是一种高度的认知与理解状态[44],在这种状态下,人对现实的本质、自我和社会将会有更深刻的认知,故高意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世界、洞察世界并改造世界。人类需要在高意识层面强化自身的优势,统筹规划并提前布局数字社会的文化建设,打造数字文明,来正确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以实现人机共善并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2 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阶思维更有价值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维层级的认知上呈现出与人类智能势均力敌的态势,但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方面仍不及人类。从克服ChatGPT的弱点和回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两个角度来考虑,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阶思维更有价值。
尽管ChatGPT使用高精度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具有媲美人类创作水平的潜能,但其在内容深度、广度、整体质量方面仍存在不足,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错误,或存在“幻觉”(Hallucination)、“事实编造”(Confabulation)等问题,或引发隐私和数据安全、算法偏见、歧视等问题。而思维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与方法,能够帮助个体洞察事物底层规律,是成功执行、解决复杂任务和问题的基础[45]。其中,批判性思维能帮助人们有效分析信息、澄清谬误、避免偏见,提升人们的理性判断和自我反思能力,同时能有效弥补ChatGPT不能辨认信息真假、欠缺有效逻辑推理能力、难以理解人类语言背景信息等不足[46]。创造性思维则是打破思维定势,从新角度来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ChatGPT的语言概率算法机制使其容易出现重复性内容,这不仅会削弱ChatGPT的原创力,还会使其仅能提供建议而在内容细节展开方面后继乏力,因此人类要将发展创造性思维作为核心任务。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虽能辅助人类决策,但不能代替人做决策并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人类需要具备在复杂环境中的决策思维,以能真正自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因此,专业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减反增,并成为了影响人工智能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
3 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综合能力更有价值
当下,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复杂性和充满价值冲突的时代环境,迫使教育培养能够更好地创造性运用知识的人,具有灵活性、适应性且流动性强的人,具备全球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以及懂得终身学习的人[47]。ChatGPT跳过学科、专业、领域等的限制,直接切入知识碎片本身,有可能打破现有的知识体系,形成更细小的知识单元,并以碎片化方式呈现各类知识,这既破除了学科壁垒,也加速了知识融合。因此,提出问题的能力、人机协同的能力等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综合能力更有价值。
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是人类创造知识的途径,但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难、也更为重要。提出问题的能力依然是人类的智慧门槛,特别是如何向ChatGPT提问、给予其易理解的提示语和清晰明确的指令,这是一种人机沟通能力,体现的是人类确立任务目标、提炼整理信息、有效表达、判断信息价值、生成创意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拥有这种综合能力的提示语工程师(Prompt Engineer),正成为炙手可热、甚至年薪过百万美元的新职业。而人机协同强调与聊天机器人、教育机器人之类的人工智能协同合作,将成为人类应具备的一项综合能力。人类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以往个人电脑、互联网、手机等的发明和使用经历告诉我们:人类需要学会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才能更好地应对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在这场人机协同演进的技术浪潮中,要让每一位数字公民都能够成功跃迁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智公民[48]。
4 构建正向可信的“人机共善”图景所需的伦理道德更有价值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带来了伦理道德问题。2023年 3月,因存在数据隐私和伦理风险,图灵奖获得者Bengio等[49]呼吁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4月,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称ChatGPT类智能化工具已暴露出跨境数据泄漏风险[50]。更严重的是,某些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不具备“传道”的育人适用性,反而在价值观误导、学习过程反智等方面已显现出反育人的威胁[51]。
对此,我们需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保持一种清醒、审慎的态度,呼唤一种面对技术理性甚嚣尘上的理智上的诚实:一方面,要厘清新技术驱动社会结构改变的巨大潜力。技术本身被认为是中性的,但如何使用技术,避免智能算法的设计存在“心计”,需要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善治”来谋求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的“善智”,助力人类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趋利避害。另一方面,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以尽力规避技术风险。在技术之强大变革力量的作用下,人类要始终坚持技术向善,保护人类的隐私和信息安全,确保AIGC生成内容的公正性、准确性并避免其价值异化、不良导向性,构建“人机共善”图景,是人类在面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应秉持的基本态度。所以,构建正向可信的“人机共善”图景所需的伦理道德更有价值。任何新技术的应用,都存在社会与技术双向适应的过程。在压实法理红线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多地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长空间,同时进行及时干预和调整,以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沿着可知、可控的状态发展,实现技术驱动社会不断进步。
四 结语
回顾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迁往往都是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掀起了一场智能化新浪潮,其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才刚刚开始。在技术作为创造性破坏力量重塑教育生态的过程中,那些胜出者往往是创造了新的生态关系的开拓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推动下,深入解构并分析其对知识观嬗变造成的创造性破坏,才能深刻诠释智能时代知识观由混乱“破坏”走向有序“创造”的演变历程,并全面勾勒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图景。以当代视角回应“谁的知识更有价值”,人类将与智能机器一起成为新的知识主体,为知识创造注入鲜活的生命力[52],使人与机器协同共生的知识更有价值。而以当代视角回应“什么知识更有价值”,答案是为未来而学、能够适应未来的知识更有价值——具体来说,应对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意识、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阶思维、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综合能力、构建正向可信的“人机共善”图景所需的伦理道德更有价值。面对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强势再造,我们需要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看清未来的方向,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教育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对新知识观的研究与思考还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
[1]OpenDAI.开放协议“人工智能宣言”[OL].
[2]Gates B. The age of AI has begun[OL].
[3]沈书生.适应与变革:AIGC产品如何改变教育过程——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J].教育研究与评论,2023,(3):15-21.
[4]王仕勇,张成琳.ChatGPT参与知识生产的技术路径、应用与挑战[J].教育传媒研究,2023,(3):53-55.
[5](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著.刘钢译.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6]王茂福,严雪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应用价值、现实梗阻与路径支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87-96.
[7](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著.胡利平,风君译.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256.
[8]Schumpeter J.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 London: Routledge, 1976:34-35.
[9]Garnter. Your detailed guide to the 2023 Gartner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OL].
[10]郭元祥.把知识带入学生生命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4):28-43、184-185.
[11](英)迈克尔·扬著.朱旭东,文雯,许甜译.把知识带回来:教育社会学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的转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5.
[12][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8.
[13]杜华,顾小清.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审思[J].中国远程教育,2022,(10):1-9、76.
[14]Müller-Merbach H. Eysenck’s advice: Why and when to define knowledge[J].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Practice, 2006,(3):250-251.
[15]Dretske F.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21.
[16]彭漪涟.逻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81.
[17]Pa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15.
[18]Scharth M. The ChatGPT chatbot is blowing people away with its writing skills[OL].
[19]Ayd N, Karaarslan E. OpenAI ChatGPT generated literature review: Digital twin in healthcare[OL].
[20]Mellon J, Bailey J, Scott R, et al. Does GPT-3 know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Us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code open-text social survey responses at scale[OL].
[21]Jeblick K, Schachtner B, Dexl J, et al. ChatGPT makes medicine easy to swallow: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n simplified radiology reports[OL].
[22]顾小清,胡艺龄,郝祥军.AGI临近了吗:ChatGPT热潮之下再看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7):117-130.
[24]顾小清.ChatGPT对教育生态的影响[J].探索与争鸣,2023,(3):30-32.
[25]Liu P, Yuan W, Fu J, et al. Pre-train, prompt, and predict: A systematic survey of prompting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OL].
[26]Gibbons M, Limoges C, Scott P,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London: Sage, 1994:36.
[27](英)迈克尔·吉本斯著.陈洪捷,沈文钦译.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0.
[28]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2):109-123.
[29]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FREIE) ecosystem: 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 “mode3”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1,(3):327-372.
[30]Apple M W. Making curriculum problematic[J].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1976,(1):52-68.
[31](美)迈克尔·阿普尔著.曲囡囡,刘清堂译.教育与权力(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
[32]龚孟伟,陈晓端.试析阿普尔批判教育思想的价值追求与理论局限[J].教育研究,2008,(10):96-100.
[33]刘复兴.论教育与机器的关系[J].教育研究,2019,(11):28-38.
[34](美)雷·库兹韦尔著.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奇点临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50.
[35](英)赫·斯宾塞著.胡毅,王承绪译.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
[36]钟秉林,尚俊杰,王建华,等.ChatGPT对教育的挑战(笔谈)[J].重庆高教研究,2023,(3):3-25.
[37]Whitehead A N.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29:10.
[38]Durkheim E. Selected writings[M]. Cambir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54.
[39]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M]. London: Macmilan, 1916:69.
[40]Taylor C.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21.
[41]Torgersen G. Teaching the unknown: How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uncertainty[OL].
[42]Education Service Australia. Preparing today’s learners for uncertainty[OL].
[43]Hancock J, Rogers M, Pollard S. Improving uncertainty tolerance in medical students: A scoping review[J]. Medical Education, 2022,(12):1163-1173.
[44]祝智庭,戴岭,胡姣.高意识生成式学习:AIGC技术赋能的学习范式创新[J].电化教育研究,2023,(6):5-14.
[45]祝智庭,戴岭,赵晓伟.“近未来”人机协同教育发展新思路[J].开放教育研究,2023,(5):4-13.
[46](美)盖瑞·马库斯,欧内斯特·戴维斯著.龙志勇译.如何创造可信的AI[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98-108.
[47]Perkins D. Smart schools: From training memories to educating mind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10.
[48]袁磊,徐济远,叶薇.AIGC时代的数智公民素养:内涵剖析、培养框架与提升路径[J].现代教育技术,2023,(9):5-15.
[49]Future of Life. 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OL].
[50]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于支付行业从业人员谨慎使用ChatGPT等工具的倡议[OL].
[51]苗逢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原理及其教育适用性考证[J].现代教育技术,2023,(11):5-18.
[52]杜华,顾小清.智能时代的知识图景:人工智能引发知识观重塑[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4):47-54.
The Re-examination of Knowledge View under the Wav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ntemporary Response to the Two Classical Knowledge Problems
DU Hua SUN Yan-Chao[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wav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as swept in and produced extensive social impacts. Based on advanced algorithms, powerful computing power and massive data,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defines knowledge, reshapes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modes, and promote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to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IV” characterized b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hich started a revolu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vity. Under this context, the two classical knowledge problems of “whose knowledge was the most valuable” and “what knowledge was the most valuable” were responded from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that “most valuable” implied absolute value judgments,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express “whose knowledge was more valuable” and “what knowledge was more valuable”. For the problem of “whose knowledge was more valuable”, attention should not be focused on the abstract human group and should be paid to the broader social nodes to explain the knowledge and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in the intelligence era, and the knowledge co-created b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as more valuable. For the question of “what knowledge was more valuable”, it was more valuable to consider the future adaptability of knowledge, the awareness of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and social risk, the higher-order thinking not easy to be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not easy to be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thics required to build a positive credible “human-machine co-goodness” prospect. This paper can lay a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evaluating and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education field,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view in the intelligent era.
ChatGP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view; creative destruction; classical problem

G40-057
A
1009—8097(2024)01—0096—11
10.3969/j.issn.1009-8097.2024.01.010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国家一般课题“人机协同时代乡村教师智能素养结构与培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BCA21009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杜华,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智能教育、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等,邮箱为jsjydh@zjnu.edu.cn。
2023年6月6日
编辑: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