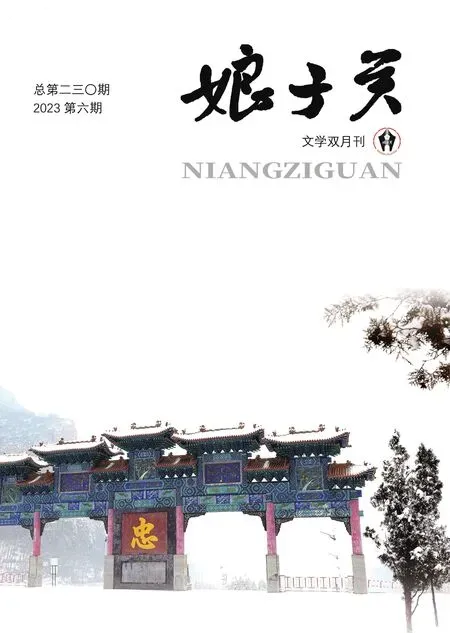花的盛开
◇谢立军
单位同事找我要老房子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说要进行摸底登记。当天下班回到家,我从抽屉里找出收藏的房屋产权证,跟婆娘说起老房子可能要翻建的事儿,她似信非信,不过想想老房子已经年代久远,她还是选择了相信。
我的单位偏居城市郊区一隅,但现在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婆娘跟我一样,对老房子是有情感的。据老一辈人说,老房子始建于上世纪70 年代中期,曾是单位职工宿舍楼,东西走向,上下两层,红砖瓦房,每套有两间面积不大的居室,没有室内厕所,厨房跟居室不相连接,中间隔着一条走廊。而我的房子处在底层端头,购买于21 世纪初期。其时,我已是离职自谋职业的人,又结婚成家了,因为没有房子,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我儿子出生的第2 个年头,遇上单位产权房卖给职工的“好事”,我幸运地获得了一个购房指标,才算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巢。那份记忆至今犹新。鸟倦归巢,人倦归家。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拥有一方小小的独立天地用来居家过日子,是一件多么幸福和开心的事情。
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父母没有能力起屋买房,因为我能体会到他们用微薄工资抚育我们兄妹仨成长的艰难。父亲贫苦出身,家里兄弟姊妹众多,高小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在家里“修理”过地球、在外搞过副业的父亲,穿上了军装进了部队大熔炉,因为表现优异提了干,算是跳出了农门。转业后,回到家乡在某林场任副职。母亲也来自农村,初中毕业后做过两年村小学代课老师,当时算是知识分子,后来她成了一名工人。他们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贪求别人的也不浪费自己的一分钱。他们节衣缩食地承担着一切生活重负。工作之余,他们在林场周围开荒种地,将泥土深深地翻过来,种萝卜、白菜,还扦插红薯枝条。他们整天地忙碌着,一年要喂养一两头猪变卖成钱来贴补家用。他们把一生的精力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家庭,让我们三兄妹健康成长,又帮助我们一个一个地成了家。
我和婆娘结婚的时候,父亲因年高而退居二线,母亲已经退休数年了,他们住在单位一套70余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里。后来,父亲开始唠叨起退休回老家大田院子的话儿,他说:“竖座房屋不容易,若是它荒芜久了,怕是挨不过日晒雨淋啊。”我的老家在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乡镇偏僻村子里,遗弃在大田院子那座红砖青瓦的平房,已像个上了岁数的沧桑老人一直无人照顾,在寂静的时光里正凄冷地日益老去。尽管父亲每过三年五载,总会花钱请人来一次捡瓦维护,更换断裂的椽皮,增添一些青瓦,但窗棂、木柱、隔扇等老朽面目仍昭示着时间对它们的伤害,屋顶旧腐的椽皮不时零星地裂断了,掉落的瓦片破碎于地,漏风又漏雨。尤其是雨季漏水的痕迹在墙壁上呈现出形态不一的图案,如同一幅幅水墨画的枯笔,十分醒目。
人言故土难离。我能够体会到父亲眷恋母亲一样眷恋老家沉寂多年的房子,还有那土地肥沃的村庄。我也出生在大田院子,它是我的衣胞地,只是待的时光不长,那份情感逐渐被岁月洗涤得失去了色彩。但面对父亲的“归去来兮”经,母亲却一反常态地没有支持,我们做子女的也纷纷站队母亲,对他未像平时一样耳提面命,拿交通不便、医疗条件不好等理由来反驳他的抉择。我直到购买了单位老房子,母亲才向我们道出父亲当初要回老家养老的真实目的。原来,他不仅仅是挂念故土、欲叶落归根,更大的出发点却是想给他这个小儿子挪腾出房子,而母亲不附和他回去的因素也很简单,只是想跟她的儿女们能够同城而居,朝夕相处地过完余生。这些,确实令我们非常感动。
陈宏谋曰:“凡为父母的,莫不爱其子。”孩子已经长大了,甚至已经结婚生子,在父母眼中他还是孩子。所以父亲对于没有给我准备房子结婚,算是他的一大愧疚,便想把自己居住的房子腾空出来。我清楚地记得,住进了老房子的那日,虽然它已有30 余年的历史了,对于我们倒是名副其实的喜迁“新居”,全家春风满面,洋溢着喜悦的神色。当晚深夜,繁星满天,月光如水,他们母子俩疲惫地沉入梦乡,我却心荡神驰、水逐风云而难眠,遂披衣下床,情动而辞发,写下一篇散文,后发表于某省级报纸副刊,其中有一段文字,我觉得很感动人,现摘抄下来:“白天中午,在附近的一个酒店里,简单地办了两桌喜庆我们房子进伙的酒席,父亲跟我的叔伯、姨父们端坐旁边的一张酒桌上,看着他舒坦地绽着笑颜喝下杯中的酒,好几回,我想离座走近他拥抱他,把对他最深情的表达全部融入这拥抱中,并跟他说,有朝一日将会购买一套大房子,把他们二老接过来颐养天年。”
那时,我在本地某文化公司打工,并利用空闲写稿。老房子仅有两个小房间,肯定是没法设置一间书房了。隔壁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妻,跟我和婆娘年纪不相上下。他们有一个小女儿,聪明伶俐。女人在城里某单位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上下班,铆足了劲儿地往前奔。男人是单位一名装卸工人,人很勤快,家里的锅碗瓢瓶擦得锃亮,不做工时负责全家一顿三餐。常常是菜到火起,香味四溢,令我这个厨艺空白的大男人自叹不如!有时候,遇上老婆带着儿子回了娘家,我下班回来累了想偷懒便去他们家里蹭饭。
当年秋天,秋老虎格外地毒辣。那天上午,周末外出采访返回的我刚走进家门,邻居就从隔壁闪出来焦急地说,我婆娘昨夜突发泌路系统结石,他们夫妻睡卧隔壁听到其痛苦之声,又听见我儿子“嘤嘤嘤”地哭着,故起床敲门问之,见状,赶紧把病人送到医院治疗……我一边焦虑地直奔医院,一边由衷地感叹道:“若不是他们深夜及时相送医院,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身居逼仄的老房子里,却能够相遇如此近邻,幸哉,美哉啊!”正如《孟子》所谓“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我想,我跟邻居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的真实写照吧。
两年后,由于某种原因,我再次失去了工作。深思熟虑之后,我抉择在家专职“码字”。在婆娘的支持之下,我奢侈了一回,配备了电脑、打印机,连接了网线,还买了部手机。每天早餐后,常常将自己关在卧室兼书房里,铆在电脑前,默默地,专注地将思绪聚拢,顺应报刊的风格与约稿要求,写缠缠绵绵的情感散文,也写惊悚恐怖的小说,还写大众化的通俗文学。我用电脑打印投稿,也用电子信箱投稿。累了乏了,就喝口茶,小憩一下,或者关闭电脑,踱出房屋走一走,舒缓一下筋骨,缓解疲惫。聊以慰藉的是,好在我躬逢一个纸质期刊红红火火的大好时代。我写得风生水起,成了身边略有名气的写手。每月,总有若干文章被报纸期刊刊用,获得一笔笔喜爱的稿费单。于是,就有同仁登临老房子来向我请教创作秘诀。我不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道”和“悟”,总是毫不遮掩地跟他们一个个说:“你看我一家人还蜗居在陋室里呢,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挣钱门道,只好依靠文字来赚点钱养家糊口啊。”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我在老房子里年复一年地写稿、改稿、投稿。每年,春季到来后,雨水繁多,气候湿润,老房子地板潮湿,甚至连墙壁都有很重的湿气;立夏过后夏至,小暑大暑处暑接踵而来。那个热呢,老房子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更加煎熬人,白天就别提了,就连晚上吹着“呼呼呼”直转的电风扇,还是难以感觉到一丝凉意;而南方的冬天,虽不像北方那样,北风咆哮,冷的彻骨,老房子却由于限制于当时的材料水平,并不紧闭密合的门窗,挡不住冷飕飕的寒气,一股股钻进了骨头缝儿里,写作时间一长,便会冻得双手关节酸痛。毋庸置疑,老房子因年久而腐旧了,不是个读书写作的绝佳境地。老房子的众多疾疴,逐渐在我脑中堆积成一个念头:就是多写稿,多赚钱,一旦赚够了钱,便马上换一套带书房的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让父母搬过来安度晚年,让全家住得舒舒服服的。
这样的念头,一直支撑着我。所以实际说,老房子不仅仅就是我们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这一点。它对于我来说,无形中已经升华为一种鞭策,一种动力,一种呼唤。我把账算得很明白,努力多创作一篇作品,就有可能离计划中的新房子又接近一丁点距离。待儿子上了小学,婆娘经邻居家女人引荐,做了另一家单位的清洁工。我真不愿意她早出晚归的。婆娘清秀雅致,娇小玲珑,典型的小家碧玉。她生于城里长于城里,且是家里的幺女,备受父母和哥哥姐姐的疼爱,从小到大就没呷过苦。当她还是大姑娘而在选择自己的命运时,明知无房的我有着一份工作也是有名无实,还是心甘情愿地成了我的婆娘。当我最终表明我的态度后,她毫不在意做清洁工,反而宽慰我:“世间最美,是劳动。何况工作量不大,待遇也好。”一股暖流顿时充满了我的血脉和身体。
我深知,婆娘是一个不物质的女人,她总劝我不要整天端坐电脑前写稿子,累坏了身子,纵然有千金也买不到健康,她说:“人生的幸福与否,并非住高楼大厦,身穿绫罗绸缎。别墅有别墅的美,陋室有陋室的好。穷人有穷人的乐,富人有富人的恼。其实,最幸福的东西不是丰富物质,而是一家人在一个屋檐下,能够平平安安地相守过日子。”坦白地讲,在漫漫人生路上,有这样一个贤惠婆娘相伴,是件幸运的事。常言道,“境由心生”,又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婆娘的“心境自然乐在其中”,无疑是一剂心灵快乐的良药。但我有我的责任和义务,况且人正当盛年,元气充沛,如果一味地无争无竞、随缘自适的话,实乃不妥。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一晃我在老房子里“宅”了4个春秋。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发表了多少篇作品、多少万文字。4年来,我的写作很难用“上班”、“下班”来分割,更难以区分八小时内外。饱经风霜的老房子里,留下了我的追求,我的负重前行,我的时光履痕……当年我搬进老房子后在屋前空地栽下的桂花树,已是枝繁叶茂。那一树的绿叶,不只是鸟儿喜欢栖居的天堂,它们在枝丫上跳跃的音符报道出绿色的魅力,更使老房子增添了一抹活泼动人的景观。我有一篇稿子写的就是这棵桂花树,说它藏着时间的味道,面对它,我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还说它像一个脉脉含情的妙龄少女,好几回,写得困了乏了,或是透过窗户静静地端详她,或是拉开门走近她,人也就精神清明了许多。遗憾的是,后来有一年,桂花树不幸被暴雪压断了树梢,自然而然地枯萎、死亡了,其时,我们一家人已经离开了老房子。但时至今日,我的记忆仍然难以抹掉它。若是非要究其原因,也许它见证了我在老房子里太多的日子之艰、创作之倦吧。
在卑陋的老房子蛰伏了6年,那个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有幸结束了自谋职业的生涯,被日渐景气的单位重新安排上班。看到儿子一天天长大,老房子更是拥挤了。还有一点,手头已有了一些积累,又感受到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年年上涨,我决定向亲戚们再借点钱提前实现买新房子计划。婆娘劝我再缓几年,但她最后还是“夫唱妇随”,选房子、买房子、装修房子,格外用心。第二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大地消瘦,青天红地,我们一家人住进了市中心一幢高楼大厦里,第一个告别了老房子夏热冬冷的居住史。新房子面积150余平米,三室两厅一书房,很宽敞,很阳光,楼与楼之间距离大,采光好,铝合金的玻璃窗,厚实的防盗门,客厅地面铺着瓷砖,卧室地面则铺木地板砖,大大的落地窗好像把房子里所有的温馨都拥在怀中。记得搬离老房子那个黄道吉日,隔壁邻居前来祝贺,赠送了一套精致的茶具,由衷地替我们高兴,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很真很真。婆娘倍感兴奋,感慨良多:“这几年因为有了他们,老房子人情味真浓啊。”千金买房,万金买邻,旨哉言也。老房子生发出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像金子般沉淀在我们的记忆里,至今难以忘怀。尤其是入住新房子后,新比邻一家子甚是清高,始终关系比较淡薄,让感受过浓浓邻里情的婆娘十分失落,愈加怀念具有人情味的老房子。
时光匆匆,物换星移。如今,熟悉的事物渐渐隐去,就连我老家大田院子的老屋也在逝水流年里倒塌了,散落一地的断椽碎瓦映照出一道心痛的记忆。同住一块的父母亲已是耄耋之年,鬓白华发,步履蹒跚,像失去水分的枯树衰朽了。高楼中的新房子也在朝朝暮暮的时光里老得深沉下去,失去了光彩照人的面目,不再显眼了。而整栋老房子只剩下两户老人家,其他住户都陆陆续续地搬走了,曾经的友好近邻也在10年前自建了房子。随着一户又一户的离开,老房子变得越来越冷寂、落寞了。我不知道离开的原住户们会不会还魂牵它?梦萦它?但我这么多年却一直在腰上挂着老房子的钥匙。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抽空打开房门清扫一下。只是每次走近表情寂静、脸上盘桓着圈圈皱褶的老房子,心海中便难免陡起层层波澜。它留存着我和婆娘的许多记忆,总是让我在里面会回到过去的日子,看到像奔腾不息的河水昼夜不舍地健行的生命活力,还有像糖浆般甜蜜蜜的亲情和邻里情。
老房子,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会被强大的机器拆除,旧貌换新颜,映入大家眼睑的是一座崭新大楼。但我们恒常的记忆犹在,遗留的日子痕迹犹在,沉积的精神和执念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