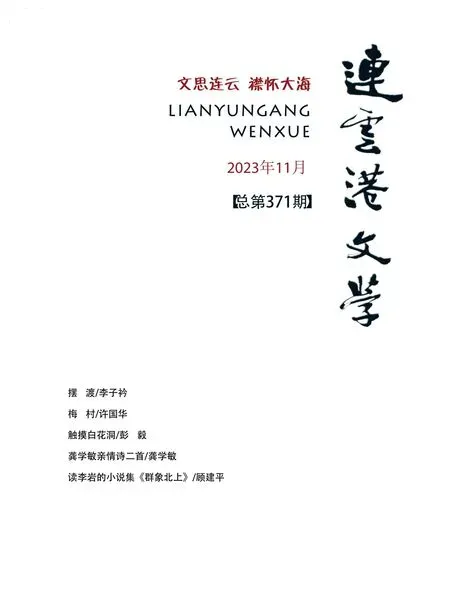触摸白花洞
彭毅
白花洞,地处深圳光明区的东大门,闻其名,已令人心驰神往。碉楼,似五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最美村落的版图上。
从观光路转入白花路,宛如坠入世外桃源,周遭的一切都“慢”了下来。远望,坐落于参天古树中的天后宫露出了金色的琉璃瓦顶,玲珑剔透,金碧辉煌。徐行,白花河(观澜河的支流)河畔,错落疏离的杨柳,临风起舞,温乎如莹。顺着村道而行,在这里能窥见:小桥、流水、农家的模样。河道中的几只白鹭,时而觅食,时而嬉戏,振翅,翩飞,荡起阵阵涟漪。或许,白花洞也是它们的家。
白花河滋润着白花洞村,也流淌着古老的故事。白花洞村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周氏先祖周礼茂夫妇率四个儿子由惠州迁徙至此,开荒垦田,聚族而居。因此处地形如木桶,易守难攻,得名“洞”,加之满山开遍白花,为风水宝地,且又是从惠州白花镇迁徙而来,为感念故土,故取名白花洞村,又名白花村。后因人口繁衍,分成了新围、马池田、地洋头、围肚、黄屋排、庙径口等小村落。白花洞村亦是革命老区。
白花碉楼与客家围屋
步入围肚一巷,入村,亦是入画。
小巷幽深,树影斑驳,天地肃静,古韵悠悠。走近一座颓壁残垣的墙体,高约4 米,灰白色的外墙上已爬满青苔,窗沿上布满了蛛网和划痕,炮楼似乎沉睡在岁月的静穆里,无怨,无悔。牌匾上标注有“黄屋排北炮楼,深圳市历史建筑线索”等字样。炮楼的旁边紧挨着一座完整的碉楼,高约20 米,身披岁月的尘埃,遗世独立。用手轻轻触摸雕楼那早已不再清晰的纹理,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凝视,遐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似有一股英雄气在炮楼与碉楼间飞扬。
古榕树、龙眼树、木菠萝的枝干旁逸斜出,枝叶错落有致地遮蔽了骄阳,也收拢了我四处张望的目光。穿越一片小树林,一步步踏入这已有300 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低矮的老屋、粗壮的古树、陈旧的小院、逼仄的古巷、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古色古香,清幽雅致。小巷两侧散落着不少客家围屋,斑驳的门扉,陈旧的窗户,像一本本被时光翻旧的书。几缕斜阳洒落屋顶,平添了几分空寂和古朴。风起,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总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究一番。
常言道,“未见客家人,先见客家楼”,漫步白花洞村,这种感受尤为贴切。不难发现,客家围屋多数是坐北朝南,依山面水而建,俗称“前有照,后有靠。”村落的后面有两座小山,一曰吊神山,一曰梅坳山,最高海拔为288 米。山峦叠翠,山势蜿蜒,和逶迤的白花河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河水揉抚着古老的村落,洋溢着别样的诗情和画意。把房子建于山水之间,顺应于天地,融合于自然,客家人是智慧的,更是虔诚的,真正做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城堡,遮风挡雨,防寒御敌。一代又一代的白花洞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把农耕文明、风水地理、中庸之道、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将围屋演变成历史的载体和文化的结晶。
遥望一座围屋,墙体中隐含着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屋顶由前向后次第升高,建筑由大堂、天井、横屋、围屋等部分构建而成。邂逅一座围屋小院,置身天井,体感舒适,心旷神怡。土砖、青瓦、木雕、壁画,都散发着客家人千百年来的人文气息。步入大堂,木制的梁、柱、门、窗、檐等彰显出浓浓的文化韵味,《礼记·月令》有云:“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古人认为在春天植树造林,是最大的功德。亦将木德比喻春天之德,谓其能化育万物。“木”亦象征着生命的欣欣向荣,蕴涵着蓬勃昌盛的隐喻,足见客家人对“以木为德”的文化的推崇和信仰。目光游离于木雕和壁画之间,精巧,灵动,传神。细细品读客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岁月的回响扑面而来,深邃,豁达,通透。
大榕树,是岭南村落的图腾。枝繁叶茂的古榕,撑起了一片天地,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万人欢。坐在石凳上的几位原住民用客家话闲聊着,大事小情,家长里短。男人们相互递一支香烟,妇女在冲泡着简易的工夫茶,凉风习习,笑声朗朗,悠闲。榕树,是当地人心中的吉祥树、风水树、乡愁树,是人丁兴旺的象征。大榕树也见证着白花洞村的历史变迁,成为村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求学归来的学子、荣归故里的乡贤,都会到榕树下转悠一番,或闲座或“吹水”或纳凉。与榕相依,与榕为善,白花洞人恰似开枝散叶的大榕树,守望互助,已繁衍成泱泱大族。或许,正是榕树下的这片小天地拉近了邻里间的情感,温馨而又和谐。得知我是来寻找碉楼的具体位置,他们疑惑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起来,“慢慢行,前边转左”。
小巷蜿蜒曲折地夹在两旁的老屋中间,向着村庄深处延伸。一座深灰色的建筑矗立眼前,沧桑、雄伟、庄严,这便是周氏族人所建的白花碉楼。建于清末民初,内部为土木结构,墙体的主要建材有黄土、石灰、河沙,再掺杂稻草、竹片等夯实而成。迄今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按照“修旧如旧”的修葺准则,主体结构保存完好,内部保留着原始风貌。碉楼呈四方立体形,下宽上窄,长5.4 米,宽7.95米,底层面积约43 平方米。每层侧面各开一扇窗,共五层,高约20 米。白花洞现存碉楼五座,分别位于黄屋排、围肚、围仔和马池田。依山环村而建,与周围的建筑相比,颇具几分鹤立鸡群的姿态。曾在枪林弹雨中锤炼,依旧气宇不凡,高瞻远瞩,傲视群雄。
驻足仰望,白花碉楼属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中式墙体门楣,西式顶层外廊,屋顶呈雨披状,博采众长,处处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碉楼南面有两个头朝下的“鲤鱼”雕塑,下雨时,屋顶的积水从“鲤鱼”口中倾泻而下。中西结合,既美观实用,又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建筑风格相互融合的历史。
俯首细观,伤痕累累的墙体、锈迹斑斑的铁门、青苔满满的窗沿,无不诉说着沧桑的过往和岁月的无情。灰尘、铁锈、蛛网,掩盖不了碉楼曾经的光辉,它携带着一身的故事,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在风起云涌的乱世,多少楼台烟雨中?曾经为族人们遮风挡雨的碉楼,现在人去楼空,在青山绿水间兀自凸起,孤独而又美丽。白花碉楼仿佛是一位沧桑的老者,在历经狂风暴雨后静静地守望着世事变迁,更像一位执着的史学家忠实地记录着白花洞村那些逝去的光阴。
时光蹁跹,岁月倥偬。枯叶卷起昨日的繁华,白花碉楼在旧故里突兀而起,独享一份孤芳自赏的寂静,了无悲喜,尤为动人。
周氏宗祠
依山而建,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堂,在白花洞村愈显厚重。
行至围肚四巷,一座灰墙青瓦的祠堂映入眼帘。据说,这座祖祠是周公的二儿子绍岐所建,为三开间两进深的布局,占地面积约120 平方米。祠堂内立有祖先牌位,逢年过节,族人们都会来此上香祭祖。“绍岐祖祠”的牌匾高悬于门额,斑驳的门檐上壁有人物彩绘,依稀可以读取到这里的过往。大门楹联“绍廉汝学;岐凤潮阳。”大门紧闭,轻叩木门上铜制的铺首,心头微漾着欣喜。每座祠堂都有自己的故事,心存敬畏,不忍惊扰。
“追远溯本,莫胜于祠”。客家人作为迁徙的民系,对故土饱含眷恋之情,他们崇尚祖制,遵循孝道,发扬优良传统,在思想观念上追记先人的恩赐,缅怀先人和故土。漫步白花洞村,祠堂文化的情愫尤为浓烈。穿过一条麻石板铺成的小巷,西南面一座岭南风格的祠堂映入眼帘——周氏宗祠,两侧雕刻有楹联:“汝高世德常兴业;南宗枝茂长发家。”祠堂为三开间两进深一天井的布局,岿然伫立的木柱,似先祖的脊梁,支撑起一片天地。精雕细刻的木雕,栩栩如生,寓意深远,奔涌着修身齐家的情怀。
置身天井,似有一股浩然正气萦绕身旁。移步后堂,香火旺盛,祖先牌位两侧刻有楹联:“凤起岐山鸣圣代;遂开廉水毓文人”。上联源于“岐山凤鸣”的典故,《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韦昭注:“鸑鷟,凤之别名。”凤,意为凤凰;岐山,为周朝发祥地,也预示着周氏的起源;凤起岐山,意为“周”在“岐山”兴起。下联“遂开廉水”中的廉水河位于今陕西省南郑区,《水经注·沔水》载:“廉水出巴岭山,北流经廉川,故水得其名。”“遂开廉水”寓意周氏曾在廉水开枝散叶,辐射四面八方。“鸣圣代、毓文人”,表达了周氏族人致力于培育高尚情操和崇高理想的精神追求。
祠堂是村落的核心,是族人灵魂的栖息地,流淌着故园往事、人文理念和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望着重新修葺的周氏宗祠,我想,这应该是民间文化开出的灿烂之花,一种高贵的信仰在清幽平宁的院落里升华。
围肚水井
在围肚巷,除了穿梭而过的风,一切都是不慌不忙的样子。
沿着小巷往回走,下坡。一位骑着三轮车运水的大叔,把“水满则溢”的哲学演绎得淋漓尽致,车轮碾压出的“水路”把我引到了井旁。
围肚水井,呈六边形,由青石板堆砌而成,井沿长出了杂草和蕨类植物,井口用铁丝网覆盖。与阿叔交谈,他说这口井曾是这一片区的主要饮用水源,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白花人,从未枯竭。大家都用上自来水了,或许古井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功成归隐。井内的铁丝网,似乎阻挡不了白花洞人对水井的眷恋。不少老人经过古井时,总会探出身子,望向井内。或者沿井边走几圈,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似乎要与昔日的老友诉说一番。
水井是大地的眼睛,盛满着苍天的泪,也饱含着大地的情。亲近围肚水井,明净,轻盈。井栏上的绳索印痕依稀可见,我未曾读懂它的过往。或许,“大爱和永恒”的秘密全部藏在时间里。掬一捧清泉,洒在我的脸上,好生清凉,似乎闻到了草木的芬芳。掬一捧清泉,洒在白花洞的土地上,好生惬意,细水长流。
我望着清澈的井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围肚水井似一位咽苦吐甘的母亲,为脆弱的村庄而撑着。再望向巍然耸立的碉楼,他似一位百炼成钢的英雄,为最初的渴望而站着。楼与水的合力,刚柔并济,护佑着一方热土,这里的人定然是无比幸福。天道轮回,是否到了我们该去守护碉楼和水井的时刻?
与水井相依的还有菜地、农田、山林,龙眼树下一个编号为NO.SZ12004 的界桩,似乎在宣示着什么。在深圳见到“基本农田保护区界桩”,着实令人心头一怔。放眼四顾,满园欣喜,茄子、豆角、辣椒、玉米秆、魔芋苗,长势喜人。戴着草帽的农人,或浇水,或锄草,正与他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原生态,纯天然,青山绿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词源源不断地汇入我百感交集的脑海。不时会冒出一句,这是在深圳吗?这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或许能让我更深刻地去理解历史、经济、生态与文化的多层含义。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商业文明。发展需要“深圳速度”,发展也需要“深圳历史”。若想读取深圳的过往,白花洞的生态环境,无疑是最贴切的版本。
我时常在都市与乡村间奔走。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确有其好。静想,一座城市更需要一些原始的元素,比如老街、老城区、古村落,古井、旧房子、旧城墙、旧物件,它们是岁月沉淀的光华。留一缕足迹,留几条雨痕,留几扇斑驳的木门,或许有人能读懂它们最初的语言。
回望。围屋、水井、基本农田保护区界桩、菜地、芭蕉树、荔枝林,与碉楼相映成趣,宛如浑然天成的农耕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