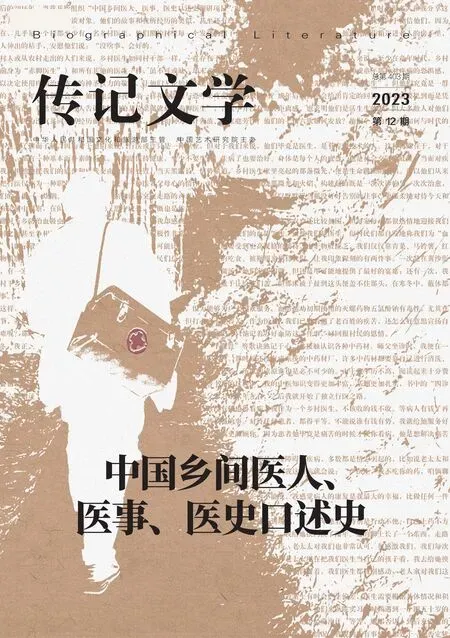在中国当代思想语境中重新讲述王安石的故事
——邓广铭四写王安石
卢燕娟
1997 年,九十高龄的邓广铭完成了他一生中对王安石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书写。3 月9 日,在修改整理完稿之后,他写下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的“序言”。之后不到一年,1998 年1 月10 日,邓广铭与世长辞。
回顾这段“四写王安石”的历史,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1 年,正当盛年的邓广铭开始第一次写《王安石》,这本107 页的小册子,以和它厚度成反比的锐气和激情,讲述了一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年轻进取的王安石,同时也是一个作为“改良主义者”的王安石;到1975 年、1976 年在“儒家”“法家”的时代话语下,邓广铭经历了两本反复增删、修改充满了时代色彩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艰难问世,讲述了一个从经济改良主义者走到更成熟的“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直至以九十高龄,在生命的终点来写这本《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邓广铭,从“序言”到篇末,反复引用苏轼“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的评价来书写一个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追求中达到了极高境界而身后遭受一千多年寥落寂寞不公待遇的王安石。而在这第四次书写王安石之前,邓广铭撰写了诸如《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1]等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章,其中的很多思路和成果,都在1997 年所写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融会体现。可以说,对王安石变法故事的书写几乎绵延在邓广铭从盛年到暮年辛勤治学的半生时光中。
而尤其令人感慨的是,邓广铭在自己生命接近终点时对王安石所作的这次书写,于结尾处增加了前三次书写所没有的一节:《身后的冷落》。1951 年的《王安石》,写到新法尽废,“从开封府传来的种种消息,无一不在加重王安石的病况,使他忧心如焚,无法排遣。到四月初六,这个六十六岁的老年人便与世长辞了”[2]。全书便也终结于此。或许,对四十出头的邓广铭来说,人生走到“与世长辞”,便是彻底的终结了。而小半个世纪的人世沉浮历史沧桑过去,走到自己生命也逼近尽头处的邓广铭,却对王安石身后的冷落,有了更多沉痛苍凉的感慨:
写到这里,我很想再插入我自己的一段感慨,是久已积存在我胸怀中的一段感慨。……然而除此之外,由于司马光正在“以母改子”的借口下,大力贬斥熙宁元丰期内参与推行新法的各级从政官员,这种严峻局势使得王安石的故旧全都畏罪不暇,谁敢再出面冒此风险?遂致前来祭吊和赠送祭品赙礼者也绝少,出现了张舜民《哀荆公》诗中所描述的“门前无爵罢张罗,元(玄)酒生刍亦不多”的凄凉场面。……埋藏在王安石坟墓中的,只是一块“墓碣”,亦即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这就更令人感到他身后所受待遇实在过分的凄凉了。[3]
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面对历史中灿若群星的人物,用前后四十六年、将近半生的时光,如此反反复复、如此不知疲倦地来书写同一个人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能够从一个人意气风发的盛年绵延到他生命将要落幕的终点,让他始终如此执着地选择同一个人物来负载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探索和追寻?甚至,直至九十高龄的第四次书写,仍对传统历史叙述给王安石变法的待遇充满强烈的不平而难以释怀,不仅在全书最后特别增加《身后的冷落》一节来寄托自己的愤激感慨,而且还满怀激情地表示:“对于这样一些荒唐谬悠的记载,是极应予以澄清、加以纠正和批判的。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全未涉及。但愿今后能有机会,再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写一些补充的篇章出来。”[4]笔者相信,若天假以年,这本《王安石》仍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书写。
在1997 年本的“序言”中,邓广铭对自己第四次写王安石的动力作了这样的回答:他认为,有宋以来的传统历史叙述,充满了对王安石的诬蔑和诽谤,至蔡上翔及以后的梁启超,立志为王安石辩冤,但由于史料掌握得不够充分尤其是缺乏科学的治史思路而未能进入历史的本质层面去把握历史,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诸如他的学生漆侠的王安石研究,“对于驱动王安石变法改制的核心力量,以及对于王安石厉行变法改制的思想、心态中最为本质的东西,把握得仍不够准确”[5]。
这样的自述表明,让邓广铭穷半生精力,付出四十六年的宝贵时间,反复四次而不疲的叙述动力,在于对历史本质的“准确把握”的不断接近。那么,伴随着这样的叙述动力产生的下一个问题就必然是:邓广铭的叙述在什么标准和意义上界定并使用这一“历史本质”?简言之,即他穷半生经历所追寻的“历史本质”是什么?而他又从哪里获得一种自信力来确认他所追寻的这一“历史本质”的合法性?
既然在邓广铭的讲述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准确把握”历史本质的不变的叙述动力,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需要我们追踪邓广铭每一次不同的书写,通过披拣他每一次书写与前一次相比,是在什么问题上有所增加、有所删除或者有所改变,去发现他在对什么问题作锲而不舍的探寻和反反复复的思考,一次又一次重新给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一让他倾半生经历反复纠缠的问题,自然也就是他所立足的“历史本质”,而在这样的追寻中,抑或可从中找到邓广铭对这一“历史本质”信心的来源。
1951 年,邓广铭初写《王安石》,开篇第一段话即指出:“赵宋政权的产生,和西汉与李唐不同,它不是农民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一项产物,而是以阴谋诡计从后周皇室中夺取了来的。”[6]这一“不同”贯穿了邓广铭在这本《王安石》中对所有历史问题的判断,因为不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赵宋政权与同是剥削政权的其他王朝相比,更加不懂得对农民的经济政治要求作最低限度上的让步,因此造成了格外严重的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和政治腐败;也由于不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与农民之间甚至没有经历过最初的结盟关系,导致它尤其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而加以防备,造成对内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化与对外防御力量的空前弱化这样互为因果的局面,这样空前激烈的阶级对立不仅产生出王安石变法的必然性,也决定了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必然命运。在1951年的初次探索中,邓广铭找到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与农民阶级空前尖锐的对立作为“历史本质”层面的答案,来回答为什么会有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为何会失败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立,在1951 年的《王安石》中,首先和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上的对立。邓广铭特意指出:“和赵顼之只为求取富国强兵的效果而要求着政治改革的见解有别,王安石的改革计划的主要部分是建基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之上的。”[7]从这一判断出发,邓广铭此次的叙述重点,放在王安石变法对过度阻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落后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上,并且在对变法的总评价中指出:“在富国强兵方面所得的成绩,还只可说是新法的副产品。新法的重要效果,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从推动社会前进方面着眼,王安石的新法是确有其一定程度的贡献的。”[8]这样的评价向我们显示出,1951 年邓广铭视野中的王安石,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尖锐的经济对立,以及这样的对立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作用,而由这样的主要矛盾决定,1951 年邓广铭笔下的王安石在历史舞台上必然扮演一个经济改良家的角色。
1972 年,毛泽东同志以王安石“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称赞打破冷战封锁来华访问的田中角荣,多少有点偶然性地造成了邓广铭二写王安石的历史契机。而当时全国学术界正在上演“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一幕,邓广铭的这次重写亦因当时权威话语要求,以“儒法斗争”结构变法派和保守派之争,反复修改审查之后,到1975 年才获出版,而仅一年之后,“四人帮”粉碎,出版社要重印此书,提出要他加以删削和修改的,正是此前指责他所缺乏而责令增加的“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文句和段落,于是又有了1976 年的三写王安石。
然而,如果剥去这两次书写所遭遇的诸如“儒法斗争”这样的时代外衣,我们仍能找到邓广铭不变的叙述动力:这两次除了“儒法斗争”语句的增删没有太大差别的书写,和1951 年的《王安石》相比,最显著的改变是增加了开头第一章《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而在这一章中,从 1951年本中被笼统表述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与农民阶级空前尖锐的对立的观点进一步深入,指出北宋王朝所面临的三大主要矛盾:
一、民族矛盾,即与契丹贵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辽和党项贵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西夏之间的矛盾;
二、阶级矛盾,即广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内部关于权利和财产再分配等问题的矛盾。[9]
而这三大主要矛盾的把握,不仅是对50 年代所把握的北宋主要矛盾具体化,而且还是在50 年代所发现的北宋经济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矛盾。换言之,进入70 年代,邓广铭的叙述重心上升到了政治文化的矛盾层面。叙述重心的转换导致了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由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转移到了“富国强兵”上,当然这一判断里包含着对当时“批林批孔”、提倡法家的时代话语的应和,但是笔者以为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邓广铭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解的深化上,因为这一主要矛盾在这次叙述中不仅完成了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的回答:邓广铭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互相牵制决定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同时也回答了何以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是落后的、卖国的而法家是进步的、爱国的时代判断,这样的回答暗示着邓广铭的思考是从对社会矛盾的判断出发来应和所谓儒家和法家的划分,从而把“儒家”“法家”这样被时代话语要求的能指放入自己的判断叙述中,其所指才因此变得非常微妙,而不是相反以儒法划分为前提去揭示社会矛盾。所以用“儒家”“法家”所指称的变法派和改革派,本身包含着邓广铭在时代共名中对历史所作出的自己的思考和回答,也决定了被称为“法家”的王安石在这一次书写中的政治改革家角色。
至1997 年四写王安石,一个最显著的改变仍发生在开头这一章,在70 年代作为主要特征增加的《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被整章删除,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章节,正如其再传弟子李华瑞指出,这一变化“大致反映了邓先生自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10]。与此同时,对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70 年代的“富国强兵”的概括之外,增加了“富民”一项。联系邓广铭在这一版“序言”开篇的自陈:“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11 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11]
所有这些改变显示出,这一次书写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进行的,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防御力量的增强。对王安石变法措施意义讨论的重心,也由50 年代、70 年代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缓和阶级矛盾的努力移向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效。
可以说,邓广铭笔下的王安石形象既伴随着他自己,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个人学术生涯和人生境遇的悲欢荣辱,也见证并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半个世纪中的大历史的升沉变迁。而从50 年代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关注,到70 年代从政治文化层面对社会矛盾的考察,到90 年代对国民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邓广铭每次对王安石故事的重新讲述,都贯穿着他通过王安石的时代对自己所身处时代处境的一次重新思考和把握;而每次对王安石时代主要矛盾的回答,都回应着他对自己所身处时代的主要矛盾的一次重新判断。而从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努力方向出发,来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从而进入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就成了邓广铭四十六年来四写王安石那些前后不乏相互驳诘辩难的历史叙述中,永恒不变的叙述动力。
正是这一不变的叙述动力的存在,使邓广铭所书写的王安石,获得了联通当代中国处境的可能性——诚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邓广铭的王安石叙述由此可以在接近文学的意义上被讲述成三个故事:解放的故事、翻身的故事、富裕的故事。
一、解放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述于1951 年,从旧中国千疮百孔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百废待举的局面。在广大农村,尤其新解放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远未完成,农民仍然处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剥削中。毛泽东同志在1950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局面是:
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的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12]
而在这一切问题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3]
同样,农民和与农民密切关联的土地问题,也是中国建设的主要问题。正是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判断出发,1951 年,邓广铭书写了一个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异常尖锐的经济冲突上的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北宋农民所承受的来自封建国家和封建统治者的严重经济剥削是他叙述的重心,而作为封建经济关系核心的土地问题也就成了他关注的焦点。
1951 年的王安石在正式上场之前,就先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准备活动中看到了自己将要进入的是这样一方历史舞台:“中下等的农户总是非常贫困的,他们经常地处在官僚豪绅、大地主和富商大贾们的欺凌压榨之下。”[14]而王安石的主要任务就是疗救这一社会病症,为此,他开出的药方是井田制,而邓广铭对井田制的阐释是:“在纪元前一千多年时,西周曾实行过井田制度,每个农民都从政府分得一些土地,每户人家都可以丰衣足食。”[15]
因为土地问题不仅是邓广铭在这次书写中的焦点,也是贯穿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井田制”本身也是王安石变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土地政策参照,更成为后人对王安石变法故事讲述的一个阐释热点,所以在此需要对“井田”一词从其历史渊源中略作追踪:
“井田”一词,最早见于《春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其云:“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其“井地”,即为“井田”。……20 世纪20 年代,胡适作《井田辨》,提出井田的均产制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未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对此说,今世学者多认为其疑古太过。实际上,“井田”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就现存古文献资料分析,中国古时曾存在“似井之字”的田制是不能否认的。[16]
一般认为这是西周的封建领主制剥削方式。
这种剥削方式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权,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庶人(农奴)无土地权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剥削的义务。具体剥削方式,是贵族们将田地分为两类,一类为贵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属农奴们集体无偿代耕,就是劳役地租。另一类大致以百亩为单位分给农奴各家耕种,收获物归农奴所有。[17]
春秋时期,周天子对土地的控制力已几乎完全丧失。诸侯们对他们封国内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对于人民的占有权也是这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原则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新的原则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一原则的改变,是土地国有制破坏的标志。从此,天子不能控制“天下”的土地,诸侯也不能控制封国内的土地,贵族们也无力经营管理他们所分到的井田。有权有势的人,强占田地为己有,不少农奴逃跑,到边远地区开荒耕种。……至此,井田制在迅速破坏。[18]
从这段简略的追踪中可以大致看出,历史上所存在的井田制,是一种土地为君主/国家所有的制度,因为在西周时代,君主和国家(天下)基本是一体的概念,庶人(农奴)在井田制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土地权利。而邓广铭在此将井田制阐释成“每个农民都从政府分得一些土地,每户人家都可以丰衣足食”,以邓广铭治学严谨扎实的作风而言,这显然不会是一个无心之失,因此只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叙述策略:邓广铭在此模糊了西周之“国”所包含的君主一家之天下的意义,而将其置换成“政府”:通过这样的置换,所突出的是井田制的土地国有性质,而这样的土地所有制是能将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生产关系的解放中获得生产力的解放的土地所有制。从而,王安石变法故事中所讲述的那个“每个农民都从政府分得一些土地,每户人家都可以丰衣足食”的井田制理想、那场怀抱着这个理想,虽然不能在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真正实现土地国有,但是通过兴修水利、改变税制、发放青苗贷款以打击豪绅兼并等为中下层农民尽力谋求福利的改革,以及这场改革要实现的“是要社会经济不再作畸形的发展,使赤贫和豪富在社会上两俱绝迹”[19]的总目标,就在实际上寄托了一个通过让人民一定程度的均贫富,获得生产关系中的有限解放,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一定程度的解放的理想。这个理想在时代局限和王安石本人出身局限的双重局限下,最终呈现出一个朝向进步的改良主义行为。所以邓广铭在50 年代给王安石的定论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对这个故事的解读,需要回到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未来经济道路所作的判断中来理解:“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20],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在经济方面的判断:“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21]。
二、翻身的故事
在讲完经济解放的故事的二十多年之中,邓广铭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处境的思考和追问,不断发展和升华。于是,70 年代,在儒法之争的时代话语外衣下,邓广铭重新用王安石讲了一个追求人民政治翻身的故事。
如上一节所分析,邓广铭首先对在50 年代笼统一分为二的社会主要矛盾有了进一步深入化、细致化的认识,进入矛盾错综复杂的内核,从这一更加深入细致的认识出发,他书写了一个比1951 年那个凭着“三不足”精神包打天下的王安石更加深沉、更加复杂,也更加有悲剧色彩的王安石。这个70 年代的王安石,要通过变法实现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协调社会贫富,而是“富国强兵”,而这一在当时的时代话语中被判断为“法家政治理想”的改革目标,邓广铭其实在叙述中赋予了它更为复杂深沉的内涵。
首先,就“富国”而言,邓广铭在这一目的层面强调了王安石“国用可足,民才不匮”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富国”的理想包含了50年代对人民经济解放理想的书写,但同时,邓广铭在王安石的“富国”理想中,进一步强调的是王安石“理财为方今先急”“理财以农事为急”,而农事的当务之急在“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的变法逻辑,把对农民的关注放在了首要位置。
接下来,对“抑兼并”之举,邓广铭进一步发掘出其在调节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意义以外的政治意义:以青苗法为例,邓广铭首先指出这是两个阶级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进行的斗争,而斗争中,他又通过王安石面对反对派的攻击,进行反驳时所说的“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一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反驳中所包含政治文化上的意义:“王安石不把庶民看作群氓,而却强调说,人民‘合而言之则圣’。”这里体现了王安石对“民”在国家权力中的话语权的认识和尊重,从而赋予了围绕新法的斗争以鲜明的政治文化意义。也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邓广铭回答了何以“受到守旧派人物的攻击最猛烈,进行攻击的人数最多,次数也最多的,莫过于青苗法”的原因:正在于此法“起到了王安石所说的‘以其所谓害者治法而加诸兼并之人’的作用,亦即‘抑兼并’的作用”[22]。对兼并的裁抑,在这里已经由经济意义上的斗争,升华到涉及国家权力中的话语权、立法权的斗争。
其次,就“强兵”而言,邓广铭一方面指出王安石“保甲法”是为地主阶级加强对劳苦大众阶级镇压力量的措施;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以民兵取代募兵的做法,与“司马光之流为求维护其豪绅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是把此外的一切全都置之不顾的。他们不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经常视若寇仇,严加防范压制,对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稍有好处的事也是拼命反对的”[23]的顽固大地主阶级立场相比,王安石把人民由国家的潜在敌人变为可以依靠以御外侮的力量的做法所体现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的判断标准在于人民地位的相对上升,由此揭示出围绕这些措施的斗争所体现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政治意义。
而在这次叙述中,邓广铭立足于对三种矛盾复杂交错的时代特征的把握,还作出了一个判断:
当时各地人民反对北宋王朝统治的斗争,是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因素在内的。因为,来自北宋王朝的残酷的政治经济压榨,其中是包含着民族压迫的成份在内的:每年输送给辽和西夏的近八十万匹、两的“岁币”,不正是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假手于北宋王朝而向北宋境内人民索取的吗?[24]
这一判断的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三大矛盾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在于从三个互相联系的矛盾出发,赋予了王安石所进行的改革在50 年代的叙述中所具备的为人民的经济解放所作的改良主义努力的意义之外,面对国内的反动政治势力和国外的侵略势力,站在接近人民(当然不是完全等同)的立场上,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政治意义,完成了从50 年代经济改良主义者到70 年代政治改革家的形象升华。在70 年代的叙述中,邓广铭特意更正了50 年代的判断,“是政治改革家,不是改良主义者”[25]。
正如美国人韩丁在考察中国这一段土地改革的历史时对“翻身”一词所作的诠释:
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26]
邓广铭70 年代的王安石故事呈现了这一从经济解放到政治翻身的发展和升华。
三、富民的故事
到1997年,如上一节所指出的,随着中国历史行进到改革开放的时代,邓广铭又站在新的历史中作出了新的判断。“富民”,成了他这次所讲述的王安石故事中最富有时代特征的叙述。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在此被表述为“富民、富国和强兵”[27],“富民”不仅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判断出现,而且地位被置于传统的“富国强兵”判断之前,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1951 年和70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的故事中,邓广铭都曾引用王安石《与马运判书》中“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来叙述王安石的理财思想,问题在于,前面的引用和阐释,都立足于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懂得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在“义利”观上更体现出法家不讳言利的务实色彩,而这一次,邓广铭赋予了“天下”以全新的阐释:
这里所说的“天下”,实际上乃是指天下百姓,这从他《答司马谏议书》中的“为天下理财,不为争利”句可以得到证明。……治国者必须先以天下的人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以使百姓富足(即所谓藏富于民),然后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依循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王安石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和他所期望实现的“富民”与“富国”,才能得出最正确的结论[28]。
联系“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时代主旋律,这段文字清晰地展示了邓广铭是如何将“富民”与“富国”的立场相融合,从而在“富民”的意义上赋予了王安石变法故事以新的时代意义。
在1997 年的最后一次书写中,九十高龄的邓广铭,面向他所亲自走过的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历史,深沉而痛切地讲述了以前任何一次讲述中都没有讲述过的王安石统一中国,恢复汉唐旧境的梦想:
这次改写,我又把王安石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议论更多地举述出来,并改换为《王安石统一中国(意即恢复汉唐旧境)的战略设想》的标题。据我暗自估测,翻看这本传记的读者,必会有人感到惊异,认为,自宋太宗到宋仁宗,不论对契丹或对西夏的作战能力,都已出现了“积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出吞灭契丹、西夏的建议,那只能是一种梦幻语言。然而我却以为……王安石的这种设想,虽再三再四地见诸他的言论,却始终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包括宋神宗那样极关重要人物的同意,这却只能说,那是由于传统势力和失败主义思潮还都十分强大,而并非因为在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形势上全都不合时宜之故。[29]
这段叹惋放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更有一番令人扼腕之处。1840年以来,现代中国与邓广铭笔下的北宋,都共同陷入一段失败的历史。所以邓广铭对北宋历史的思考,也就是他对20 世纪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思考。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让我们理解:在邓广铭四十六年的叙述中,人民的解放就是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的富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意愿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这一切最终与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在终极意义上高度一致。这一叙述逻辑绵延在邓广铭历经四十六年、四次书写的王安石变法故事中,始终不变,显然已经成为他一个执着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