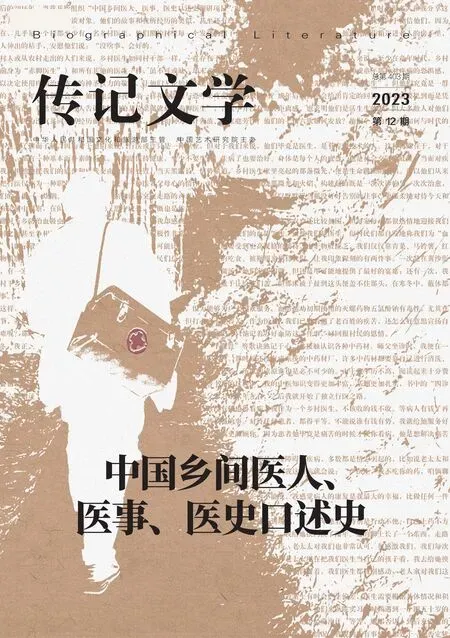严向华:一名基层乡村医生的日常
严向华/口述 陆又沁 严一明/整理
从医:露宿整晚 幻想成为医生
从1999 年算起,我从医已经24年了。1999 年,我从周口卫生学校(现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毕业以后,去扶沟县人民医院实习了一年,然后开起了个体诊所。说到当初为什么学医,这和我患病求医的一段经历有关。我生活在豫东地区的农村,1991 年上初中的时候,每年到春节放年假,村委会就会放露天电影。农村放电影就是搁在大街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农村小孩兴奋激动地乱跑,有一次跑出汗之后又淋了一场大雨,再长时间蹲在屋檐下看电影。到了第二天一早我腿就受凉了,疼得无法行走。
父亲领着我去看病。一开始先去村卫生室,村卫生室看不了;去镇上,镇上也看不了;只好去县上,县医院当时设备不齐全,只好又跑到市里的医院去看。检查完之后,医生怀疑是受了大凉(即风寒)。路途艰难,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农村的拉车子。从村里到市里需要走80 里地,父亲拉着我往返于各村之间,辗转送我去周口市看病。为了凑齐医药费,父亲东拼西凑借钱,甚至卖掉了自留地里长了多年的杨树。我还记得看病那天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到了周口市,医生已经下班了,我们在医院外头露宿了一晚,第二天才见到医生。那时候没有什么检查的仪器,医生只是怀疑我骨膜受了凉(现代医学叫筋膜发炎)。医生诊断完,我在医院输了一个星期的水(即输液),然后做牵引、口服中药、用药泡脚,治疗一个多月后才回家。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在农村看病有多难,条件不好,还得跑到大医院。从那以后,我重回到乡村中学读书,就开始幻想自己能成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
等到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教师,去西华县师范学校读书,可我坚决要去周口学医,因此和父亲闹了很大的矛盾。我开始用绝食反抗,一连躺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等到父母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偷偷爬起来找点东西吃,之后又躺回床上。母亲拗不过我,向娘家人借了去学校的路费。那是我第一次坐大巴去市里,只用了一个半小时。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拉着我看病那天用了整整一天!来到周口卫生学校,我读的是当时国家定向招收的社区医学专业(社区医学是研究如何维护和促进人群健康的医学学科),这个专业是为将来农村发展成社区以后,为社区卫生服务作准备的。虽然凑齐了路费,但5000 块钱的学费对我的家庭来说实在难以负担。直到毕业,我也只交上了一半的学费。等到工作之后把学费凑齐,我才拿到毕业证。
卫生学校跟初中是一样的,白天上课,还有早晚自习。那时候,卫校课时压缩得比较多,学时短。比方说,原本有160 个课时,大概就压缩到80 个课时,或者100 个课时,快速地给我们讲完,让我们先记先背。老师说,等你们以后进入社会,参加临床实践的时候,再慢慢理解就好了。也就是说,卫生学校所学课程很多,但都不够深入。
第一年我们学习语文、英语、数学、生物学、化学,值得一提的是,化学是生物化学。下学期开始学习“三理一剖”,就是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解剖学。后来学“内外妇儿”,就是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还有护理基础学、免疫学、皮肤科学、伦理学、心理医学,等等。又比其他临床专业多了一个中医,学中医基础学、中医方剂学、中药学。这样的课程设置相当于现在的全科医学。在农村,像上呼吸道感染、腹泻,还有痢疾,这些都是地方病、常见病。我考虑到农村小孩疾病比较多,所以在儿科领域下功夫最深。
到了周末,就有一名姓穆的老师来作短期培训,给我们上两节中医针灸课,毕业了还给我们发结业证书。参加工作之后,我又跟着当地的一个针灸比较有名气的大夫学习了半年。我们在学校学理论的时候,老师要求两个学生对扎,就是你扎我的穴位,我扎你的穴位,这样来找感觉。有时,老师还会带我们去沙河河堤采中药,教我们认识中药。
行医:病人康复是最大的幸福
刚开始行医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病人找我看病。有时候一天也就来一两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泄劲,这学好了一身技术,却无用武之地。我躺在小床上,唉声叹气,甚至想继续回去帮父母种地,当时我的媳妇就对我说:别泄劲儿,慢慢来,等到你能看好一两个病人,他们就会给你作宣传,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你看。2003 年年初,“非典”疫情暴发,我所在的行政村有大量从京返回的务工人员,他们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去北京卖花子(即绿植),到了农历三月再回村。这是我们村很多人的谋生手段。大量的人从北京回来,虽然各个村口都有人值班把关,但是村民依然很紧张,甚至发烧了也不敢去医院看病,这个时候就有些患者开始找到我了。我坚持看医学方面的书,一边接触患者,一边查阅资料。白天看病,晚上学习,后来患者越来越多,他们一个传两个,包括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都在帮我介绍,说严医生看得不错,收费少,说话还和气。这些患者大部分是农村的,也有县城的,还有在市里的。
患者越来越多,从早上7 点到晚上10 点,我都在接诊,中间甚至没有休息时间。那些年开诊所的还很少,我就住在诊所,不分昼夜地干。晚上有人打电话,也要出诊,去患者家里给他看病。晚上一般都是发高烧、急性胃肠炎这些情况。患者来不了医院的,我就拿着医药箱,带上药,去扎针。遇上特别严重的病人,我就去给他们输水,等他们输完水了,病情有所好转,再带去卫生室观察。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我晕倒在诊所,才意识到必须要转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现在,我每天早上5 点半起床,洗脸刷牙,喝点水,再到公园去转转,或是到沙河去游泳。锻炼完之后回来洗洗脸吃完饭大概7 点半,就开始准备工作,中午休息两小时,晚上8 点准时下班。
就这样几年之后,有了一定的积蓄,我的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说到收入,之前我们个体诊所都是自负盈亏的。到了2010 年左右,参加新农合之后,政策规定要进基药,实现零差价,就是医疗药品进什么价卖什么价,老百姓得到了大实惠。我们的收入就靠政府补贴,由国家承担起来,补处方费、诊疗费,一个月报补一次。但事实上,新农合也给基层卫生室、个体诊所带来一些压力,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入网、交报表,但愿意到基层工作的医务人员并不好找。那个时候,政府还给我们每个卫生室、诊所配备了一体机、诊疗床和血糖检测仪,这都是政府补贴的。另外,政府为了更好地给老百姓作健康服务和宣传,还筹建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督导我们定期上门服务,给群众作血压、血糖的检测,一个星期去几次,然后再上报回来。我们通知老百姓,让他们去社区服务中心作体检,这些费用都是政府补贴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我自己就是一名签约的全科医生,这些签约的居民们大多是老年人、困难人群和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他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之后,我们不仅会一直保持联系和沟通,还会有很多医疗服务,比如说一般的诊疗服务,还有一些血压、血糖这类的检验项目。最主要的是,有很多患者行动不方便,我们可以到他们家中治疗、护理。过去老百姓看病要跑很远,今天很多人足不出户就能看得到病、看得好病。而且,有的病如果控制不住,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绿色通道,转诊到上级医院。
最初行医的时候,病人主要得的是季节病和地方病。每年春夏交接、四五月份,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上呼吸道感染、湿疹、荨麻疹等,这都属于常见病、多发病。到夏季和秋季交接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季节病。夏天里消化不良、饮食不卫生,就会出现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急性胃肠炎。夏天中暑的病人比较多,到了立秋之后会出现秋季腹泻、肺炎。秋季跟冬季交接的时候,流感来了。平常没有流感的情况下,还会有儿童发烧、受凉的情况出现。
我们这最常见的病是幼儿急疹,6 个月到一岁的儿童,患这类病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手足口病、腹泻。幼儿急疹是最令家长心情急躁的一个病,因为儿童会出现反复高烧,一开始烧就是38.5 度到39 度以上,吃退烧药也退不下来。特别是头两天的时候,这个高烧是反复的,即使是喂布洛芬,体温也只会降到37.5 度到38 度之间,不会落回正常。家长非常着急,会反复打电话问你。到第二天,发烧的间隔时间会拉长,七八个小时烧一次,当然体温还退不到正常水平,那个时候家长会更急。到第三天的时候可能就12 个小时烧一次,比第一天、第二天的病情有所缓解。这种情况我会耐着性子跟家长反复讲:不用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是一个过程。这种病我见了很多,只要按医生的叮嘱用药,三天之后疹子一出,烧就退了。整个病程就是三到五天,90%的病人三天以后就退烧了。烧退之后,孩子身上的皮疹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过个两三天,皮疹一下去,病就全好了。孩子病好了,他们的父母还会给我打电话,说“严医生,太感谢你了”。
现在看病比以前方便多了。有了微信,我还可以在微信上给患者看病,方便和患者的交流。患者可以在微信群里跟我咨询问题,我一一解答,让他们自行买药,还能科普一些医疗常识,比如换季时的注意事项。另外,我还可以用微信打视频给患者看病,这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病患,像新疆、海南等地。他们本身是周口人,去外地之后,他们的孩子有病了还给我打视频,让我看舌苔,交流症状。我在线上诊断,他们再根据我的处方去拿药。这个比过去没有微信要方便多了。
我长期生活在农村,过去老百姓看病太困难,我自己就是个例子。但是百姓没有钱也得看病,我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不该收的钱不收。等病人有钱了再给,实在紧张,不给也就算了。我从内心发觉到,行医是个天地良心、行善积德的事。对待任何患者,都得平等。不能说谁有钱有势,我就给他服务好一点儿;患者没钱了,我就对他另一种看法。我都是平等对待的,甚至你没钱我更照顾你。因为患者他毕竟是痛苦的时候才找你看病,他是想解决痛苦的。
抚今追昔,将近百年的发展,新疆哈萨克小说在不同的题材、丰富的生活故事文本及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探索和尝试,将小说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创作了诸如《车祸》《额尔齐斯河小调》等经典之作。当然,从当下人文教育的视角及社会价值的转变来看,怎样实现文学教育功能的最大化,怎样开拓以小说来培养读者人文精神的途径,对于新疆哈萨克小说的创作仍有研究和探索的价值。在此,我们不仅希望新疆哈萨克小说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能够继续坚持人文教育为本,推动其文学教育的发展,同时更希望具有高水平的小说理论家对新疆哈萨克小说进行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使其获得更强劲的创作动力。
还有一种病人,他们找我看病,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就好一半儿了。这些人大部分的病都是心理障碍性疾病,多数都是情志引起的,比如说老太太和儿媳妇生气、两口子吵架这种事。有时候我开导几句,他们就感觉心里舒服多了。有很多病人,到我这看病就会说:“严医生,我不吃你的药,咱俩聊聊天,我的病都好一半儿了,我身上净是劲儿了。”
我经常给我的孩子讲,要日行一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今天条件是变好了,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变。我感觉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幸福,比做任何一件事都高兴。
基层抗疫:治好病人也成就自己
2002 年,在实习的时候,我看了大量的“红眼病”(红眼病在医学上称急性流行性结膜炎,是一种暴发流行的眼部传染病。每年7、8、9 三月,因天气炎热、湿度较大,细菌和病毒易滋生和入侵,为此病多发季节)。它的流行大概持续一个月。当时整个周口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红眼病患者,这是一次大流行。听老一辈说,这种病十年流行一次,那一次是最严重的。
那个时候,从早到晚,我都在接触病人。因为他们一染上就是全家人,当地流传有这样的说法:两个人一对上眼儿就感染上了,也就是与红眼病患者两目直视便会传染。其实,这并没有科学依据。最主要的传染途径还是接触性传染,像一家人共用一条毛巾、一个脸盆,就好比你摸了他拿过的东西,一揉眼就感染上了。农村老百姓他们不知道怎么防疫,得了病只能去找医生看病。
之前,我也没见过红眼病患者,头一天还掌握不住治疗方案。来的患者总是出现见光流泪、眼巩膜发红、淌眵目糊的症状。经过老师的指导,晚上我连夜查阅资料,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总结出了一个治疗方案。首先用抗病毒类的药物,然后用我们地方老一辈传下来的偏方,用柳树叶子熬水,放凉,再用毛巾冷敷,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再加上口服清热解毒药,患者系统治疗三四天,就恢复正常了。还有患者总是问我,为啥不给他输液。我还是那一句话,医生要有医德,不需要输液的,千万不能输液,能吃药好的就不打针,能打针好的就不输液,还得坚持住这一个原则。何必扩大这个治疗费用呢?
2003 年,我刚行医不久,就暴发了“非典”疫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很紧张,我被通知要定期配合村委会去各个路口当哨点儿,登记、管理外来人员入村的情况。我们挨家挨户给老百姓量体温,教老百姓防护措施,告诉他们不要聚集。非典疫情持续了三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跟着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从早上8 点到晚上8 点,另有一班人是从晚上8 点到次日早8点,在各个路口严格把关。其实直到非典结束我也没遇见一个非典患者,可能就没传到我们这里。
有一天刚结束工作,我接到了一个大姨的电话,她非常着急地说想叫我去她家看看,家里的大爷可能是病重了。这个大姨的子女外出务工去了,都不在家。老两口都八十多岁,大爷长期卧病在床,过去都是找我看过病的老患者。我接到电话之后,赶紧骑辆电动车赶到他们家。经过仔细检查,我发现大爷确实是病危了。我把大姨拉出房间,告诉她:“大爷的病情确实控制不住了,给大爷穿上衣裳吧。”大姨把衣裳找出来,我给大爷穿上,整理好后,大爷就断气了。我让大姨给家属打电话,叫子女赶紧回家奔丧。那一晚,我就陪在大姨身边,守了大爷一夜。
这件事情结束不久,又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打来的,说她的孩子9 个月大,在家突然高热惊厥,眼往上翻、面部乌青、四肢抽搐。这种情况一般是孩子长时间高烧不退,家长不知道,后来发现晚了,孩子烧得开始抽搐了(表现为突然发作全身性或局限性肌群强直性和阵挛性抽搐,多伴有意识障碍。既往可有高热惊厥发作史。惊厥常发生在病初体温骤然升高阶段。发作前可伴有咳嗽、咳痰、发热等呼吸道症状或其他类型感染症状)。此时非常危急,时间一长,牙关紧闭的时候会咬住舌头,孩子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叮嘱她,先固定孩子的头部,然后反复揪孩子的耳朵,掐合谷穴、角孙穴,物理降温。大概持续几分钟之后,孩子会有所好转。我当时啥也不顾,骑电动车去给她家送退烧药。我们提前约定了一个地点,把药放在那里之后,家属再去拿药,全程不接触。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我只有一个信念,得把孩子的命救回来。孩子的母亲拿了药,赶回家喂给孩子吃了,后来也好转了。事后想想挺后怕的,我去送药也有潜在的风险,很可能感染新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吃药之外,揪耳朵实际上是刺激耳朵上的穴位,这是针灸学说。耳朵上有几十个穴位,它们与经络相连。在紧急情况下,特别是高热惊厥、不省人事的时候,揪耳朵有助于苏醒,同时捣小天心穴、掐五指节和耳后高骨穴,效果非常好。
我之前在大街上遇见有一个人突然躺倒了,当时情况紧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心脏不好,还是低血糖。我马上打了120,扔下手中的物品,跪在地上俯身开始掐人中穴、合谷穴。给他掐醒之后,他的家人对我非常感激。事后有人问,你不怕吗?我说我不害怕,这是医生的职责,咋会害怕?我最担心的是我能不能把他救回来。
其实在诊室,我经常遇到高热惊厥的患者。坐诊时突然听到排队的人群中有人喊:“快!快!赶紧!俺孩子不中了!”孩子抱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丧失意识、不省人事了。老百姓家里平时不常备退烧药,有时直到孩子高烧晕厥,才想起看医生。大概在2006 年、2007年那几年,这个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有时我一天就能碰见好几个。最早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还有点慌乱。时间长了,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处理起来就游刃有余了。
还有一个高热惊厥的孩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抽搐不止、没有意识了,我给他扎人中穴、合谷穴、涌泉穴、百会穴,让他迅速地清醒过来。然后采用物理降温、吸氧这一切所有能用的方法去抢救,孩子当场就醒来了。我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非常高兴的。孩子抢救过来后,家长那哭的呀,跟咱磕头说谢谢,对我感激不尽。医生和患者之间,实际上大家的目的都是想看好病。医生其实最希望的就是患者去相信他,然后接受有效的治疗方案,大家一起去战胜病魔,没有哪个医生不愿意给患者看好病的。多数的基层医生都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费用,帮患者解除病痛。
疫情有段时间需要居家,陪孩子学习、做家务也成为我的日常。当然,钻研医学书籍是我多年的习惯。这个时候,我开始关注《伤寒论》当中有关瘟病的知识和临床经验,希望将来能在疫情解封之后有用武之地。我发现,《伤寒论》中有关瘟病的论述,有详细的治疗方案,结合西医的治疗理念,会有不错的效果。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中西医结合会缩短新冠的病程,不让它发展成重症,疗效好。轻症的患者,简单地吃点药就好了;中度的患者,就用药让症状变轻;重症的患者也可以用药降回到中轻度上来。
后来新二十条防疫政策出台之后,大量患者挤到卫生室和诊所里看病。我把这种理念投入到新冠治疗的实践当中。2022 年12 月8 日,接到上级通知,基层卫生室和诊所可以开始接诊了。紧接着,政府又下文,要求必须无条件接诊新冠病人,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接诊。当时医院就诊人数激增,无法满足大量病人的就诊需求。因此,各个卫生室、诊所成为了抗击疫情的重要战场。从12 月12 日起,新冠疫情患者不断增多。我的诊室8 点开门,那段时间每天早上7 点半,就有几十个患者在门口排队。我从12 月12日那一天早上开始,每一天都提前去给患者看病,一天大概看一百多个患者,中午只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那时候吃饭都没人送饭,只好让自己的孩子把饭送过来。又担心孩子感染,就让孩子把饭搁到我的三轮车上,等孩子走了,我再自己去取。然后告诉患者,让我稍微休息几分钟,把饭吃了,吃完紧接着再看。基本上每天都看到晚上10 点多,才往家里赶。回家之后再洗洗涮涮就十一二点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接着起来干。这样连轴转了十三四天。
这些患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症状:咽喉疼、浑身酸疼、声音嘶哑,有眼疼的、牙疼的,后期还有出现丧失味觉的。对于这些不同的症状,我一人一方、对症下药。但是药品短缺,退烧药非常紧张,后来政府紧急调查卫生室急需哪些药物,然后进行统一采购,解决了燃眉之急。
十四天之后,疫情感染病例人数突然断崖式下降了。这个时候病人极少,多是后遗症患者。轻症的好了,中症和重症的一般都住在大医院,一些医院住不下的轻症患者,就留到基层卫生室。这些后遗症患者,有的口服抗病毒的药,有的给他们输点营养药物。个别心肌损伤的患者,出现胸闷的,用供氧的药物。又坚持了大概半个多月,这次新冠疫情算是基本告一段落了。
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吃了不少苦,还经常把能吃苦挂在嘴边。从1999 年开始算起,我行医二十多年了。医生这个职业让我养活了家庭,也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每天都把看病救人当成积德行善。看病治好了病人,也成就了我。农村变成社区,群众从跑百里找医生看病,到享受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我就是这些变化的见证者。但是我很担心,因为大多数村卫生室、诊所收入不高,但工作量很大,导致现在年轻人毕业之后,想尽一切方法留在城市,不愿意到基层工作,最不济也去乡镇卫生院上班,谋个编制。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未来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