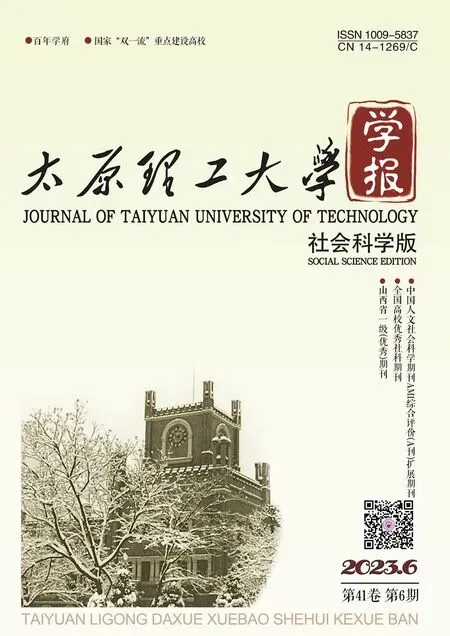康德“象征”概念探析
张梦薇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康德哲学中充斥着很多二分的难题: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概念、自由和自然,相较于这些区分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分裂的二者结合起来。与“图型”(Schema)联结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一样,“象征”(Symbol)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异质性关联这一难题,作为对理念的感性展示,它借助于“类比”把理念和我们的感性直观关联起来,但与图型法章节式解读,康德并没有对“象征”进行专门的阐述,而是将其置于“美是德性——善的象征”这一命题当中。显然,对于这一命题而言,康德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解释“象征”的本质,而是要去阐明美和道德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回应两者之间的关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这一命题的争论和误解都是从“象征”概念的误解开始的。比如Henry Allision就诉诸审美理念以诠释为何美可以作为道德的象征,他认为正是通过审美理念,理性理念才能以一种超感性的方式被间接地加以展现,美象征道德这个问题才能得以澄清[1]。Paul Guyer也将美和道德的关联区分出不同的层面,并将崇高也引入到这一论题之中,作为美和道德产生关联的一个面向[2]。总的来说,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象征”关系关涉的反思规则的相似性,转向内容之间的对比(1)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批判和讨论可参考周黄正蜜《康德论美与道德的关联》(载《世界哲学》2015年第五期);周黄正蜜《美作为德性的象征》(载《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二期)。。就此而言,我们就有必要对“象征”进行考察,厘清它在康德哲学中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尽管“象征”服务于美和道德之间的关联问题,但它本身作为一种来源于修辞学的传统,所具备的使概念变得可感的表象方式对于康德哲学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隐喻式思考和感性化的表达是我们理解概念的重要辅助手段,这样一种感性化倾向也对后来的浪漫派哲学家,乃至谢林和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旨在对“象征”概念及它所隐含的康德哲学中的感性化倾向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展开。第一,对概念直观的三种方式(实例、象征、图型)进行比较,澄清象征的理论背景和运作机制。“象征”和“图型”一样,都是联结直观和概念这两种异质性事物的中介。但由于“象征”所指向的理性概念的特殊性,使得“象征”拥有最特殊的运作方式——仅关涉反思规则类比上的相似性。第二,阐明“象征”作为“生动描绘”,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修辞学传统的感性化表象方式,这种表象方式对于概念的把握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康德对“生动描绘”的修辞学用法进行了哲学式的反思,将隐喻式的思考方式跨界提升为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方式,使其为自己的哲学思考服务。第三,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感性化表象方式的“象征”何以会在晚期著作《实用人类学》中被康德所排斥?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康德区分了“象征”的使用场景——先验哲学层面和日常经验层面;另一方面则是根源于康德晚期哲学发展的感性化倾向,尽管这种表象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概念,但在康德看来,概念式思考才是哲学的根本立场。
一、象征:联结理性概念与直观的中介
在康德哲学中,“象征”作为一种联结异质性事物的中介而出现,是对理性概念的一种感性化处理。对他而言,概念和直观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先天认识形式,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两者的共同作用是我们全部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这种重要性被康德表达为:“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3]。如果我们将直观和概念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这种不可分割性看作是从直观到概念这样一种上升的路径,那么在对概念的运用过程中,两者的不可分割性则可以被视为一种从概念下降到直观的路径。概念的运用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先验运用和经验运用。先验运用指向自在之物,与本体世界相关联;而概念的经验运用则指向现象世界,与我们经验的对象相关联。由于本体界的超越性,我们只能对概念进行经验运用,也唯有这种方式才是可能的。在康德看来,这种经验运用对于概念而言是获得其实在性,或者说获得其客观有效性的唯一方式。如果概念只停留在思维中的逻辑形式这一层面上,没有指向任何经验性的直观或材料,那么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没有所指”“在内容上就完全是空的”[3]。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称“要显示概念的实在性永远需要有直观”[4]。鉴于此,概念和直观的这种不可分割性就在两种层面上显示出来:一是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另一个则是对概念,或者说对知识的运用过程中。然而,直观和概念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形式,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异质性事物,因而两者之间的勾连也必须要借助一个中介物才能实现。康德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概念,与之相对,也就有三种中介物,或者说三种不同的直观方式:(1)实例——经验性的概念;(2)图型——纯粹知性概念;(3)象征——理性概念(理念)。
对于经验性概念,借助“实例”,即举例的方式就可以获得与自身相对应的直观,比如“狗”和“花”,我们都可以通过特指某一只黄色的金毛、一朵白色的郁金香等来对它进行直观化的说明;纯粹知性概念则需要借助“图型”来完成。“图型”作为勾连异质性事物的中介,相较于其他两种方式而言在康德那里享有最高的地位。与“实例”的方式所不同,“图型”并不为概念提供具体的例子,而是给概念提供一个获得直观的普遍性的处理方式或者规则——时间的先验规定(2)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知性概念只能通过图型与直观发生关联,但“图型”作为一种直观化的方式却并不仅仅限定在纯粹知性概念,也可以运用于纯粹感性概念(几何学概念)或者经验性的概念。这里经验性概念的再次出现表明,对它而言获得直观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对于理性概念而言,康德则引入“象征”作为它关联直观的方式。与经验性概念和纯粹知性概念所不同的是,理性概念超越现象世界,归属于自在之物。它超出了我们能够认识的范围,因而准确地说,不可能有任何直观可以与之相对应。但是,按照康德之前的理解,概念如果缺乏直观,它就只具有逻辑形式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也就丧失了意义。因此,为了使理性概念获得意义,就需要借助“象征”这种表象方式,赋予它一定程度上的实在性。
康德将“象征”的本质内核理解为一种“类比”(Analogie)关系。类比关系并不追求内容上的相似性,而仅看重关系上的,或者说形式上的相似性。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对“类比”有一个这样的界定:“类比并不像人们通常使用这个词那样,意味着两种事物的一种不完全的相似,而是指完全不相似的事物之间的两种关系的完全相似”[5]。“权利”和“力学中的推动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两者之间由于存在着一种相似的作用—反作用的关系,就可以对其进行类比。这样一种仅就关系而言并不关涉内容的类比关系,就为我们提供了把握理念世界的可能性,我们就可以用“对子女的幸福的促进”和“父母的爱”两者之间的关系,去理解“人类的福祉”和“上帝里面我们称之为爱的未知者”的关系[5],或是用“手推磨”和“一个赋有灵魂的身体”去把握“专制国家”和“君主制国家”[4]。
这种类比关系可以在数学关系中得到更加明晰的理解。在Y=KX这个方程式之中,对于任何一组X和Y而言,具体数值无论如何变化,两者之间的常数比例K是恒定不变的。X1和Y1之间的关系就和X2和Y2相一致,即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类比关系。诚然,概念之间的类比无法像数值那样被量化,但这种类比关系上的相似性也仍然是可设想的,差别仅在于类比关系的不同。比如当康德说 “美作为德性的象征”,就是在强调美和德性在反思规则这一类比关系上具有相似性,美是对道德的感性化展现。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使无法获得直观的理性概念借助一种间接的方式,即和直观的类比,而非直接的直观,保证其概念的实在性,“象征”也就完成了勾连概念和直观的使命。借由“象征”对超经验概念的把握,我们不仅获得了联结两种异质性事物的另一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象征”展示了认识概念的另一种方式——一种反思规则上的相似性,这就使得外在于经验世界的内隐事物能够同身处经验世界的人类主体关联起来,由此所获得的象征性的知识不仅拓展了我们认识的边界,同时也彰显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
二、象征:作为感性化表象方式的“生动描绘”
“象征”作为理性概念获得客观有效性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动描绘”(Hypotypose)。Rodolphe Gasché[6]对“生动描绘”一词做了详细的词源考查:Hypotypose来源于希腊语,hypo-指在某物之下;-typosis指由模具制成的图形,一种形状、轮廓,它既有哲学层面的用法,也有修辞学层面的用法。哲学层面的用法(其动词hypotypoun)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形式”“形状”“模型本身”;而其修辞学的用法则是出现在西塞罗的《演说者》中,指“清楚地解释,对事情进行视觉的呈现,仿佛它真的发生了”,但它所做的却比“解释”或“澄清”多得多。康德沿用了“生动描绘”一词的传统含义,并进一步将其定义为“Darstellung”(展示,给概念提供一个相应的直观)(3)“Darstellung”,邓译本将其译为“演示”,李译本则译为“展示”,这里为避免“演示”和推演之间关联的可能误解,采用李译本的“展示”。和“subiectio sub adspectum”(付诸直观、摆在眼前)[4]。这其实也就是对概念的感性化(Versinnlichung)过程,或者说是我们直觉的表象方式(intuitiven Vorstellungsart)——与逻辑的、论证的、概念的表象方式相对[4]。“生动描绘”包含两种表象方式,直接地对概念进行展示的“图型”及间接类比的“象征”。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是试图借助感性的、直观的表象去理解把握高阶的、复杂的对象。这种感性化的处理方式,使得概念这种僵死的逻辑形式变得富有生机,成为活生生的、向我们敞开着的表象。
对于这样一种感性化表象方式,我们需要将其与 “表征”(Charakterismen)和“审美标志”(aesthetische Attribute)区分开来,它们同样也是以感性化的方式展现概念。首先,就“表征”而言,康德将其视为直接借助语词或者符号对概念的单纯表达[4]。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再生产性的想象力依靠联想律发挥作用,借助语词或符号表示概念。语词、符号和概念之间的关联是固定的,只是一种再现关系,语词和符号也并不包含任何与后者相关联的直观。比如把“1”看作是对“一棵树”的表征,在这种表征关系被确定下来之后,符号“1”就是对“一棵树”这个概念的复现。在表征关系中,“符号只是作为看守者伴随着概念,以便伺机把概念再生产出来”[7]。与之相反,对于“象征”而言,象征物必须指向被象征物的直观,“它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而只是通过加入而引导到直观,并通过直观引导到概念”[7](4)符号一词在康德的文本中对应两个不同的词“Charakter”和“Zeichen”。这一句引文的德语原文:“Charaktere sind noch nicht Symbole:denn sie können auch bloβ mittelbare (indirecte) Zeichen sein,die an sich nichts bedeuten,sondern nur durch Beigesellung auf Anschaunngen und durch diese auf Begriffe führen”(AA,7:191),这句话中“Charakter”一词在Victor Lyle Dowdell(1996年)和Robert B. Louden(2007年)两版英译本中都翻译为“characters”,李秋零的中译本将它译为“个性”,对应的原文是“个性还不是象征”。笔者认为这里应当将其译为“符号”更为妥帖,而且在紧接着的下文当中,康德还说“in welche letzteren das Zeichen (charakter) den Begriff nur als Wächter(custos) begleitet”(AA,7:191),从这里就很清楚地看出,此处康德所说的“Charakter”是指符号,而非个性。。概而言之,表征关系强调的是想象力借助联想律对概念的再生产;象征关系强调的则是借助关系的类比为概念赋予直观。
其次,“象征”还区别于“审美标志”(aesthetische Attribute)(5)在李秋零译本中,Attribute被译为“标志”,而在邓晓芒译本中,“Attribute”和“Symbol”一样均译为“象征”。如若混用,会加大我们对“象征”的理解难度,故采取李秋零的译法以作区分。。审美标志与审美理念相关联,为理性概念提供诸多表象,从而鼓动诸认识能力处于鼓舞生动的状态之中。乍看起来,这和“象征”对理性概念进行感性化确有类似之处。然而,审美标志并不是对理性概念的展示,它被康德定义为“一些形式,它们并不构成一个被给予的概念的展示,而是仅仅作为想象力的附带表象而表述与此相联结的后果和这个概念与另一些表象的亲缘关系(Verwandtschaft),人们把这些形式称为一个其概念作为理性理念不可能被适当地展示的对象的标志(审美标志)”[8]。审美标志与理性概念之间的关联是内容上的相似性或者说在内容上存在着亲缘关系。“朱庇特的鹰”“爪中的闪电”和“孔雀”分别作为“天帝”和“天后”的标志,这三者作为表象本身,在内容上和“天帝”“天后”的形象具有相似之处。鹰的威严、冷峻,孔雀的骄傲、美丽等都会促使生产性的想象力不断扩展、思考更多的东西,并将这些产物附会在“天帝”和“天后”这两个概念之下。就此而言,“审美标志”区别于“象征”,前者涉及表象内容上的相似性,而后者仅是在反思规则上、形式上的相似性。与此同时,“审美标志”借助生产性的想象力对概念进行扩展,这就与借助再生产性的想象力对概念进行单纯复现的“表征”区别开来。
康德称“通过象征而有的知识就叫做象征的(symbolisch)或者形象的(figürlich)”[7]。正如上文所强调过的那样,这样一种感性的、直觉的表象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形象化的“生动描绘”。当康德说借助象征使得概念能够被运用于感性直观之上,从而赋予其意义时,其实也就是在强调概念依赖于“生动描绘”这样一种感性化的表象方式。Günte Zöller进一步把康德这种从概念引向感性直观的做法视为一种隐喻式的思考,将这种感性化的处理方式称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s)。他认为借助概念隐喻,康德把概念“从一个通常更为人所熟知的研究或论述的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通常是更为陌生的领域的隐喻,而经历了全新的发展,或者获得了新的解释和形态”[9]。可以看出,Zöller所强调的同样是“生动描绘”在两个领域之间的勾连作用,借助这样一种隐喻式的表达,概念可以更加清晰地被表述,进而也就更加容易地被我们所构想和接受。
这样一种隐喻式的“生动描绘”思路,很难不将其与诗学、修辞学中广泛使用的隐喻式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两者的目标都是借助我们所熟悉的、容易直观和被理解的东西去把握更加复杂、抽象的事物。尽管康德对修辞学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消极(6)从康德对于各种美的艺术的相互比较中,我们可以窥见康德对于修辞学的态度。他重点批判了运用修辞的语言艺术——演讲术。他将“演讲术”理解为一种运用言辞去“说服”人的艺术。它本身承诺要对理念有所表达,但却通过“美丽的幻相捉弄人”,听众无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知性事务”的满足,因而康德认为演讲术是不值得敬重的。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2-173.,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这种带有修辞学色彩的、感性化的表象方式,并看到了它对我们把握概念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对“生动描绘”的修辞学用法进行了哲学式的反思,将隐喻式的思考方式跨界提升为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方式,使其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所服务。无论是“隐喻”“象征”还是“类比”,它们本身都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用法,康德一方面将它们所诉诸的“清楚明白”“形象化”的要求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又对它们的使用范围和具体内容进行限定,比如“象征”仅就其类比规则而言,不关涉任何对象的内容。这样一种隐喻式思考方式在康德著作中的大量使用,使我们能够得以更好地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思想。Zöller把这种思考方式视为康德的哲学创新,并认为这对于康德哲学而言“不是辅助性的和补充性的,而是基本的和必要的”[9]。
三、象征:感性化表象方式及其限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象征”作为感性化工具,使超越性的“理性概念”间接地拥有了与之相对应的直观,进而在现象世界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实在性。就此而言,“象征”是联结异质性事物的中介。另一方面,“象征”作为一种“生动描绘”的方式,所包含的感性化表象、隐喻式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概念。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象征”对于康德哲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不用说,康德把美向道德的过渡这样一个重要的体系性问题最终归结为“象征”关系——“美是德性—善的象征”[4]。美和道德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唯有通过反思规则类比的相似性才得以勾连——直接地令人喜欢、不涉及任何利害、具有一致性及普遍有效。借由“象征”,道德不再是一个仅仅停留于本体界的超越性的理念,美将道德理念引向直观,使其获得一定的客观有效性,并进一步赋予它意义。也正是因为“象征”关系不涉及内容的特性,使得美在对道德促进的同时,也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此而言,“象征”成为从审美领域到道德领域过渡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的哲学体系建构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实用人类学》(1798)中对“象征”有不一样的评价。他批评称,总是以“象征方式”表达自身的人缺乏“知性的概念”,是缺乏理智能力的表现。这类人是“未开化的”,甚至是“野蛮的”[7]。比如人类幼童或者未被人类文明所驯化的原始人,他们无法借由清晰的概念来表达自身。除此之外,即便是拥有健全理智的人,尤其是诗人(比如荷马),如果他们需要借助象征方式进行创作,那么在康德看来,这样的活动同样是缺乏概念的表现[7]。就此而言,我们就需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康德对“象征”的态度何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使用象征方式表达自身在什么意义上与缺乏理智能力相等同?
为了回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关注“象征”的运作领域。康德在这里改变了“象征”所指向的概念领域,他不再像《判断力批判》中那样,将“概念”严格限定在“理性概念”的范围之内,而是泛指一切的“知性概念”。乍看上去,这似乎和此前所表述的立场相矛盾。但其实,即便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也没有否认“象征”在知性概念范围内的作用。与理性概念的“象征”所不同,知性概念的“象征”不再是跨越现象和本体这样一种先验哲学层面上的使用,而是一种经验的、日常语言层面上的使用。这种经验层面上的使用非常常见,比如“根据”(Grund)就是充当某物“基础”(Basis)的东西,“导致”(folgen)就是“从某东西中流出”(woraus fliessen),这些知性概念都是借助于“象征”式的类比而对其本身有所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目标领域的转变就为解决康德对待象征态度的转换问题提供了第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区分“象征”在先验哲学层面和日常经验层面使用的不同,康德所批判的也正是在日常经验层面上借由“象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人,而非是在先验哲学的层面上。在日常经验中,我们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智能力直接对概念进行表达——“缔造和平”,但我们缺乏这样的概念,而只能以“埋掉战斧”来对它进行间接地类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康德将依靠象征表达自己的人看作是缺乏理智能力的,更不必说那些“永远”需要依靠象征进行表达的人。而在先验哲学的层面上,一旦我们接受康德对现象和本体的划分,那么本体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不可知的,必须借由“象征”这一表象方式实现对属于本体界的理性概念的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象征”确实透露出我们作为有限存在者的局限性。但是同时,我们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绝对的二分状态之中,还在不停地借助“象征”去尝试接近理念,这就体现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不断超越有限性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力量。
更重要的是,康德对待“象征”态度的转变向我们彰显了他所坚持的概念式思考的根本哲学立场。不可否认,康德自己哲学中也引入了大量“生动描绘”式的感性化表达,当他将这种感性化的表象方式和概念论证式的表象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两种表象方式之间取舍的问题。康德肯定感性化表象和隐喻式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问题,但他认为概念式的表象对于哲学思考而言是更加根本的。他对这种表象方式的推崇和当时哲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密不可分:在康德晚期,以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等为代表的浪漫派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对于浪漫主义哲学家而言,人永远无法直接把握最原初的、绝对的、整全的真理。人类理智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借助“诗”或“艺术”及它们所包含的感性化的表象方式来完成对绝对真理的间接把握。这样一种间接地把握方式注定了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理,而不能实现对真理的整全了解(7)关于浪漫派哲学的进一步讨论和批判,参见先刚.谢林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吗?[J].世界哲学,2015(2):13-21.。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的发展不再执拗于概念式地把握,越来越多地出现依靠“理智直观”(8)这里的“理智直观”需要和费希特、谢林等人所使用的“理智直观”概念区别开来。康德意义上的“理智直观”仅是指一种不受认识结构和能力限制,一下子把握对象的超越性能力。费希特和谢林则将“理智直观”视为我们意识活动的根本运作方式。“天才”“预感”“神谕”等某些感性化的神秘体验对真理进行表达。这种倾向不断升温,并且由于这种方式丝毫不费力就能达到“尖端的洞识”[10]而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康德十分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感性化表象方式泛滥地使用会对哲学造成危害,甚至会导致“一切哲学的死亡”[10],因而他对隐喻式的、感性化的表达展开批判,并将其在根本上看作是一种理性能力的缺乏。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对“象征”态度的改变,根源于“象征”所代表的感性化表象方式在哲学中的滥用可能导致哲学思考陷入“迷狂”和“幻景”之中。
在康德看来,哲学的真正事务“就是通过系统的探讨而过渡到清晰的洞识”[10],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认识能力,借助概念去推演、论证,只有经过一系列辛苦劳作,才能获得真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康德坚持概念式的把握具有根本性地位,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感性化表象的作用,或是推翻之前关于“生动描绘”的论证。他认为:“只有在人们通过前者(概念的方式)已经将原则纯化之后,才可以使用这种表象方式,以便通过感性的、尽管只是类比的展示来使那些理念赋有生命,但却总是有些陷入迷狂的幻景的危险,这种幻景就是一切哲学的死亡。”[10]康德对待两种表象方式的态度就借此向我们揭示出来。感性化表象方式在哲学中的运用必须以概念式的表象方式为前提,并且需要时刻警惕陷入迷狂幻景的危险。与此同时,康德态度的先后转换也向我们揭示了“象征”所代表的感性化表象,或者说隐喻式思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助力于我们对概念的把握;另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理智的欠缺,我们无法仅通过概念对其进行把握。
四、余论
康德对以“象征”为代表的感性化表象方式的反思和批判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发展,感性化表象方式乃至隐喻式思考对他之后的浪漫派哲学家谢林、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都看到了感性化表象方式对概念认识的重要性,承认“诗”“文学”乃至“艺术”对把握绝对真理的重要作用。浪漫派推崇诗化的哲学,而在谢林那里,以感性化方式进行表象的艺术更是承担了对绝对者客观化的任务。艺术把哲学用概念的方式难以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绝对者由此在现象世界中得以呈现。换言之,谢林将艺术“当作哲学的工具或官能”,哲学和艺术分别是绝对者的两种不同呈现方式——“隐秘的”(esoterisch)和“显白的”(exoterisch)[11]。这也就是说,对谢林而言,概念式表象和感性化表象是在同等的层面上把握绝对者,两者并无高下之别。与此同时,谢林所强调的“象征”,已经不再是康德那里弥合两种领域的一种辅助性手段,而是认为在象征式的呈现中普遍者和特殊者“绝对地合为一体”[12-13],特殊东西就是绝对者的直接表达。就此而言,“象征”就不再是出于人类理智限度无法直接把握绝对者的一个带有妥协性的次等级的手段,而是我们直接把握绝对者的重要方式。
而对于黑格尔而言,尽管他也承认感性化表象方式的重要性,但是哲学最终必须走向概念式表达。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他对待哲学和艺术关系的态度上体现出来。在黑格尔那里,尽管艺术是精神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与哲学相比,感性化的表象方式必然要在概念式的思维中被扬弃,精神必须摆脱宗教、艺术,最终进展到哲学。一旦我们停留于感性化的表象方式,就意味着“对概念式思维的排斥”,乃至进一步地“对真实的普遍性的放弃”[14],这就势必会有消解为纯然隐喻和幻相的危险。Klaus Vieweg将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精准地概括为“黑格尔坚持概念艰苦卓绝的劳作,强调将表象必然地被扬弃于概念式的思维中……他表明艺术、宗教和哲学间的区别,并勾勒出前两者的欠缺和‘理念诗’的界限。文学和宗教的形式并不是研究哲学的适当形式。思想既然以自身为对象,则它的这种对象亦必须具有思想的形式,它自身亦必须提高到它自己的形式”[14]。这也就是说,对于黑格尔而言,感性化表象确实有助于概念的可理解性和直观化,但它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就注定了它无法成为哲学思考的根本立场,唯有概念式的表象方式才得以和哲学相配,这就与浪漫派哲学家及谢林的哲学立场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