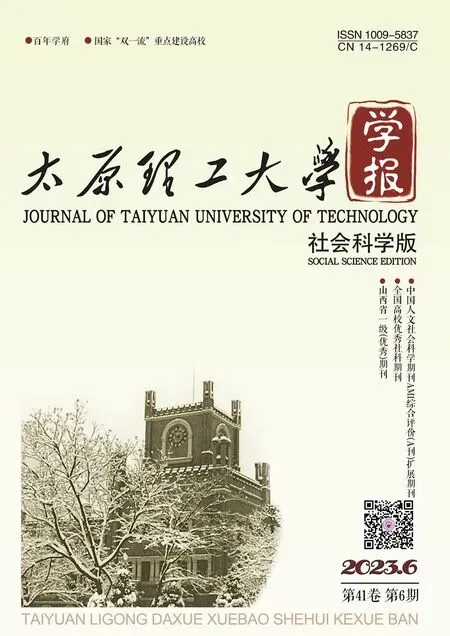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道德专家
陈 海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一、引言
人工智能的相关话题在近几年里已经成为各行各业探讨的热点,哲学界也不例外。其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问题又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在所有和人工智能相涉的伦理问题中,我们也可以做出两大类问题的区分,即一类是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伦理问题,另一类是以人工智能为样本或论据来展开讨论的伦理问题。本文想要探讨的“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道德专家”这一话题显然属于后者。那么,人工智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是道德专家呢?这一问题的提出,源自近几十年里哲学界对“道德专家”问题的相关讨论。在此,本文将试图说明人工智能比人类更有可能成为道德专家。为此,本文将首先考察专家(expert)和专家化(expertise)这一组概念(1)其实,将expertise翻译为“专家化”只是一个权宜之策,事实上,笔者认为expertise更类似于汉语中的“专长于某事、擅长于某事”的意味,使用单个汉字对应翻译的话就是“专”。,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道德专家(moral expert)和道德专家化(moral expertise)等概念的探讨,最后通过对人工智能成为进行区分来推导出人工智能成为道德专家何以可能。
二、如何理解专家和专家化
“专家”和“专家化”这组概念,在曾经的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在晚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开始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为此,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展开对这些概念本身的考察。针对“专家”和“专家化”这组概念,有过较为完备的讨论的是布鲁斯·D.韦恩斯坦(Bruce D.Weinstein)和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等人。
(一)韦恩斯坦和德雷福斯等人的讨论
韦恩斯坦明确指出存在如下两类专家,他们要么专长于“知道”某事(认识上的专,epistemic expertise),要么专长于“做”某事(行动上的专,performative expertise)[1]57。韦恩斯坦的区分很容易让人想到认识论研究中关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区分(2)关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中文翻译也有着不少争论,笔者认为目前来看没有一组特别好的译名可以对应这一组概念,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采用英文原文进行表述。。事实上,哲学家们关于专家/专家化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正是基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区分展开的。认识上的专是一种为某一特定领域中的命题提供强有力辩护的能力,而行动上的专是一种在实践中根据规则和典范呈现出良好技能的能力,并且两类专家中的任何一类专家都可以合理地不同意另一类专家的观点或行为[1]57。显然,在韦恩斯坦的理解中,认识上的专对应的就是Knowing That,行动上的专对应的就是Knowing How了。紧接着,韦恩斯坦又对“专家”(expert)、“专家意见”(expert opinions)和“专家化”(expertise)三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根据韦恩斯坦的表述,一个人能为某一特定领域中的命题提供强有力辩护,那这个人就是认识上的专家,一个人能在实践中根据规则和典范呈现出良好技能,那这个人就是行动上的专家;而当一个专家在其专业领域内为某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时,我们就说这一观点是专家意见;而专家化则是指能够提供专家意见或在某一领域具有某种或某些技术(skill)的能力[1]58-59。
德雷福斯等人则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入手,对“专家”和“专家化”展开理解。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要讨论伦理专家这一问题,因此很自然的就从人们的伦理生活入手,他们将人们日常遇到的和道德相涉的情况称为“伦理应对”(ethical coping),而在应对的过程中又要涉及所谓的“伦理技能”(ethical skills)。德雷福斯等人根据人们对技能(skill)掌握的程度不同,把人分为五大类,掌握技能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新手”(novice)、“进阶菜鸟”(advanced beginner)(3)有研究者将advanced beginner翻译成“老手”,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日常语言中对“老手”一词的理解的。参见夏永红的《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载于《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1期。、“合格者”(competence)、“熟练者”(proficiency)、“专家”(expertise)[2]232-236。从这一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专家”就是指那些对某一些技能的掌握程度最高的人。虽然德雷福斯等人对技能的区分是从伦理技能入手展开的,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一区分也适用于其他领域,而笔者在这里引用德雷福斯等人的区分时,恰恰是需要有意识地略过他们在伦理学方面的考量的。他们在区分五类人的时候,对应使用的词其实不是十分严格,比如novice和advanced beginner显然是指人,但competence、proficiency和expertise则明显是指人对技能掌握的程度(但为了统一起见,笔者也将competence、proficiency和expertise翻译成对应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expertise在行文的其他地方也直接对应着“专家”)。同时,从表述的细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韦恩斯坦和德雷福斯等人关于skill的理解是存在差别的。在韦恩斯坦那里,skill更类似于一种可以独立于人存在的技术,人可以具有掌握这一技术的能力;而在德雷福斯等人那里,skill就是一种能力,故笔者直接将其翻译为“技能”。但在大部分时间里,skill代表的是“技术”还是“技能”的区分并不是十分重要。还需指出的一点是,包括韦恩斯坦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试图沿着德雷福斯等人的策略,通过对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来区分一个人在该领域是否称得上是专家,但这势必会遇到区分熟练程度的界线不够清晰这一问题。边界是否清晰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此需表明的是,这种熟练程度上的差别确实存在,但是想要清晰地进行区分着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先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而不深入讨论其界线。
(二)重新理解专家和专家化
韦恩斯坦和德雷福斯等人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说清楚“何为‘专家’”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界定还有可以进一步修正的地方。下面,笔者将结合他们的研究给出笔者自己的理解。
首先,在谈论专家或专家化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确定讨论的起点。之所以要对韦恩斯坦和德雷福斯等人的界定进行重新整合,而不能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专家/专家化理解的起点是不一样的。以德雷福斯等人的研究为例,他们在文中明确指出,他们讨论的对象是伦理专家(化)这一现象,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他们讨论的起点。既然这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遇到的现象,那么我们也不会去质疑将这一现象作为讨论的起点的合理性。但在韦恩斯坦的研究中,他将专家分为了两类,其中一类(即行动上的专家)非常类似德雷福斯等人提到的伦理专家,但认识上的专家则大为不同。由于在韦恩斯坦的研究中,专家是和专家意见密切相关的,虽然他已经明确指出“专家的意见并不必然是‘专家意见’”[1]70,这反过来恰恰表明了专家意见本身是可以离开专家而存在的,这就等于给“专家意见”扣上了形而上学式的紧箍咒。那么一旦“专家意见”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内涵,我们在讨论“专家意见”时,其研究起点就必然会成为这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专家意见”。而既然我们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专家意见,那么衡量和判定专家的标准也就变得异常清晰,即能够持有这样的专家意见的人就是专家。如果笔者的理解没有问题的话,那么韦恩斯坦自己承认他所区分的两类专家在意见上不一致亦是正常的也就不足为奇了[1]57。
但是,如果专家/专家化可以如韦恩斯坦所说的那样被简单直接地分为两类,那么问题反而变得清晰多了。而事实上,我们似乎可以区分两类专家化,但很难区分两类专家,因为一个既是认识上的专家又是行动上的专家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所以,笔者认为将作为个体的专家确定为讨论的起点并不合适,因为我们总可以要求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算是专家”。那么,我们不妨假设存在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专家意见,同样,我们也可以假设存在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专家行动,并据此得出如下结论。
专家:一般而言,当某个人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持有某专家意见或实施了某专家行动,那么我们可以称该人为该特定领域的专家,该人在该特定领域已专家化(或该人专长于该特定领域)。
但专家、专家意见、专家化这三者在现实世界中又是同时聚集于该专家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不可能只有其一而没有其二其三。套用基督教神学家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专家、专家意见、专家化三者呈现一个“三位一体”的态势(有需要时,可以用“专家三”来进行表示)。如果存在这样的专家意见,讨论的起点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关键就在于,存在这样的专家意见吗?
目前可能暂时无法明确地回答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意义上是否存在这样的专家意见,但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这样的专家意见是存在的。这里可以采用的论证策略是:如果我们暂时无法提供面向未来的或将来的专家意见的判断标准,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哪些是面向过去的或历史上的专家意见(4)面向过去的或历史上的专家意见是比较容易判定的,首先要保证不出错,一旦出错,再权威的专家给出的意见都不会再被视为是专家意见;同时,在不出错的前提下,专家意见肯定要比一般人的意见给出得迅速、及时,其解释和辩护也要更为有力。,然后通过已有的专家意见的形成过程来确定可能形成面向未来的专家意见的方法论。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大学里教授物理学,他授课时所讲的内容(专家意见的一种)就是面向过去的专家意见。当他在研究引力波的时候(引力波在当时尚未得到实验的证实),我们也会认为他关于引力波的看法是属于专家意见(即面向未来的专家意见),因为我们认可或认同了爱因斯坦关于引力波研究的科学方法(这里的科学方法并不是指爱因斯坦的方法,而是一种被广泛认可或认同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而爱因斯坦采用了如此的方法,从而获得了方法论上的认可或认同)。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根据本文的推理过程,专家意见是专家之所以为专家的表征,但并非某一专家所给出的意见都必然是专家意见。还是以爱因斯坦和引力波为例,我们认为爱因斯坦对引力波的看法是专家意见并不是因为这是爱因斯坦的观点,而是爱因斯坦采用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如果爱因斯坦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谈论引力波,那么想必大家也都会对他的看法一笑而过了。有一种反对之声认为,有的专家总是能够给出专家意见,难道这不能够成为支持“先有专家、后有专家意见”的依据吗?对此,笔者认为,“专家”和“专家意见”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电脑硬件和运行某一软件得到的结果,连接两者的桥梁是这一软件或程序,而软件就是专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或方法论,这才是保证专家给出的意见是专家意见的关键。
三、有道德专家吗?
既然我们对专家/专家化进行了概念分析,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轻易地知晓“存不存在道德专家”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虽然德雷福斯等人在研究中将伦理专家视为是专家集合中的一个子集,但实际情况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先探讨“专家”和“道德专家”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引入所谓的“专家化辩护”(expertise defense)来展开对“道德专家”的讨论。
(一)道德专家、道德哲学家和道德上的专
皮特·辛格(Peter Singer)早年曾指出,在当代道德哲学领域里,主流的哲学家都不认为存在所谓的道德专家[3]115。布兰德·胡克(Brad Hooker)也曾指出,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说一个专家是在某一领域里总能成功实现一致达成的某些目标的人,但是在伦理学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关于‘如何才算成功回答了道德问题’的一致目标”[4]。胡克的疑问非常直接地让我们开始思考,如果存在道德专家,那么道德专家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究竟有什么异同。
承接前文,韦恩斯坦延续自己对“专家化”的区分,将道德专家也分成了两大类,即认识上的道德专家和行动上的道德专家,认识上的道德专家又被韦恩斯坦分为三类(分别为专长于描述伦理学、专长于元伦理学和专长于规范伦理学的人),行动上的道德专家则是指专长于过良好生活的人[5]61。如果这样的表述仍不够明确,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更为现实的例子:认识上的道德专家最典型的代表群体就是道德哲学家们,而行动上的道德专家最典型的代表群体可能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道德楷模。那么如果我们把道德专家理解为专家的一种,根据上文的表述,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界定。
道德专家*:一般而言,当某个人在道德领域持有某专家意见或实施了某专家行动,那么我们可以称该人为道德专家,该人在道德领域已专家化(或该人专长于道德领域)。
但与上文关于专家的界定不同,这里关于道德专家的界定似乎很难被轻易说服。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道德哲学家在行动上非常没有道德,那么这个道德哲学家还能被称为道德专家吗?这里可能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道德上的知或知识是否不仅应该包含对于道德命题的知或知识还应该包含按照这些道德命题去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在这里,笔者还是倾向于将道德命题的知或道德上的知识,与依据道德命题去行动区分开来。
辛格很明确地表示,道德哲学家在成为道德专家这件事上有优势,若非如此,大家就会觉得道德哲学本身没有存在的价值了[3]117。笔者十分赞同辛格的观点。在儒家传统中,王阳明就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正是因为知行合一并不容易。当然,在道德上做到知行合一也并非易事,但根据辛格的理解,“知”对于“行”是有重要帮助的。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在认识层面上知道更多道德事实或道德知识的人,在行为上也更容易更道德,至少比知道更少的人更容易道德地行动(5)关于该论点,下文将在“专家化辩护”这一部分继续展开,在此先略去不表。。但辛格的这一态度恰恰也明确地表达了“道德哲学家不必然是道德专家”的立场。
如果说道德哲学家不必然是道德专家,那是否意味着道德哲学家还是有可能成为道德专家的呢?如果可能,那应该如何成为?在不断地追问中,笔者将对道德专家的描述推向了一个十分极端的位置。
道德专家:当某个人在道德领域持有所有的专家意见并且实施了所有的专家行动,那么我们可以称该人为道德专家,该人在道德领域已专家化(或该人专长于道德领域)。
倘若我们对道德专家的理解从道德专家*中的合取式表述变成了现在的析取式表述、单称表述变成全称表述,就不难看出我们对于道德专家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未必会对道德专家提出如此严苛的要求,但当你遇到一个所谓的“道德专家”时,他恰巧给出了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不符合道德预期的判断时,至少你不会承认他的“道德专家”这一称谓。我们也可以假设一种统计意义上的道德专家,即一个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做出的判断或行为都是合乎道德的人就是一个道德专家。但由于我们很难确定究竟多少次犯错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做如此的范围界定总是容易陷入喋喋不休的无谓争执,而当这样的范围难以被准确划定时,我们更应该采取的策略是放弃在此种意义上使用该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讨论道德专家概念,那我们还不如不使用这个概念。这与亚里士多德眼中有道德的人很类似,都具有“不会在道德上犯错”这一属性,但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相信存在这样的有道德之人,而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彻底的道德专家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理念或概念而存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但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这样的道德专家,道德上的专(moral expertise)确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上文中做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比喻,认为专家其实是一个专家三式的存在。但道德专家和专家似乎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专家只要是在某一小点上能给出专家意见即可达成,那么道德专家则必须要在道德相关的方方面面都不出错才能达成。也就是说,专家是专家三式的,但道德专家和道德专家意见、道德上的专或专家化不是“三位一体”的,道德上的专家意见和道德上的专是共在的,道德专家要包含所有的道德专家意见和道德专家化。所以,彻底的道德专家似乎是如此难以达成,但道德上的专家意见和道德上的专还是可以达成的。从另一个角度讲,相比较讨论道德专家,我们更应该(也更可能)讨论道德上的专。
(二)专家化辩护
那么,既然(彻底的)道德专家很难达成,我们是否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尽可能接近道德专家”这一目标呢?也就是说去追求道德上的专,通过不断达成道德上的专,来不断接近一个道德专家的目标。那么谁人又是更容易达成道德上的专或专家化的个体或群体呢?在此,引入近几年常被讨论的“专家化辩护”(the expertise defense)这一概念,来表明道德哲学家似乎是更容易达成道德上的专家化的。
简单地说,所谓“专家化辩护”所要捍卫的观点就是认为哲学家们接受的特殊训练足以让哲学家们(在做出直觉判断时)能够避开大众直觉的干扰[6]332。莫提·米兹拉希(Moti Mizrahi)进一步概括,如果专家化辩护要取得成功,那么必须要能够表明(a)专家(职业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和新手(非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是不一样的(判断涉及真值),以及(b)专家(职业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比新手(非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更好(判断涉及真值)[7]53。但专家化辩护也并没有得到哲学家们的一致认同。比如,作为处在实验哲学支持者阵营的米兹拉希认为专家化辩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此,他给出了三个论证,试图表明(a)和(b)都是不对的。
论证一
前提1:如果有(a),那么和非哲学家不同,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是不受非相关因素影响的。
前提2: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和非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是一样会受到非相关因素影响的。
结论1:所以(a)与事实不符[7]56。
论证二
前提3:当直觉判断不受非相关因素影响时才是可靠的真循者(truth tracker)。
前提4:(无论哲学家还是非哲学家)直觉判断都会受非相关因素影响。
结论2:所以直觉判断不是可靠的真循者[7]57。
论证三
前提5:知觉判断不能通过训练得到提升。
前提6:直觉判断也类似于知觉判断。
结论3:所以直觉判断不能通过训练得到提升[7]60。
米兹拉希的三个论证看似很有道理,但经仔细考量,还是会发现一些言过其实的地方。在论证一中,米兹拉希对(a)的理解似乎有偏颇,即使我们承认专家和新手的直觉判断是不同的,也不意味着专家和新手的判断是完全对立的或相反的,更不意味着连影响做出直觉判断的因素也完全不同。从某个角度来看,(a)中所表明两者直觉判断的不同,很可能就是(b)中所表述的“专家的直觉判断更好”这种情况。所以论证一成立,但对反驳专家化论证没有意义。论证二成立的一个更大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承认,无论专家还是新手做出的直觉判断都是有真值的,否则这个论证也没有意义。而论证三涉及的是关于直觉判断的理解(直觉判断是否和知觉判断是类似的),比如,我本人对直觉判断的理解(我对直觉或直觉性判断的理解与米兹拉希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直觉不仅仅是知觉判断那样的单一构成判断,而是复合的判断,而且直觉判断是可变的)和米兹拉希有出入,我对论证三的有效性也就会有质疑。虽然米兹拉希在重述专家化辩护时提到了,无论是专家的直觉判断还是新手的直觉判断都会涉及真值,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直觉判断也并不必然涉及真值(比如,我们在探讨道德判断时,有时就会有意识地避开“道德判断是否有真值”这样充满争议的问题),这是米兹拉希在重构专家辩护时的疏忽。
因此,基于以上理由,笔者倾向于将专家化辩护重述为:专家(职业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比新手(非哲学家)的直觉判断更好。那么,将专家化辩护作道德专家化辩护理解时,这一辩护的表述似乎可以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道德哲学家的(直觉性)道德判断比非道德哲学家的(直觉性)道德判断要更好。这里值得展开辨析的分别是“直觉性的”和“好”。首先,“直觉性的”判断在原始的专家化辩护里是很重要的,因为专家化辩护作为一个实验哲学家们攻击的对象,其被攻击的点就在于职业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直觉判断之间的差异。但在道德专家化辩护里,做出的道德判断是不是直觉性的并不致命。其次,所谓更“好”,米兹拉希认为专家的直觉判断比新手的判断更可能是真的。但当我们在讨论道德判断时,我们仍然会为存不存在道德知识这样的大问题争吵不休,因此笔者更愿意用上文提及的“专家意见”来暂时替代“命题的真”,即更接近于专家意见的判断就是更好的判断。
四、如何理解作为道德专家的人工智能
那么,倘若要讨论“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成为道德专家”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自然会面对“人工智能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徐英瑾就曾提出“既然人工智能产品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生物体’,我们又怎么保证此类产品能够经由与人类身体的相似性而承载人类所认可的道德规范呢”[8]259这个问题。这之中所涉及的讨论和争执非常多,但首先需要表明的是,我们通过对人工智能概念的梳理,可以找到人工智能和道德专家或专家化相契合的部分。
“人工智能”这个词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被提出来之后,其内涵和外延就一直不稳定。我们现在常常提及人工智能的时候,该术语可能是表示一些类似大数据技术、人脸识别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这样的已被应用或将被应用的技术,也有可能是表示一些类似于特斯拉机器人(Tesla Bot)这样的仿人产品。但在本文的讨论中,则把“人工智能”限定在“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AGI)的概念范围内。
所谓通用人工智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能够像人类那样胜任各种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8]76,更直白一点说就是一个“人造人”系统。这个人造人未必需要具有人类的形态,但它一定能像人类一样处理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专用人工智能”,比如AlphaGo就是一个专门用来下围棋的智能系统。但无论是通用人工智能还是专用人工智能,起初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了模仿人(既模仿人的思想也模仿人的行为),无论是模仿一个整体性的人(通用人工智能)还是模仿人的某一方面(专用人工智能)。
随着广义的人工智能行业在近二十年的长足进步,人类在专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还是以AlphaGo为例,我们已经看到,几乎全世界的顶尖围棋选手都不是AlphaGo的对手。但是众多领域的专用人工智能的类人表现甚至超人表现,是否就意味着通用人工智能也能实现类人或超人的表现呢?徐英瑾认为不能,他的理由在于“一切真正的AGI系统都应当具备在无监督条件下自行根据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切换工作知识域的能力,(而目前作为专用人工智能系统基础的)深度学习系统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自动切换,所以)都不可能演变为AGI系统”[8]77。那么根据以上的辨析,我们可以认为,虽然通用人工智能不是简单地将专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叠加就能实现的,但是一个可以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系统必然可以像多个(甚至是无穷多个)专用人工智能系统那样工作。
但是,人工智能真的仅仅是一个模仿人的智能的系统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对“人工智能”(无论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都带有极高的要求,这里先引用一段著名的小品对白。
赵本山: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范伟: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赵本山:回答错误!公布正确答案!
高秀敏: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6)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因出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节目《卖车》(赵本山、范伟、高秀敏主演)中而被大家熟知。
这虽然是一个喜剧段子,但却能从中体会到我们对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两者期待的巨大区别:我们可以接受人是可以犯错的(“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但我们接受不了人工智能犯错(“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无人驾驶领域。首先我们也认为无人驾驶汽车的制造商应当对无人驾驶汽车事故负责(但究竟应当负责到什么程度在此暂且不论),但我们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事故和一般的驾驶事故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无人驾驶汽车一旦发生事故,我们都会感到一定程度的恐慌,甚至有人会要求停止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和生产,态度是十分苛刻的。比如,根据特斯拉(Tesla)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车辆安全报告显示,“公司的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安全水平是美国平均的8.9倍,安全性同比提升25%”(7)具体数据可参见2022年1月24日发布的《特斯拉车辆安全报告》,网址:https://www.tesla.cn/VehicleSafetyReport;韩忠楠2022年1月24日发布的“特斯拉最新发布!自动驾驶安全水平是美国平均的8.9倍,Autopilot安全性同比提升25%”,网址: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1-24/doc-ikyakumy2232506.shtml.,但人们依然会觉得自动辅助驾驶系统不够安全。而因人为驾驶失误导致的交通事故,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却从未导致人们要求汽车停产(可能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存在这样的抗议,但在当下,提出这种抗议几乎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其本质上是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待更高,几乎不允许出错,而对于人本身却宽容得多。我们总会在朝着某一目标努力的过程中进行不断地调试,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修正、再试错、再修正的过程。人工智能兴许也能做到试错、修正、再试错、再修正,但人在试错修正的不断推进过程中甚至是可以改变最终的目标的,而人工智能不会(至少不会被允许)改变目标。引入行动哲学常讨论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工智能是不存在“薄弱意志”(weak will)一说的,人工智能认定了应该去做某事它一定会去做某事,也就十分完美地实现了“知行合一”(这里先不纠结于人工智能的“知”和人的“知”之间的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恰恰又不是对人类的模仿,而应当是人类的榜样(在这一点上,AlphaGo的成功又是一个很好的佐证)。AlphaGo通过实战,已经证明了自己显然是一个围棋专家(如果我们引入专用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话,至少AlphaGo是专长于下围棋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捣鼓出一个Alpha Ethics专长于道德判断或伦理上的事务呢?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笔者在前文提到,我们对于道德专家的期待就包含了道德专家在做出道德判断时是不应该犯错的。而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期待也是要求人工智能系统不出错。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和道德专家至少已经存在一些共同之处的。但我们也会发现,人工智能和道德专家从目前来看至少还是两个极为理想化的概念。如何让两个相对不接地气的概念获得实质意义上的联系成为笔者所要讨论的重点,笔者采取的论证策略是,分别从“人工智能”和“道德专家”开始推导,最终两者皆可收敛于“专家意见”,因此得到“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专家”的结论。
关于人工智能,笔者在上文中已经表明,虽然通用人工智能不是简单地将专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叠加就能实现的,但是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肯定可以像专用人工智能系统那样工作。也就是说,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达成,必然包含了(任一)专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达成,那么也必然可以推导出存在一个专用于道德判断的人工智能系统。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接受人是可以犯错的,但接受不了人工智能犯错,因此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认可就必然包含了“不能犯错”这一属性。而一个专用于道德判断的人工智能系统给出的“不犯错”的道德判断,那就是道德上的专家意见。
关于道德专家,笔者在上文中也已经表明,当某个人在道德领域持有所有的专家意见并且实施了所有的专家行动,那么我们可以称该人为道德专家。上文也表明了,作为一个正常人,能够达成道德专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人工智能不一样,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摆脱人类包括七情六欲在内的所有的非理性干扰因素,全然地执行所有的专家意见。有批评者提出,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通用人工智能如果真的实现了,是不是有可能人工智能也会跟人一样,具有了七情六欲,从而也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对此的回应是,人工智能在将来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到和人一样的地步了,我们还会称之为“人工智能”吗?或许我们会直接称之为“人”,并且由于我们尚未制造出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工智能,我们不会根据一个设想的未来的人工智能形态来理解当下的人工智能形态,因此在我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当中,人工智能依然是不会受到非理性因素干扰的。至少在当下,我们认知的人工智能还是不具备七情六欲等非理性的属性或能力的。综上所述,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能够出现一个道德专家,那么最有可能成为这个道德专家的恰恰应当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这里笔者的推理全部是建立在对人工智能和道德专家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之上的,两者可以通过专家意见这一概念建立联系,具体怎么样的专家意见才算是专家意见,还有很大的可讨论空间(前文笔者也举了爱因斯坦的例子,但这些例证也都还会遇到挑战,笔者将在其他研究中继续展开这些讨论)。但从论证“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道德专家”这一任务来看,不展开对专家意见具体内容的探讨影响也不是很大。
五、结语
当代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的哲学讨论非常多,作为道德哲学的研究者,笔者想要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来为解决道德哲学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引入人工智能概念来评析和理解道德专家概念。通过考察,笔者认为道德专家本身是一个严苛的概念,作为个体的人更应该追求道德上的专而非追求称为彻底的道德专家,倘若真的想要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专家,那么人工智能系统恰恰是最有可能成为道德专家的事物。
本文的初稿曾在2021年10月30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人工智能与社会认识论”学术论坛上宣读,并在2021年12月19日召开的“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论坛——前沿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会议上做过线上交流,感谢浙江大学李哲罕研究员、湖南社会科学院宋春艳副研究员对拙作的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