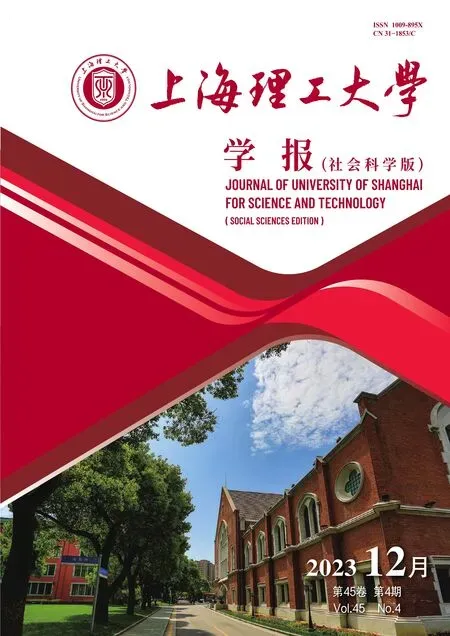论约翰·金塞拉的生物区域主义诗歌创作
杨永春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约翰·金塞拉1963 年出生于西澳珀斯。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其文学造诣开始被诗坛和学界认可,随即他成为文学多面手。他是一位异常多产的诗人[1]489,也是 “一位按任何标准算得上的奇才”[2],“一个俄尔普斯式的喷泉,一个想象的奇才”[3]。人们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才能和成就不吝赞美之词。自从1983 年发表诗集《冰冻的海洋》以来,金塞拉已经出版了30 余部诗集,其中著名的有《夜鹦鹉》《谷仓:一部田园交响曲》《闪电树》《狩猎及其他诗歌》《袋鼠病毒项目》《善行:内陆的沧海桑田》《洗羊的消毒水》《沼泽田园诗》和《小麦地带》等。他还编辑了数种文学期刊和诗集,著名的有《捕鸟者之歌》《盐碱读本》《诗歌》《库那皮皮》《路桥:当代澳大利亚诗歌》《诗歌评论》《棱镜》,以及颇具影响力的《企鹅澳大利亚诗歌选集》,还自创诗歌杂志《盐》。他的抒情诗以澳大利亚西部生态为背景,描绘了那片土地的苍老、寂寥和美丽。
一、金塞拉的反田园倾向和生物区域主义的渊源
美国生物区域主义学家迈克尔·布兰奇(Michael Blanch)指出生物区域主义的核心在于“把家园意识扩大为多维概念,既包括我们的人类邻居,也包括动植物、地理上的水土山河,甚至天气和气候等”[4]。他还指出:“地域身份是自然界深刻塑造的文化建构,因此生物区域主义更在意自然在塑造人类文化活动和身份中扮演的角色,因此生物区域主义视域下的家园意识暗含着更大的伦理和环境责任。区域身份主要讲我们从哪里来,生物区域主义主要讲我们对于家园的责任感,愿意为了守护家园担任管家的职责。”[4]综上,生物区域主义强调自然对于文化演变有着重大的影响(Nature VS Culture),人类对于生态之殇怀有愧疚之心,担负有再造生态平衡的伦理责任,人类应该担当自然的守护人和监管者之任。
澳大利亚虽然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享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的美誉,但经过殖民主义的野蛮开发后,在淘金热、农牧业过度发展,矿业潮(Mining Boom)等冲击下,环境和资源的承载经受了重重考验,留下了现在难以应对的生态问题。在文学创作领域和文学批评理论上,涌现了大量“自然为导向的文学”(帕特里克·墨菲语: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和生态批评话语。这些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游记和随笔等,本文重点关注澳大利亚的生态诗歌。从殖民主义时期的诗人哈珀(Charles Harpur)、佩特森(A.B.Paterson)、戈登(Adam Gordon)、劳森(Henry Lawson)、肯德尔(Henry Kendal)、布伦南(Christopher Brenan)、尼尔森(John Shaw Nellson)到民族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斯莱赛(Kenneth Slessor)、林赛(Norman Linsay),一直到现代的霍普(A.D.Hope)、赖特(Judith Wright)、金塞拉(John Kinsella)等诗人都将笔触深入这块独特的大陆,或歌颂这里的鸟语花香、山川壮美,或哀叹与这片大陆格格不入,更多的是关注如何与这片大陆建立起和谐的家园意识,从而建立起合适的身份,使得所谓的“二手的欧洲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得以“诗意的栖居”。
风景诗歌起源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传统田园诗。以古希腊的特俄克里托斯和赫西奥德的田园诗以及古罗马的维吉尔的《牧歌集》为代表,展示了人们对于乡村以牧羊人为代表的生活理想化的追求。H.M.艾布拉姆斯将田园诗定义为:“一种特意而为的传统诗歌,表达城市诗人对于牧羊人和其他农人在理想化的自然背景中安宁和简朴生活的怀旧式想象。”[5]202安德鲁·泰勒则认为:“田园诗作为一种体裁或风格,从城市的视角创作,探讨乡村题材,来阐明城乡之间潜在的张力。”[6]这种张力掩盖了传统田园诗中的和谐、安静和其乐融融,也揭露出城乡之间不公正的恶性关系。风景诗歌无疑属于田园诗的范畴,但是在极其陌生的澳洲大陆,如何接受风景是诗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埃瓦尔·英迪克也说:“澳大利亚的自然诗歌或风景诗歌是一个遭受重创的东西,其特点是疏离和与世隔绝。”[7]金塞拉的风景诗歌是反映白人在与世隔绝的西澳地区开发丛林、挖掘金矿和过度耕牧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他还与自己的硕士导师安德鲁·泰勒和格兰·菲利普斯在西澳创办风景与语言研究中心,定期开展田野考察,举办学术会议,编辑电子期刊《风景和语言》,极力推动人们关注这一地区的生态问题。
金塞拉也认为传统田园诗“通过对乡村世界的诗歌化和浪漫化给予受教育阶层的赋权工具,是他们对于舒适、权力和控制的真实写照”[8]1-5。按照金塞拉的理解,传统田园诗是城市对乡村,进一步延伸到对自然所占有的一种优越权。这其中还蕴含着殖民主义的内涵,白人不仅仅对自然,对土著人也占有优势支配地位。因此他说:“我有责任去推翻田园诗的剥削和失能的语言,激进的田园诗人就是要强调对自然界的虐待和人与自然层级互动中的不平等和非正义。”[8]7-11
二、生物区域之殇
殖民主义时期诗人们笔下的生态环境是陌生和危险重重的,例如查尔斯·哈珀的诗歌《四坟河》中开头悠闲的丛林风景变成了后面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之地。亨利·劳森的名篇《赶牲畜人的妻子》和芭芭拉·贝恩顿的《被选中的人》和《尖嗓子的伙伴》等都将丛林变成在虐待、强奸和谋杀中一个无情的参与者,不给受害者提供一丁点的庇护和安慰。澳大利亚早期作家对自然的疏离和不信任渐渐过渡到今天作家们对风景的赞颂,在其中寻求一种归属感,尝试在这片陌生的大陆建立起一种家园意识。这和金塞拉最近的作品相关,他的作品表达出对自然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对土著人与土地的传统关系表达一种尊敬,其作品充满由于祖辈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杀戮土著人的愧疚,体现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白人知识分子的良知。
世代的耕牧会和土地形成深深的依存关系(place-connectedness)。在诗歌《谷仓》中,作者写道:“家族的骨灰,就这样大小,会让灵魂、星辰和土壤各行其道。”[9]351970 年代以来回归自然深得人心,金塞拉本人也从珀斯逃到了澳大利亚西南的雨林里过着公社式的生活,在这片人类新发现的阿卡迪亚中发现新的壮美。他的出生地约克镇就坐落在小麦地带的核心地区,位于天鹅河的上游埃文河谷地。他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片属于 “羊毛和小麦”的风景,关注它们如何受到剥削成性的地主们的影响。他从2009 年至今一直和妻子居住在离出生地约克不远的小镇图吉,除了赴英国讲学外从不曾离开。
格罗特费尔蒂教授谈到生态批评时说:“它反映人们令人不安的意识:我们到了环境极限的时代,一个人类行为的后果在破坏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时代。”[10]小麦地带过度农耕和砍伐丛林导致严重的盐碱化。诗集《谷仓》中描述的主题就是盐碱化带来的诅咒,就如同金塞拉在《相当迷恋》(2000)一书中所说:“土地生态已经被毁灭了,盐是我作品中最突出的意象。”[11]盐成了终年不化的“热雪”意象,在阳光下闪耀着炫目的光芒,刺痛人的眼睛,也刺痛着人的内心。为此金塞拉特意将自创的文学期刊命名为《盐》(Salt)来警醒世人。盐碱化导致一些人家的祖坟上也是盐渍斑斑[11]。在诗歌《为什么剥光河岸边的最后一棵树》中,他鞭挞了麦田地区清除丛林来种庄稼而导致的生态毁灭。“我们清除,那些河岸直到河水,流着红色的尿液,直到盐碱悄悄爬到,周围的水坑。”[12]67“红色尿液的河水”意味着雨水冲刷走了表层土壤,加剧了盐碱化趋势。盐碱化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灌溉和牲畜饮用而修建水坝导致加剧了地表径流。在诗歌《雀儿》中描写盐碱牧场为“水坝的下游/只有盐碱/缓慢的侵蚀”。正如诗歌“水泵/干旱”里面描写那样,盐碱侵蚀的地表围绕在水泵周围。
两股含盐的水流
注入下面的水坝。
一场煞费苦心的
麦田幽会——整个流域
如此精致的雕刻
侵蚀备受钦佩[12]68。
含盐的河水在麦田地区肆虐,整个埃文河流域都受到盐碱侵蚀,麦田和盐河的“幽会”的确是煞费苦心,它们“雕刻着”麦田地区的地貌,盐碱化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生态问题。
金塞拉的诗集《神曲:区域地理之行》(Divine Comedy: Journeys through A Regional Geography,2008)就将为生活多年的约克镇附近的布莱克威尔山以寓言的方式既称为天堂,也称为炼狱,因为人们造成的有害后果有目共睹。他在诗集序言就解释这两百多篇诗章并非但丁的译文,而是自己对于宇宙观的焦虑。他为何焦虑?关注与世代依存至深的生物区域之殇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三、生物区域之愧
为了表明和传统田园诗决裂,他说:“如果空地上的狐狸死了,教堂庭院被喷洒了农药,墓地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外围树丛,体育场上满是闪闪发光的除草剂和农药会怎样?城市窗台花圃上的田园诗可不会革命,只会暗中结盟。我们必须学会切肤之痛。”[13]15结合上文中他呼吁推翻田园诗的剥削和失能的语言来看,他的生态批评的观点确实属于激进派。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环境”的万物平等的朴素思想和“学会切肤之痛”的急迫感,金塞拉要救赎白人祖先欠下的环境破坏的原罪,将良好的生物区域归还于环境和这里的原住民。这些政治倾向激进的反田园诗还有他的诗集《谷仓》(1997)、《狩猎》(1998)和《新阿卡迪亚》(2005)。金塞拉笔下的阿卡迪亚和传统田园诗中阿卡迪亚的和谐和谦恭的旨趣相去甚远。《狩猎》尤其表达了他对于掠夺自然的农耕做法(大规模清理、单一种植和盐碱化)以及驱逐原住民的愤怒。这三部作品都是描写西澳小麦地带(Wheatbelt)生态环境。这是一片和英国面积相当的澳大利亚西南广袤区域,为澳大利亚及世界提供谷物的主产区,也是金塞拉生于斯、长于斯且守护于斯的地方。
“他的诗歌中的人物充满悲悯感染力,常常因为心生愧疚而憔悴不堪,进而产生自贬。这些并不是现实的人物,而是逝去的人,那些仿佛逃离犯罪现场的肇事者一样的人物。”[14]513-514“对于金塞拉来讲,到荒野中不是为了(像梭罗那样)和神恳谈,而是接受荒野的折磨——去感受它的刺痛。”[14]148诗集《谷仓》的卷首语写道:“写诗就是为了忏悔和转移,乡村之行无不联想到愧疚,诗歌主人公都是受害者。”[15]194
为了免于庄稼遭到鸟类的啄食,农民们枪杀和毒杀一种叫环颈鹦鹉的鸟类(因其叫声类似于英语的二十八,故其英文名为Twenty Eights)。
他们拿起农夫的枪
恶毒的人们将麦粒下毒
看着鸟群窒息而亡
鸟的舌头伸得老长[16]66。
在标题诗《狩猎》中,作为主人公的少年和表兄弟猎杀了大量肆虐农场的野猫和野兔,尽管猎杀带来短暂的喜悦,他们还是深感羞愧和负疚,坦白道:“彻骨的寒冷穿透骨髓,烤火也无济于事。”其他类似的诗歌还有:《水手刀》《淹死在小麦种》《鸸鹋捕猎》《收割的拖拉机》《孩童死亡》《南十字星座下面的私刑》,这些诗歌反映了人们冒犯和触怒大自然的后果。由于缺少对大自然的敬畏感,白人定居者贪婪无度的农耕开发造成了土地盐碱化,空中喷洒农药和化肥加剧了土壤退化,更为严重的是殖民者赶走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土著居民。乡村生活没有让人们享受宁静与和谐,而是在利益驱使和技术驱动下变得越来越凶残,招致自然的报复就愈演愈烈了,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性循环。
养羊业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农牧业源头。作为关注生态的诗人,金塞拉在诗集《谷仓》中使用了 “动物迫害”来唤醒对动物们的尊重——作为生物圈的成员。直到最近,绵羊养殖者才同意停止残忍的割皮驱蝇法——剥去活羊的皮避免绿头苍蝇的攻击。在诗歌 《绵羊升天记》中,作者写道:
太阳吸走了浓雾
绵羊湿透的衣服
可以给农民带来羊毛
他们在火边暖着身子
计算着羊的头数和价格
思考着屠宰[16]21。
在另一首诗歌 《风灯:阅读》中,他描写了如何屠杀绵羊的血淋淋场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为动物福利遭受践踏而倍感愧疚。
肋条上裹着的羊毛
挂在锈迹斑斑的晾衣线上,
诡异地拍打着
在灰色的天空下[16]89。
诗歌 《到达荒凉小屋》提醒人们无数的兔子因为皮毛和兔肉在麦田地区惨遭屠戮。事实上,兔子和其他被引进的野生 “害兽”,如狐狸、山羊和鹦鹉都以保护庄稼和家禽的名义遭到了大规模屠杀。因此,在标题诗 《谷仓》中,作者对于动物之殇愤怒写道:
在收获季节
卡车在鬼魂的啜泣中隆隆驶过
咆哮声和凄厉的嚎叫声穿过鼓鼓囊囊的谷仓
令人沮丧[16]59。
农场动物的鬼魂在哭泣,野生动物在嚎叫和咆哮,仿佛他们的内心遭受了重创。这些诗歌就是让人们关注乡村生活的阴暗面——偏见、贪婪、剥削、愚昧和对自然的麻木。
大自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它也会报复人类的愚蠢和野蛮。白人的牲口由于误食有毒的灌木而大批死亡,因为它们没有本地动物的天然抵抗力。这些对于无知的惩罚令农民们迷惑不解,眼睁睁地看着死羊的皮毛挂满铁丝篱笆。
这风景下面暗河翻涌
布满了成片的毒灌木
我们看见整群的羊群死在了地上[16]87。
诗集《谷仓》中多首诗歌描写金塞拉见证自己的多名亲戚在麦田事故中丧命,暗示大自然进行的报复。
十字架在成倍增加
拐弯处就有四个[16]5。
类似的报复还有在谷仓中被小麦吞噬,被拖拉机不幸碾压致死,神秘的孩童走失,来不及抢救而夭折的婴儿等。在失衡的生物群落里这些不幸看似偶然,实则反映出人与自然的恶性循环。通过动物屠杀致使物种丧失,破坏了原有乡村的宁静和谦恭,浪漫化的阿卡迪亚式生活被逐利的殖民开拓者瓦解殆尽,令人扼腕。诗人金塞拉在麦田地区作为见证人感受生物区域所遭受的破坏之痛,通过写诗来忏悔。
四、生物区域之解
修斯戴斯在他的著作《空空荡荡:麦田文学史》中利用 “事件/见证人”的模式列举了费西(Albert Facey)、古 德(Cyril Goode)、波拉德(James Pollard)、尤尔(J.K.Ewers)、科恩(Peter Cowan)、休伊特(Dorothy Hewett)、戴维斯(Jack Davis)、梅因(Babara York Main)、乔丽(Elizabeth Jolley)、弗拉德(Tom Flood)和金塞拉十一位麦田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对于作为人造景观的麦田地区的生态关注。这其中金塞拉集中关注位于麦田中心的自己的家乡约克镇和埃文河谷的生态灾难,反思未来的出路和生态和解的可能性。他的诗歌是对土地的情歌和赞歌,也是土地的宣言。
为了对抗盐碱化,农民们种植怪柳,希望可以降低地下水位,抑制盐碱蔓延。成群的雀类却因此得到了难得的栖息地。年少的金塞拉幻想“加入位于盐碱热雪中的怪柳林里的脆弱的雀类王国”(诗歌《雀儿》),在 “阔嘴莺和红顶知更鸟中间发现宁静,当雨水冲刷过鸟谷,我的内心就充盈了”(诗歌《隐士之歌》)。和鸟雀为伍,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发现内心的安宁,在“荒原”一般的麦田地区这样的奢望弥足珍贵,表达了诗人诗意栖居的美好理想。拆除牧场篱笆,欢迎动物们回归也是弥补失衡的生态关系的举措。“我们熟悉地走遍牧场每一英亩,袋鼠们认得我们,逗留不走”(诗歌《我们在此屋小住》)。诗集《果酱树山谷》中有几首诗歌也是描述这样的 “解放姿态”,这也是恢复牧场生机的关键步骤之一。袋鼠在原来放牧牛群的地方逗留就是这种处理方式转变的证明。
端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当务之急,应放弃人类中心论,以平和的心态和平等的眼光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全世界的秋千不过是钟摆而已”(诗歌 《果酱树山谷》),“在那些自称为技术先知的人中可没有救世主,他们那一星半点的慷慨不过是长袖善舞的有钱的上流人士在轻松挥手”(诗歌 《轮回祈祷》)。诗人的谦卑态度和殖民开拓者的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诗歌 《蜂房自由》中诗人捍卫蜜蜂自由筑巢的权利,警告家人不要那么傲慢地接近蜂房,“我警告家人不要那么接近蜂房:好奇又傲慢,我确定讲清楚并且成为蜂房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共存”[17]33。
万物平等是生物区域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金塞拉对于本土物种和引进物种同样视为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没有厚此薄彼。上文坚定捍卫引进蜜蜂的“蜂房自由”就是明证,本土蜜蜂在地洞筑巢,而不是树枝。他认为那些野生的狐狸、骆驼、山羊、猫狗不是害兽,不应该被乱棍打死。诗歌 《山羊》写道:
对于我们,它只是一只该活的山羊,
城里别动队见到就恣意猎杀的确可笑,
随着推土机开进丛林,新房屋竖立起来,
为了奶、肉和纤维养在圈里的山羊掘出草根来觅食[17]27。
在群落中,生物共生互栖,互利互惠。倒塌干枯的约克桉树就像 “失去物质的星体一样空洞”,被白蚁蛀空 “一圈圈的年轮”,成为野蜂的巢穴,它们在树洞中涌出,“狂乱紧张地进出这些裂缝”[17]33。在诗歌 《抵达果酱树山谷的第一行诗》中,诗人描写这种鸟、树和寄生植物之间有趣的共生互惠的关系。
褐嘴莺在此!槲寄生的鸟
已经在槲寄生果实成熟的地方,
为果酱树播下种子,那里
各种渴望花蜜的鸟儿
考验着花朵
在各色紧绷着的瘦长鸟脖子下面下垂着。
这种寄生会产生一个链条。
我可不想成为一部分,随着时间
有东西会滴答作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18]。
在干旱的麦田地区,水箱的漏水关乎生死,在混凝土的裂缝处藻类丛生,酸橙树茂盛,层层叠叠的矿物和植物在裂缝绝处逢生,引得刺嘴莺来喝水筑巢。
在反思技术中心论的种种弊端的前提下,诗人倡导无为而治,“在悬崖顶端和行人稀少的变幻莫测的天气中,精通技术的城市诗人不想知道太多,他们的感受是否被记录下来,谁会去那里”(诗歌《转世祈祷2:羊头半岛之巅》)。“不管多少人曾经侵入过这里,我们都没有权力呆在这里,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另一次入侵。我们是访客,是闯入者,一定要把权利归还给土地的传统监护人(土著人)(《分水岭:关于西澳麦田从约克到格蕾丝湖的埃文河流域的谈话》)。”所以,诗人要学会“ 拥抱清冷的早晨带来的刺痛,鹦鹉的翻飞、狐狸的尖叫和兔子的实用”[18]55,尝试和这里的生物区域融为一体,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学会切肤之痛”之后,金塞拉尝试通过号召植树造林来缓解盐碱化,恢复土地原来的生产力,打开牧场围栏来恢复动物的栖息地,营造更多的良性动物生存环境,在和谐共生的生物群落中救赎原来殖民开拓者犯下的生态原罪。
五、结论
金塞拉关于麦田地区的生态诗歌创作独树一帜,突显其在区域生态遭到破坏后的痛心疾首和痛定思痛的感受,在愧疚之余,努力找到生态和解之路。他的诗歌创作都是向大师致敬,表达对生物区域主义的坚定支持。《谷仓:田园交响曲》是向贝多致敬,《新阿卡迪亚》是向维吉尔致敬,《神曲:区域地理之行》是向但丁致敬,分成“地狱:近距离”、“炼狱:决裂”和 “天堂:休闲中心”,形容麦田区域生物群落生活在极端的环境中,诗人的妻子崔西·瑞恩作为他的导师和向导带领他穿越地狱,通过生态和解奔向 “诗意栖居的”天堂。《果酱树山谷》是向梭罗致敬,诗人并非寻求在麦田里和神恳谈,而是希望作为见证人呼吁公众关注生物区域的福祉。
本文结合生物区域主义的理论作为框架,探讨澳大利亚生态诗人金塞拉的诗歌创作,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他激进地反田园诗创作的倾向。他认为传统田园诗中有关乡村环境的浪漫化和怀旧情绪对于环境保护有害无益,应该摒弃。他用诗歌反映盐碱化、动物屠杀和物种丧失等痛心现象来惊醒世人,呼吁通过植树造林来缓解盐碱化,开放围场欢迎动物的回归使得动植物能够互惠共生,尝试在麦田地区建立家园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