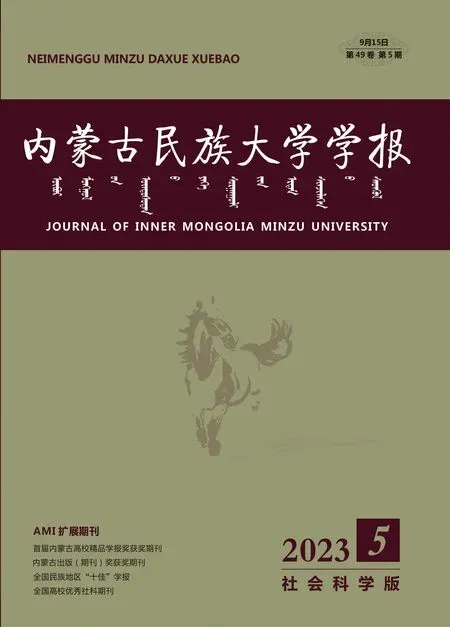古人的自然认识与生态伦理思想考述
萨其拉,那仁毕力格
(1.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杂志社,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内蒙古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中国古代有“不事而自然”“无为而自然”之说,体现了古人“凡是无意识的、非人为的、不假于人之力而然者都是自然”[1]的认识。自古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复杂多样,涵盖着自然认知的多重涵义。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通过人脑反射出本源、本质、价值,实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功用。人适应于生态系统并且适度索取自然资源的双向性关系,既是本质统一的本体问题,也是透彻认识自然规律并且采取社会行为的根本基准和价值体现。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
人类从自然万物中获取所需的资源,这不是单向性的索取行为,而是饱含适度索取自然资源和合理保护生态系统的双向性关系。人类置身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不断积累着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互惠互利、共生同存的知识。古人以“天人合一”的表述来体现自然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知范畴里矛盾统一的哲学论题,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古鉴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将为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方案。儒家的生态伦理的特质,与仁、义等儒家基本观念有密切关系。儒家生态伦理不是一种补救措施而存在,而是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2]由此可知,古人的自然认知与生态伦理意识相应呈现了万物和谐共生的社会伦理思想。
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指自然与人的辩证、共生、相谐的关系,具有“天者广大自然,人者最优异之生物”[3]之义。《诗经·大雅·荡之什》载入周宣王时期的尹吉甫《烝民》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4],表达了人是天之所生,有物象也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好善美品德的思想,既从物质和精神的哲学关系说明了人的德行源于物质基础的本原问题,也从万象之间“物统事理”的哲学视角阐释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念。“天人合一”观念起源于西周时代,多层含义都与自然界有关。张岱年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一文中认为:“人遵从自然规律是天道、也是天和人的协调。”[5]道家对这一论题也有“天人合一”的哲学阐释,包括三大要义:“一是对大自然的热爱;二是对事物存在多样性的尊重;三是对个体感性生命的珍重”[6],这些论点清楚地解释了人在生态链条中作为重要一环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张载《西铭》有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7]1,张载《语录》有言:“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7]269—270,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人是自然万物中“一物”的唯物观念,形象地描述了人类是“天地”的产物之义。天地之道涵盖万物生成的、物质的、结构的规律,被称为万物之母。天地之道既是自然规律,也是万物之变的本质,衍生出包括人类在内,万物皆为同类之义,这是古代人与“天人合一”之说相辅相成的对自我起源的解释,体现着万物同根同源的认识本原。
张载的《正蒙·参两》进一步解释了生成万物的阴阳结合规律,以阴阳循环和万物荣枯来比拟自然规律[7]31,对万物以“阴”“阳”二元对立统一规律为前提,通过阴阳的相兼相制,从生物学角度解释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辩证规律,呈现了事物产生的本原理路,体现了自然界与人类共同遵循并且往来互动、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其他史料也载入了与此相应的认识。《宋史》记载,古人认为,克服人的私心并且知晓万物的存在,就是“天人合一”之道[8],折射出对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认知。《荀子》从更深层的法理讲述“天行”的规律、不因人为而改变之道[9]109:修养德行之人不会遭遇天灾的吉凶之道;节约资源是循环利用资源的途径之一,这样就不会造成寒暑涝旱等灾难的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史料中涵盖了古人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应当采取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治理措施、裁择其他物类来奉养人类的自然生态认识,以此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
从哲学的范畴来审视古人对生态链的认识,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辩证关系。古人通过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来感悟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形式、作用以及万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自然界在时空维度上规律运转,呈现在空间维度上保持相对静态、在时间维度上保持绝对动态并且持续更新的存在形式。万物在地球的自然地理空间之中的盛衰荣枯,是在时间维度上以季节为周期的相对动态的循环往复过程。人作为万物之首,一方面站在遵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的立场,与万物共同进行循环往复、更新换代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对自然界的普遍规律适度发挥能动作用,改善人类自身的生活条件,丰富日常生活的内容。
二、“必依山川”的生态伦理意识
古人对“天人合一”的生态认识,源于自然、回归自然,与“必依山川”之说相呼应,体现了古人生态伦理意识渐进提升的过程。一些人认为,没有经过加工、没有添加、没有被污染的,持有原生性“自然”状态的“东西”才是“自然”(nature)。实质上,人类只有通过演绎、范式化、人为操作等过程,才能在人类认识里产生抽象的“自然”概念。额尔敦高娃和那仁毕力格在《建构蒙古族传统生态观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古往今来,人们对“自然”的定位和解释呈现出的差异,取决于人们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意识,在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实践活动中,也体现了不同情况[10]。古人的生态伦理意识说明,在人们的伦理意识范畴之中,儒家认为物性由天地所生,道家用万物之德来表述物性[11,12]。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既体现了理性的一面,又蕴含着古人的朴素认知因素。古人以自然万物之中的物种(例如山川、树木)作为载体,体现了当时的生态伦理意识。
西周时期产生的“必依山川”之说,比“天人合一”更为具体地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形象的”和“抽象的”认识区别,饱含了古人认为“山川”对社会生活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的生态理念,古人认为,“山川”同国家的兴旺发达具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周幽王二年(前780年)伯阳父所述的内容[13]146除了涵盖古人的信仰意识之外,还体现着古人认为自身同山川共生共存的生态伦理意识,将保护山水上升到关涉自身生死存亡的高度。古人已经知道维系自身生存“必依山川”,并且认为“山崩川竭”是“亡国之徵”的生存法则,“必依山水”“天人合一”“天父地母”的具象化认识将自然万物与人类自身的距离最小化,并且体现出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伦理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苌弘对刘文公说:“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14],说明了周朝的灭亡以“川震”为先兆的情况。西周时期的伯阳父形象地描述了山崩地裂、河川干枯与国家存亡之间的关系,认为国都应该建造在依山傍水之处,宗庙社稷应当建造在山顶水源之处[15]。由此可见,古人对自然认识经历了从宗教信仰到生态伦理意识的逐渐演进的过程。
生态链条中与人类生活关系最直接的是“山”和“水”。周朝人已经认识到“山川”的重要性,不仅谈到“川竭必山崩”的自然万物互联互依的自然内在规律,而且以“国”“山”“川”三者的关系呈现了当时的自然观。古人的这些认识体现了与人类生存密切联系、与国强富民息息相关的社会功用思想,在哲学层面深度体认“山”和“川”对国家兴衰和百姓贫富的重要意义,与古人自然认识密切关联,体现了古人依靠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千丝万缕关系的古朴的生态伦理意识智慧[16]。
西周是人伦思想的萌芽期,陈晓云和陈立柱在《说“国必依山川”》一文中认为,西周“开始了中国历史理性认识的新时代,人们已能从现实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人的作用值得重要。”[15]用“必依山川”,以及“山崩川竭”来描述国家兴亡,是古人形象思考的映射。《荀子》记载,“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9]123古人认为万物的成长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只认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是无法全面了解自然规律的。在认识论范畴,古人将自己视为自然万物的一员,涵盖了古朴的本体认知思想,对本源的认识,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蕴含着生态哲学的古朴含义,映射着人与自然万物相谐而共生同存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对早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概括,认为人类认识自然的原点是自然界万物或者物象[17],是对“山”“水”“动物”“植物”的感知性形象认识,是物性和感性的简单结合,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互链关系,这是人对自然的生态性认知的升华过程。孟子的人性观认为:“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18]。古人用杞柳和桮棬比拟人性和仁义,犹如图腾信仰,形象地将自然万物赋予人伦意识,成为各种活动的伦理基准[19]。“必依山川”是以山水为具体生态载体,从生态系统内在联系出发而提出的生态本位思想的结晶,关注生态破坏而导致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
三、以古鉴今的价值取向
古人“天人合一”和“必依山川”的认识在“与物同体”“爱惜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上得到体现,表达了自然万物“同根同源、互惠互利、共生同存”的生态哲学的深层含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具有“以古鉴今”的时代价值。
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劳动过程中与自然逐渐产生依附、加工制作、过度索取的二元哲学关系。在生态哲学范畴中,人类早期受生态环境的制约,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华均和刘玉屏在《从古代蒙古法中蠡测游牧民族对生态的保护——兼谈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文中认为:“由生态的人到社会的人的转化时期,人类经历了由适应自然、尊重自然到利用自然的漫长时期”[20],当今社会用“生态文化”的概念就能够关联各种社会制度、伦理道德、文化含义。古代儒家自然认识的核心思想是“天、地、人”三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仁民爱物”的生态善性原则。《论语·述而》提到了伦理道德与抽象认识结合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1]的生态伦理意识,意在告诉人们不能把野生动物赶尽杀绝,要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使它们繁衍生息,人们应当以仁爱之心待物,这样才能可持续地获取利益。《周易·系辞》认为,阴阳相反相生,运转不停,是自然万物盛衰荣枯的本源[22]360。由阴阳之道衍生的人类仁德之见,既是善行的根本,也是人的智慧结晶。张新民在《先秦儒家的生态哲学观——以“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观为致思论域》一文中认为,这是“提倡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一种生态智慧和思想”[23]。葛根高娃和乌云巴图在《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一书中认为,“以自然为本”的自然认知逻辑和“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哲学含义具有相似之处,关涉生物盛衰荣枯的自然规律,涵盖生态自我恢复和人类适度索取资源有机结合的生态伦理意识[24],这就是对自然资源适度保护和利用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用阴阳之合、万物生长的规律来描述内在关系[13]1926,“天人合一”之说通过儒家和道家的人与自然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哲学概念,展现了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25,26]。古人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在深层次上源自天道本体,与天的“阴阳对立”、地的“刚柔相济”的统一规律相呼应,人的社会生活以伦理意义来体现天地之德。古人“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以宇宙论的“天人合一”为学理基础,张新民在《先秦儒家的生态哲学观——以“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观为致思论域》一文中认为:“天道和人间的秩序一体不二,人文秩序根本就不能脱离自然秩序而凭空发展,也不能脱离与人类‘仁’与‘义’行为,亦即以人性为基本依托的社会伦理德德行为。”[23]对生态的认识方面,儒家思想涵盖着爱护自然万物这一核心要素,《孟子·尽心章句》谈到了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之理[27]。包庆德在《天人合一生存智慧及其生态维度研究》一文中认为,道家“尝试克服人在实践中可能对外界环境造成的根本性影响。”[28]古人形象地认识自然万物,带有在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推崇爱护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意识。
古代哲学的“与物同体”的本体认识论包含“以自然为本体感知并不离所指意蕴的辩证逻辑”[29],古人的生态伦理意识取决于自然认知的哲学意象。在生态伦理观方面,自然认识和生态伦理意识既克服各自的局限,也互鉴互融。“天人合一”和“必依山川”的自然认识和生态伦理意识充分体现了古人对生态环境的关怀,吴丽娟在《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变迁中的体系危机与维度转换》一文中认为:“巩固并内化了对自然的亲情意识和自然之子认知;知恩图报的感恩意识;对自然具有义务意识的天人之约观念;对自然的善恶观的推己及物思想等朴素生态伦理意识”[30],渗透在生态保护法制和约定俗成的各项习俗文化之中。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生计常识和符合生态链顺畅循环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世代相传,成为有效、合理、适度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伦理知识。
《周易·文言》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22]350之说,这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理想存在方式,包括阴阳对立、先天与后天之别等内容。这里所谓的“先天”,是指自然规律的前导,在未发生自然变化时加以引导;所谓“后天”,是指遵循自然万象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人类需要适度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古人的自然生态认识呈现着本真特征,以古谈今会对当前对自然的认知和生态伦理意识带来回望、启迪、重构效应。以自然和人的相谐为本,以爱护自然、保护生态链、遵循自然万象更新规律为行为准则,以信仰和禁忌习俗为前身的习惯法、成文的律法规制渗入生产生活,构成有机生态链,有效地保护生态平衡、遏制环境破坏,遵守自然资源循环再生规律,是人类早期生态伦理意识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古人的实践活动时常体现对生态的脆弱性、修复的缓慢性的关怀伦理意识,动态地、适度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重视自然资源的恢复规律,主张人与自然相谐相处,并且颁布法律或者律令,遏制滥杀滥伐、滥挖滥采、过度索取自然资源等破坏生态链的行为。古人采取以自然为本的生态性经营方式,具备了“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是古人生态伦理意识的主要驱动力,有效地约束了贪婪索取和过渡利用自然资源的不合理行为。
四、结语
大自然既是能量的宝库,也是生命的源泉,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各种资源。人是生态链条中的一个节点,通过社会活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多重关系,“天人合一”和“必依山川”之说是古人认识自然的起点。人顺应自然生物的繁盛荣枯规律,与万物相谐而共处,是从古到今流传的生态伦理道德。古人的万物和谐共生思想是生态伦理意识的本源,含义深沉而厚重,是在万物“同根同源”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古朴哲学。张节末在《禅宗美学》一书中提出:“自然并非无关于认知主体(人)的单纯作为认知客体的自然,它是在人的感官和智慧谛视之下的自然。”[31]古人认知中的“自然”,在哲学范畴里用“天人合一”来表述,体现着以“必依山川”为主要载体的生态伦理理念,说明了“川竭必山崩”的自然万物互依互联的关系,阐明人类生存“必依山川”的深刻关系。人在与自然的多样关系方面,既遵从自然的普遍规律,又对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能动地、适度地发挥作用。“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价值理念,在战略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上呈现出“以古鉴今”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