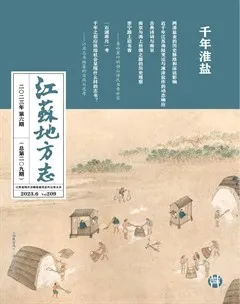乡愁小记
◎凌 子
(江苏苏州 215200)
牵肠挂肚,乡愁浓浓又淡淡。是时间沉淀成记忆,是乡土气息与乡间土灶上的烟火气萦绕心头。肠胃有记忆,童年多野趣,乡愁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回望与回味。炊烟袅袅,乡愁系于味蕾。咀嚼蚕豆的快乐,夏日小桥下垂钓的闲适,农忙时节农家“饭菜一锅熟”的紧凑情景,仿佛就在昨日,下笔已成记录。
“吴江青”
翡翠青,立夏的蚕豆,活色生香。清炒嫩豆子,撒一把细杆香葱,青葱一片;剥开,一瓣瓣,温润如玉,加入腌苋菜,煮汤,鲜爽啊。
是“蚕时始熟”而名,还是“豆荚状如老蚕”故名?脱不了活生生的蚕桑印记。记忆中,蚕宝宝食桑叶日长夜大;我们的童年,在咀嚼着蚕豆的快乐中逐渐长大。
蚕豆枯老了,豆粒呈现陶瓷般光泽,那是阳光把“天青色”投射在豆壳上?色彩学上由此多了一个专有名词“豆青色”,令人遐想。
老蚕豆爆炒,喷香,咬得牙齿咯嘣作响。老婆婆望豆兴叹,小孩子们则欢天喜地。夏至的阳光特别慷慨,嚼一把端午的“炒现豆”(加入点盐水则成“盐津豆”)则格外过瘾。
年少时就学于小镇上,学校不远处有座“梅兰桥”。但吸引学生流连的,不是“梅兰”,更非“站在桥上看风景”,而是那一小包“麻子豆”,用裁成小方块的旧报纸包得有棱有角,恰似迷你的三角粽。报纸隐隐透着油墨香,而“麻子豆”粒粒精致,释放出浓郁的甘草味。“麻子豆”亦茴香豆也,炒制者人称“麻子”,和善而微胖,四五十岁光景,手艺是祖传的。当在《孔乙己》中读到“茴字有四种写法”时,惊诧,经典不远!小镇另一处,也是在桥堍,有“老虎豆”,气派大些,开始称斤售卖。改革开放了,我们初中毕业了,也就极少光顾“麻子豆”“老虎豆”了。
一度为小镇茴香豆的“小”而汗颜。看看人家大上海老城隍庙包装讲究的茴香豆,何其高大上——扁阔,栗黄色,且有奶油香味!后来明白了,人家的品种叫“牛踏扁”,而家乡的蚕豆小而紧致,细腻而玲珑,特谓“吴江青”。别有风致“吴江青”,是小家碧玉,可能也是“同桌的你”?
中年时进县城,居住在东太湖畔,曾经陌生而遥远的吴江“西横头”亲近了。“西横头”就像浙江温州,重商,敢闯。计划经济年代,摇着船,贩卖农产品。印象极深的是大头菜和大白菜。大头菜腌制,暑天当粥菜,开胃。大白菜被当作“年菜”,买回来还要包裹好,悬挂于屋梁上。香大头菜肉丝汤,鲜洁无比,今天还向往;大白菜不稀奇了,不过“青菜”一族而已。

吴江香青菜
青菜是菜中百姓,不稀奇,更不贵。此番引起我注意的是西横头的“香青菜”(现已打上地理标志,不免“名贵”)。香青菜特征鲜明,叶皱,叶缘锯齿状,叶脉细而白,密布叶面,犹如绣花筋。筋织成锦,因而又作“绣花锦”。当年,无所谓,看着偌大棵的香青菜,谐音,想当然呼作“瘦八斤”,可能是由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联想出来。“肥美”为上,“瘦八斤”上不得台面,不受待见。想不到风水轮流转,今天是“素美”时代来了,香青菜一下子逆袭成了香饽饽。炒食,糯而香,香而鲜。尤其是经霜后,淀粉转化为糖分,那个味,难以割舍。是好风水成就了好品种,东太湖西南岸,空气、水分得天独厚,而独特的“小粉土”何处能寻觅!小粉土俗称“夜潮泥”,有点浪漫吧。
“口音难改,口味亦然。”吴江人口中的费老(费孝通)念念不忘“乡味”。他曾写道:“我们家乡特产一种小茄子和小黄瓜,普通炖来吃或炒来吃,都显不出它们鲜嫩的特点,放在酱里泡几天,滋味就脱颖而出,不同凡众。”费老所言的家乡特产小黄瓜,最著名的要数平望酱黄瓜,又称酱乳瓜。黄瓜青色,也有乳黄色的,但作酱菜多用青乳瓜。而今列为“中华老字号”的平望酱黄瓜,有上百年历史,工序繁多,产品需经“百日”涅槃,味至淳厚,色转深黛方成。20 世纪50 年代,作为特殊军需品,运送到前线慰劳志愿军将士。
吴淞江,吴江的母亲河,牵引湖海,继本来,开未来,本色永葆。如果作一幅江南写意画,很可能是“小桥流水乌篷船,粉墙黛瓦青石巷”;如果用一个典故为“吴江青”作注,那一定是“莼鲈之思”,秋色满东南,风流千古。
钓夏
真闲静,夏日午间,水面上银光闪烁,那是风与阳光在切磋。农人们珍惜这难得的一刻午休,小孩子却不安宁,趁机溜出家门。
村头水泥桥下,荫凉。石块砌就的桥墩坡,硬生生辟出一方独立天地——坡陡峭,需攀爬,但一到桥底,就有大块大块的护坡石,突出水面,可立,可蹲,有的还可坐。小桥不远处,有竹林,小屁孩们如小麻雀群集,喧嚣纳林间。

小溪穿石桥
桥下,通常只我一人世界。我的年纪有点尴尬,向上够不着“半小子”,向下不屑与“小屁孩”为伍,就像鱼漂漂浮在水面,既入不得水,又上不得天,只能独自“钓夏”。
钓虾最妙。用一根细竹篾,甚至可以用一根细线,系上一粒螺蛳肉,放置在石隙口,轻轻晃动几下,不必操心,很快虾须探出来了,过不了多久,长长的虾钳也伸出来了。水面宁静,时光如在打盹。只要有小小的耐心,虾总会全身出洞。这时,轻轻牵引,小抄网悄悄一抄,晶莹如玉的虾就到手了。更多的时候,不讲究,就用小竹匾甚至是淘米箩“抄”,基本十拿九稳。虾一被抄起,如梦初醒,急急地跳,眼前便溅起一个个灵动的星星。河水清澈,流经桥墩时隐隐拉出婉转的水纹,虾能感知,它们在石隙中潜伏。
小虾太单薄,也喜欢凑热闹,但钳不住螺蛳肉。就像鳑鲏鱼闹钩,不受抬举。我要钓的是大虾,抱籽大虾,品质好,但不是重点。引得钓兴的是大雄虾,背壳发亮,须长而有力,钳宽大威武泛出金属般的蓝光,戏称“老拇钳”。“老拇钳”城府深,轻易不上钩。虾须出没,虾身就是不出洞,可谓神出鬼没。试探过几回,终于伸出长长的钢钳,夹住螺蛳肉,有时一用劲,直接夹劫去了。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就着婉转的水纹,来回逗引,引得“老拇钳”晕晕然,一发狠,全身“冲”出洞,早早伺候的网抄起了。好多回,我与网中的“老拇钳”对峙,大青虾那油菜籽般光亮的小眼珠鼓凸还打着转,仿佛昭示一百个不服气。钓趣尽在其中。
稍长后,看过齐白石水墨画《虾》,有所触动——虾们才是真正把画画在水中的画师。不过白石老人的虾画得密集了,我记忆中的钓虾情景清朗而利索,画面中央就一只大青虾“老拇钳”,至多陪衬两三只白玉柔须的少年虾。
不知何时起,龙虾横空出世。大多栖居水渠、水坑。龙虾粗糙,一身坚硬的盔甲,头盔硕大,双螯如戟。炎炎午日,龙虾藏在洞中,从那洞豁口,一眼就能看到露出的虾须。一吞吐,水变浊,原形毕露。最初的一段时间,仅是好玩,用细竹棍捅一下,龙虾便缩回去,缩得太猛,便弹出来,竖直眼球,愤愤然,一副呆霸王相。待盱眙龙虾以各种口味闪亮登场,才省悟这玩意儿也不赖,大可大快朵颐。对付龙虾,乡间顽童多用“赶网”粗鲁捕捉,偶起雅兴,也钓。只是这回的钓直奔主题,饵料,更多时候是“空饵”送到龙虾跟前,这呆霸王一困惑,一发昏,两只大钳连竿一并钳住,真是狠角色!龙虾煮熟,一袭大红袍,气派。
无钩钓夏,钓田鸡。田鸡是青蛙属的昵称,言下之意,滋味妙如鸡。当年的田野“野”,孩童也“野”,抓青蛙谈不上破坏。蛙眼偌大,光亮,但对静止的物体几乎如盲,视而不见。看到眼前活动的小东西,舌尖如簧,飞速出击,也不辨青红皂白,想当然以为是飞虫一类的美味。因而,只需用一根细长的稗草秆,就可直截了当地“钓”。稗草秆梢,掐留得一小穗,状蠕虫。发现田间草丛中的青蛙,悄悄探杆过去。一抖一抖,引得蛙儿跃起,一口咬住秆头小穗,迅捷提入敞口箩头中,猎物到手。特大个头的青蛙,我们称之为“戆鸡”。钓到“戆鸡”,别提多带劲了。
也可如钓虾一般,用一根细线系上饵料钓田鸡。饵料有点残忍,有时干脆就用一条剥了皮的小蛙腿,“戆鸡”就好这口。多半时候,我们就着水渠、田埂草丛,胡乱钓,不愁没上钩的。上钩的往往是灰不溜秋、小不点儿的小田鸡,孩子们称它为“麻姑田鸡”。恰似小癞子,与“青蛙王子”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小麻鸡特别多,饥不择食,不多时间就能钓上一小兜。喂给鸡鸭吃,鸡鸭吃了,生的蛋特别大,尤其是鸭蛋,双黄,腌制后油多,蛋黄呈朱砂色,好不诱人!
田鸡无辜,鸡鸭也无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乡野渐远,童年的“钓夏”沉入梦底。间或一激灵,化作水花,化作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一只只,跃然。
一锅熟
炊烟袅袅,乡间土灶。土灶上安大铁锅,俗称镬子,结结实实。
南方小年夜腊月二十四,家家蒸团子,用大劈柴,硬柴旺火,灶膛亮堂堂,灶面热气腾腾。团子出锅,点上红印记,那真叫喜气洋洋。
烟火气催生镬子气,当年农家,灶台便是家的中心。难忘饭菜“一锅熟”。
计划经济年代,油米金贵,柴也得节省。或许食材贫乏,或许劳作艰辛,善持家的农家主妇,总在劳作一天后来个“一锅熟”,省料,快捷,但“镬子气”太重,火候不到位的话,就成了“整锅闷”。记得母亲有时把大青菜放在饭锅里一起蒸,为了省那一把柴火,结果,大青菜像染了病,又蔫又黄,水酷酷,毫无菜味,但也是无奈。双抢大忙时节,捞一把螺蛳,随锅一炖,也能让农家汉子就一口烈酒,吃得津津有味。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江村文化园内灶台图
“一锅熟”都用竹制的蒸架,如“井”字,一格可置一碗盆,用来蒸团子、糕点最合适不过。再捏几个小塌饼,贴在锅沿上,乘机一锅熟。
不得不提的是一道农家菜法宝——农家自制“大酱”。大酱多用大豆(蚕豆或黄豆)作原料。对于农家生活而言,酿制大酱(俗称“合酱”)是件大事。清代苏州风俗志《清嘉录》有专门条目介绍:“谓造酱饀曰罨酱黄,饀成之后,择上下火日合酱,俗忌雷鸣。”籍贯吴江的费孝通先生在回忆“乡味”时,亲切地称“这酱缸是我家的味源”。洁白鲜嫩的茭白、光滑紫亮的茄子,上锅一蒸,蘸点大酱,绝对的美味。也可以将食材裹上大酱直接“一锅熟”,油汪汪,香喷喷,彻底征服你的味蕾。
秋收过后,临近播种冬麦,这是小孩子们最快乐的时节。牛犁田的时候,孩子们就跟在铧犁后,捡拾泥中翻出的野获。有野荸荠、泥鳅,最惊喜莫过于捡到小黄鳝。黄鳝细长,阳光下泛出金属一般光泽,昵称“金丝黄鳝”。金丝黄鳝肉质特别紧致,酱炖的话,鲜美无出其右者。
记忆中,家乡的一锅熟总能把不同的食材炖出各种各样的美味,蒸土鸡蛋、炖丝瓜汤,道道爽口开胃,就连咸菜豆瓣汤也能炖出独特的味道来,更不消说那些鱼肉荤腥。如今,当年那些食材已不再那么难以取得,却很难再找到那种对一锅熟的期待感和镬子气熏蒸下的满足感。
苦中作乐一锅熟。回望炊烟,忽记得土灶蒸团子有一禁忌:不争气,蒸不透;回落水,塌台面(团子塌馅)。把握火候,才能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