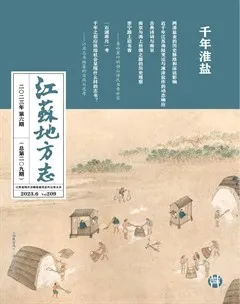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讲张”:苏州城的前朝梦忆
◎陆浩斌 沈 阳
(山东济南 250100)
幼时,在外婆家午觉醒来,外婆总会打趣道:“从苏州回来咧。”这其实是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睡觉怎么会和苏州扯上关系?不过,外婆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在她小时候,也是这么听来的。而在奶奶家,总是听奶奶说出一个叫“gang zang”(前字一声,后字四声)的词语,它是聊天的意思。那个时候,总觉得这个词很土,因为这个词和普通话对应不上,以为是“深乡下”里流出来的词汇。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读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了解到,儿时颇为困惑的这两句话,背后竟凝结着吴地百姓数百年来的血泪忆痕:元亡明兴之际,朱元璋和张士诚争霸江南,成王败寇之后,江南地区和苏北片区,就开始流传着“梦赴苏州”和“讲张”这两个话语。
对于张士诚,朱元璋曾如此评价:“且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唯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1]
张士诚究竟是何人物,让吴地百姓如此缅怀,让昔日对手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一
元末乱世,张士诚一介布衣,以不辨顺逆,敢问天命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而弓手丘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高邮守李齐谕降之,复叛。杀行省参政赵琏,并陷兴化,结砦德胜湖,有众万余。元以万户告身招之。不受。绐杀李齐,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僣号大周,建元天祐。是岁至正十三年也。……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士诚自高邮来都之……二十三年九月,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2]
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建都苏州。至正二十七年,苏州城沦陷,张士诚统治苏州共12 年。作为逐鹿天下的失败者,张士诚必然受到胜利者的压抑和丑化。但从存史材料来看,其在安置流民、减免田赋、整顿吏治、疏浚水利、通商外藩、礼贤下士等方面,颇有建树:
张士诚起兵,招纳流移,安抚百姓,盐城流民大半归家。[3]
(田赋)悉免夙逋。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并赐高年粟、帛及贫民粥糜。[4]
泰定间,周文英奏记,谓水势所趋,宜专治白茆、娄江,时莫之省也。士诚阅故籍,得文英书,起兵民夫十万,命吕珍督役,民怨之,及役竟,颇得其利。[5]
太尉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不烦一兵,强远自格,天人咸和,岁用屡登,厥德懋矣。[6]
在群雄并起中,张士诚治下的江南颇有一番乐土气象。对于张士诚保境安民,元末明初文学家高启更是大发感慨:“今天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6]有此间乐土,士人“争趋附之”“富贵赫然”。[7]
张士诚治下,值群雄争霸之际,虽然外部压力带来社会治理成本上升,但苏州一地税收,与元仁宗时的八十万石相比,也只是增至百万石。与稍前元廷所据时的横征暴敛相比,则大为宽减,汲取并不苛刻。彼时,张士诚虽接受元廷名爵,但并不听命,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顾祖禹道:“元之复亡,未始非士诚先据平江,竭彼资储之力也。”[8]
二
破陈友谅后,朱元璋发布《平周榜》,进攻吴中。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平江城破,张士诚被俘至应天,自缢死。朱元璋随后对支持张士诚的吴地官绅百姓进行了惩罚。首当其冲的是张士诚政权的高官们:“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9]紧随其后,朱元璋又对苏州城中的富民下手:“(九月)克平江,执张士诚。十月乙己,迁苏州富民实濠州。”[9]最后,明政权则是不分贫富,大规模往濠州进行人口强徙,“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10]当然,其中的移民人口并不仅限于苏州,而是囊括了张士诚治下的百姓。明代谈迁《国榷》载:“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
由于是强制性的迁徙,暴力手段自不可避免:“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谴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11]沿途,或死或伤或哭或号,不难想象。
关于苏州人口大规模强徙濠州之事,于《明史》等官史可见。而更大规模的强徙苏北,则未见于官方记载,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族谱、县志来寻蛛丝马迹:
灶户以吴人居多。相传张士诚久与王师对抗,明太祖怒其顽固,恶其民而迁之,摒弃于滨海,服以世世劳役,藉以侮辱之。[12]
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13]
据曹树基估计,洪武年间,苏北共接收移民81.4万,主要来自张士诚所治旧域百姓,而最大的一支则是来自苏州地区,后世称之“洪武赶散”。[14]

阊门寻根纪念地碑(陆浩斌 提供)
离开繁华的姑苏城,迁居荒芜的江淮,故地从此成梦乡,这些流散的苏州故民饱含血泪心酸,只有冀望于梦中回到故土,故有“梦里赴苏”的地方俗语。在今苏州阊门立有“寻根碑”以为追念。
出生贫苦的朱元璋,对于苏州城中的富户豪民,或有着切齿之恨。他曾借助各种政治案件,查抄、洗劫江南财富。当洪武之末,不幸坐累者,举族谪戍边徼,第宅荡然。
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湛族,三世不宥。[15]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2]
洗劫豪民、人口大规模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朱元璋去世三五十年后,苏州城依然一片萧瑟,“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16]朱元璋对于苏州百姓的报复远不止于此,“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对于苏州(并松江)施以重赋,使得“吴民世受其患”[17]。
三
洪武七年(1374),苏州知府魏观,因迁治所于张士诚王府旧基而遭诛,受之牵连的还有江南文坛领袖高启。苏州作为张士诚“蛟盘之地”,朱元璋又加之重赋强徙,自忖颇不得人心,任何唤醒张士诚统治记忆的举动,对现政权而言都可能是在聚气谋逆,挑战皇权。作为统治者,自然对此非常警觉。事实上,这样的警觉也并非无的放矢。明代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三记载了一则故事:“高皇(朱元璋)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明末钱谦益记载了苏州城中深厚的张士诚记忆:“余尝过张士诚故宫,废墟残堞,鞠为茂草,有足悲者。及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概。”[18]
所谓的“讲张”,在今天吴语方言片区中,是“聊天”的意思。而“讲张”意同“聊天”,并没有直接的原委。明代,人们只能通过窃窃私语的方式“讲张”。明清鼎革之后,百姓就不必藏着掖着了,人们对张士诚已然偏向神格化:
张王庙在娄门外塘南,祀士诚,又有(张)士信庙在后。[19]
王没后,江浙民立祠祀王,事为明太祖所知,民乃以金饰王容,托称金容大帝;或赭王容,称朱天大帝。后更称都天,托之于唐将张巡;或称周王,托之晋孝侯周处;亦或称行灾大帝。[20]
苏人祀王尤虔,家各立庙,范王兄弟暨太夫人像祀之,岁时水旱,祭祷维谨,而讳之曰五圣,即今所谓五通神也。[20]

民国初年江苏省政府所树张士诚墓碑(源自《斜塘镇志》)
时至今日,苏州民间依然热衷于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大街小巷里就会有星星点点的香烛插在地上,俗称“烧久思香”,这里的“久思”就是张士诚“九四”的谐音,“吴俗七月晦日,民间以棒香遍植庭阶,其名称甚俚,实为张王作生日也。”[21]
可谓“金容永袭都天号,翻比朱明国祚长。”[22]
四
事实上,苏州城中还有一些类似于“讲张”的政治话语,比如“建文故事”:
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庚辰(建文二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洁地,直不取也。[23]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建文帝上台之后,任用大量吴越籍贯的官员,改弦更张了朱元璋对于吴越之地的特殊歧视政策:“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2]而在明中后期,“建文故事”的发明创造中,吴中文人群体便是主要参与者。
苏州城接二连三出现和明廷“离心离德”的思想暗流,其实涉及一个更为宏大的国家地缘异质张力矛盾。自从安史之乱后,关中王气黯然,大量流民迁徙江南一带,江南人口、经济水平飞升。上古以来东西对峙的主流脉络受到了改变,自宋以后,南北关系格局取而代之。
明初虽然实现统一,然分裂之痕,并不会因为政治统一自动弥合,朱元璋曾直言对江南富庶之地的观感:“吾诸将皆生长濠、泗、汝、颖、寿春、定远,习勤苦,不知奢侈,非若江南耽逸乐者比。”[24]“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25]
江南原本“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海洋贸易风生水起,巨富更是遍布江南各镇,“因下番买卖致巨富”“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而朱元璋据鼎后认为:“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则人皆惑于利”“故尝禁其往来”。[9]
淮右在宋金之际,地处南北交接,渐染北俗,元季又隶属河南江北行省,近于北制,与江南各有法度。明季肇立,出身于淮右的朱元璋,所用治国之术,偏于北俗的社会内敛均衡,悖于江南所延的外向均衡。故以同质、均质化而混一,则必然出现“适淮履,削吴(越)足”的悲剧。故“士诚之思”“建文故事”,皆依南北矛盾之构,皮相而论。
五
“吴自唐以来,号称繁雄,至于元,极矣。”[16]身处繁雄极矣的江南,张士诚的统治策略一方面是萧规曹随元季“法网疏阔,征税极微”[26]的旧制;另一方面是其作为成长和活动于海滨一带的商人,有其具身的效率知识,暗合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商人主政的宽弛传统。在无朝廷牵扯压制的条件下,张士诚更以地方性的“具身知识”提升地方生计效率。[16]这一内洽咸和、仁以待民之举,确曾造福一方。世人论及士诚之败,多言其适逸苟安,所用非主国命师之道。看似持正,实是庸常之见。盖江南自有风俗,通食货之便,致使上下逸豫,难以雄图。魏源尝道:“选精兵于杭嘉苏,无异于求鱼于山求鹿于原。”反之,“选精兵于江北,则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也,不可以胜收也。”[27]士诚纵有问鼎之志,亦无问鼎之兵,岂可为无米之炊?昔时,钱镠据吴越,亦是“守之以谦”。士诚籍于江南以成,亦赖江南而败。士诚之败,亦是江南之败。天赐江南饶,而断乎其勇。
随着年岁的增长,辈分之差造成的话语的自然迭代,现已日渐寡闻“梦赴苏州”和“讲张”这两句话了,它们大概也不会再流传下去了。地方记忆、地方话语,也就逐渐变成了地方故老口中的掌故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