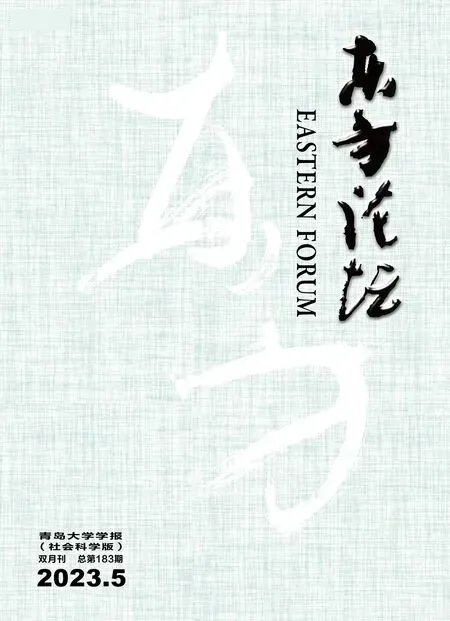周代“尚贤”学说的系统阐释
祁 志 祥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①参见祁志祥:《周代:“神”的祛魅与“人”的觉醒——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重写中国思想史”发凡——中国思想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反思与构想》,《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周代思想界讨论的中心问题,不是神道,而是人道。周代讨论的人道集中体现为内圣外王之道。在外王之道中,君主必须通过大臣百官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大臣百官呢?当然是贤人。“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②《管子·枢言》,《二十二子》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于是,“尚贤”,成为周代人道学说、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对周代的尚贤学说作出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与阐释,试图为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周代外王之道中的“尚贤”主题
“贤”,指品行高尚。如《周礼·大宰》“三曰进贤”,郑玄注“贤”:“有善行也。”《庄子·徐无鬼》云:“以财分人谓‘贤’。”同时也指才能杰出。如许慎《说文解字》云:“贤,多才也。”综合二义,“贤”指才德杰出的人。关于贤才的类别和高低,文子有过独特的划分:“智过万人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①王利器:《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14—515页。“尚贤”,即把有才德的“英”“俊”“豪”“杰”任用到各层各级管理万民的官吏岗位上去。“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②黄淮信:《鹖冠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1页。
周代的文、武之道是对尧、舜、禹、汤之道的继承。“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③《墨子·尚贤上》,《二十二子》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9页。所以“尚贤”成为周代政治之道的一个重要主题。《尚书·周书·周官》早就提出“推贤让能”“举能其官”的要求。《周礼·大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其中两项就是“进贤”与“使能”。《礼记》崇尚:“大道之行也……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放宏议。“尚贤”成为除老庄外各家普遍强调的主张。管子指出:“霸王所始,以人为本。”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管子说的“争人”,指人才的争夺:“论材量能,谋德而奉之,上之道也。”(《管子·君臣》)晏子为齐相,一再向景公建议“举贤以临国”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十三,《二十二子》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67页。。冉雍向孔子请教怎么为政。孔子提出三条原则,其中之一是“举贤才”⑤《论语·子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页。。《墨子》一书专设《尚贤》篇,提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墨子·亲士》),“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上》)的命题,并从“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的角度,论证“尚贤”是“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 《墨子·尚贤下》)。荀子重申:“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⑥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4页。
具体说来,“尚贤”包括哪些做法呢?晏子提出“知贤”“用贤”“任贤”:“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十)尸子提出“用贤”“求贤”“尽贤”“进贤”“知贤”数端:“国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尽,此其三也。”“为人君者,以用贤为功。”“虑事而当,不若进贤;进贤而当,不若知贤;知贤又能用之,备矣。”⑦魏代富:《尸子疏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6—47页。文子提出“知贤”“爱贤”“尊贤”“敬贤”“乐贤”五项,并以此重新解释“仁义礼智乐”的涵义:“知贤之谓‘智’,爱贤之谓‘仁’,尊贤之谓‘义’,敬贤之谓‘礼’,乐贤之谓‘乐’。”(《文子·上仁》,据杜道坚《文子缵义》校改)如此等等。周人主张,通过多种“尚贤”措施,让“英俊豪杰各以大小之材处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从而最终实现“四海之内,一心同归”,“上唱下和”( 《文子·上礼》)、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
二、“尚贤”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周人反复强调“尚贤”。为什么要“尚贤”呢?周人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首先,这是选吏任官、治国安邦的需要。“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可者,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中》)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君主是适应统一天下大义、为民平暴治乱的需求,被人民大众推举产生的。由于他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选择“贤可者”为三公九卿、大臣百官共同治理天下,管理万民。尚贤使能,授贤为官,是君道的必然选择。“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①《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二十二子》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9页。“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吕氏春秋·开春论·察贤》。)“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吕氏春秋·开春论·期贤》) “圣人举贤以立功。”(《文子·上义》) “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州之高,以为九卿;一国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文子·上礼》)“禹之治天下也……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②钟肇鹏:《鬻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汤之治天下也……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汤政》)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吕氏春秋·不苟论·赞能》)。齐桓公所以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关键原因在于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管子·小匡》)。“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故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受言结辞使辩,虑事定计使智,理民处平使谦,宾奏赞见使礼,用民获众使贤,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制天地御诸侯使圣。”用人得当,则群臣献功。“下不怨上,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鹖冠子·道端》)要之,“国有俊士,世有贤人。”(《荀子·大略》) “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慎行览·求人》)。
其次,“尚贤”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兼并诸侯、称霸天下的现实需要。当时的诸侯国,“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大多事与愿违,兵败国削,被人吞并,什么缘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 《墨子·尚贤上》)于是,不肖在上,贤者居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使不肖临贤,虽严刑不能禁其奸。”(《文子·上礼》) “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墨子·尚贤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正本清源,唯贤是举,量能授官,努力营造“无德不尊,无能不官”( 《文子·上仁》)的健康政治生态。“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天地之性也”。( 《文子·上礼》) “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荀子·大略》)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集聚)贤而巳。”(《墨子·尚贤上》)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各国竞相争夺人才,招贤纳士、礼贤下士就显得更加迫切。“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尸子·明堂》)。
再次,以贤取官,进贤为臣,也是打破爵禄世袭制度、解放人才创造力的需要。世卿世禄制是夏商以来朝廷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其本质是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被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王位世袭制,世卿世禄制也相伴而生。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确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有爵位与官职者,世代都享有采邑和封地。西周沿袭了这种制度,但到东周出现了松动和瓦解。春秋时期,适应兼并他国的需求,甚至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①《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82页。的呼声。与此同步,面对爵禄世袭制,人们纷纷要求打破束缚,唯才是举,能者上、庸者下。鬻子公然声称:“夫国者,卿相无世(世袭),贤者有之。”(《鬻子·道符》)墨子不仅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个振聋发聩的口号,而且明确主张:“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墨子·尚贤上》)针对世卿世禄制度,荀子旗帜鲜明地呼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在任人唯贤、打破世袭的爵禄制度限制方面,孔子是个实实在在的践行者。公元前513年,晋国的魏舒“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派了十个人做县大夫。孔子对这种打破宗族世袭制、直接任命地方官吏的做法深表肯定和支持。他说:“魏子之举”,“近不失亲”(大夫中的一个是魏舒的庶子),“远不失贤”,“以贤举,义也”(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秦穆公打破惯例,对虞国奴隶百里奚“爵以大夫”、“授之以政”,对此,孔子也大加赞赏,认为这是秦国能称霸西戎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压制、排挤“贤人”的做法,孔子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鲁国大夫臧文仲执政很长时间,对于“直道而事人”的“贤者”柳下惠不仅不安排职位,反而三次撤掉了他的官职。孔子愤愤然批评说:“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
三、“求贤”与“举贤”“让贤”
既然选贤任官对于天下安康至关重要,所以君主必须以“求贤”为务。在“求贤”问题上,君主必须放下身段,礼贤下士。“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夫士不可妄致也……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尸子·明堂》) “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吕氏春秋·季冬纪·不侵》) “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规制?”(《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 “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说,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贱也。”(《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指贤士)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 “文王之见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数。”(《尸子·治天下》)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 《史记·鲁周公世家》),唯恐怠慢天下贤人。
君主求贤,切忌自大而轻贤。《尚书·商书》记载商汤王左相仲虺的告诫:“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②《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周书·洪范》记录箕子对武王的告诫:“汝则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周人还认识到:“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恃君览·骄恣》)“亡国之主……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控制)容而不极(尽言),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之贤士),何益焉”(《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
周代统治者认识到贤士的宝贵重要,礼贤下士,招贤纳士,于是“举贤”“让贤”在周代传为美谈。周人的举贤,崇尚出以公心、光明磊落,传诵着不避亲、不避仇的佳话。最典型的例子是祁奚荐贤。《左传·襄公三年》记载:“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晋语七》详细叙述了祁奚向晋悼公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午接任自己任职的故事。“祁奚辞于军尉,公问焉,曰:‘孰可?’对曰:‘臣之子午可。……午之少也,婉以从令,游有乡,处有所,好学而不戏。其壮也,强志而用命,守业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直质而无流心,非义不变,非上不举。若临大事,其可以贤于臣。臣请荐所能择,而君比义(宜)焉。’”于是晋悼公委任祁午为军尉。一直到晋平公死,军队中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失误,证明祁奚推荐自己儿子是正确的。
晋大夫臼季举荐晋文公仇人之后的故事,也颇富传奇色彩。臼季奉命出使,在冀邑郊外住了一宿。这天他看到冀缺在田中锄草,妻子给他送饭来,夫妻相敬如宾。“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臼季觉得他是个难得的贤才,一上去打听,才知道他就是冀芮的儿子,而冀芮恰恰是当今晋国君主晋文公的仇人。但他还是把冀缺带回到国都,向晋文公举荐为官。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臼季答:“国之良也,灭其前恶,是故舜之刑也,其举也兴禹。今君之所闻也,齐桓公亲举管敬子,其贼也。”最后,晋文公亲自接见了冀缺,任命他为下军大夫①薛勤安、王连生:《国语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473页。。
臼季引述的齐桓公亲举仇人管仲任齐相的故事,《国语·齐语》中有生动的记载。管仲与鲍叔牙原来是一对好朋友。齐君死掉后,公子诸当上了国君,是为齐襄公。不过他每天沉迷于享乐,二人预感齐国会发生内乱,管仲便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则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不久,齐襄公被人杀死,齐国果真发生了内乱。管仲想杀掉小白,让纠能顺利当上国君,遗憾的是管仲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射偏了,只射到小白的腰带,小白幸免一死。后来,鲍叔牙和小白抢先回到齐国,小白就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即齐桓公。即位后,齐桓公打算封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却对桓公说:“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说:“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你难道忘了吗?鲍叔牙回答说:“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失犹是也。”不过这时,管仲被扣在鲁国。鲍叔牙设计让人将管仲带回齐国。“桓公亲逆之于郊,而与之坐而问焉。”(《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最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也成为功劳卓著的“春秋第一相”。
上面的例子既反映了齐桓公能够不计旧恶用贤,又反映了鲍叔牙能够胸怀坦荡让贤。让贤的例子,《国语》中记载很多。赵衰是跟随晋文公流亡多年、辅佐晋文公回国夺取君位的重要功臣,后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第二霸主,居功至伟,颇受文公倚重。但他从不争权夺利,不计较个人地位,而是一再让贤。《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问他谁可以担任元帅,他举荐郤縠;让他担任卿士,他又推荐栾枝、先轸和胥臣。后来上军帅狐毛去世,晋文公让他继任,他又推荐先居。晋文公称赞他的让贤为“不失德义”,每次都让给社稷之臣,利于晋国。
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惇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郤縠。”公从之。
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取五鹿,先轸之谋也。郤縠卒,使先轸代之。胥臣佐下军。
公使原季(即赵衰)为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狐偃之兄)之智,贤于臣,其齿(年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狐毛卒,使赵衰代之,辞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乃使先且居将上军。①薛勤安、王连生:《国语译注》,第460—461页。
赵衰一再让贤,晋文公很感动:“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于是,文公把原来的三军扩充为五军,任命赵衰担任五军之一的新上军统帅。狐偃死后,先且居请求文公委派上军副帅。文公说:“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请令衰也从子。”晋文公便派赵衰担任上军的副帅。
有了这样一个传统,晋国让贤蔚成风气。晋悼公时,任命张老为卿,张老辞谢说:“臣不如魏绛。夫绛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学不废先人之职。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且鸡丘之会,其官不犯而辞顺,不可不赏也。”悼公五次任命张老为卿,他都坚决推辞,于是让他任中军司马,命魏绛为新军副帅。(《国语·晋语七·悼公使魏绛佐新军》)晋定公时,少室周为晋国重臣赵简子驾车。他听说牛谈力气很大,觉得牛谈为赵简子驾车比自己更合适,于是将车右的职位主动让给牛谈。赵简子对此很赞赏,便安排少室周为家里总管,说:“知贤而让,可以训矣”(《国语·晋语九·少室周知贤而让》)。
四、“知贤”的意义与门径
上级求贤,下及举贤、让贤,尚贤成为周代社会上下流行的一种风气。对于君主而言,求贤必先知贤。有贤士、圣人而不能认知,这对君主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因此,君主具备识贤知士的素质和眼光,就显得特别重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②《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页。只有贤主,才能识贤得贤。“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吕氏春秋·季秋纪·知士》) “贤主得贤者而民得。”(《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君主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是看他能否正确辨别忠、逆或贤、不肖。“凡乱者,刑名不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 “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吕氏春秋·仲冬纪·至忠》)只有“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 《吕氏春秋·季冬纪·士节》),才是真正的贤士。“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贤君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肯定为自己补缺纠偏的大臣是“贤士”“忠臣”。反之,昏君自以为是,不知己过,视忠为逆,以贤为不肖。“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 “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吕氏春秋·似顺论·似顺》),而败莫大于不自知。
君主如果不能确定自己的判断力绝对准确,那么,根据民意的评价来选贤,也不失为一个参考方法。“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0页。民众的反映是选贤的标准:“民者,贤、不肖之杖也。”(《鬻子·撰吏》)民众的反映也是选吏的标准:“民者,吏之程也。”“明主撰(选)吏,必使民兴(举也)焉。士民与之,明上举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鬻子·撰吏》)选贤任官,就是要把人民爱戴的人选上来:“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撰(选为)卿相矣”(《鬻子·撰吏》)。
“知贤”还包括在各种环境下的动态考察。晏子主张:“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不取。”(《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十三)文子进一步提出:“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施,穷即观其所受,贱即观其所为。视其所患难,以知其所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观其仁;振以恐惧,以观其节。”(《文子·上义》)鹖冠子提醒说:“异而后可以见人……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鹖冠子·天则》) “富者观其所予,足以知仁;贵者观其所举,足以知忠。观其大(端也),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使之不隐,足以知信;贫者观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贱者观其所不为,足以知贤;测深观天,足以知圣。”(《鹖冠子·道端》)《吕氏春秋》提出了外用“八观六验”,内用“六戚四隐”的考察贤才方法。“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外结合,家庭中、社会上的表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季春纪·论人》),还要注意“举之以语,考之以事”(《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二十七),听其言而观其行,言行一致地加以考察,防止夸夸其谈,口惠而实不至。此外要注意其是否贪恋爵禄私利,考察其品节高下:“夫上士,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易退也;其下,易进难退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十三)。
五、“用贤”的原则与“任贤”的理念
知贤、识贤之后,把人才任命到合适的官员岗位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用贤和任贤了。
“用贤”的基本原则,是用得其所,德位相配。管子说:“爵材禄能,则强。”(《管子·幼官》)尸子说:“君子量才而受(授)爵,量功而受禄。”(《尸子》卷下)荀子说:“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荀子·致士》)“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防范的问题,是德不配位、能不当官。正如《管子·立政》指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贤人并不是完人。用贤为官,要从大处着眼,取其所长,不计其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贤不能求全责备。晏子指出:“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有不能赡也。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二十四)文子指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圣人为之。”“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文子·上义》)尸子指出:“羊不任驾盐车,椽不可为楣栋。”“使牛捕鼠,不如猫牲之捷。”“夫买马不论足力,而以黑白为仪,必无走马矣;买玉不论美恶,而以大小为仪,必无良宝矣;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伊尹、管仲不为臣矣。”(《尸子》卷下)正如《吕氏春秋》指出:人人都有不足,即便是尧、舜、禹、汤、周武王这样的圣王亦非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天下便无可用之人。“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吕氏春秋·离俗览·离俗》) “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用贤实即用众人所长。“物固莫不有长……人亦然……无丑不能,无恶不知。……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
用贤的第三条原则是出以公心,去除亲疏。墨子强调:“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墨子·尚贤中》)尸子重申:“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避远近,不论贵贱。”(《尸子·明堂》) “尧举舜于畎亩,汤举伊尹于雍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仁者之于善也,无择也,无恶也,惟善之所在”(《尸子·仁意》)。
礼贤下士不仅体现在求贤环节的态度上,也应当落实在用贤的具体行动中。要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吸引贤士,表达对贤人的足够尊重。“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吕氏春秋·慎大览·报更》)要为贤人提供必要的用武之地和活动条件。“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墨子·尚贤上》)
君主“用贤”,还必须防止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人主之害,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荀子·致士》)君主“用贤”,也须戒备臣下妒贤嫉能,相互排挤。“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蔽公者谓之‘昧’,隐贤者谓之‘妒’。奉‘妒昧’者谓之交谲。交谲之人,妒昧之臣,国之秽孽也。”(《荀子·大略》)“任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所谓“任贤”,即“尽贤”,也就是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开展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作用。
君主用贤,不仅是用他们的专长来管理万民、为天下做事的,也是用他们的智慧来匡正自己不足、补救自己过失的。君主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如果刚愎自用、讳疾忌医,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败莫大于不自知。”(《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 “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 “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吕氏春秋·似顺论·似顺》)古来英明的君主清醒地认识到“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甚”这一点,所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鬻子·禹政》)他发布告示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鬻子·禹政》)周代君主继承了尧舜禹汤的谏议之道,“武王有戒慎之鼗”(《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在制度设计上,“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朝臣百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帮助君主“举过”,以确保君主最终决策万无一失。
因此,君主“尽贤”,就必须有听取贤臣不同意见,尤其是尖锐的批评意见的胸怀,容许并鼓励贤臣百官发挥其举过匡失的谏议功能:“贤主……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吕氏春秋·贵直论·贵直》) “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吕氏春秋·贵直论·壅塞》)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吕氏春秋·贵直论·直谏》)真正的“忠臣”“贤士”不是“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的“谀臣”,而是敢于“外匡其邪,而入其善”的谏臣。“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是以美善在上,而怨雠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墨子·鲁问》)所以,君主对待贤士百官所言的态度或方法,应“后其言”,让其言无不尽;应“顺其言”,让其言有自信;应“记其言”,令其不妄其所言;“验其言”,以核实其言的正确性。“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吕氏春秋·审应览·审应》)周人特别提醒君主:“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适。”(《文子·符言》) “使言之而是,虽商夫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人君卿相,犹不可用也。是非之处,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其计可用,不差其位;其言可行,不贵其辩。”“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能够“任贤”“尽贤”,是贤主明王,反之,“亲习邪枉”,“疏远卑贱”,“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则是“暗主”“昏君”。“如此而欲安海内,存万方,其离聪明亦以远矣”(《文子·上仁》)。
能否尽贤,关键取决于君主的态度。《鹖冠子》总结说:“故北面而事之,则伯(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麾而使,则厮役者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徒处。”把贤人当作师傅相待,就能称帝;把贤人当作朋友相待,只能称王;把贤人当作徒隶使唤,就会沦为亡国之君。
综上所述,周代的“尚贤”学说,涉及君主“求贤”(“进贤”)、“知贤”(“识贤”)、“用贤”“尽贤”(“任贤”)等各种问题。此外还谈到“育贤”问题:“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这是对君主的要求。在群臣之间,又有“举贤”“让贤”的传说和美谈。可以说,“尚贤”是重视“人道”的周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尤其突出。这在迷信鬼神的殷商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李斯《谏逐客书》)周代开辟的这一“尚贤”传统,成为汉代“举秀才”“察孝廉”的直接依据,在魏文帝实施的九品官人制和隋唐科举选人制度诞生之前,它一直是古代选吏任官安邦济世的人才选拔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