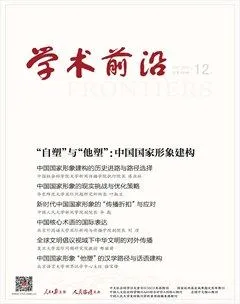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付继存
【摘要】知识产权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自主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实现知识产权法治现代化,需要自主创新的、适应实践的价值立场与态度。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与防范权利过度扩张,不是分别对应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共利益,而是在整体上作为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的手段。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具有同构知识产权领域内的各种价值和理念的能力,是我国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价值取向 激励创新 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4.010
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的两个基本逻辑
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防范个人和企业权利过度扩张,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这是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的根本遵循,也是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取向。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与防范权利过度扩张,不是分别对应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共利益,而是在整体上作为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的手段。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坚持了“以我为主”、是否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公正合理,都取决于是否实现了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完整理解这一价值取向,需要厘清其中的两个核心逻辑。
一是促进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创设知识产权制度,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是要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要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让各类创新要素不断涌现、集聚、重组与优化,进而激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而保护创新又是为了保护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而巩固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以产权方式激励创新,也能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无论是以产权方式激励创新,还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都是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创新与其他公共利益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与转化的辩证关系,两者统一于公共利益整体。从知识产权法治的角度看,欠缺激励创新的公共利益是不可持续的,欠缺其他公共利益的激励创新是残缺不全的,这都会损害整体公共利益。
二是激励创新和促进其他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立性。激励创新需要有力保障创新主体对创新成果合法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以及通过成果转移转化获得收益的权利。19世纪,部分欧洲国家在反专利浪潮中曾废止了专利制度,但很快都恢复了该制度。专利制度以明确和保护专利的支配权和使用权的方式激励创新,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个人和企业等民事主体对知识与信息的不当垄断,会阻碍正常的科技、文化、教育与商业等活动,最终会妨碍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扩散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福利。只有防范不当垄断,才能保障公众接近知识与信息的自由,涵养创新的“水土”,增进公共健康、公平、可持续发展等福祉。要想防范不当垄断,就要维持合理的公共领域,削弱创新主体对部分行为方式的垄断,限制垄断的时间与地域。两者的对立性可以概括为:垄断不足,创新受挫;垄断过度,其他公共利益受损。在支配权、使用权的保护与开放不断平衡博弈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不断发展完善。
由此看来,两者兼得的基本含义是,知识产权法既要适度合理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又要实现激励创新与维护其他公共利益的总体均衡。激励创新与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在特定情境中的实现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两者没有绝对的先后次序,因而也不存在为了某一种公共利益而完全摒弃另外一种公共利益的情形。相应地,不能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盲目地剥夺他人的创新性贡献,也不能为了激励创新,无原则地容忍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在知识产权法治实践中,各国普遍通过为保护客体设置实质要件与程序要件、为权利设置时空与利益的边界等方式,将专有利益与公共利益、专有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因此,只有依法、符合比例地保护符合条件的智力成果或工商标记,而且符合条件的智力成果或工商标记都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才是真正的两者兼得。
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的理论统合力
首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可以統合我国在四十余年的知识产权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包括“法律本土化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利益平衡理论”“协同保护理论”“司法裁判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强国建设理论”“国际战略理论”等。[1]这些理论成果从实践根基、法律目标、方法路径等不同侧面描绘了知识产权法治的理想图景,并体现出共同的理论前设。
然而,无论哪种理论,都是追求知识产权法治现代化的一种路径探索或方法论尝试。“法律本体化理论”侧重强调从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实践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知识产权学理。“制度创新理论”特别关注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与新兴科技对创新激励方式与路径的新需求。“产业发展理论”“强国建设理论”“国际战略理论”侧重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目标。“利益平衡理论”提供了知识产权法的解释模式与利益衡量方法。“协同保护理论”“司法裁判理论”侧重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这些路径要么从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实践出发,要么从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实际需求出发,要么从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目标出发,要么从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模式出发,展示了知识产权法的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体现了知识产权理论探索的实践性、自主性与时代性。“法律本土化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主要回答了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制度模式、实施方式与技术路径等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产业发展理论”“强国建设理论”“国际战略理论”主要回答了该知识体系的价值目标。“利益平衡理论”“协同保护理论”“司法裁判理论”主要回答了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基本方法。只有以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为价值取向,上述理论才能相互连接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
其次,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能够平息知识产权研究范式之争。受移植欧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影响,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普遍采用保护论范式,但是限制论范式更符合知识产权制度的使命。[2]这两种范式的核心争议并非保护或废止知识产权,而在于对待知识产权保护与激励创新的关系有所不同。按照保护论范式,只要有利于激励创新,就应当给予尽可能多的保护,除非损害到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按照限制论范式,只有在不利于激励创新的情况下,才应当适度给予创新主体保护。这两种范式所秉持的共同理论前提是,知識产权保护与激励创新是二元对立的:要么是激励创新越多越好,要么是知识产权保护越多越好。
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作为一个辩证的整体来看待。保护的目的是激励创新,限制的目的是促进公众接近知识与信息的自由,培育创新系统,最终也是为了激励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激励创新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是对保护论范式与限制论范式所秉持的共同理论前提的超越。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只是实现最优的激励创新效果的“两只手”。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强度与知识产权的期限、行使限制两者的最佳配合是实现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的实践作用力
一方面,知识产权立法的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以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为指导。在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视野下,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观包括正义价值、效率价值和创新价值等。[3]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时代构建,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强调人本主义的“创新发展”、公平正义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面向世界的“开放发展”、利益平衡的“共享发展”,以此保持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正确方向。[4]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应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价值观。知识产权立法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一脉相承。知识产权立法的权利定位也取决于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知识产权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发明的财产权,能够为新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的知识成果提供法律保障。知识产权作为市场竞争工具,既能够提高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或市场竞争力,又因其具有的专属性而成为高水平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同时,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知识产权事关国家战略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产权,尤其是对重要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事关产业发展主导权。因此,知识产权立法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保障总体国家安全为根本旨趣。
另一方面,执法体系与司法体系是否高效,也取决于是否坚持了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执法司法体系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保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特色。只有构建合法、高效、顺畅、有力的执法体系,以较高的违法成本来保证执法效果,才能切实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维护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知识产权授权确权、侵权赔偿的规则解释与政策导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司法体系重在以司法专门化、信息化、“三审合一”、指导案例改革为抓手提高审判质量效率,确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民事和刑事保护规则。知识产权民事保护应当审慎适用惩罚性赔偿,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应当形成遏制违法犯罪的强大震慑。这些都体现了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的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在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的指导力。
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的知识论意义
首先,应当以财产权规则与市场经济的相关原理使知识产权法逻辑化。知识产权法学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类财产权知识。财产权法律的价值共识、基本原理、共同框架与共通规则是知识产权法的知识基础,也塑造了知识产权的内容、取得、归属、丧失、变更、交易与保护规则。这些规则以市场机制为运行前提,相互之间形成了有机关联的知识体系。立法确认或授予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以产权方式补贴创新主体。这种补贴要通过知识产权的自主实施、许可、转让、质押与证券化等市场化运作方式来实现。立法规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就是防范市场主体不当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或工商标记,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赔偿是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导向的,也是由市场来决定创新成果或工商标记的价格的。因此,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对具体规则的设定与解释具有约束力。
其次,应当以公共政策的相关知识重塑知识产权法的价值体系。知识产权是解决多领域问题的公共政策工具,是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与创新系统的重要制度要素。在国内,“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文化多样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政策关键词,是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的核心要素,也是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价值支撑。国际上,知识产权规则是信息获取、公共健康、公平、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多领域共用的全球规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需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是避免知识产权只与多边贸易机制深度融合,扭转知识产权全球价值的单极化倾向。二是处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和“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的冲突。三是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原则,协商制定知识产权规则,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互学互鉴、互惠互利、互尊互信。公共政策的法治实践是知识产权规则重塑与知识产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源泉。不同公共政策的博弈,尤其是激励创新与实现其他公共利益的平衡,决定利益的具体分配,公共政策的实现程度决定知识产权的设定与保护。在这一意义上,知识产权作为一类财产权形式,只是利益分配的结果。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ZFG82009;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1]吴汉东:《试论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知识体系》,《知识产权》,2023年第1期。
[2]宁立志:《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3]冯晓青:《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24期。
[4]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试论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责 编/韩 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