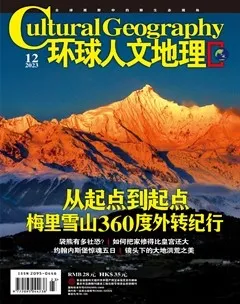在哈库拉的纯蓝里
程华
整整七小时飞行后,落地马尔代夫首都马累。
绝对称不上大气的机场,极其普通的最高警察总署,与之一墙之隔造型憨实的国防部,泊于码头样貌平庸据说是“总统游艇”的小船,人车乱入红绿灯形同虚设的公路……我怀疑自己穿越时空到回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如此说来,我们一家三口的热带之旅,应从次日早登上飞往哈库拉的水上飞机时才真正开启。准确地说,是从登上身形微胖的大红色水飞,惊见被统称为“小黑”的驾驶员大脚上那双花哨的塑料夹趾拖鞋开始。
在我的眼神暗示下,儿子彭彭和他爸面面相觑。与我们少见多怪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水飞驾驶员与副驾上同伴一脸淡定谈笑风生。显然,所谓“安全操作规程”在这里不好使。直到发动机轰鸣,螺旋桨搅起滔天巨浪,心头忐忑才慢慢消解。
水飞拉高。水飞,顾名思义再高不会太高。空中几大朵棉花糖似乎伸手可及,也有些在机腹下懒懒游弋。朵朵缝隙间,露出大片惊艳的薄荷蓝,蓝成梦的汪洋。洋面上点缀粒粒珍珠般的小岛。
40多分钟后,水飞凌波踏浪徐徐降在哈库拉水上码头。走过如同悬于波光之上的500米栈桥,两头弯弯极富童话色彩的多尼船、飘扬在酒店白色尖顶上的三色旗、一杯浓郁的鲜榨热带果汁、船型大堂里戴着头巾笑得温婉的女子欢迎了我们。据说酒店是斯里兰卡人经营管理的。后来那些天,我发现同款笑容在岛上俯拾即是,包括相互间语言不通的游客。发自内心的明亮笑容,想必是可以被无限复制粘贴的。
同属蓝色系的海洋与天空,深浅色号各各不同:海是湛蓝与碧绿的混血儿,而天蓝得纯正不带一丝杂色。浅海上呈弧形排列的几十间水屋,巧妙地将海天一分为二。白色尖顶小屋与白云遥相呼应,不动声色地成为海天之间的绝佳链接。
水屋宽敞,落地门外大海碧蓝。透过镶在实木地板上一块巨大的玻璃,可见色彩妖娆的鱼虾,慵懒的龟,身段柔软的鳗鱼逡巡于脚下。彭彭和他爸立即顺扶梯下水,与珊瑚、海草、鱼虾们打成一片。我坐门外露台上,端一杯咖啡,看三三两两戴潜水镜穿潜水服套脚蹼的人鱼一般漂过眼前。
作为全世界热门打卡地的马代吸引着各地游客,拥有成熟酒店管理的哈库拉有令人舒心的饮食住宿娱乐等服务。海边餐厅里,无论主食主菜烧烤烘焙水果酒水……每个人几乎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款。
乘快艇前往附近岛上一个村落,导游再三吩咐:为尊重当地风俗,请女客着装一律上不露肩背,下不露膝盖以上部位。
事实上岛上女人着装的“严谨”程度远超想象:30多摄氏度的天气,个个长袍加身外搭玄色头巾,手里却拿着新款苹果手机,让人恍生“这到底是哪个世纪”的时光错乱感。听说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本地男人可娶几房老婆……
这里环境保护的理念与力度让人击节。禁止捕鱼捉虾捞海产品,连沙都不得私自携带出境。一朵花、一棵树、一枝珊瑚、一只鸟、一尾鱼……生灵们享受着最柔软的呵护。除防着自然界天敌,它们不用担心遭遇来自人类的伤害。从水屋到栈桥,从码头到沙滩,从林荫下到海上吧,宽皮大脸的热带阔叶植物在阳光下绿得发光,颇有白玉兰神韵的鸡蛋花羞怯怯藏在草丛里,也绽放在如花似玉的女人鬓间。
趿着拖鞋踩在雪白细沙上,总见寄居蟹不知疲倦地背着灰白色蜗壳,成群结队如入无人之境。行人绕行,唯恐踩到出行的队伍。到底是小孩,彭彭忍不住捉一只,观赏一番又轻轻送回原处。
六只黑翅白腹的鸟儿以“天罡北斗”阵型包围彭彭,叽叽喳喳盘旋俯冲,直到彭彭幡然醒悟——它们是冲着搁在沙滩椅边的一只乳酪面包。彭彭赶紧懂事地捏碎面包分而喂之,小鸟们方才心满意足不紧不慢振翅而去——想来得有何等受宠,才惯出如此撒娇撒野甚至“撒泼”的小精灵呀。
每日,小岛在风与海鸟的吟唱中悠悠醒来。如果说白日像一首明艳的歌,那么夜晚一定是迷离的梦。每至暮色四合,全天开放的海上酒吧充满浪漫气息。长着亚洲面孔的驻唱歌手怀抱吉他低吟浅唱,不同肤色游客一杯清酒,微笑,倾听,喁喁轻谈。
小麦肤色短发微卷的胖老板很忙。他喜欢笑着对游客竖起大拇指,不时明星般兴冲冲与大家合影,生意间隙还格外钟意手机游戏,老是趴在彭彭身边潜心观战。而我被对面金发少年的侧颜吸引:天庭饱满,隆鼻、深目,长睫毛如扇子,他望着台上女歌手的眸子净如月光,嘴角隐带一丝温和的浅笑。
夜愈深。信步踱出酒吧,月清浅,海亦清浅。几尾鱼沉默着游来游去,仿佛遨游于透明的空气中,看得人都痴了。而女歌手沙哑带磁的歌声袅袅而来,如雾霭漂浮于洋面,最终隐入深不可测的夜色中……
最美时辰,当属小岛黄昏。
丽日西垂,芒刺渐收,阿波罗驾着太阳马车缓缓归去。蓝白主打的天穹被缤纷色彩取代:橘黄、酡红、雪青、秞蓝、石綠、淡粉、浅青、月白……那是摄影界的“Magic hour(魔法时刻)”。整日滚打于钢筋水泥丛林中,满满烟火味的城市夕阳让人习以为常。此刻,这无垠海平面之上的炽烈晚霞,瞬间击中了人的灵魂。每分钟光与色在变幻,海天仿佛自带滤镜,万物如此奇幻夺目、恢弘辽远……
下午5点到傍晚7点的黄昏海钓令人神往。由两名当地“小黑”驾船,载着十几名身穿救生衣乘客的快艇从码头出发了。
一路海钓一路渔获,浪花激起阵阵欢笑,快艇渐入大海深处。不知何时,大块铅灰色云团吞噬了绚烂霞光,天色骤然暗下来,清澈的海水如同墨染样深黑。
风乍起。一浪甩来,船如秋千。我一趔趄,心头一颤。
即刻调头返航。海上天如凡人心,说翻脸便翻脸。风挟雨扑向船身,浪不断高起,船摇摇晃晃。驾驶舱“小黑”用飞快的手势示意不要慌,坐稳。
又一浪扑上甲板,全身湿透的游客们发出惊叫。海面白雾迷蒙,快艇举步维艰,雨与浪一齐砸下。我和彭彭爸从两侧护住彭彭。我们从彼此的眼神中读出了极力克制的不安。我唯一能做的两件事,一是默默祈祷,一是抱住彭彭。心里一遍遍问自己:在深不可测的海里,救生衣管用吗?
快艇不知在恐惧中挣扎了多久。终于,风停雨住,一带灯光依稀闪现在遥远的海平线。有人欢呼,有人笑骂,有女子拽住丈夫失了魂地嚎啕。
岸边,一群人热情地伸出手。我起身走两步,双脚竟有些踩不着点。
磕磕绊绊下了船,着地的感觉从未有过地踏实。看看表,7点30分,比预计返程迟到30分钟。这30分钟,险些成为一段走不完的旅程。
平日早该打烊的海边餐厅里,橘色灯光下,香喷喷的饭菜、柔和的笑容扑面而来。颤着手倒上一大杯啤酒,一家人使劲一碰,“叮当”声中才想起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
没有月饼。没有月光。但此时,在异国海边,阖家平安。我想,这个中秋是无法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