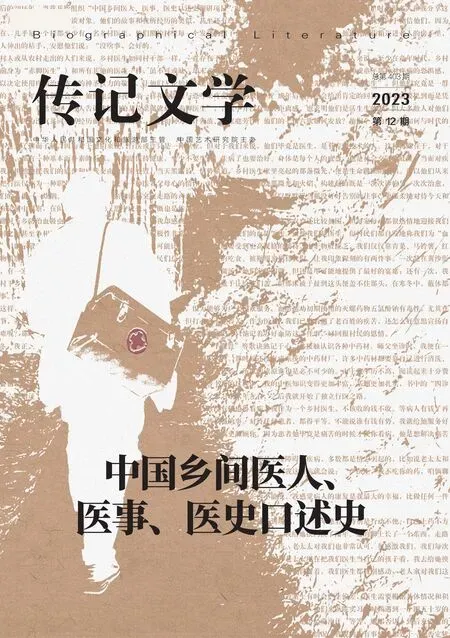读图的记忆
——蒙学记之三
与 之
连环画时代
我在小学时代,没有太多机会读到文字的经典,对文字和经典的了解都是在半文半图的形式中进行的,比如连环画。
中国古代本来有配图绣像的图书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连环图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作为民众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发展得很快,大量优秀画家投入创作,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着力打造一大批精品图书,还有专门性的《连环画报》期刊,可谓达到了中国连环画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峰。在我即将上学读书的20 世纪70 年代初,“解决下一代的精神食粮问题”被重新提出。周恩来总理在1970 年9 月和1971 年2月两次指示尽快恢复连环画的编创工作。随后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期长达四个多月,据说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人民美术出版社代表姜维朴,就有关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
于是,在我1972 年上小学之后,便有了阅读连环画的机会。最先读到的连环画主要是样板戏的内容,比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海港》《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等。后来品种逐渐增加,现实、历史、神话传说等题材的连环画也陆续出现,有讲述真人事迹的,如《刘胡兰》《金训华》《黄继光》《白求恩在中国》;有经过虚构加工的,如《闪闪的红星》《小英雄雨来》《鸡毛信》;也有经典名著改编的,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过我们经常看到的还是革命题材的故事。
连环画一般都来源于原始的文学作品,除了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学经典外,也包括样板戏的剧本和演出脚本,以及已经成型的革命文学作品。相较于纯文字性的文学,这种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艺术形式显然更为平易通俗、喜闻乐见,具有更加有效的社会教育作用。毛泽东同志1949 年提到:“连环画不仅孩子看,大人也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1]对于刚刚启蒙的小学生而言,更是当时可以接触到的文化读物。我们日常听到的文学故事,在老师、长辈那里往往被几经压缩、删削、改编,到了有连环画可读的时候,才较为完整地接触到了文学作品的样貌,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系统走进文学的世界其实就是从连环画开始的。
文学为我们绘制出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概貌,阅读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孩子认知、学习人生的开始。许多人都知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恩格斯曾经说,读过《人间喜剧》,“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童年的文学阅读给了我们关于世界和人的最早的轮廓。当时读得最多的是革命故事,刘胡兰、刘文学、海娃、小英雄雨来等少年英雄的事迹可谓深入人心,我们都让家里的大人制作了红缨枪,模仿着“站岗放哨查路条”。当时我们一到放学就开始玩“打仗”游戏,每个人都手持红缨枪,模拟再现小英雄们的战斗故事。这些情节,都是从连环画中看来的。
连环画中的少年英雄不少,刘胡兰、雨来、海娃、王二小、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其中离我们最近的是合川的刘文学,为了保卫人民公社的海椒,竟被行窃的地主王荣学杀害了,牺牲时年仅14 岁。有一天,刘文学的母亲被请到了我的小学,学校指定几个学生代表和她合影留念,我也被选中了,那份高兴难以言表,中午连饭都来不及吃就按要求赶到北碚留真照相馆。集体合影印出来后被放在照相馆橱窗里展览了好久,外公也很为此自豪,还特意向几家亲戚介绍,让他们去照相馆参观。
那时的连环画,以国内文学作品的改编绘制为主,外国作品只有改编自苏联的几种。我见过的就是高尔基自传三部曲,改编绘制成了三册:《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虽然只是一些小小的图画,却也已经展开了一个阔大的异域风情的新天地:阿廖沙那披着纱巾的胖胖的外祖母,时而严厉时而温和的外祖父,俄罗斯冬夜里温暖的壁炉、高大的白桦林,压在伊凡背后的那个巨大的十字架,可怜的瞎子格里戈里,还有那个瘦小而凶恶的继父……这个世界并不比我看过的中国更快乐,但却似乎更为丰富和多样,生活的缤纷和人生的曲折都自有一种无法道尽的魅力,它们深深地埋藏在了我的心底,成为我默默向往的“远方”。直到新世纪初年,我有机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普希金的皇村到托尔斯泰庄园,一路走着,其实都是在寻找这些连环画中的意象。
儿童天性就对视觉艺术、对美术绘画有特殊的好奇和敏感。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载自己用 “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影描,“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3],那就相当于是早期的连环画了。我们那时的小学有美术课,但课上并没有多少严格的训练,就是因为有连环画的存在,我们也无师自通地进入到了对绘画的学习和模仿之中。记得看了一段时间的连环画之后,我也找来白纸,画好一排一排的分格,然后仿效连环画的方式,自己凭借想象构思和描绘故事,就仿佛是要制作新的连环图画。绘制的过程完全处于“自嗨”的高潮,一边编造情节,一边描绘主人公的各种动作和细节,口中还念念有词,仿佛是在为画中跌宕起伏的情节配音。当然,编织这一类故事基本上都是一时间心血来潮,最终都半途而废了,然而却总能让我再一次地重温那些故事和图画的意趣,因而长期乐此不疲。

连环画《童年》插图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我获得的第一本连环画来自父母对学习考试的一次奖励。后来,外公和舅舅们也以这种方式来鼓励我的学习,于是我的连环画就开始有了积攒,积攒到一定的数量,我自己也就觉得必不可少了,开始到处寻找有连环画出售的地方。当时在北碚,我只发现了两处,一是城里的新华书店,二是郊外团山堡的一个供销合作社。父母每个月从重庆市区到北碚外婆家来看我一次,每一次来都带我到新华书店去买上一本连环画,我自己则努力将一些压岁钱攒起来,抽空到供销合作社去等待,遇到有新书出版就赶紧买下。

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插图
连环画并不太贵,一开始就是几分钱一册,大多数不超过一角,后来逐渐厚了起来,价格也开始提高,一角五,两角,两角五……不过,与价格比起来,更让人担心的是根本买不到。书店不是天天都上新品种,常常是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出现一册新的,碰上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星期天,那就得排长队,有的书大家都想要,排队就特别长,排到最后也就买不上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失落,也有点怪父亲,觉得他实在太晚带我出来。
总之,读连环画是会上瘾的,希望自己的藏书越来越多,现有的几种翻腻了,每天都在幻想,还有哪些书我没有看过呢?有一天,二舅从他就职的文星中学给我带回来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书又黄又旧,连封皮和最后几页也没有了,但是那图画描绘得细腻清晰,和我看得比较多的那些斗争故事的粗犷画风差异很大,虽然已经很旧了,却让人觉得精美非常,我爱不释手。二舅告诉我,这是著名画家的作品,属于工笔画,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连环画绘画一等奖。后来我才知道作者是赵宏本、钱笑呆,书的出版早在我出生之前,市面上已经没有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这本书都被我精心保存、收藏起来,虽然它是我所有连环画中最旧最破的一本。
看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也好像知道了二舅夏夜里的那些西游故事的来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猜测,其他的西游故事是不是也在这些连环画中呢?我不断向二舅打听、询问,盼望他能够再找几册回来,哪怕就是比这一册更旧更破也可以。二舅却十分为难,说:“这些书都是十多年前的了!”唉,十多年前?那时不知道有多少好看的书啊!这是我对“十七年”的最早的印象,经常憧憬地幻想。
这片憧憬还曾被意外地放大过一次。后来的一天,有亲戚给五舅说媒,介绍了一个教师的女儿,五舅上她家走动有时候也带着我。记得那个中年老师温文尔雅,听说我喜欢连环画,就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家过去有很多很多的连环画,什么《大闹天宫》《武松打虎》《天仙配》《杨门女将》《孔雀东南飞》《孟姜女》《红楼梦》《哪吒闹海》,应有尽有,简直把我听呆了,这些书名绝大多数我都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听上去却又那么有趣、那么有吸引力。我连忙问:“这些书呢?能不能借我看一看?”老师也是叹了口气说:“现在没有了!”
这一次的失落与其说是打击了我还不如说极大地诱惑了我,隔着时间,眺望五六十年代,隐隐约约中似乎有无数的瑰丽的色彩、无数琳琅满目的连环画在召唤着我,真不知怎么才能读到。朝思暮想之后,这些图书也就潜入了我的梦境,成了那里的迷离光影……
我的“三国梦”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连环画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十七年”的作品又陆续再版重印,或者重新绘制,推出新版。
那时我在重庆沙坪坝天星桥中学读初中,继续热衷于收集阅读连环画,不过方向有了变化,一般的革命故事已经不太感兴趣了,主要精力集中在历史故事和文学经典改编的连环画,例如《东周列国志》《杨家将》《岳飞传》《水浒传》,等等。其中,我倾情关注最多的是《三国演义》。
连环画《三国演义》最早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于1957 年,全套共60 册,有7000 多幅图画,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一套连环画作品。参与绘制的画家人数众多,其中不乏像王叔晖、刘继卣这样的国画大师。全套图书以工笔刻绘为主,但也包含了其他艺术形式,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堪称当代艺术经典。1979 年,出版社重新组织力量编撰绘制,推出全套48 册版本,一时间引爆市场,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就连在我们这批初中生中也出现了“三国热”,大家纷纷购买、寻找、交换连环画,都期待能够迅速集齐,尽快知晓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历史细节。
但是真不容易!当时的沙坪坝新华书店也是间隔很长时间才出售一册两册,经常是在星期天早上,人流如潮,有时候一开大门几乎就是抢,我们这些初中生哪里抢得过。后来有人囤积品种高价出售,让我们也是逡巡良久,颇费踌躇,因为实在想要,却又实在囊中羞涩。我还算运气好,在家中舅舅们的帮助下,七拼八凑,已经接近完整,就差那么几册了。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我们班有个家住三医大的上海同学,见多识广,我比较相信他的见识。他也喜欢《三国演义》连环画,常常和我交流收集的信息,只是收到的品种就差得太多了。有一天,他启发我说:“你这么辛苦地积攒《三国演义》连环画,不就是想知道历史的细节吗?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三国演义》一读,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又何苦这么劳神费力呢!”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只是我也没有《三国演义》小说啊,更不知道哪里买得到。这个同学压低声音,神秘地说:“也许我就可以想办法弄到!不过,如果我真的帮你弄到了,有个条件,你搜集的三国连环画得由我来挑选,凡是我缺的品种都归我,行不行?”我当时对三国故事已经近于“走火入魔”了,的确十分渴望进一步读到真正的原著,又想这种书哪里容易弄到,就让他先去找找无妨,于是就不假思索地点了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上午,这位同学就抱着厚厚的两大册《三国演义》来找我了,说:“书弄到了,现在你带我去你家取我的连环画吧!”我吓了一大跳,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只好极不情愿地把他带到了家中。看着他狠狠地在我费尽心思的收藏中自由抽取,装入准备好的书包中,那种心痛真是锥心刺骨啊!
更让人沮丧的则是第二天,我偶然经过学校不远处的一个小书店,一眼就发现那套刚刚出版的《三国演义》小说正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书架上,随时可以自由购买。而此时此刻,我马上就要集齐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却已经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打这之后,我好像再不能集齐《三国演义》连环画了,直到我上了高中,兴趣转移,不再关注连环画,半套《三国演义》连环画一直蜷缩在书柜的一角,精美而零落。
不过,从这一天起,我真的逐渐走出了半文半图的阅读,开始在文字的经典里认识这个世界了。那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的《三国演义》被我读了很多遍,充分地满足了我细究魏蜀吴历史的愿望,也由此出发,进一步探寻了陈寿的《三国志》、班固的《后汉书》,历史的视野不断扩大,连环画的时代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