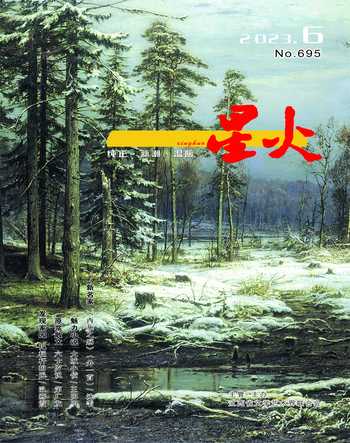从黑暗中寻找光
于燕青,做过执业药师,散文、诗歌、小说见于《大家》《北京文学》《散文》《散文选刊》《诗刊》《诗选刊》《作品》《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文学港》《广州文艺》《四川文学》《黄河文学》《福建文学》《山花》《雨花》《山西文学》《山东文学》《鸭绿江》《延河》《西湖》《在场》《飞天》《厦门文学》《阳光》《鹿鸣》等刊,收入各种散文年选。出版个人集《逆时花开》《跌倒》《情感档案》《内心的草木》《漫过水面》,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散文上榜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作品》期刊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1
那时,军营里的孩子没能赶上父辈激情燃烧的年代,就把狠劲撒游戏上了。什么过关呀,点兵呀,一群孩子举着木质手枪在家属院区里疯跑。也有文静点的游戏,比如弹玻璃珠、甩图票、赢柿子核、下棋等等,玩恼了照样开打,专打脑壳,边打边喊:“砸烂你的狗头!”于是开瓢破瓜是常有的事。在这帮军营的小伙伴里,我属于胆小无能之人,从未开过别人的瓢,但也没被人破过瓜。小伙伴里我最喜欢沫沫,沫沫与我同岁,长得还跟我有点像,和我一样害怕打架。于是我总和沫沫一同上下学,大人们看见我们在一起,就喊,哎呀看呀,这俩孩子天天在一起,好得像对双飞蝶!我后来就把这种关系称为蝴蝶闺蜜。是的,当初我和沫沫就是蝴蝶级闺蜜。
我们就读的那所小学校离军营有点远,尤其是冬天放学后,我和沫沫走着走着就走进夜色里了。一切景物都随着夜色的加深渐渐暗淡,最后,我只看得见身边的沫沫,沫沫就成了夜色的中心。我不是一个可以同时交往很多朋友的人,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我的感情都是单一的,专一的。也就是说,只能是双飞蝶,不能群蝶乱舞。也许我骨子里有快意恩仇的江湖气,好就一竿子好到底,两肋插刀;坏就恩断义绝,不相往来。反正,有了沫沫,我就有了专一的对象,其余的孩子就形同虚设,如同一大堆塑料花里,唯有沫沫是鲜花。我和沫沫心灵相通,我们之间的体己话连父母也不会知道。
那天,吃完晚饭,沫沫的母亲和我的母亲,还有别的阿姨都坐在家属区的空旷地聊天。我的母亲和沫沫的母亲吩咐我们去炊事班讨要一些木板,因为两家都买了小鸡,都需要打造鸡窝,于是我和沫沫就到了炊事班。已是暮色四合,那个炊事兵弓着腰不知在干什么,走近时,沫沫忽然指着我对炊事兵高声喊道:“叔叔,他们家有小鸡,要木板钉鸡窝。” 我愕然,鸡窝还没钉,我先被钉在那里了,也就是说我呆住了。沫沫显然有意这样说的,她的声音里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也许她仅仅是为了显示她比我聪明,可以占我的便宜。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竟然不忍心戳穿她的谎言,我知道我已经越过善良的底线,滑进无能的深渊。炊事兵让我们在那堆废木板里随便挑。当我们带着各自挑选的木板来到母亲们面前,夜色已经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夜色掩盖了她,却掩盖不了她的谎言。沫沫再次迫不及待地述说了她如何向炊事员说的话,依然是炫耀的口气,占尽别人便宜的自得,声调也高了八度,以至她说话时带出了颤音。沫沫的母亲没有说话,我的母亲也没有说话。但我的眼睛能穿越夜色看到我母亲脸上的不快。我也觉得自己很窝囊,很无能,连戳穿伤害我的人的勇气都没有。夜色暗黑汹涌,席卷了一切。
2
很快,又有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里。她叫丽斯,丽斯取代了沫沫在暮色里留给我的虚空。丽斯家是从外地来的。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跳橡皮筋,动作优美,漂亮得恍若仙人,看上去已经开始发育了。她穿白衣服和浅蓝裙子,都是天空的颜色,让她的美无比纯净。我被她的美惊呆了,她让我相形见绌,让我自卑。从此,我和丽斯的友情里就包含了我的崇拜。
那天晚饭后,我们四个孩子在灯光下围成圈打老K,各家打各家的。正当我犹豫不决地举着手里的两张牌,丽斯连忙对我说:“我们是好朋友,你放心,我不会吃你的牌!”于是我坦然地甩出“老K”,结果她出尔反尔,一下子就用“小2”捕获了我的老K,我傻眼了。无疑,我输得惨不忍睹,而人生的牌局又何尝不是输局已定?“三岁看大,八岁看老。”我日后处世为人的不会遮掩已初见端倪,如同项羽乌江自刎的悲剧在鸿门宴时就已注定。夜色也帮不了我的忙,因为灯光太亮,我的狼狈一览无余。我的轻信,我的毫无智慧,让我低下了头,躲避那明亮的灯光,让自己成为灯光下的暗影,成为“灯下黑”,仿佛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记得有人带着痛惜地说了句:“啊,燕青太憨直!”我没敢抬头看那说话的人,后来我怎么也想不起是谁说了这话。我潜意识里一定是想忘记那些事,忘记自己的愚蠢与失败。我以遗忘来掩盖自己的失败。我能记住的是那团灯下黑。
那阵子我喜欢讲故事,还喜欢讲傻子的故事。说的是有人告诉一个傻子,在人家的婚礼上该笑,在人家的葬礼上该哭,也就是与欢笑的人同欢笑,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可傻子总也分不清那些新婚祝福和充满褒扬的悼词,分不清那些为活人和死人准备的花束,分不清为红白事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于是傻子常常红白颠倒,不合时宜地在人家的婚礼上哭,在人家的葬礼上笑,所以他总是挨揍。这个故事能够安慰我,让我知道有比我更傻的人,仿佛找到一个垫背的。母亲愤怒极了,她说你以为世上还有比你更傻的吗?母亲禁止我再讲傻子的故事,否则我会一直讲下去,我需要创造一个比我更傻的人来安慰自己。
那个下午,军营里一群孩子去木工棚捡刨木花,我也去了。那时刨木花是烧饭最好的引燃物。木工师傅一下一下地推着手里的刨子,刨子底下就开出一朵一朵好看的花来。木花刚一成型,就被那些眼疾手快的孩子抢走了,我赶不上趟,连一朵也没抢到,别人的篮子都装满了,我的篮子还是一无所有。我想我这辈子完了,我又傻又笨,总是让母亲失望。我差一点就哭出来了。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高大的人,也许是工头,他是赶来阻止我们的。他其實挺和蔼的,他语调很慢,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这样做很危险,刨子一不小心就会刨去你们的小手指……他所说的“你们”其实不包括我,我根本来不及伸出我的小手指。可是他只对着我一个人说话,因为那些篮子装满了的和半满的孩子们早撒丫子跑了。也许我觉得我不必跑,挎着一个空篮子逃跑有多可笑?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篮子是空的,也许他看见了我的空篮子,也许他只是觉得犯罪未遂也该得到教育,他说得语重心长,很像一个营养师对一个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说着营养过剩的危险。
我仰着头一动不动地听他训话,仿佛我对说话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其实,我的眼里噙满了委屈的泪水,哪怕稍稍低下头,或是改变一下姿势,泪水就会流下来。我必须保持这个姿势,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被夜色的黑、灯下的黑笼罩,那样的黑侵入我的肌肤骨血。
3
我一直没能聪明起来,却勇敢过一次。那天我看到两兄弟正在打我的两个弟弟,懦弱的我、从不敢跟人打架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一下就冲上去了,我用自己的身子挡住那两个男孩的拳脚,像虚张声势的稻草人,没有章法地挥舞着一双螳螂般的胳臂。而那两兄弟敦厚的身形,出手的武猛,像是生来就为了打架。整个过程我只觉得昏天黑地。我敢参与斗殴了,这是怎样的飞跃?我感到兴奋,以致拳头落在我的头上身上,也不觉得疼。打架很快结束,也许他们觉得打我这样的很丢脸。可我却很阿Q地觉得我赢了,我打赢了,我有了可以炫耀的资本了。我看到不远处我的母亲正和另一位母亲聊天。我并不认识那个女人,甚至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我之所以认为她是一个母亲,是因为她的年龄在那里摆着,那时候我们周围还没有剩女,没有丁克族,生不出孩子的女人不能说没有,却是极少的。我披散着头发,歪斜着衣领跑到我母亲那里去炫耀,像一个从战场上凯旋的将军。我把自己说成是英雄、施暴者。不管怎样,我要让我的母亲相信我狠狠地揍了对方,还因为另一个母亲在场,我越发添油加醋,就好像那兄弟俩已经被我打趴在地,永不得翻身。生活有时很戏剧很讽刺,我万万没想到,那个女人就是那兄弟俩的母亲。我本想昂首挺胸一次,却弄巧成拙再一次抬不起头来,明明是挨揍的,却说自己揍了别人。还好那母亲没有计较,否则我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我后来看了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其中一段写的是,汉娜作为纳粹集中营看守被开庭审判,法庭上她否认那份笔录是她写的,可当法庭要核对她的笔迹时,她立马改口承认是她写的,揽下了罪名。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文盲。包括当年放弃单位的升迁机会,报名去集中营当看守,都是为了掩盖她是文盲这一事实。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团漆黑的影子。
4
中学时期的一个暑假,军营里的孩子被组织起来练习射击。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我们都学会了开枪,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的笑脸比阳光更明媚,因为我的射击水平不错,是那群孩子里的佼佼者。
我们还参加了公社组织的青少年射击比赛。比赛开始了,我瞄准时发现有几根摇曳的树枝遮挡了靶面,可是射击口令已经下达,四野八荒皆是黑压压的人群,说什么我也不敢在这么声势浩大的场面下报告此事。同学们子弹已上膛,万籁寂静。我仿佛已看到验靶人摇着小旗报告我被剃了光头。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想起教练反复叮嘱的检查标尺之事。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呀,因为选定不同的标尺,瞄准的点也不同。若前一轮的射手和我们采用不同的标尺数据,而我们又没有调整标尺,那神枪手也白搭。我不知道我落在如此糟糕的境地,怎么还有心思提醒别人。
经我提醒,好几个忘记调整标尺数据的人重新调整了标尺。丽斯这只美丽的蝴蝶就在我的身边,她差点就扣动扳机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她惊叫起来:“哎呀,好险!”我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摇曳的树枝不折不扣地遮断了我所有的视线,我几乎是闭着眼睛胡乱发了三枪,嘭!嘭!嘭!每一发子弹都像在我的胸膛里炸开。果然,三发都没中,我吃了鸭蛋。只有我一个人零分。
除我之外,她们的成绩都不错。她们胜利了,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有两人三发三中10环,丽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兴奋地跳了起来。
偏偏一个靶场工作人员认出了我,他认识我的父亲,他说:“你不是于政委的女儿吗?”我更尴尬了,我这个吃鸭蛋的丢脸的女儿什么也没说。我走到远处,远离人群,远远地坐着看她们欢呼雀跃。我暗自忧伤,没有人想起我,没有人安慰我。此时的丽斯像一把美丽的凶器扎在我的心脏上,让我的失败那么突显。阳光太烈,没有可以遮盖的东西,一切都暴露无遗。就在此刻,人性的黑暗就这样滋生了,那是夜色的黑、灯下的黑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以致我的心里长出了阴影。阴影引导了我的思维,我想,如果我当初不提醒她们,此时就有人陪我一起伤心了吧?至少有丽斯和我一同承担那份失败。从那以后我和原来的我不太一样了。应该说,我被阴影一次次吞噬,最终成了阴影的一部分。
参加工作后的我对结交朋友很警惕,我怕朋友再次对我使绊子,欺骗我,伤害我。然而人不能没有朋友,尤其我后来独身一人在外工作。与T成为好友纯属偶然,T从未对我说过心里话,但人有时也需要掏肝摘肺地倒一倒自己,有些东西积在心里久了就像泛滥的洪水,必须开闸泄洪,否则会被冲垮。当年我就是为T开闸泄洪的人。那些天T迅速消瘦,我看着T的眼睛,觉得她很像一本小说里那个失恋的人,就说:“你好像失恋了!”没想到,一句玩笑话让T哭得稀里哗啦。于是T对我说出心里话,原来T与单位里那个很帅的浪荡子相爱,不久,浪荡子又爱上另一个女人,于是T就失恋了。那时正流传02号病,我们就叫那个浪荡子“01号”,暗喻他比02号病危害更大。我们把T的情敌叫“花瓶”。于是我与T成了知心朋友,我们之间说关键词,说暗语,“花瓶”,“01号”等等,只有我俩你知我知。我与T再次像蝴蝶双飞。后来01号又回心转意来找T,因为T的家庭条件好,01号需要这样的婚姻。01号还对我大献殷勤,让我帮忙促成此事。我明知这桩婚姻对于T不适合,可我没有提醒T,反倒帮了01號的忙。我并没有得01号的任何好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被阴影驱使,我害怕朋友伤害我,我不知道T什么时候会伤害我。与其让她伤害我,不如我先下手为强。我想起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不知道曹操是不是也经历过无数次被人伤被人负被阴影覆盖。
T的父亲后来为了避免这桩婚姻,把T调到另一个城市去了。从此,我与T远隔千山万水,从此,伯牙弦绝已无声。上帝惩罚了我。多少年过去了,我再难交到像T那样亲善的朋友了,再没有这样的蝴蝶与我共舞。暗黑的阴影已经波澜壮阔。很多年,我一直和阴影作斗争。
后来,我开始阅读,我读了很多书。其中,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让我看见了生命之光。书中描写孤儿奥列弗经历了无数磨难,尤其是他被命运带到贼窝,却不肯同流合污,他逃跑,又被抓回来,受尽折磨,却仍然保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从黑暗中寻找光,那是黑暗势力夺不去的生命之光。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给我很大的震撼。海伦·凯勒出生不久就被疾病夺去视力和听力,1887年她与莎莉文老师相遇,开启了她艰苦卓绝的生命历程,1899年6月她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她写了14本书,最著名的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石墙的故事》等。她致力于为残疾人的事业奋斗,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美国十大偶像”。马克·吐温说:19世纪有两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可以说海伦·凯勒终生生活在黑暗之中,可是她没有被无边的黑暗与死寂吞噬,她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想起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她本身就是世界上的光。正是阅读拯救了我,我在文字中看到了“光”,文学书籍让我在黑暗与阴影中找到了光。我不再被人性中的暗黑挟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