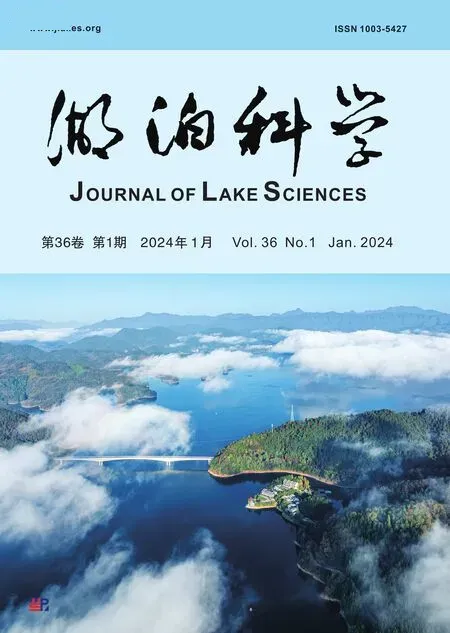我国城市水源水库水质风险成因及对策*
朱广伟,许 海,朱梦圆,肖 曼,国超旋,邹 伟,张运林,秦伯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水库是人类长期生产实践中,为对抗自然变化而建造的水资源调控工程,对于保障人类生产、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是水库大国,截止2019年拥有大小水库98112座,其中面积大于1 km2的水库5156个,是面积大于1 km2天然湖泊数量(2670个)的近2倍[1]。当前我国仍在使用的最古老水库是安徽寿县安丰塘,该库始建于春秋中期(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引淠河、涧河之水筑坝而成,现有面积34 km2,库容0.9046×108m3,兼具灌溉、蓄涝、生态、航运等多种功能,灌溉面积达450 km2[2]。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快,人口及产业集聚地快速提高,对水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水资源调蓄能力强的水库作为水源地。如上海市在长江口建设了青草沙水库水源地,2010年10月通水[3];源于丹江口水库,惠及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个省市24座城市1.1亿人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4年12月正式通水[4];杭州市、嘉兴市的千岛湖引水工程2019年9月投入运行[5]。截止2020年,我国340个县级以上城市及55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1093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中,属于水库或湖泊类型的有444个,属于河流型的有336个,属于地下水型的有313个[6]。从供给人口占比看,湖库型水源地供给最多,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杭州、福州、青岛、苏州、香港10个典型城市为例,其湖库供给人口占比为72.9%[6]。拥有大型水库水源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该城市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之一。
与河流或天然湖泊相比,水库一般深度大、颗粒沉降充分、水温分层稳定、底泥扰动小[7-8],水质相对更加优良。然而,作为流域水资源的调蓄单元,水库又往往具有流域汇水区面积大、水力停留时间短、水位波动大、生态系统脆弱、水质年际变化大等特点[9],水质容易发生“突变”[10]。如贵阳市水源地百花湖水库1994年9月下旬发生低氧、黑臭、死鱼的“黑潮”事件[11];长春市水源地新立城水库2007年7月在暴雨及罕见高温叠加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大面积蓝藻水华[12],导致供水中断;秦皇岛市水源地洋河水库2007年7月突发卷曲长孢藻(Dolichospermumspiroides)水华,引发水体土臭素(Geosmin)浓度高达7100 ng/L[13];韩国首尔水源地Paldang水库2012年8月因放线菌滋生导致水体Geosmin浓度高达3157 ng/L[14]。因此,水源水库又往往成为突发水危机事件的敏感水体。
本文基于调查研究,结合文献调研,对我国水源水库面临的水质风险现状、成因及预防对策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城市水源水库的水质安全保障提供参考。
1 我国水源水库常见水质风险类型
1.1 水质异味
水质异味是水源水库水质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水库中产生异味的物质是一些挥发性有机物,最常见的异味物质有3类:(1)萜类化合物(terpenoids),如2-甲基异莰醇(2-MIB)、Geosmin等,一般由丝状蓝藻或放线菌等生物代谢产生;(2)类胡萝卜素衍生物(carotenoid derivatives),如β-环柠檬醛(β-cyclocitral)、β-环紫罗兰酮(β-ionone)等,一般由原核生物、真核生物生长或死亡代谢产生;(3)挥发性有机硫化物(volatile organic sulfur compounds),如二甲基硫(DMS:dimethyl sulfide)、二甲基二硫(DMDS)、二甲基三硫(DMTS)等,一般由有机质腐败过程中细菌分解代谢产生,也可由蓝藻生长产生[15]。
尽管从医学角度看,多数异味有机物都没有明确的毒性,但是却能导致明显的感官不悦。特别是人的嗅味阈值一般比口腔触觉阈值灵敏几个数量级,一般浓度达到纳克级的异味物质就能被嗅觉捕捉到。尤其是在煮开水、洗澡等对自来水加热时,由于异味物质的挥发性,异味的感觉更为明显,更容易引起受水用户的投诉。
2-MIB及Geosmin是我国水源水库中最常发生的异味物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中对2-MIB及Geosmin的限定值均为10 ng/L。而上海青草沙水库在正式供水的第2年(2011年)起,每年夏季都出现2-MIB浓度升高或原水超标问题[3]。2007年7月9日至8月底,洋河水库在鱼腥藻与微囊藻混合种群暴发水华时持续50余天发生高浓度Geosmin问题[13]。2017年5月8日,深圳水源地石岩水库中检测出12种异味物质,其中2-MIB浓度最高[16]。2009-2012年的每年秋季,密云水库中均发生浮丝藻在次表层大量滋生问题,导致局部水体2-MIB浓度超过100 ng/L[17]。2020年7-8月调查中发现,溧阳市水源地天目湖沙河水库中2-MIB浓度超标,绍兴市水源地汤浦水库中Geosmin浓度超标[18]。除了2-MIB及Geosmin以外,其他多种挥发性有机物产异味也有报道。如2011年12月-2012年2月期间,呼和浩特水源地金海水库因硅藻(直链硅藻属)、金藻(钟罩藻属)大量滋生发生了醛类化合物异味问题,异味物质包括庚醛、2,4-庚二烯醛、2,4-癸二烯醛、2-辛烯醛和己醛等[19]。底泥释放的条件模拟实验表明,水力扰动、pH变化及温度变化均能引起底泥释放DMTS、双(2-氯异丙基)醚(BCIE)等异味物质释放强度的明显变化[20]。尽管水源地水体异味物质浓度超标并不意味着水厂的出水超标(GB 5749-2022是要求出水达标),但对水厂出水构成巨大超标风险,增加了原水的处理成本,需要高度重视。
1.2 藻类水华及藻毒素问题
藻类水华是由于水体浮游藻类大量滋生集聚在表层水体,明显影响水色,甚至遮蔽水面的一种生态学现象。目前成为困扰我国南方地区水源水库的一种常见水质问题。生态环境部颁布的“水华遥感与地面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1098-2020)中建议,当水体藻类细胞密度大于1×107cells/L时,则可能达到轻度水华;而当细胞密度大于1×108cells/L时,则可能达到重度水华。当然,细胞数指标仅仅是构成藻类水华是否发生的必要条件,还要结合现场感官状况判别是否发生。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遥感中心加强了对重点湖库藻类水华的监测力度,提高了各地对水源水库藻类水华问题的关注度。
形成水华的藻类以蓝藻门的一些常见种属为主,如微囊藻(Microcystisspp.)、长孢藻(Dolichospermumspp.)、束丝藻(Aphanizomenonspp.)、浮丝藻(Planktothrixspp.)、假鱼腥藻(Pseudanabaenaspp.)、拉氏拟柱孢藻(Raphidiopsisraciborskii)等。偶尔也会发生硅藻门、甲藻门、绿藻门、裸藻门一些种属的藻类水华,如汤浦水库2010年5月发生了链状弯壳藻(Achnanthidiumcatenatum)为优势的硅藻水华[21]。山东潍坊战略水源地峡山水库2019年6月出现了以拟二叉角甲藻(Ceratiumfurcoides)为优势的甲藻水华,角甲藻生物量高达86.31 mg/L[22]。三峡水库建成后,大宁河回水段2007年4、5月及2008年5月均发生了以波吉卵囊藻(Oocystisborgei)、小空星藻(Coelastrummicroporum)、实球藻(Pandorinamorum)等为主的绿藻水华[23]。2016年三峡库区前置库高阳湖、汉丰湖、长寿湖等均出现了空球藻(Eudorinaelegans)为主的绿藻水华[24]。裸藻门藻类水华一般出现在浅水、有机质浓度较高的水体中,在水库中开敞水域较少。但在库尾湿地、水库支汊回水区等能够发生,如北京市海淀区上庄水库的库尾湿地2013年7月出现了血红裸藻(Euglenasanguinea)为主的裸藻水华[25]。天目湖沙河水库库尾平桥河湿地在2021年10月也发生了裸藻水华。总体而言,从发生频次、强度及危害看,蓝藻门形成的水华都是最严重的,是水源水库水华防控的重点和难点。
藻毒素释放是蓝藻水华有别于其他门藻类水华而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蓝藻门形成水华的常见藻类大都能产生藻毒素,对水源水库水质安全产生更大挑战。其中最常见的是微囊藻毒素(Microcystin,包括多种异构体,简称MCs)。MCs是一类多肽类毒素,GB 5749-2022将饮用水中MC-LR(MCs多个异构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浓度上限设为1 μg/L。据位慧敏等文献分析,我国有文献报道进行MCs调查的水库有37个,其中22个水库中检出MCs,报道文献中MCs总量(包括细胞内MCs和细胞外MCs)超过1 μg/L的水库有北京的官厅水库、秦皇岛的洋河水库及福州的山仔水库,而胞外MCs浓度偶尔超过1 μg/L有山仔水库、官厅水库及贵阳市的阿哈水库[26]。蔡金傍等2005年对华北地区某水源水库做了MCs的周年变化调查,发现藻类死亡期的9-10月水库胞外MCs浓度达到峰值,为1.73 μg/L[27]。这一发现具有普遍性,即发生蓝藻水华的水源水库中,藻细胞大量死亡期由于胞内MCs的大量释放,反而是MCs危害较大的关键期。此外,近年来随着极端天气、突发藻类水华等事件频发,水源水库中发生藻毒素超标的问题可能变得更加常见。
1.3 铁锰超标
铁、锰均是地球化学性质比较活跃的金属元素,对环境条件中的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温度等较为敏感。还原条件下,水库底泥中的铁、锰能够还原成溶解态的Fe2+、Mn2+离子,释放到上覆水中,威胁水厂取水的水质安全。而在氧化条件下,水体Fe2+、Mn2+则会发生氧化反应,转化成固体沉淀物而离开水相。铁锰还原溶解、氧化沉淀的多变性质对水源地水质、输水管网、用水设施、人体健康等产生影响,比如堵塞输水管道、形成锅炉结垢等,甚至使自来水出现黄水、红水的现象[28]。GB 5749-2022中规定,自来水中铁、锰离子的达标阈值分别为0.3和0.1 mg/L,而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水质标准》(第二版)中将锰的阈值设定为 0.5 mg/L。
我国水源水库发生季节性铁、锰超标的问题较为普遍。由于深水水库在热分层期间普遍存在底层缺氧情况[29],此时如果分层期间下层水体缺氧严重,或者底泥中活性铁锰含量较高,就会发生下层水体高浓度铁、锰离子现象。因此,水温分层稳定、下层厌氧层厚度抵达取水口水层时,铁锰超标问题就会威胁水厂取水的水质。洪继华等1982年发现了天津水源水库于桥水库在水温超过25℃时锰含量显著增加[30];台州水源地长潭水库2008-2013年夏季均出现水体铁、锰浓度超标,最高值一般出现在8月,铁和锰的最高值分别为2.42 和1.20 mg/L[31]。贵州六盘水市水源地双桥水库因大量枯枝落叶沉积到坝前,2017年夏季原水中锰浓度达到0.236 mg/L,通过底层排水1周后,才降至0.130 mg/L[32]。萍乡市水源地山口岩水库2018、2019年夏季下层水体中铁、锰浓度达0.45、0.29 mg/L,对供水安全产生威胁[33]。厦门市新建水源地莲花水库受底泥高锰的影响,2018年下层水体中锰浓度为3.22 mg/L,达到中等污染程度[34]。由于流域大量种植桉树,南宁市水源地天雹水库水体有机质浓度高,加剧底层缺氧,引发了水体铁、锰浓度超标,并成为取水口发生“黑水”的原因之一[35]。
1.4 有机质偏高
水源水库的流域工业污染控制一般较严格,有机有毒污染物的事件极少出现。但是许多水源水库的流域植被茂盛,会出现天然有机质含量偏高问题。水源水库中与有机质相关的水质指标包括高锰酸盐指数(CODMn)、总有机碳(TOC)、溶解性有机碳(DOC)及有色溶解性有机物(CDOM)等。由于TOC仪进样管孔径的限制,TOC并不能包括所有颗粒有机碳,而天然水体中颗粒有机物的成分复杂,变化较大,稳定性差,因此实际调查中常用DOC而非TOC。在检测DOC时,除了使用TOC测定仪直接测定外,还常用水体有机官能团在254 nm波长时的吸收峰强度UV254表征。GB 5749-2022中规定生活饮用水中的CODMn的浓度上限为3 mg/L。尽管对DOC浓度没有确切的规定,但是近年来随着对饮水中消毒副产物(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BPs)问题的关注[36],水源地水体中高浓度有机质需要去除,导致制水成本增高。因此,DOC浓度也逐渐成为考量原水水质优劣的参考指标之一。
就全国而言,水源水库中天然有机质浓度过高问题并不普遍。但是在流域植被好、环境温度低、水体有机质自然降解速率低的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该问题较为普遍。如哈尔滨水源地磨盘山水库冬季冰封期水体大量积蓄分子量介于5000~10000 D(1 D=0.9921 u)之间的大分子有机质,DOC浓度约为5~6 mg/L,UV254约为0.19 cm-1,导致制水工艺中加氯消毒时形成较高的三氯甲烷生成势(trichloromethane formation potential, THMFP)及水合氯醛生成势(chloral hydrate formation potential, CHFP)[37],威胁水厂出水水质。南开大学李尧等研究天津水源地于桥水库水体有机质对消毒副产物生成的影响时发现,尽管从水库上游到下游水体DOC及氨浓度呈下降趋势(DOC浓度介于3.03~11.88 mg/L之间),但是水体中比紫外吸收率(SUVA)强度(UV254吸收峰强度与DOC浓度比值)却呈增加趋势,导致制水中卤代乙酸、三卤甲烷类消毒副产物生成风险偏高[38]。宋武昌等调查了济南市水源地引黄水库鹊山水库中有机质组分与消毒副产物生成势的关系,发现水库中DOC介于2.26~3.25 mg/L之间,年均值为2.32 mg/L,高值期出现在8-11月,但该水库水仍具有较高的三氯甲烷类DBPs生成势,与该水库DOC中小分子有机质占比高有关[39]。
相比较而言,南方水库中难降解天然有机质浓度可能较低,但会发生因藻类疯涨、生物量高而引起的有机质偏高问题。宋倩云等比较了金华市水源地金兰水库与太湖、钱塘江水源地水体有机质的DBPs生成效应,发现DOC浓度与DBPs生成势的关系密切,金兰水库DOC浓度仅为1.30 mg/L,而钱塘江九溪水厂取水口、太湖贡湖水厂取水口DOC分别为5.96和10.34 mg/L,后两个水源地水体中DBPs风险显著高于金兰水库[40],其中太湖的DOC高与太湖水体藻类生物量高密切联系。Hong等调查了东江源头新丰江水库、东江下游供水枢纽深圳水库及香港4座供水水库中天然有机质浓度、藻类状况及其对水厂DBPs的影响,发现6个水库中DOC浓度变化在很大程度受水体藻类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影响;天然有机质中芳香烃占比对DBPs产生量影响最大[41]。因此,即使在一些外源有机质不高的南方水源水库,也可能发生水体有机质高引发的水质问题。
1.5 营养盐超标
在水源水库的水环境保护中,管理上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营养盐超标。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的规定,水源地的二级保护区(湖库水源地的二级保护区水域一般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1500 m范围内的水域)内至少应达到Ⅲ类水的水质标准,相应的典型水质指标总磷(TP)、总氮(TN)、氨氮(NH3-N)和CODMn浓度上限值分别为0.050、1.0、1.0和6 mg/L;而取水口为一级保护区(湖库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水域一般为以取水口为圆心、半径500 m范围内的水域)的水质要求为Ⅱ类,相应的TP、TN、NH3-N和CODMn浓度上限分别为0.025、0.5、0.5和4 mg/L。目前在湖库水源地管理中经常遇到的水质问题是TP、TN的超标问题。表1列举了中国科学院野外站联盟项目(KFJ-SW-YW036)收集与调查中获得的22个水源水库营养盐浓度等水质指标状况。

表1 我国典型水源水库水体营养盐状况*Tab.1 Nutrients concentrations in typical reservoirs used as drinking water sources in China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多数水源水库的TP处于Ⅲ类水水平,一些优良水库年均值能达到Ⅱ类水,极个别能够达到I类水,浅水水库或河流特征明显的水库甚至处于Ⅳ类水浓度范围(TP>0.05 mg/L),如盐龙湖、青草沙水库、富春江水库等,表明部分水源水库的营养盐浓度达标面临挑战。对TN而言,大多数水库的年均浓度超过1.0 mg/L,处于Ⅳ类水水平,部分水库能到Ⅲ类水水平(0.5~1.0 mg/L之间),几乎没有能达到Ⅱ类水的,这导致目前在水质考核上没有将TN的达标状况纳入考核要求。所有调查的水源水库中,氨氮浓度都优于Ⅱ类水,且绝大多数达到Ⅰ类水。而对于CODMn而言,绝大多数水库能达到Ⅱ类水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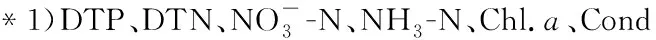
按照《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的TP指标单因子划分,22个水体中只有东江水库处于贫营养状态(TP<0.010 mg/L),17个水库处于中营养状态(TP<0.050 mg/L),盐龙湖、青草沙水库、富春江水库及丰满水库4个换水周期快的河流型水库则处于富营养状态。而依据SL395-2007中Chl.a指标的单因子划分,绝大多数水源水库处于中营养状态(Chl.a<0.026 mg/L),大沙河水库、龙王山水库的年均值处于富营养状态(Chl.a≥0.026 mg/L)。需要注意的是,对于Chl.a指标而言,年平均值会大大低估水库的富营养化风险。因为水库中Chl.a浓度存在极大的季节差异,尽管年均值Chl.a浓度不高,但许多水源水库都存在春季、夏季阶段性Chl.a浓度陡然升高、甚至出现藻类水华的富营养化风险。
2 我国水源水库水质风险成因分析
尽管我国水源水库的水质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往往存在相互联系,如藻类水华与营养盐问题、水质异味等密切联系,存在“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总的来说,水库水质风险的成因大都与外源营养盐入库负荷过高、内源污染物的累积过度、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失衡及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突变有关。异味问题、藻类问题、铁锰问题、有机质问题及营养盐问题等大都与营养盐及污染物的内外源负荷过大有关,本质上与人类活动强度过大有关。而气候、水文因子也常常成为水质问题突发的促发因素。归纳起来,目前我国水源水库水质问题的成因主要可分如下4方面。
2.1 流域开发强度过大
尽管流域地球化学元素背景能对湖库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43],但影响水库水质的外界压力大都来自流域及水库中的人类活动,特别是水库流域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强度。水库流域的土地利用方式中,一般将建筑用地、农牧业用地、茶果园用地等人类活动强度大、面源污染负荷高的类型称为“开发”用地,开发用地的占比称为流域“开发强度”。尽管目前还没有全国尺度开发强度与水库水质之间的精准关系,但大量研究发现,对具体水库而言,开发强度越高,水库水质就越差。史鹏程等调查了江苏省17个水源水库的异味物质状况,发现苏南水库流域植被好于苏北,与苏南地区水源水库水质更好的现象一致[44]。Rose等调查了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冈州52个湖泊和水库的水华强度相关因子,发现湖库蓝藻水华强度与流域裸地、建设用地的占比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常绿林地的面积占比呈显著负相关[45],说明流域开发强度越大,湖库中的蓝藻水华风险越高。
流域开发强度一旦过大,多数水库的良好水质难以稳定维持。美国中部密苏里州32个不同营养水平的水库调查发现,贫营养水库(n=5)的流域林地占比介于42%~97%之间(均值61%),牧场占比均值为20%,农田占比为0,其余为裸地;中营养水库(n=13)的流域林地占比均值为63%,牧场占比均值为27%,农田占比为2%,其余为裸地;富营养水库(n=12)的流域林地占比均值为33%,牧场占比均值为40%,农田占比为17%,其余为裸地;而重富营养水库(n=2)的流域林地占比均值仅为6%,牧场占比均值为28%,农田占比高达53%[46]。如果将牧场及农田定义为开发用地,贫营养、中营养、富营养及重富营养水库流域的开发用地占比分别为20%、29%、57%及81%。因此,就美国中部水库水质保护经验可以推断,若要维持水库贫营养,流域开发强度不宜超过20%,若要维持中营养,则不宜超过30%。当然,具体的占比比值还与土地开发的结构(空间距离)及开发管理模式(水肥管理、种养殖类型等)有很大关系,此值仅供参考。
我国水库开发强度与水质关系的分析也体现出二者的密切关联。吴一凡分析了绍兴水源地汤浦水库流域不同土地类型的氮磷产出负荷,发现单位面积耕地、园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年均总氮入河量分别为17.76、21.58、3.16和2.20 kg/hm2,年均磷入河量分别为5.06、1.42、0.67和0.75 kg/hm2[47];该水库流域2019年的耕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占比分别为11.03%、16.15%、65.48%、3.24%和4.10%,开发强度为30.42%,该水库的确也面临着富营养化的风险[47]。2017年溧阳市水源地沙河水库流域土地利用格局为林地54%、农田16%、茶园10%、湿地9%、建设用地7%、水库4%,开发强度为33%,该水库同样存在季节性富营养化风险;其中外源磷负荷中,农田及茶园贡献了61%,建设用地贡献了18%[48]。
2.2 底泥淤积与内源释放
水库是人为改变河流流态及物质时空滞留过程的产物,具有显著高于天然湖泊的底泥淤积速度。据邓安军等统计,截止到2018年,我国水库的平均淤损率达11.27%,其中黄河流域为36.76%,长江流域为4.25%,年均淤损率为0.41%~0.49%[49]。Rahmani等调查了美国中部大平原地区堪萨斯州24个州管水库的淤损情况,发现这些平均年龄为52年的水库淤损率均值为17%,最大淤损率达到45%,年均淤损率最大为0.84%[50]。郑丙辉等用210Pb及137Cs计年法测定发现沈阳市水源地大伙房水库中心库区的沉积速率为0.75 cm/a[51]。史鹏程等采用沉积物捕获器收集颗粒沉降物的方法估算了流域植被良好的千岛湖淤损情况,年淤损率约为0.07%[8]。随着流域物质在库底的快速淤积,大量有机质、营养盐被埋藏到水库深水区,热分层期间底层易形成缺氧环境,营养盐、铁、锰等物质则会溶解释放,重新进入水相形成内源,高有机质及厌氧的表层底泥环境还能引起放线菌等的大量滋生,代谢产生2-MIB、Geosmin、DMTS等异味物质,成为水源水库的水质问题的风险源。因此,许多水库随着库龄延长,底泥淤积增多,水质风险变大。
贵阳市水源地百花湖1990s发生的“黑水”事件[11],溧阳市水源地天目湖2005年4月发生的水质异味,温岭水源地太湖水库2015年5月发生的水质异味现象等,都与坝前底泥中有机质大量蓄积及温跃层形成后的腐烂分解过程有关。我国水库中普遍存在的夏季水体锰超标问题也大都与底泥中有机质过度积累有关。大连市水源地碧流河水库底泥内源释放是冬季取水口中上层水体锰超标的原因之一[52]。孙传喆等通过泥柱培养估算了天津市水源地潘家口水库底泥营养盐释放通量,发现夏季和冬季平均每天溶解性活性磷(SRP)释放通量分别为5.28和2.30 mg/m2,而溶解性无机氮(DIN)的夏季、冬季日均释放通量则分别为-0.66 及44.04 mg/m2[53],该水库面积为72 km2,这意味着内源释放磷的平均负荷可达102 t,对水库的水质达标及夏季藻类水华风险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2.3 生态系统结构失衡
水库中藻类水华问题、水质异味问题的本质都是水生态结构失衡问题。在相对健康的湖泊生态系统中,藻类、水草等初级生产者与浮游动物等初级消费者、不同食性鱼类等消费者,乃至底栖动物、细菌等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物质传递及能量流动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有害藻类不易过度增殖而形成危害。湖库生态系统成熟度的表征包括多个指数[54-55],如总初级生产量(total primary production,TPP)与总呼吸量(total respiration,TR)的比值TPP∶TR,该值越接近1,表明生态系统越成熟,大于1则表明该系统还在发育中;又如联结指数(connectance index,CI)和杂食指数(system omnivory index,SOI),这两个指数也是越接近1表明生态系统越成熟,生态系统的自我平衡能力就越强,低于1则表明生态形态的自我循环效率不高,成熟度低;此外还包括Finn’s循环指数(finn cycling index,FCI)和Finn’s平均路径长度(Finn’s mean path lenth,FMPL)以及生态营养转化效率(efficient of ecological nutrient transfer,EE)等。水库构建之后对原河流水生态系统中物质收支及能量流动均产生巨大的影响,将河流异养生态系统转变成湖泊自养生态系统[56]。水库本身具有的水量变化大、消落带水位落差大、总体初级生产力偏低,使得水库中生态系统结构相对简单,食物链单一,季节变化大,生态系统脆弱,藻类水华、水质异味等问题在物质传递与能量流动受阻过程中容易偶发。
澳大利亚水源水库中蓝藻水华问题多发,可能与水库中浮游动物食性的小型鱼类密度过大有关。Hunt等通过围隔实验模拟研究了食浮游动物的澳大利亚盖氏黄黝鱼(Australian gudgeonHypseleotrisspp.)种群密度与蓝藻密度之间的关系,发现黄黝鱼种群大小能显著改变桡足类浮游动物群落结构,进而影响桡足类浮游动物对蓝藻生长的压制作用,黄黝鱼密度与蓝藻水华强度呈显著正相关[57]。Lazzaro等调查分析了13个巴西水库的食物链结构,发现鱼类结构与蓝藻水华风险关系密切:蓝藻密度与杂食性鱼类(omnivorous fish,OM)密度呈正相关,与肉食性鱼类(facultative piscivores, FP)密度呈负相关,而与草食性鱼类(herbivorous fish)密度关系不大,叶绿素浓度及丝状蓝藻密度与FP∶OM比值呈显著负相关[58]。这表明水库生态系统结构平衡与否对一些水源水库的水质影响甚大。
我国既是水库大国,也是水库渔业大国,从水库兴建之初就大力发展水库渔业[59]。渔业养殖对水库食物链及水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过多的鲢、鳙投放量对中营养状态或贫营养状态的水库水质保障有负面的影响。刘其根等采用Ecopath模型分析了本世纪初鲢、鳙参与下千岛湖的食物网特征,认为该生态系统呈现出了高生产力非稳定生态系统的一些特征,但在精准管理鲢、鳙生物量的情况下,也表现出了稳定生态系统的特征[60],藻类生产与鱼类消费逐渐达到基本平衡。于佳等基于2016年千岛湖的食物链调查数据,再次进行Ecopath模型分析发现,千岛湖生态系统中藻类的EE值为0.37,高于碎屑的生态转化效率(EE值为0.13),牧食食物链的占比明显大于碎屑食物链;千岛湖的TPP/TR为6.51,远高于1,CI值为0.26,SOI为0.13,FCI为5.27%,生态系统处于不成熟状态,说明近年来千岛湖生态系统总体规模增大,稳定性和复杂性增强,但营养交互关系变弱,系统抵抗外界干扰能力低,初级生产的转化效率低,食物网简单[61],存在蓝藻水华等生态灾变风险。
2.4 气候与水文变化
近年来以增温、极端天气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幅度增加,成为我国水源水库水质风险的重要驱动力。水库中以藻类为主的初级生产力不仅受营养盐浓度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温度、光照、来水过程等气候与水文因子的影响。增温是湖泊蓝藻水华的催化剂[62],也能加快湖库中有机碳的分解[63],提高微生物反硝化脱氮速率[64],加剧底层缺氧而增加底泥磷释放[54]。李渊等基于遥感反演的湖体水质变化研究发现,近30年千岛湖流域气温增高明显,水体藻类生物量同步增高,气候学上的增温是30年来千岛湖透明度下降的重要贡献因子[65]。李慧赟等模拟了未来气候场景下千岛湖的热分层变化,发现未来增温加剧将导致千岛湖温跃层拐点深度变浅[66],藻类生长层将更加集中在表层,通过浓缩效应增大藻类水华风险。
暴雨过程能够在短期内对水库的温度场、水下光场、营养盐及藻类种源等水环境产生脉冲式改变,为藻类水华或者水质“突变”提供契机[67]。受东亚季风影响、热分层明显的大型水库中,夏季暴雨往往能带入大量磷,高磷水团首先进入水库的底层滞水层与上层混合层之间,而在暴雨之后这些磷逐渐扩散到上层水库混合层中,刺激藻类生长,引起蓝藻水华,被称为“季风水华”(monsoon blooms)[68]。在西安市水源地金盆水库,季风往往带来秋汛,在9月发生降雨量大于50 mm/d的暴雨,携带流域大量有机物进入水库,水库底层缺氧加剧,温跃层遭破坏,下层水体中高浓度磷通过混合作用大量进入上层水体,表层水体的TP甚至可达0.224 mg/L[69-70],造成短期水质灾变。
高温热浪兼具了高温和强光的双重影响,并常常伴随持续静风,能够显著改变蓝藻异常增殖的环境条件[71],促进蓝藻水华快速发生。近年来高温热浪的发生频次、持续时间及强度都呈增加趋势[72],成为湖库藻类水华频发的重要因素。黄群芳等发现2016年8月千岛湖库尾入湖口蓝藻水华与高温热浪事件联系紧密[73]。国超旋等发现2016年8月“涝旱急转”后的持续高温晴热是富春江水库蓝藻水华“突发”的重要促发因素[74]。
极端干旱能导致水库容量急剧下降甚至接近干涸,生态系统崩溃或发生突变,污染物缓冲能力降低,往往对水库生态系统产生剧烈影响,导致水质灾害。在2015年极端干旱背景下,Rego等调查了巴西西北部半干旱区5个水源水库藻类对极端干旱的响应,发现当水量降至库容10%时,多种水华蓝藻细胞密度均大幅增高,包括阿氏浮丝藻(Planktothrixagardhii)、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aeruginosa)、浮游鱼腥藻(Anabaenaplanktonica)及拉氏拟柱孢藻(Cylindrospermopsisraciborskii)[75],水库水华的风险大增。Hwang等分析了2012-2015年的干旱事件对首尔水源地Paldang水库的影响,发现干旱导致水库缺氧加重,磷浓度上升,水华风险增加[76]。2022年我国长江流域的极端干旱也引起了鄱阳湖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多个河流型水库暴发蓝藻水华,给一些具有水源地功能的水库水质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3 水源水库水质风险应对策略
水源水库的水质安全事关城市基本生存安全,必须高度重视。技术策略上,应对水源水库的水质风险,要从水库流域的整体系统考虑,制定基于水库水质目标的流域管理方案,协调人与自然矛盾,探寻绿色发展与高质量保护协调的途径。具体技术上,建议构建从流域到库体、从监测到修复的技术体系,包括水源水库监测预警技术、流域污染削减与拦截技术、水库内源控制技术、生态调控技术等。具体的技术方案如图1。

图1 水源水库水质风险应对的技术策略Fig.1 Technical strategy of water quality risk prevention in reservoirs using as drinking water sources
3.1 构建监测预警系统
构建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是快速掌握水库水质变化趋势、实施精准风险防控的前提。本世纪初国家生态环境部门构建了以流域跨界监督为主要目标的岸基栈房式自动监测系统,如千岛湖上游新安江的街口自动监测系统。但该系统是通过延伸至水体浮台的取水泵抽水进入岸基自动监测设备,对水质实施定期监测的。早期的自动监测系统存在取样代表性差、易污染等问题。2004年,在美国自然基金会资助下,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Trout湖生态站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鸳鸯湖生态浮标为基础,发起了全球湖泊生态观测网络(Global Lake Ecological Observatory Network, GLEON)[77],在全球湖库生态研究领域推广投放在湖库中心、依赖太阳能供电、水层剖面监测自动化运行、数据与监测设施能够远程控制的浮标式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使得生态浮标技术在全球快速发展。近年来,随着水质传感器技术、信息无线传输技术、大数据综合诊断分析技术等软、硬件技术的不断进步,水源水库的水质在线监测技术也发展迅速。我国自主研发的湖体生态监测浮标技术日渐成熟,湖库水源地的自动在线监测浮标已出现国产化趋势[78]。
基于高光谱遥感水质监测原理的高光谱近感水质实时在线监测技术开始出现,有望克服我国在水质传感器设备发展滞后的问题。尽管我国在湖库水质监测浮标的支撑件、数采系统、剖面机械动力、远程传输等方面的技术日渐成熟,但在水质浮标的核心配件传感器探头方面的进展仍相对滞后。目前市场上稳定可靠的水质探头还是大量依赖进口。近年来,基于高光谱遥感水质监测技术的设备与原理,我国多个科研团队开发出了高光谱近感水质监测仪,通过布设在近水面的高光谱信号采集设备,辅以水位、光合有效辐射等相关信息的自动监测,构成水面多信息同步采集系统,结合后台的各种水质反演算法开发与不断优化,能够实现水质断面Chl.a、TN、TP、CODMn、CDOM、透明度、水温等多指标的连续采集,还大大降低设备的维护成本[79]。
开发基于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水质风险预测预警系统能为水源水库水质风险防范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Zhang等基于密云水库入库河流古北口水质断面的高频监测数据,开发了BP神经网络算法,构建了密云水库水体溶解氧(DO)、CODMn、NH3-N等指标时空变化的预测模型[80]。Wang等开发了基于混沌理论的非线性经验动力学模型EDM,能够依据水温、pH、透明度、光照强度、蓝藻生物量等水库监测数据对日本水源地Kamafusa水库中的2-MIB浓度实施短期预测[81]。李慧赟等应用三维水动力生态模型AEM3D等,开发了基于高频自动监测浮标支持下的千岛湖关键水质指标及水华风险的预测预警系统,实施千岛湖水体未来7天Chl.a、TP、TN、DO等指标的逐日空间场的自动预测[82],并通过“秀水卫士”水环境管理平台实施在线运行,为千岛湖水质安全保障提供了技术支撑。
3.2 加强流域土地开发管控及污染源削减与拦截
清洁流域是水库水质安全的根本保障,是水源水库水质风险防范的首选技术途径。从技术类型上,水源水库流域污染的源头削减与拦截技术又可分为4个方面:(1)土地开发管控技术;(2)点源深度削减技术;(3)面源削减与输移拦截技术;(4)河口湿地入库屏障技术。
土地开发管控是水源水库水质安全保障的治本之策。其核心思想是基于水源水库的流域自然地理背景和水库水质保护目标,控制流域开发强度,调整流域人类活动类型和生产生活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从根本上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水源水库高质量保护之间的协同。在该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应注意如下几点:(1)控制土地开发总强度。一个水源水库应守住林地、自然裸地等土地扰动极少用地类型的占比底数,一般应保持在60%以上,可因流域自然地理特征和保护目标适当提高。(2)优化土地利用状况的空间结构。流域污染物从发生到进入水库,其输移入库占比与污染物发生点与水库水体的空间距离、输移线路密切联系,距离越远,入库占比越低;发生点的水土保持越好,入库占比也越低。应优先控制水库临湖面、入库河流两岸及河流源头涵养区的土地开发强度与开发方式。(3)注意对茶园、果园、观赏植物园等经济林开发强度的控制。茶园、果园、观赏植物园(如樱花园、梅园)等虽然在植被类型上属于林地或灌木,在景观上的绿化率较高、土地扰动强度较低,但此类用地大都存在化肥、有机肥投放量大等问题,不能混作人类活动强度低的自然林。溧阳市水源地天目湖的流域调查发现,单位面积茶园氮、磷排放强度都明显高于稻田等一般粮食作物用地,控制流域茶园开发成为保障天目湖水质的重要举措[83]。
水源水库流域一般不存在大的工业点源。如果存在污染较重、规模较大的工业点源,一般建议采用污水管网外排出流域等工程措施予以解决。对于生活污水的点源,应根据水质保护压力适当实施深度处理削减技术,包括:(1)对于较大城镇的污水处理厂,通过工艺调整,强化污水处理厂的脱氮除磷能力,实施更严格的污水厂排放的出水水质标准;(2)增加污水处理厂尾水的湿地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避免尾水直接入河。点源污染深度削减技术方案往往需要与水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相结合。
面源削减与输移拦截是水库流域营养盐控制的重要技术策略。在源头削减方面,既要精准施肥,控制施肥时间,又要注意耕地及茶果园的缓冲带建设,增加施肥后及土地耕作过程中面源污染的原位拦截率。此外,在入河、入库区域,构建湖岸线、河岸、田边、村旁等陆水交错带面源拦截带十分重要。输移过程的拦截主要依靠各种水利工程措施及湿地进行。水库流域的河流大都坡度大,来水不稳定,与村镇等人口稠密区联系紧密。在河流上构建滞水区、湿地斑块等是非常有效的净化措施。根据河流地貌及村镇污染源分布,在河流的村庄段(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陡坡段、缓流区等设置拦水坝,构建储水池及湿地系统,能有效增加磷的沉降、氮的脱出及有机质的降解。需要注意的是,河流湿地需要定期维护,否则磷的拦截能力会下降。Audet等评估了丹麦使用了3~13年的湿地对氮、磷的净化能力,发现氮的去除能力能保持稳定(40~305 kg N/(hm2·a)),而磷的去除能力则随湿地吸附能力饱和而下降(-2.8~10 kg P/(hm2·a)),湿地老化后甚至成为磷的源而非汇[84]。
河口湿地,或者水库前置库,是流域营养盐入库前最后一道拦截净化屏障。根据水库的地貌特征及防洪安全,前置库可以灵活设置,如直接构建拦河坝形成河流湿地区,也可以拓宽河道,旁路引水构建人工湿地,形成旁路净化系统。溧阳市水源地天目湖大溪水库探索了河口湿地净水效果,浅水区种植了香蒲、水蓼、灯芯草、芦苇等湿生植物,能将大量的磷蓄积在湿地底泥中,降低了水库敞水区的磷负荷[85]。Kwun等在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某水源水库河流入口开挖了深约3~4 m、库容17万m3的沉积物捕获槽,对河流来水中氮、磷削减效果明显[86]。
3.3 控制内源
从陆地生态系统中不同地貌单元的生态功能看,水库是流域物质的“汇”,存在功能逐渐 “老化”、自净能力不断下降的风险。流域自然与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量有机物、营养盐、泥沙等,在水库底部不断累积,而底泥中的有机质不断分解,营养盐、污染物逐渐累积、活化。此外,随着库龄增加,水库库容萎缩,库底物质累积,磷、氮、铁、锰、硫等内源释放强度增大,水库内源释放风险加大。因此,从库容维持和水质保障方面看,应密切关注水库底泥的内源释放风险,必要时开展底泥疏浚。
疏浚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水库治理工程手段。只有当水库的底泥活性磷、有机质含量较高,且内源释放是水体富营养化较为重要的原因时,才建议疏浚[87]。底泥有机质含量、磷含量、氮磷内源释放速率、下层水厌氧状况、铁锰含量、水体上下层混合强度,以及氮磷外源负荷与内源负荷比值是判别水库是否需要疏浚的重要依据。溧阳市天目湖沙河水库于2008年实施了坝前1.5 km2的表层高有机质泥层的清淤(清淤深度30 cm),清淤量45万m3,在清淤后约10年内,水库春季水质异味问题都很轻。贵阳市水源地阿哈水库于2015年10月-2016年5月实施了10万m3的生态清淤,清淤后底泥中磷、氮、铁、锰等含量显著下降,间隙水溶解性磷浓度下降4倍[88],底泥对水体营养盐的影响明显减轻。
近年来出现的扬水曝气(water-lifting aerator)技术在水库内源释放遏制方面的应用日渐成熟。在水深大、夏季热分层稳定、疏浚难度大、内源污染风险高的水库中,黄廷林等开发出了扬水曝气技术在西安水源地金盆水库等应用实践,通过将下层滞水层缺氧、低温水提至水库表层,形成温跃层上下水层间的对流交换,显著增加下层水体氧浓度,改善表层底泥的理化特征,遏制底泥中氮、磷、铁、锰的厌氧释放,同时也可以降低表层水温,加快藻类垂向混合,抑制藻类在表层水体的过量生长[89]。
3.4 调控生态系统结构
生态系统调控是通过完善水库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输移和能量流动效率、降低水库生态系统中的物质累积比例、提高营养盐和污染物生态净化能力的一种水质调控生态技术。水源水库水质保障中常见的生态调控技术有3类:(1)鱼类调控技术;(2)藻类生长抑制技术;(3)生态浮岛氮磷净化技术。
鱼类调控技术是通过调整水库中不同营养级鱼类的结构和比例来实现控制藻类等初级生产者在水体中过度增殖的一种生态技术。目前我国水库渔业十分普遍,但关于鱼类调控遏藻的技术策略仍有分歧。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技术策略是投放高营养级的肉食性鱼类、控制浮游生物食性鱼类(鲢、鳙、鲤、鲫等),控制小型鱼类,提高浮游动物生物量,强化浮游动物对浮游植物的直接控制作用。如德国水源水库Saidenbach水库在投放鲢密度10 g/m3条件下,水体透明度明显下降,30 μm以下浮游植物生物量及30 μm以下颗粒有机碳均明显增高,桡足类浮游动物生物量显著下降,枝角类浮游动物生物量下降,不能改善水源地的水质[90];相比较而言,采用大规格鲑鱼投放后则有效提高了水库水质[91]。因此,该研究者认为鲢、鳙等滤食性鱼类控制蓝藻水华的技术仅适用于天然大型浮游动物缺乏的富营养水体[90]。但肉食性鱼类投放控藻也有许多失败例子,如Jurajda等在捷克赫林斯科市水源地Hamry水库开展了4年的鱼类调控,包括拟鲤、鳊鱼、鲈鱼等清除工程,但仍无法有效控制水库中的藻类生物量,该水库外源营养盐负荷偏高、上行效应主导了藻类生物量的变化[92]。我国目前多数水源水库的鱼类调控思路与国际上有所不同,由于鲢、鳙等养殖是我国水库管理中的重要技术手段,合理投放鲢、鳙等滤食性鱼类成为水库生态调控的基本手段。肖利娟等在广东富营养水库甘村水库的围隔实验表明,密度为50 g/m3的鲢投放能有效控制该水库的藻类水华;冬季起捕后则因藻类失去鱼类牧食压力,水华风险反而增高[93]。鱼类调控技术的核心是精准诊断水库食物链结构,并在上行效应有效控制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方案,避免盲目过度投放鲢、鳙。
微囊藻由于细胞体内具有调节上浮的伪空泡结构,可以通过加压破坏其伪空泡和降低其表层光竞争能力的方式进行控制。丛海兵等对微囊藻细胞团实施0.4~0.6 MPa静水压力后,发现大部分微囊藻细胞团在水柱中下沉[94],细胞的生物活性及环境危害下降。我国湖库水华中较大比例是微囊藻水华[95],该技术能成为富营养水源水库微囊藻水华控制提供一种技术选项。
生态浮岛脱氮除磷及生境修复技术本是一种城市河道水体修复技术,但是在水质较好的水源水库的应用很少。唐伟等通过对浮岛浮体结构改造、耐低营养的浮岛植物筛选、人工介质组合、浮岛植物收割管理等研发,开发出适用于深水、营养盐较低(水体总氮约为1 mg/L,总磷约为0.02 mg/L)的水库生态浮岛脱氮除磷及生境修复技术[96]。在千岛湖库尾等中营养水域应用后发现,总氮和总磷的去除率分别可达2.89和0.08 mg/(kg·d)[96],并吸引了大量鱼类产卵,鸟类觅食,在发挥脱氮除磷功能的同时,为水库生物多样性维持提供了重要载体。由于大多数水源水库存在水位落差大、消落带生境差、生物多样性低等问题,生态浮岛技术在水源水库的生态调控方面也具有应用前景。
3.5 创新管理技术
在水库水质安全保障中,管理是引领,技术是手段。如何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来提高流域居民保护水质的主观能动性极为重要。目前,我国在水源水库水质保护管理理论和技术方面正处于不断探索实践阶段。水源水库的水质保护中,行政管理上涉及林业、农业、城建、旅游、水利、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规划、条例等各种管理手段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作。
跨区域生态补偿是近年来广泛探索的管理技术,但是成熟、成功的方案不多。李建等分析了长江流域70个国家级水库水源地的生态补偿状况(依据2016 年水利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2016年)的通知》(水资源[2016]383号)),发现补偿效果相对较好的是贵阳市水源地红枫湖、长沙市水源地株树桥水库及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这3个水源水库都通过生态补偿措施将水库水质维持Ⅱ类[97]。由于补偿者与受补偿者之间在补偿费用、补偿机制等方面诉求的不断变化等,多数水源水库生态补偿方案都要经历较多的利益博弈过程。
设置专门水源地管理机构、制定专门水源地保护法规是较为有效的管理措施,在水源水库水质保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溧阳市设立了天目湖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公室,由分管副市长牵头,具有多部门协调的功能,推动了江苏省人大在全省水源地保护条例出台,有效保障了天目湖水源水库水质的长期稳定。杭州市为保护千岛湖水质,从2012年起实施了3轮新安江共保生态补偿试点,2019年成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2020年出台了《杭州市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管理办法》,在制度创新上探索了大型水源水库的水质安全保障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水质保护效果。
4 结论与展望
水源水库在我国大城市供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水源水库普遍面临富营养化、水质异味等方面的挑战。提高水源水库的水质安全,首先应在水库生态学理论上加大研究投入。水库生态学是一门发展中的交叉学科,水库的水质变化、生态系统结构演替过程、功能变化及其驱动涉及到气候、气象、水文、水动力、水生态、地球化学、流域地理学、渔业科学、微生物学等多个学科,水质与生态系统变化机制复杂,生态调控的响应周期长,水库生态学理论的不足影响到了水源水库的水质安全保障。其中,急迫解决的理论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条:(1)水库水体的异味发生机制,哪些藻类、在何种条件下产异味?细菌是如何参与到水体异味的形成的?(2)蓝藻水华发生的机制与阈值,光照、温度、营养盐、水动力及食物链等多要素如何调控蓝藻生物量的?不同属、种的蓝藻形成水华的条件差异是什么?(3)水库食物链结构与水质的关系,在营养盐相对缺乏、水文条件变化较大的动态体系中,如何维持与水质目标相一致的食物链结构?
在水源水库的水质保护技术方面,目前虽然存在监测预警、污染源削减、食物链调控、应急处置等多种技术,但仍缺乏精准、高效的水质风险防控技术。从技术发展方向上看,更为精准的监测预警技术、更为安全的应急处置技术、更为科学的食物链调控技术、更为高效的外源拦截净化技术,以及更为绿色共赢的流域保护管理技术等都是今后发展的热点。
致谢:本文在全国水源水库问题调研、分析及数据整理中得到了许多学者支持,包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陈隽、沈宏、邓绪伟、李林、毕永红、叶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苏命,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陈敬安、王敬富,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杨军、陈辉煌,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谭香,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谢永宏、李有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郭跃东、谭稳稳,暨南大学韩博平、肖利娟,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赵先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王雨春、胡明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施坤、李未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