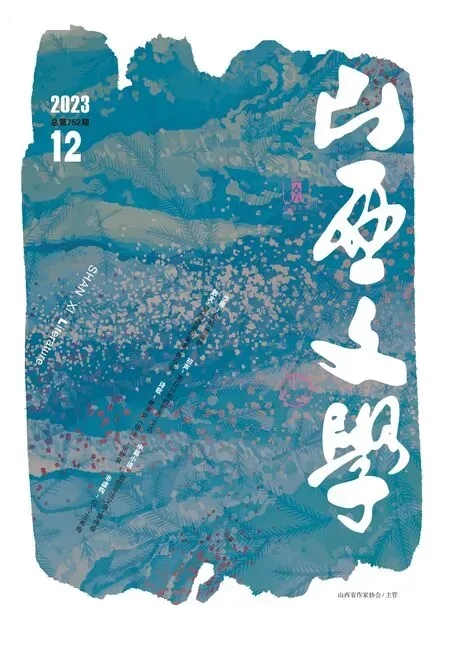黑白分明的世界
艾 达
[编者语]《黑白分明的世界》是一幅画,用的是“点彩”画法。即“用不同颜色的小点来完成一幅画,离近了看是无数彩点,离远了看有具体形象,通过色彩的细微不同来呈现”。作者艾达很有耐心,把艺考生的每一个点都呈现在小说里,考验的是读者的“色感”,以及发现“细节”的能力。
小说不靠故事推动,人物也若隐若现,情绪好像也不是十分饱满。可是,当小说读完,掩卷之后,作者的笔力才渐次呈现,有了具体指向。就算这是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我们的调子也要尽量轻柔。
“右边第二条路,一直向前走,走到天亮为止。”作者这样说。
云朵的手里拿着一支墨绿色的铅笔,疲惫的时候,她就把铅笔夹在鼻子前,狠狠嗅着那种软木头的气味儿,这种气味让她上瘾,其中有一种成分若隐若现,让她想起娘娘家过年点燃的松柏。那团噼噼啪啪的火叫做“旺火”,只要从火堆上跳过去,就能保佑一年顺利。云朵记得火光让她周遭都很暖,一股松香味儿笼罩着她,而祖宗牌位就被供在旺火前的桌子上,怎么说呢,就好像祖先的灵魂都围绕着她,把她包裹在一个暖烘烘的琥珀里,她都想落泪了——这并不是一个许愿的仪式,但她还是悄悄许了愿。
学校里有一条鄙视链,理科生鄙视文科生,文科生鄙视艺术生,艺术生鄙视体育生。在高二的意向摸底后,艺术生的身份就意味着,在班里,老师不会再点你的名字回答问题了,作业爱交不交,就算你旷课,他们也不会有什么过激反应。同学们也不再和你讨论一道数学题,而是半是羡慕,半是鄙视地说,“真好,你不用交这套黄冈卷了。”
云朵是来自文科重点班的学生,成绩中游,写完意向书后,语文老师把她单独叫出来说,“你努努力上个二本没问题,干吗非要去学画画?”
云朵有个学习不错的哥哥,父母非常骄傲。云朵成绩平平,一犯错就被破口大骂,骂完,父母似乎想起了什么,宽恕似的说:“行啦,我们对你没要求,你巴结着点你哥,以后要饭要到他跟前,让他赏你碗饭吃。”
早上六点半,云朵走向艺术楼,扶手是新刷过的,红油漆滴在楼梯上,有点像血迹。云朵之前来过这栋楼,老早盖完后一直空着,有一次在四楼开个英语讲座,云朵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去听,楼里没有装修,洋灰水泥,还露着一些破塑料絮,她们走上四楼找教室,楼道里一个电箱上赫然用红油漆刷着一个“死”字,大家一股脑儿尖叫着往下跑。她们怕是记错了楼层,但那究竟是谁的恶作剧呢?
从五楼开始,楼道上沿台阶摆满了油画,楼梯正对着的是一个房间,门口摆着断臂维纳斯的等身石膏像,这是赵爷的办公室,旁边就是画室了,占据了一整层楼,中间打通,因为是顶楼,光线非常好,显得明亮而空旷。画室是赵爷承包的,他是内蒙人,身材高大,面色黝黑,并不会画画,是个商人。
学校有规定,特长生如高三去学校以外的地方学特长,要额外交两万块钱违约费。可以这样理解,画室就和学校食堂有同样的性质,食堂也是承包的,有人一下承包了十年,云朵入学的时候还有五年,因为这样,饭做得差,各种投诉反映都没有办法,因为学校管不着,但学校有责任不放学生出去,只能让他们去食堂吃饭。
不过大部分学生还是自动留在学校的画室了,因为各班班主任也会给学生家长打电话,说在学校安全,文化课也可以跟得上,家长们都很赞同。只是你要是真的抽空回教室上一节课,老师就问:“你怎么回来啦?”
在画室,云朵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她来自重点班,而画室的大部分学生成绩都很差,这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要通过艺考,他们的文化课达到280 分就可以上个不错的二本。在画室有这么几类人:从小学画画的;为了冲到更好的学校学画画的;成绩太差,待在班里又影响别人,被班主任苦心劝说来学画画的。班主任也不想这样的人留在班里影响自己的升学指标。
在来这里前,云朵曾在另一个叫馨艺的画室学过一年多的素描,她认为自己是有基础的,但进画室测试后,赵爷说,你算是没有基础的,或许你以前学过,但你学的不符合艺考。云朵不服气,毕竟赵爷只是管理人,是个外行。
教画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阿光,湖南人,另一位是王老师,山东人,他们都不高,都爱嚼槟榔。
学生们最爱阿光,他和气,和大家打成一片,笑起来像弥勒佛,就连“阿光”这个外号都是大家给起的,因为他剃光头。而另一位王老师就有些怪异,体形瘦弱,仿佛随时要被吹走,完全看不出山东人的样子,而且他不爱说话,看上去还有点落魄。但他学校更好些,是国美毕业的。云朵说,有一次我们谈到泥塑,他很有兴趣,他问我们,你们猜我第一次玩泥巴捏了什么?坦克?陶罐?房子?佛像?他一一摇头,我们猜不着了,我们琢磨,王老师大概小时候就天赋异禀。但他说,他捏了一口棺材。他爸看见,一脚把它踩烂,还给了他一巴掌。他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做棺材的。
阿光是西美毕业,他的毕业作品被人看中,50 万拍走了,这是赵爷告诉大家的。关于王老师,赵爷所提甚少。但画室还是有了传闻,说他毕业之后去北京的公司做了设计,被同事抄袭,受到打击,身体也不好了,于是重拾绘画,被赵爷请来了。这个传闻大家都相信,因为看王老师的样子,的确像是这么回事。
除了两位老师,还有两个负责管理画室的助理,一个还兼任画室买卖画材的生意。画室的左侧旁边有个小仓库,里面存放着一些画材,最开始的时候赵爷强制大家在画室买了一套玛丽颜料,说我们买别的色彩不统一,有需要的可以在画室买。偶尔,赵爷也会拿出一些速写板、水粉笔之类的便宜东西作为奖品,奖励给进步比较大的同学,并且他一定会当众奖励,让画室里所有人都看到,这就让被奖励的人很尴尬。云朵也被奖励过一个速写板,在做范画的时候,赵爷把她叫到一边,所有的同学都扭头看她。速写板她早有一个,这个新的实在用不上,而且容易让别的同学眼红,就一直在家里放着。
云朵偶尔回一次教室,下课和关系不错的文化班同学一起吃饭,同学看着她的手指很惊奇,哇,你的小拇指好亮。云朵低头,发现自己的右手小拇指的关节处油亮油亮的,是磨出了茧子,画素描排调子的时候,小指要在画板上来回摩擦。
画室最多的时候有将近80 个同学,大家家境各有不同。育才高中刚好建在一个斜坡上,在学校里感觉不出来,出了校门很明显,向左走要爬坡,那边是九几年后开发的城区,有银行、商场、家属院。而向右走下坡,便是老城区,那边有夜市、老旧小区、自建房。大家一同推车子出来,向左向右各自分别,虽能看出家境的一点差异,但也没太差的。
因为云朵的好朋友是要向右走,云朵也想从那边绕回家,路上能和朋友说说话,但她父母一直禁止她走那边,就是因为太乱了,以前夜市那边经常出事,路边有喝醉的起了争执,拿刀子捅人。
“你们条件算很好的。”赵爷说,“去年有个学生,顿顿吃馒头咸菜撑了三个月,实在过不下去了,借手机发了条短信给他妈:我已弹尽粮绝。”赵爷说完,看向画室里的两个复读生:“是吧,李伟当时是这样吧?” 两个复读生点点头。
这两个复读生是去年没考过,还留在这个画室接着学的,成了画室的“元老”,因已经经历了一次,大家有什么事都问他们。其中有一个皮肤黝黑,总穿着一双拖鞋,赵爷每次说什么,都会拿他举例,他成了典型的失败的案例。赵爷说的,他都应和着,就像想减刑出狱的囚犯一样配合,但听说,他私下也骂赵爷。
考试考素描、色彩和速写三科,都是先从素描开始练,这是基础。先练立方体,然后是石膏像,最后再到人物写生。一堂课开始,阿光先画范画,大家围着看,看完回到位置上,自己再临摹一幅,其间阿光和王老师就在画室里巡逻——站在你身后,然后退后两步,眯着眼睛看一下。到了放学时间,验收合格才可以回家。云朵有一次画一个陶罐,画进去了,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塑造罐口,自觉没什么时间吃午饭了,但阿光看了后,却说可以走了,因为罐口的细节刻画得特别好。
“细节”是阿光在巡逻时常喊的一个词,它可能是指一块衬布的褶皱,也可能是一串葡萄的高光,总之是那么一点点小东西,但有了它,画面才能出彩。阿光说,考试的时候没有细节也要创造细节。给你一个立方体,它总归有个缺口,有个裂痕,有那么一点磨损吧,把这些画出来,就像真实的了,它又不是刚从厂里拿来的。
画完一幅完整的,阿光就让大家把画板靠墙摆成一排,依次评点。有时候也测试,把画交上去,再发下来就有评级。“妈的,我又是B。”有人抱怨。也有成绩差也气定神闲的,别人就会问他,“喂,你是不是准备买证啦。”买证就是买“艺考合格证”,根据江湖传闻,有的美院会卖艺考合格证,比如一张南方艺术学院的,市面上是十万元一张。但这是真的吗?孩子们问阿光,阿光摇摇头。但王老师说,是有的,他是国美毕业的,他班里有一个富二代,那人是个色盲,根本画不了画。
评画的时候大多是紧张的,但也有例外。有一次交完作业,阿光把画得差的速写一张一张吸在了展示板上,拍拍手让大家一起过去看。大家一看就想笑,但又不敢笑。阿光用教鞭指着健哥的速写说,你画的是哆啦A 梦吗,还圆咕隆咚的小拳头,又指着小亮的画说,你这个人是刚出土的吗,怎么都僵了。大家再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画得差是要挨骂的,但你画成这样,老师都不忍心说你,老师也笑。
那几幅画在展示板上留了一周,你不能看,一看就想笑,后来赵爷把画收了,嫌做范画的时候大家老去看那些画。等到大家都快忘掉这件事,有人说,哎,你还记得健哥那幅画吗,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又笑了,整个画室里都充满了欢快的气息。
画室的桌子上摆满石膏头像,大家都挨个画过,小卫、布鲁斯特、阿里斯托芬,还有阿波罗。阿波罗最帅,但最难画,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很难找型,还要找到明暗交界线,让学生们纷纷叫苦。反而是阿里斯托芬最好画,脸上都是皱纹,头发也是垂下来的直发。学了画画,才知道老年人好画,因为脸上很多皱纹,画重了不太要紧,还有沧桑感。年轻人皮肤光洁,一画多就容易脏。
画室的一个大箱子里放着各色塑料水果、陶瓷罐子和酒杯,每次写生的时候,阿光都去里面掏出几件,摆好衬布,把罐子酒杯一一摆好。学生们根据自己所坐位子的不同,可以选择构图,常用的是C 型构图和S型构图,这样画面错落有致,才有美感。赵爷他们抽完烟,随手把烟头扔在陶罐里。有时候大家会去拿一些,画素描的时候用烟嘴的那个白色的棉絮来“擦”画,可以让颜色重的地方渲染开,云朵也很喜欢这一步,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更精细的地方直接用手指去擦,更柔和。
画室里还有一些画册,很多是阿光买来的,这些画册都比较贵,都是好几百一本的,很厚重,装帧很好。阿光放在那里让学生翻看,自己休息时也会看。其中有一本莫奈画册,云朵很喜欢,经常靠在窗台前看。云朵说相比风景和人物,她最喜欢静物。随手翻开一幅油画静物,桌上一堆散落的水果,还有一个插着雏菊的细长陶罐,几片花瓣落在衬布上,显得又古典又寂静,云朵说看到这样的画就会感觉心很稳,没有那么浮躁了。
对云朵这些艺考生来说,看这些大师的作品只是闲暇时的调剂,主要还是临摹那些比较适合艺考的书。市面上流行的绘画书主要有两种风格,美院风和联考风。艺考首先要过联考,每门要到60 分,三门一共180 分以上,才能参加校考。这两种风格有不同的要求,联考风要求黑白灰强烈,明暗交界线明显。简单地说就是要画得黑、卡点准、对比强烈。
阿光给大家讲过评卷现场,会租一个大操场,把所有的画摊开,评卷人员手拿长教棍,给这些画进行略略地分类,黑白灰强烈的画有视觉冲击,老师一眼可以看到,可以分到高分那一档,画面太淡雅的即使画面很细致,因评卷老师不会细看,也容易被忽略。为了能有更强的色彩对比,有的人甚至用颜色更黑的炭笔画画。
和联考风不同,美院风则追求高级灰,整个画面最好呈现出一种灰色调,要求画面细腻,转折微妙,过渡自然,看上去浑然天成,画面干净。虽然两位老师都是美院毕业,自己也追求美院风,但在教授学生时,都按联考风来教。毫无疑问,美院风应付联考不占优势,而且需要花费更大的工夫,需要天分来领悟,对这些半路出家的艺考生来说实在画不来。而联考风比较套路,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能照猫画虎,运气好就能应付过联考。
长时间画这种风格的画,阿朵觉得,仿佛自己的生活被简化了,收缩成一个黑白分明的概念的世界。
素描和色彩画久了也枯燥,学生渐渐失去兴趣,只是机械地重复。这时阿光会和王老师商量,教一些别的东西来调剂,比如学习点彩画法。这是修拉创造的一种印象派的画法,即用不同颜色的小点来完成一幅画,离近了看是无数彩点,离远了却有具体的形象,整个画面通过色彩的细微的不同来呈现,可以锻炼学生的色感。画完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同样一张静物照片,大家会画出不同的效果,有的整个色调很亮,有的却很暗沉,但都很和谐,画面统一,这就是成功的,不成功的是有的色点很跳,离远了一眼就能看到,融不入整体。
阿光说云朵色感很好,一个苹果放在衬布上,有衬布给它的颜色,有光线给它的颜色,还有离它相近的物体给它的颜色,这些色彩非常丰富,阿光说的色感好,是说她能捕捉到这些环境色,色感不好的人只能看到物体的固有色。
但云朵的造型能力不好,对骨骼理解不深,画头像时上调子上的贴不上骨骼,画得很平,没塑造起来,这个问题画室很多人都有。王老师说大家可以买一个小的石膏头骨,多观察琢磨。他学画时他舍友就买了一个,每天在手里把玩,睡前也不放手,有一次半夜睡着了,头骨从床上滚下来,骨碌碌滚到地上,吓下铺的兄弟一跳。
云朵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太大进展,想起前段时间馨艺的老师问她现在的情况。云朵把自己的几幅习作拍给馨艺的老师看,老师让她周日下午来一趟画室。其实云朵的心思也不稳,到了快暑期集训的时候,有一些同学离开了画室,去找了学校外面的新画室。云朵问了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他说育才太大了,两个老师,根本顾不过来你,他去的那个画室一共八九个艺考生,老师都很关注,可以手把手教。同学还偷偷告诉云朵,画室的画材比外面卖得都贵,一罐颜料多卖一块五呢,他找到一家便宜的画材店,把地址给了云朵。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画室人太多,阿光和王老师都有几个偏爱的学生,会多去指导,剩下的人只有画完了被点评一下,老师给学生分出了等级,自然会更关注那些画得好的。云朵只能算中等偏上,因为画室里几个是从小学画的,童子功,画得比较扎实,一接受这种艺考的训练,提升很快,老师都当宝贝,希望他们可以冲刺到最好的美院,这样放榜出来,画室明年可以招收到更多的学生。
周日下午,云朵带着自己的几幅画去馨艺画室,馨艺离云朵家很近,在过了马路的第二条街道内,街口有一家花店,店员总是穿着一件绿色围裙,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处理花材,旁边的垃圾桶丢着蔫了的太阳菊,有灰霉的多头玫瑰和花瓣掉了一半的向日葵,更多的是修剪下来的花枝,走过去的时候可以闻到湿漉漉的植物根茎的气味儿。画室就在这个店旁边的小巷子里,这个巷子的名字特别好,叫“幸福巷”。云朵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彼得·潘》,“右边第二条路,一直向前走,走到天亮为止”,这是彼得潘告诉温蒂的去永无岛的路。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街道上一直走,云朵想。
馨艺是一个带小院的二层楼,老师是一对夫妻,楼上男老师教初中以上的学生素描,楼下女老师教小孩画一些简笔画,小孩不好管,总是闹哄哄地跑来跑去,女老师总被气哭,上楼无助地拉一拉男老师的胳膊,让他下去管。男老师和女老师非常恩爱,男老师经常买花束送给她,玫瑰、百合和绣球,这让画室的女孩非常羡慕。那些玫瑰干枯了就插在陶罐里给学生写生,男老师对女老师的宠爱,大家都看得出来。
云朵再次来到馨艺,觉得人少了很多,原来女老师怀孕了,肚子已经很大了,行动不便,带不了小孩,新学期就没再招生,只剩男老师在楼上带年龄稍大的孩子。指点完云朵的画,男老师透露出一点意思,想让云朵到这里来集训,他来教。云朵说要考虑一下,因为男老师之前没带过集训的学生,云朵也不敢冒险。回家和父母提了一句,他们说,那画室八成开不下去要倒闭了,这些搞艺术的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当从馨艺出来的时候,云朵想起那个她在馨艺认识的男孩,白白净净,不爱说话,总是戴着一副白色耳机闷头画画。他的画架不是从画室买的铁制收缩画架,而是一座真正的木头画架,上面钉着钉子来支撑画板,云朵刚来馨艺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有一次他爸骑车过来交学费,来的路上,车坏了,他爸一路把车推到画室门口,把他叫出来一起修车,他爸蹲在地上修,他就在旁边低着头扶着车子。那时老师等着上课,挺着急的,出去看了好几次,回来抱怨说,先让孩子进来画画嘛。云朵也在心里想,快进来吧,快进来吧。但最后老师还是先讲了,空隙间云朵瞥向窗边,他们没有修好那辆车,一起推着车子走了。
云朵后面没再回过馨艺。八月的时候,赵爷带着大家去北京丰台集训了两周,那边的画室和育才有合作,也接待全国各地的艺考生。
云朵的一排笔袋上,按硬度插着2B-8B的铅笔,木色的是“玛丽”牌,一支一元。而那种墨绿色印着烫金字母的,是“三菱”牌,一支三元,画室极力推荐大家购买,但也没人把全套配成“三菱”,大多是和两种牌子混着用。去北京的第一天,北京的那个负责女老师拿了一个垃圾桶,让大家把其他杂牌子的铅笔都扔了,那是垃圾,她说。
第二天大家临摹陶罐时,女老师又冲进来,“谁没冲厕所,是没长手吗?你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素质真差,我们也接待过别的城市来的,怎么就没出过这种事! 再让我看见一次,我让赵老师把你们带回去。”女老师气冲冲发完一通火,大家都很懵,但谁也没敢说话。
除了育才,还有内蒙的一个画室也带了学生在这边,内蒙的男孩女孩普遍比较高大,一进到画室就很显眼,写生的时候也很强势,挤在前面的好位置,不像云朵她们一样不好意思。有时候两个画室的学生会在一个教室画画,北京的老师也会更偏爱他们。
云朵说在北京的十几天一直感觉不好,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可能是头一次出远门这么久不适应,也可能是,一直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这种细碎的感受白天来不及咀嚼,晚上却像蚂蚁一样咬得你不舒服。可是赵爷强调,你学画,想考上,就得吃这样的苦。云朵知道,其实赵爷一直看不起大家,他只是想赚大家的钱,他的态度是那种,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儿的吗,你就是差,才选了这条路。
也不止云朵有这样的感觉,有一天云朵醒来,发现另一个女孩坐在床上,直勾勾地看着前面,云朵问她,她也没反应,过了一会儿她回答,她想回家了。同宿舍还有几个女孩,晚上回来带了几瓶酒,还有一瓶很小的二锅头,玻璃瓶的,说从小超市看见的。云朵之前除了果啤从没喝过酒,抿了一口试试,除了难喝没觉得有什么,结果半夜胃里烧得慌。
集训结束最后一天,赵爷叫来一辆大巴,带大家去798 艺术区,路边有很多卖画的,就是你坐那里,他给你画一幅,收30 块钱。大家看见了都说,这简单,我们也干得成,等艺考完那个暑假我们也去路边给人画头像赚钱。
从北京回来之后,大家都有些蔫蔫地。感觉自己就是在破地方的破画室里用破铅笔画画的人,可能一辈子和美院没什么缘分。云朵也格外失落,她的“同桌”回新疆去了,她爸妈离婚,她爸在新疆做生意,她跟着落了新疆户口,到时候去那边考,要更好考一点。
“怎么啦,怎么啦,” 阿光看到大家的状态,只好说:“有的人很早就确定了要当画家,可能从小就开始学,我们画不了他们那么好,但我们画得差不多也可以上个好大学。”
阿光的话没太奏效,大家无精打采地临摹着照片。阿光说,不临了,我们现在写生,早上谁最后一个进画室?
于是,三十几个学生撑着画架,错落着围着一个被选中的模特男孩。男孩端坐在一把蒙上衬布的靠背椅上,光线在右边,打过来的时候照亮了空气里的灰尘。大家都盯着男孩看,男孩有些害羞,正襟危坐,不敢马虎。过了一会儿,周遭就只剩“刷刷”排调子的声音了,男孩松口气,有时歪一下头,有时摸摸鼻子,大家对他很宽容。当然,有时候也会幅度大一点,“啧,别动”,那是暴躁的女生忍不了了。
除了画画,你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盯着一个人看一整天了,云朵有些感动。有那么一天,你的任务就是盯着他看。看他头发生长的走向,看他嘴唇上的两条细纹,也看光影怎么贴着他的骨骼和肌肉表现:如果你是双眼皮,那么光线会在你的两层眼皮间投下一个小小的阴影。
对画者来说,笔触就是他们的语言,写生还在继续,云朵的调子比别人的都轻柔——这在艺考中并不讨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