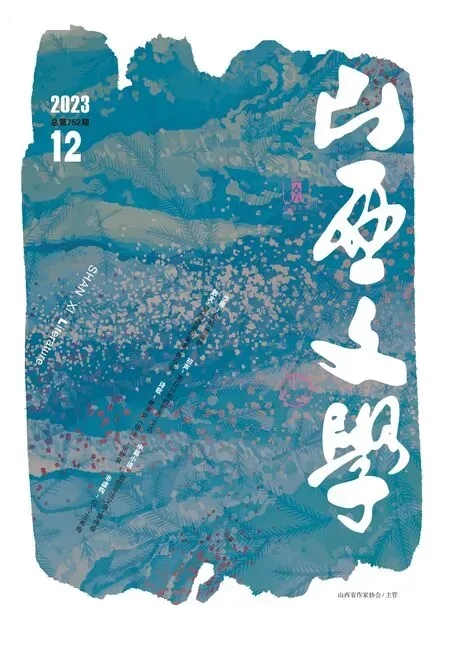现在开始喝酒是不是早了点
钱墨痕
在英剧里总能看到这句话,现在喝威士忌是不是早了点,但只要这句说完,两人必定开始喝酒,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从来没有太早而不能喝酒的时刻。常在河边走,喝酒的人免不了酒醉,但再怎样的醉酒也不会让人们放弃酒精,这可能是记吃不记打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第一次印象深刻的醉酒是2014 年代表江苏去山东培训,那天我们几个江苏的到得晚,山东哥们没说罚酒三杯的话,只说你们是南方人,不欺负你们,一瓶两口喝完就行。那年二十岁的我,想着输人不能输阵,率先站了起来。第二天我衣着整齐地在床上醒来,记得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个大三的山东青年作家在给张玮讲自己新写的长篇,而我倚靠着一个山东诗人。天色很暗,他指着远处的一团漆黑告诉我那座山就是徐志摩坠机的地儿。
两年后第二次醉酒是在台湾,我们大陆过去的被叫作陆生,宿舍四个人,一个带着女友一起来的,一个迅速在陆生中找到了女友,剩下的我和杰哥时常互相打气去跟台妹做朋友,但台妹从来不搭理我们,唯一理我们的是学校附近的小炒店的老板娘。我们吃腻了食堂,常去那儿点几个菜然后喝一杯,即使老板娘的厨艺乏善可陈。那天我和杰哥喝得好好的,在陆生中找到女朋友的那个与女友吵架,过来找我们喝酒。他之前没喝过酒,看我们小口抿着金门高粱,说很难入口吗?然后一口喝掉半玻璃杯,我们自然不能丢了老酒鬼的名声,节奏被打乱之后则一发不可收拾。那是我第一次(也许第二次)睡在大街上,杰哥第二天告诉我,起夜时看见我躺在床下,探完我的鼻息后才进的厕所。
第三次醉酒时已经去了北京,一个来鲁院培训的老乡带我改善伙食。我喝着酒看一桌人吹了整场的牛逼。那几天胡迁刚死,虽然我们互不相识,但仍心有戚戚。逝者已逝,活着的还这个X 样,不自觉我就把自己搞多了。研究生宿舍的床很高,离地有一米五,我没法像往常一样把盆放到地上再精准地吐进去,便把盆拿上了床。那天不出意外地吐了好多,但意料之外的是在半夜睡熟之后那个盆在床上翻了。醒来之后室友跟我说,“坠机不好受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在那之后就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醉酒了,倒不是武艺练成了,只是相比于坠机的苦,更苦的地方比比皆是。这篇小说源于我身边一些朋友的经历,她们都是很好很快乐的人,但摆脱学生身份进入社会后,总能遇到这样那样我能理解却难以解决的问题。小说最早叫《淹没》,讲的是婚姻中的人慢慢被日常琐碎所淹没的状态,它跟前传《山海》(表姐方海生的故事)一样都取名于我很喜欢的歌谣,改名的《坠机》则更关注婚姻失序后无措的惶恐以及处理办法。婚姻不是一切问题的起点,但对于婚后的人们来说,平日里与世界发生的所有矛盾会在婚姻这个载体中得以交汇,一旦交汇得不恰当,两条线只会越走越远,或者在天上飞得好好的,忽然就掉下来了,连伞都来不及跳。这样的例子在我身边有一些,说不上来感受,谈不上惋惜,只觉得遗憾。
开头提到记吃不记打,人们总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事,即使犯过错,也坚信一切都是意外,下一次狂风暴雨再来的时候,自己一定会像海燕一样,起码不至于像之前那样坠机。我知道有些事情很难改变,但仍希望能通过这篇小说来祝福每一段可能处于坠机中的感情,以及那些还得平稳飞行一会儿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