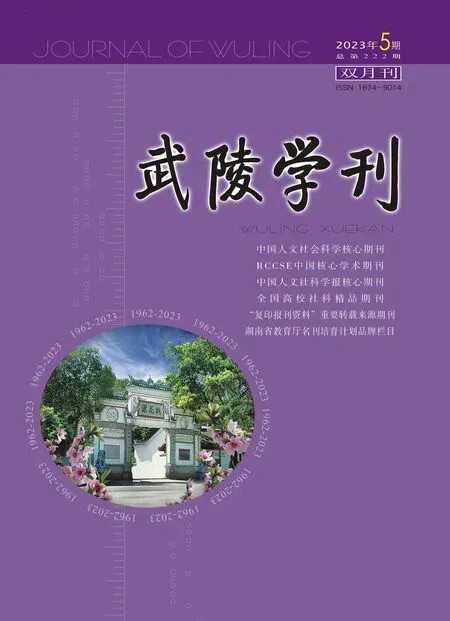明儒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研究
——以《南赣乡约》为核心
王翠英
(三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当代中国乡村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的时期,“转型中的乡村伦理出现了传统理念与现代意识间的冲突与紧张”[1],广大乡村道德主体因此陷入道德迷茫与困惑之中。因此,在全面振兴乡村的时代背景下,丰盈乡村道德主体的精神世界,进而发挥道德软实力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样是社会转型期,明儒王阳明在南赣地区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可以为当代中国乡村道德建设提供方法论启迪。
一、王阳明乡约治村的历史背景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3],王阳明博大精深的心学理论及其乡约治村思想都源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一)明初乡约治村的兴起
明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就广大乡村而言,明朝统治者不仅重视乡村经济发展,而且重视乡村道德主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为取得良好的思想建设成果,明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全方位推进乡村道德建设。
明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参考前制在广大乡村实行里甲制度,中叶之后里甲制度逐渐演化为保甲制度。无论是里甲制度还是保甲制度,其实质都是以户为单位通过户籍制度将处在江湖之远的村民编制入册,使其牢牢固定在熟人社会的范围内,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流民窜走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将乡村道德教育对象稳固起来,为乡村道德建设提供了保障。除里甲和保甲制度之外,明朝还在乡村推行里老制度,也就是赋予乡村有威望的老人治村的权力。里老制度是典型的“以良民治理良民”的道德范式。乡里有威望的老人被赋予惩恶扬善的权威,他们凭借自己的道德权威,调解宗族村民间的矛盾纠纷,具有道德裁决权,里老制度的实质是引导村民行善积德。此外,“(明)朝廷还下令在县城和乡里设立旌善、申明二亭”[4],将村民所行善事或恶事进行公示以昭告天下,发挥乡村道德教化的引导和惩戒作用。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规民约,是北宋陕西蓝田吕氏兄弟订立的《吕氏乡约》。吕大钧作为关学传人致力于乡约治村,但是其范围局限于蓝田一地,且持续时间不长,社会影响也不是很大。在大儒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增损后,吕氏兄弟乡约治村的影响才遍及全国。虽然《吕氏乡约》经王阳明增损后名声大振,但是其现实生活中的执行情况仍值得商榷。有学者考证,朱熹只是对乡约治村的理论进行了完善,杨开道认为:“朱子自身是否用过乡约,都是一个疑问。”[5]换言之,乡约治村虽兴起于北宋,却并不曾普及甚至也没有引起大宋朝廷的重视。但是到了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已经开始强调乡约治村了:明太祖朱元璋制《圣训六谕》,另行乡约;明成祖朱棣制《乡约规条》,第一次以国法的形式颁行乡约。明朝统治者对乡约治村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乡约治村的实践,明朝因此成为传统社会乡约治村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和重要阶段。
也就是说,王阳明的乡约治村实践是在明初统治者重视乡村道德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王阳明独特的乡村境遇
王阳明出生于礼部尚书之家,从小家境殷实,受到了良好的儒学教育,有着非常扎实的儒学理论功底,这为他日后开山立派奠定了良好基础。按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逻辑进路,明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考中进士,曾一度担任刑部、兵部等要职。1506 年,明武宗继位不久,宦官刘瑾擅政,朝臣戴铣、刘健等人联名上书弹劾刘瑾,反遭刘瑾迫害入狱,王阳明不顾个人安危上书武宗论救,惹怒刘瑾,自己被杖责入狱。出狱后,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任驿丞。龙场位于贵州西北,当时的龙场万山丛棘,蛇虺魍魉遍布,蛊毒瘴疠令人生畏,王阳明曾这样描绘龙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恶劣:“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6]802“居夷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6]1228更重要的是龙场处“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6]876。这样,王阳明就从嘈杂的世事中沉寂下来,生活变得简单、质朴。
王阳明生活在一个社会变动、道德混乱的年代,混乱的世道及其曲折的人生经历,促使他有了新的人生思考。王阳明在赴龙场之前一直在研习程朱理学以及佛老之说,痴迷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但是在龙场,王阳明无雅会文士之机,澄心默坐,他原本芜杂混乱的心开始澄明起来,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了新的理解:“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6]120王阳明在龙场悟到了典章制度之外人性至美的光辉,意识到龙场这样的乡村才是明朝道德救赎的希望所在,由此他把道德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民间底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朝堂。很显然,王阳明的这一学术进路没有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可,所以阳明心学长期被朝廷视为“伪学”“异端”,而历史却给了王阳明一个佐证自己理论的机会。
王阳明在龙场谪戍期满后,几经周转再任南赣巡抚,在赣南地区征剿贼寇获胜,但他深刻感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6]168。为帮助平乱之后的“新民”破除“心中贼”,王阳明在其管辖地区大力推行乡约,寄望乡约能帮助“新民”实现道德认知转化,于是《南赣乡约》诞生,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由此拉开帷幕。也就是说,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与其传奇的个人经历关系甚大。
二、王阳明以乡约为核心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
王阳明南赣平乱后,为保证赣南地区的长久稳定,他在此进行了全方位“破心中贼”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
(一)建构了以礼、法、德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乡村道德治理体系
王阳明在赣南地区进行的乡村道德治理,根本目的是想唤醒广大村民的良知,他认为,人人自觉认识到良知并能按照良知行事,社会就能稳定。当然,王阳明并没有对山野之民进行简单的良知教育,而是采取了“法—礼—德”三位一体、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治理方式进行教育感化。
法、礼、德三位一体是儒家道德建设的传统和根本主张。孔子对法、礼、德的道德建设功能进行了阐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刑(法)来规约道德行为容易收到实效,而单一的刑(法)虽然能立竿见影,道德主体却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道德治理手段,不能根治道德问题,而且刑(法)使用过当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造成白色恐怖气氛。德的教化虽能使道德主体明白所以然,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容易使道德建设疲软乏力、流于形式,而且单一的德化教育见效时间较长,无助于提升道德建设的时效性。显而易见,德、法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而礼作为制度性规定,能将德、法的长处集于一身:礼作为制度,具有强制性,克服了德教乏力的局限,但又不似刑(法)的刚性,不会引起社会恐慌;礼作为“道德”制度,具有教化作用,克服了刑(法)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足。因此,孔子在乱世中致力于复礼的实践,他创立的儒学被称为礼学。王阳明在赣南地区的乡村道德实践,重点强调的也是礼,形成了以礼为中心、以德法为两翼的乡村道德治理体系。
具体而言,在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体系中,礼为《南赣乡约》,法为“十家牌法”,德为书院和社学。
“十家牌法”实质上是一种保甲制度,规定每十家设一牌,并将十家丁口的职业等信息标注出来,供轮流巡查时对标核查;及时申报人口流动情况并对牌进行调整,否则便会被认定为黑户,有一家隐匿盗贼则另外九家须连坐。很显然,“十家牌法”具备刑罚律例的严苛特征和刚性约束。
书院是古代贤达讲学布道的场所,王阳明通过创办书院以讲学的方式进行乡村道德教育,帮助村民提升道德认知。王阳明一生创办了很多书院,大多是专门开展乡村道德教育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龙冈书院。龙冈书院位于贵州龙场地区,受教者均为当地成年百姓及儒生,文化水平不高,王阳明讲学的内容重在联系村民的日常生活实际进行道德教化,而不是传授抽象的心学义理。社学则始于元代,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社学,主要针对孩童进行道德教育。王阳明在赣南、广西思田等乡村设立社学,以教化乡村孩童。书院专注成人,社学专注孩童,书院隔日讲学,社学每日开课,就这样,王阳明将乡村中的主要人群纳入他道德教化的范畴。
法和德作为道德治理手段均有局限性,熟知道德建设规律的王阳明深知乡村道德建设只有作为法的“十家牌法”和作为德的书院与社学是不够的,所以他在赣南地区订立了《南赣乡约》,并以此为中心统领乡村道德建设。显然,《南赣乡约》是以乡约形式出现的道德建设之礼,具有一定强制性,既能有效克服书院和社学道德教育乏力的缺陷,又不像“十家牌法”那般严苛,能为广大村民所接受,它将书院和社学道德教育之义理以世俗规范的方式传递到道德主体的内心深处,提升了书院和社学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由此王阳明建构了以《南赣乡约》之礼为中心,左手牵法(“十家牌法”的法),右手挽德(书院和社学的道德教育)的乡村道德治理体系。
(二)提出了以《南赣乡约》为标识的乡村道德治理方案
如上所述,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体系是以《南赣乡约》之礼为核心的,梳理《南赣乡约》便可管窥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主张。
《南赣乡约》分为谕民文告、乡约条例、实施程序三个部分。
谕民文告阐述了制订《南赣乡约》的缘由和目的,是乡约的导语部分。在谕民文告中,阳明先生指出人的善恶皆在一念间,均受人心驱使;制订乡约就是为了淳化人心,通过人心的淳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营造出“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7]125的良好乡村伦理氛围。
乡约条例共15 条,内容涉及乡约组织构成、乡约运行规范、风俗礼制规范等三方面,是《南赣乡约》的主体部分。《南赣乡约》首先对约内职位设置作了明确规定,规定设约长1 人,约副和约赞各2 人,约正、约史和知约各4 人,并对相关职位的人员的产生和职责作了规定:“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逐日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7]125其次对乡约经费来源、会期、约会纪律和内容类别(彰善或纠过)等运行细节都有详细规定,如“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7]125。最后是风俗礼制,王阳明用儒家礼制对赣南地区乡村习俗进行了规制,是《南赣乡约》的核心,涉及乡村婚丧嫁娶、宴请、借还、买卖、邻里、新民等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虽然结合赣南当地习俗对乡约进行了儒学阐释,但是他没有完全沿用赣南旧俗,而是批判了当地一些陋习弊俗,特别是对神仙巫术和攀比奢靡之风进行了严厉批判,《南赣乡约》明确指出“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7]127,“毋大奢”[7]125,这些规约对改进赣南地区乡村落后文化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改善陋习弊俗提升了当地的乡村道德水准。
《南赣乡约》还对乡约的实施程序诸如约会前、约会中的流程作了说明,并对约会程序乃至约长等人的言语、动作作了详细规定:“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7]127“酒复二行,遂饭”[7]128等。
这样,王阳明通过《南赣乡约》的谕民文告、乡约条例、实施程序,将进行乡村道德治理的原因、内容以及措施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南赣乡约》约定的虽是世俗之事,但是它蕴含了儒家为人处世的基本行为准则。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王阳明针对广大村民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以“体用”的方式宣传了自己的“致良知”学说,这对提升村民的道德素养产生了积极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明代的乡规民约与宋代乡绅制订的侧重道德教化的乡约是不同的,明代的乡约多由官方制定,由此比宋代多了一些训诫性的外在规约。《南赣乡约》开篇所指出的“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7]125,少了宋时乡约中“劝”“规”的意蕴。而且《南赣乡约》还将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的精神引入其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8]的“圣谕六言”在《南赣乡约》中虽没有原文呈现,但其精神却被发扬光大:“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7]125“圣谕六言”之精髓都体现在《南赣乡约》中,其“官制”色彩由此可见一斑。简而言之,《南赣乡约》从订立程序到内容构成再到言语表达,都与之前的自发协商、身教大于言传的乡约有所不同,《南赣乡约》的诞生标志着官方力量已经正式介入乡约治村,虽然官方与民间乡约治村的目的一致,但乡约的性质已然不同。
三、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的实践特色
王阳明是史上少有争议的立功、立德、立言的圣人,乡村道德治理是王阳明实现立功、立德、立言的主要场域。《南赣乡约》不是王阳明的理论著述,而是其道德实践的事功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
(一)内外发力:育良知与立规约并举
程朱理学是王阳明时代的官学,它虽然为儒学找到了本体依据,但是其过于侧重道德思辨,导致了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分离,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便使人们拘泥于道德知识的学习,没有充分重视和激发人伦日用中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从而使人心被物欲蒙蔽。虽然朱熹反复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将践行伦理纲常理解为出于外在的道德命令,而非源于本心,尤其对那些蛮荒之地的山野村夫,他们是无法弄清朱熹“格物致知”的义理关系的,其道德行为完全是事功式地由自发认知所支配。
与朱熹相较,王阳明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发明本心,从内部入手,强调良知之教的重要性,并针对广大乡村道德主体的实际情况,以书院、社学的德化教育引导村民回归本心认识良知,确立自己的道德主体精神。可见,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是以内部发力育良知为基础的,但王阳明深知通过书院和社学来进行德教的长期性,所以他在引导村民回归本心认识良知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乡约”,为道德建设提供保障。
王阳明制订的乡约是以礼的方式存在的,它弘扬了儒家传统道德,并以此化民风正民俗,但是其乡村道德治理过程却是以“法”为主。《南赣乡约》中没有微言大义等义理内容,都是用最简洁的言语对村民的琐碎生活进行直截了当的规约。《南赣乡约》重视读约、宣言、戒谕、申诫、彰善、纠过等仪式,对乡村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作了规约。与《吕氏乡约》“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7]9不同,《南赣乡约》奉行“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7]125的理念,要求所有乡民必须全部入约、入约之人必须全部赴会,偶有生病或急事无法赴会则需提前请假,无故未赴会者不但要“罚银一两”,还要纠过,可见《南赣乡约》的强制性特征。《南赣乡约》用强制性的规约驯化村民,虽然略显机械,但是在践行乡约的过程中广大村民的礼仪观念和道德观念得到了有效提升,乡村道德建设成绩显著。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方略是内外兼顾、双向发力的,这既是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实践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之一,也是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实践的特色之一。
(二)立足实际:物质与礼俗双向互动
王阳明订立《南赣乡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赣南乡村的长治久安,因此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南赣乡约》订立之时,正是赣南地区动乱之际,人口流动性较大,寄庄和新民较多,而寄庄者“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7]126,这就加重了同甲人的负担,新民又常常侵占原乡民的田产,使得寄庄人户、新民与乡民之间矛盾不断。为此,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进行了规约:对寄庄人户,约长应劝令其“及期完纳应承”[7]126,嘱其不可重蹈覆辙,否则便“削去寄庄”;对新民,勒令退还田产,“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7]126,而且要求乡民“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7]126。这样,《南赣乡约》事实上不仅对不同身份类别的村民的义务进行了规范,也给予不同身份的村民同等权利,充分保障了乡村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王阳明此举看似旨在解决村民间的具体矛盾,实际上是在夯实乡村道德建设的秩序基础。
与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相较,《南赣乡约》忽略了长幼尊卑分班之礼,这说明王阳明不太在意繁文缛节式的软性道德问题,他更在意现实的道德建设,所以《南赣乡约》里既有“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7]127等关乎“冠婚丧祭”的礼俗规约,也有拜兴之礼、酌酒之礼的规约,这样就可以通过现实性的礼俗约定来重建乡村道德秩序。《南赣乡约》不但凸显了礼俗规约的实用性,还对村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了针对性规定,比如,经济层面有“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7]126,邻里纠纷方面有“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7]126,彰善纠过方面有“若有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卖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诫。不悛,呈官究治”[7]126,惩治腐败方面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7]126等。
可见,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既关注乡村道德建设的物质基础,又积极推进礼俗等乡村实际道德问题的解决,并且重在从乡村实际生活出发解决乡村道德建设问题。
四、王阳明乡村道德治理实践的当代价值
王阳明以《南赣乡约》为中心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对当今的乡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乡村道德建设
在城市化、现代化浪潮中,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经历着全方位的嬗变,传统乡村道德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现代乡村道德体系尚未完全确立,村民的道德认知陷于迷茫、困惑之中。对于广大乡村的伦理道德变迁,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进行引导,比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19 年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积极推进乡村的公序良俗建设,帮助广大村民树立新思想、革除旧观念,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由于各种思潮的冲击,当代乡村仍然存在“婚恋金钱化”“孝道利己化”“生态意识淡化”等伦理道德问题,这说明乡村道德建设和基层治理任重而道远。
王阳明在进行乡村道德治理时,立足于当时赣南地区乡村道德生活中的“大奢”“阴通贼情”“揽差索财”等实际问题,主张内外发力、辨证施治,不仅注重外部约束,而且更加注重村民道德认知的提升,因此取得了良好的乡村道德治理效果。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告诉我们,乡村道德治理必须以乡村道德问题为标靶,不仅要注重外在的道德规约或感召,更要重视和加强对村民进行内心体悟的道德训练。王阳明这种“内外”发力、以问题为导向的乡村道德治理路径的有效性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我们今天进行乡村道德建设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展专门的、有针对性的、非运动式的乡村道德教育活动。
(二)坚持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乡村道德治理路向
王阳明的乡村道德治理实践的最大特色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乡村道德治理。《南赣乡约》是针对赣南地区的实际制订的,其规范与解决的问题都是困扰赣南地区村民多年的实际问题,具有明确的、具体的问题指向性,不是对道德议题的泛泛之论。“立足实际”这种接地气的、直接指向当地具体道德问题的乡村道德治理方式,对今天中国的乡村道德治理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当代中国的乡村道德建设方案多从宏观角度设计,对村民实际道德生活的具体针对性不强。尽管在城乡一体化、信息化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乡村已不再是偏远之地,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乡村道德建设的一致性增强了,但各地乡村仍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和文化传统,因此乡村道德建设仍然要体现乡土气息,因为乡土气息是乡村道德主体的情感所在、精神所系。我们应遵循王阳明立足实际以民为本的道德治理思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原则和目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符合当地实际的乡规民约,提升村民的伦理认同,因为“伦理认同是潜隐在历史线索和民族政策等现实要素背后的文化因子”[9],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群体道德状况的重要因素。虽然“伦理”与“道德”经常会被等同使用,但实质上“伦理”更微观也更贴近人们的情感、心理,当代广大乡村之所以出现乡愁难平、乡情难近等现象,就在于乡土伦理的离散。乡规民约承载了村民的伦理认同,有了乡规民约,则村民内心的道德感便充盈了,便不会再有所谓道德迷茫与困惑了,所以当代的道德建设方案应该让乡规民约真正落地生根,充分体现它的乡土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