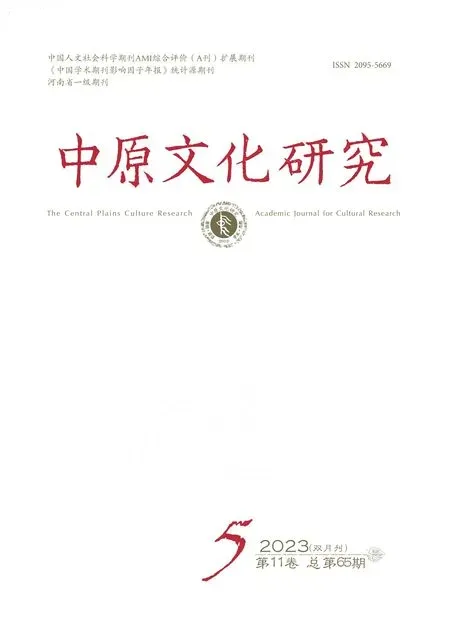何以行孝:王船山诚孝之“心”的逻辑展开*
陈力祥 吴 可
船山云:“孝者,生理之不昧者也,在人为心,在天为理。”[1]1131孝既是天理的一部分,又是人心的共同之处。在天为理,是众之所基,在人为心,是人之所同,本身应是人与生俱来的德性,但船山所处的明末清初之际,神州陆沉,败行丧伦,世人行孝常徒慕其名而不得其心,立孝在外却不能尽诚于己。因此,船山对孝这一问题展开了思考:孝是什么?为何要孝?何以行孝?种种问题最后只落到一处:这作为天理的诚孝之“心”,究竟是如何推扩出去,从而指导人身的孝道实践的。
船山所说的“心”是一切事、物、理的尺度,“事无定名,物无定象,理无定在,而其张弛开合于一心者如是也”[2]273,也就是说,人对天理的追求和把握应由心生发,以心缘求,不能执着于寻找作为主宰的某一事某一物,对孝的体认自然亦复如是。船山有言:“夫忠孝者,生于人之心者也,唯心可以相感。”[3]704从形上角度看,孝本质上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投射,其价值内涵源于天理,落实之依据则有赖于人心,需要用“心”去感通和把握孝的形上之理。从形下角度看,孝虽投射于人身,但“言君子之于其亲,存没一致,恒存于心”[1]1104,人“身”有存没,“心”却恒存,“存没一致”的恒存之心便成为“孝”在人世间存在与运行之依据。
由此可见,船山的“心”不仅是人对天理进行认知、把握“孝”形上之理的依据和方法,还是人践行天理、指导“孝”形下实践的原则和指归。人可以通过“心”这一媒介体认孝道的本质,实现天人之间的融贯,船山以“心”行孝的孝道实践系统由此建立。
一、“持志以诚意”的行孝之基
诚孝之“心”是孝道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界定何为心之“诚”的状态。于此,船山回答可归为三层。
其一,“诚”是不自欺的。“不诚者,自欺者也”[4]414,船山“自欺”的“自”指的是“心”,即“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4]417,而“自欺”的“欺”并非传统的欺骗之意,而是“因其弱而陵夺之”[4]419的欺凌之意。所以在船山这里,“自欺”实际上指的是从自己心上发出去的“意”欺压、陵夺了自己的本心。而“诚”的状态恰好相反,“诚者,尽其心而无所苟”[5]170,即心志坚定,不为意欲所乱的自足、自慊状态。其二,“诚”是善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礼记·中庸》),当人复归于“诚”时,就会坚定为善去恶的道德选择,“唯其诚,是以善;惟其善,斯以有其诚”[4]1053。在船山看来,“诚”与“善”互为前提,诚孝之心与恻隐、羞恶之心也并无甚区别,均为善端,只是呈现方式不同:“事亲、从兄,是从顺处见;恻隐、羞恶,是因逆而见。”[4]942故所谓“诚”,自然是以人性之善为导向的。其三,“诚”是符合理的。船山在提及四子问孝时说道:“至于四子问孝,答教虽殊,而理自一贯。总以孝无可质言之事,而相动者唯此心耳。故于武伯则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动所性之爱;若云‘无违’,云‘敬’,云‘色难’,则一而已矣……而无违于理者,唯无违其父子同气、此心相与贯通之理。顺乎生事之理,必敬于所养,而色自柔、声自怡。顺乎葬祭之理,必敬以慎终,敬以思成,而丧纪祭祀之容各效其正。”[4]609对于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子问孝,孔子的具体回答各有不同:云“无违”,云“敬”,云“色难”,但细究其理,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即无违于父子同气、此心相与贯通之理,顺乎生事之理、葬祭之理。最终之解都会归于“一理”,也就是天理,“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故心之“诚”的状态即为人子顺应“生而不昧”的孝之德,以“心”贴合天理。这三种心之“诚”的状态互为因果,实则一致,总的来说即为人坚守心志、为善去恶、复归天理的自洽状态。
明确了心之“诚”的状态,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坚守心之“诚”,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辨析“志”“意”之别,从而“持志以诚意”。船山曰:“自一事之发而言,则心未发,意将发,心静为内,意动为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则因心发意,心先意后,先者为体于中,后者发用于外,固也。”[4]419他从事情的发生机制(表象)与概念的内在联系(本质)两个方面出发,对“意”与“身”“心”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从事件之发生机制来看,心未发为内,意将发为外;从概念之本质上来说,心先存为体,意后发为用。按照船山的思想理路,孝道通过“意”的联结实现由“心”入“身”,行孝之实践按照“孝之心—孝之意—孝之行(身)”的逻辑顺序展开。按此逻辑,在理想情况下,只要人人都从诚孝之“心”出发,事亲行孝应为理所当然之举,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就在于“意”与“志”有别,“意”之发用并非只由“心”决定:
意者,心所偶发,执之则为成心矣。圣人无意,不以意为成心之谓也。盖在道为经,在心为志,志者,始于志学而终于从心之矩,一定而不可易者,可成者也。意则因感而生,因见闻而执同异攻取,不可恒而习之为恒,不可成者也。[6]150
船山认为,“志”是人心中的事物当然之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意”包括心中所有偶然生发的念头,会被多种因素影响。所谓“志大而虚含众理,意小而滞于一隅也”[6]167,在船山孝道思想的逻辑中,“志”虚含了“诚孝之理”,并以此生诚孝之“心”,诚孝之“心”带动“诚孝之意”的发用,最终落实到行孝之实践。但在此过程中,诚孝之“心”并不能统摄所有的“意”:“意不尽缘心而起,则意固自为体,而以感通为因。”[4]419“意”的最终发用不只来源于心,还会被身边的事事物物与所见所闻干扰,且这些干扰多出于个人之私欲,“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7],这些私意、小欲便会生发意之“乱”。又因为“心”与“意”并非单纯的体用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意累其心,心欲救之而无益;意如其心,则心之正者得以常伸。”[1]1486“意”对“心”具有反作用,当二者同向相如时,执意便能为心;当二者反向相累时,意乱就会危心。所以在船山看来,若放任意欲之“乱”,就会危害到原本的诚孝之“心”。
船山曰:“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6]258虽然圣人纯乎志而无意,不受意欲之“乱”的干扰,但对于庸人、中人和君子来说,“志”与“意”的存在呈负相关,二者此消彼长。君子为了避免沦为中人、堕为庸人,必然需要“持志”功夫。“持志”就是坚守心之定向:“盖心之正者,志之持也。”[4]417在心中生发的念头中筛查出何为意欲之私,何为性之所诚,如此便能“立心为主,而以心之正者治意,使意从心,而毋以乍起之非几凌夺其心”[8]66,而后治意欲之乱,正心之本体,推扩“心”之诚以克制意欲之迁流,诚孝之“心”才能更好地落实到诚孝之“行”。
船山云:“抑事亲从兄之道,固身、心、意、知之所同有事。”[4]688孝悌之道是身、心、意、知的综合发用,其中“身”是行孝的直接主体,“心”“意”“知”均属实践之前的认知领域,“一志所发,心也;随念所发,意也;觉体所发,知也,而天下之物,其理著见,皆所以触吾之心意知而相为发者也”[1]1469,天下之物的存在及其道理的显现均有赖于人“心志”“意念”“知觉”的相互发用,事亲之理亦是如此。因此,在船山孝道思想实践体系中,“心”是行孝的根本动力,“意”是“心”与“身”之间的联结点,孝道通过“意”的联结由“心”入“身”,但因为“意”会随见闻而起,受个人私欲之干扰,危害原本的诚孝之“心”,所以船山认为有必要落实“持志”的功夫,坚定心性之所诚,以治情欲之迁流,只有以此为心性前提,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好地事亲行孝。
二、“心存爱敬,外修其礼”的行孝之方
“持志以诚意”是行孝的心性基础,但还未涉及具体的人伦与社会关系。孝道的践行不仅要“知”孝之理,还要有“行”孝之法,如何才能将诚孝之“心”真正落实到“知”与“行”两方面呢?对此,船山说道:“言诚者曰:‘外有事亲之礼,而内有爱敬之实。’”[4]528船山认为行孝之法一为里诚,即内有爱敬之实;二为表诚,即外有事亲之礼。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内无爱敬之实,而外修其礼,固是里不诚;内有爱敬之实,而外略其礼,则是表不诚。事亲之礼,皆爱敬之实所形;而爱敬之实,必于事亲之礼而著。爱敬之实,不可见、不可闻者也。事亲之礼,体物而不可遗也。”[4]530“爱敬之实”与“事亲之礼”作为事亲行孝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法,前者为体,后者为形,知行表里,缺一不可。
其一,船山认为具有知爱、知敬的心是行孝之法的根本要求和内在方法。“爱敬”一词所出甚早,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5]1215船山对此注解为:“孝悌之德统天下国家之治,而孝悌之实则爱敬是已。爱之推为贵老、慈幼以相亲睦,敬之推为贵德、贵贵、敬长以成顺治,皆立其本而教大备矣。”[1]1113-1114“爱敬”是孝悌之实,是人诚孝之心的基本要素,如二程所言:“及其既生也,幼而无不知爱其亲,长而无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见乎外。当是时,唯知爱敬而已……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9]所谓“敬其所尊,爱其所亲”(《礼记·中庸》),“爱”与“敬”是人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情感,二者可以相互作用:“以其敬、将其爱,以其爱、延其敬,而后追远之道备。”[10]425“亲亲者,爱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11]51同时,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鬼神之德,礼乐之体,凝于人者为爱敬之心,神无方而不遗,故四海之内,人皆涵爱敬于心,以为性情而无殊也。”[1]904“爱”与“敬”是人人皆有的性情之德,可以共同促成“孝”在现实中的行动。
其二,船山以爱敬为礼之体,事亲之礼是爱敬之心的外在表现形式。“礼之本无他,爱与敬而已矣。”[11]51“‘礼仪卒度’,敬之谓也。‘笑语卒获’,爱之谓也……故心无不有焉,无不实焉,无不容焉,礼斯秩焉。”[10]425人有爱敬之心,就能事亲以礼。虽然爱敬之实与事亲之礼有体用之分,但并无逻辑之先后,二者是同时发生的,船山曰:“爱敬与事亲之礼而同将,岂其于未尝事亲之先,而豫立其爱敬乎?”[4]528意思是爱敬并非在事亲之先,以心行孝的过程也并非以内外为先后的两截功夫,因此船山对爱敬之心与事亲之礼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将二者视为内外交相省察的功夫,并提出“以无违而中礼”和“以礼而得无违”的两条行孝路径。
(3)具有一定的系统设计和开发能力。编程能力是对编程思维的训练,系统设计和开发是要求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要分析当前的问题,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完成系统的开发,最后达到对问题的解决。系统设计和开发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
盖自孝子而言,则所当致于亲者,无违中之条理品节,精义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尽心竭力以几之,没身而固不逮,岂有余力以溢出于非礼之奢僭,是以无违而中礼也。自求为孝子者而言,虽尽心竭力以求无违,而未知所见为无违者,果能无违否也。故授之礼以为之则,质准其文,文生于质,画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达于天子,皆有随分得为之事,可以不背于理,而无所不逮于事亲之心,是以礼而得无违也。[4]603
所谓“无违”,自然是无违于“爱敬之心”的内在要求,所谓“中礼”,对应的自然是“事亲之礼”的表现形式。船山将行孝之法的实施方式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为理想情况,即自身本为孝子,其行孝方式是由内达外、自诚而明的,故而能“以无违而中礼”。这种情况设想的是,人在面对双亲时,行为被爱敬之心所主导,丝毫不违背心之“诚”,当做到尽此孝心时,便自然而然地不会有任何余力做出僭礼之事,其行为自然是符合事亲之“礼”的,这种诚心诚意、自然而然的行孝之法被船山称为“以无违而中礼”,是圣人之专属,也是常人之榜样。二是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即自求为孝子,以事亲行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行孝方式是以外治内、自明而诚的,即“以礼而得无违”。这种情况适用于大多数人,对于他们而言,爱敬之心与事亲之礼之间并非全然贯通,存在着前文提到的意欲之“乱”的干扰,所以不能只凭当下所想去衡量其行为是否“无违”于“爱敬之心”,还需要依照一个参考标准去执行,这个外在的参考标准便是事亲之“礼”。以“礼”作为“无违”之标准,顺从孝礼,做好为人子的分内之事,便能不悖于理,自明而诚,以外在之礼治内在之心。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以心行孝的实施方式在“无违”与“中礼”的次序上并不一致,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对“心”的运用也有所差异。若是“以无违而中礼”,自然是顺其爱敬之心,发乎事亲之礼,均是“心”的自然流露,不必用力;但若是“以礼而得无违”,则需格外关注和发挥“心”的主观作用。船山言:“如为子而必诚于孝,触目警心,自有许多痛痒相关处,随在宜加细察,亦硬靠着平日知道的定省温凊样子做不得。”[4]411“定省温凊”是指子女四时侍奉父母,早晚请安,问寒问暖,属于事亲之礼的一种,“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5]16,人子行孝有诸多细节,若只讲求平日里知道的冬温夏凊的样子,浮于孝礼之表面,那么心诚与否也是看得出来的。“以礼而得无违”的事亲之礼并不能取代爱敬之心作为判断依据,它只能弥补“心”被“意”所乱时的行为偏差,最重要的行为衡量标准还是诚孝之“心”。如朱子言:“如事亲以孝,须是实有这孝之心。若外面假为孝之事,里面却无孝之心,便是不诚矣。”[12]阳明亦有言:“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13]船山亦是此意,诚孝之心为根为本,礼仪节文为枝为叶,即便是以外治内的行孝之法,其根本还是需要一个诚于孝亲、知爱知敬的“心”,否则事亲之礼就会流于表面而不能恒常。
总而言之,在具体的行孝方法上,船山以“内有爱敬之实,外有事亲之礼”作为双重要求,按内外先后次序分为“以无违而中礼”和“以礼而得无违”两条行孝路径,并强调在“以礼而得无违”的现实情况下,诚孝之“心”仍是事亲行孝之根本。
三、“一而不执”的行孝之度
船山孝道实践思想的逻辑展开在于诚孝之“心”的推扩,孝本生于心,先天具存,不需要通过学习和思考就能对其进行感知和体认,但孝不能只存于心,还要施之于行,所以需要充此心之全体大用才可以行孝:“盖孝友之德生于心者,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苟有其心,不能施之于行,则道不立而心亦渐向于衰矣。学以能之,虑以知之,乃以充此心之全体大用。”[1]669指的是运用心本身所具有的思维和情感能力,“扩而充之者,尽心所本有之术也”[4]950,通过“尽心”发现人心中本有的孝,进而充分体认、培养和发挥心中的孝,将诚孝之“心”的本来面目落实于现实的孝之“事”。
但需要注意的是,“心”的作用是无尽的,“极心之用,可以大至无垠,小至无间,式于不闻,入于不谏”[2]274,充“心”之用并非易事,极有可能迷失方向,歧路亡羊。所以船山认为,在行孝过程中,还需要遵循“一而不执”的用心尺度。船山曰:“古之圣人治心之法,不倚于一事而为万事之枢,不逐于一物而为万物之宰,虚拟一大共之枢机,而详其委曲之妙用……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之用,又患其执也。”[2]273“患其不一”的侧重点在于“一”。“一”即前文提到的“持志”功夫,强调的是对心志所向的坚守而不至于被物欲所役;而一之用“患其执”的侧重点在于“不执”,强调的是在坚守的过程中,还要避免对自己当下心意的执着,警惕走入歧途而不知返。综合来看,“一”是无不及,“不执”是无过,二者相合,便能达到“无过无不及”的恰好状态。
将船山“一而不执”的用心原则置于事亲行孝的实践之中,具体表现可归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坚持诚孝爱敬之心,此为用心之“一”;另一方面则要根据对象和现实情况变通行孝之法,知常达变,此为“一”之“不执”。用心之“一”恒常不变,“一”之“不执”却时有不同,二者其实就是“质”与“文”的关系,船山曰: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则必伤于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为敬。不可为敬,是不能资于事父而同敬矣。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同以爱,而非以爱父者爱母。以爱父者施之母,则必嫌于疏略,而非所以爱母。非所以爱母,不可为爱。不可为爱,是不能资于事父而同爱矣。爱敬之同,同以质也。父与君、母之异,异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后质如其质也。故欲损其文者,必伤其质。犹以火销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14]
以“敬”“爱”为例,敬父与敬君都是“敬”,爱母与爱父都是“爱”,但却不能以敬父之行为来敬君,否则就会流于粗俗鄙陋;也不能以爱父之行为来爱母,否则就会嫌于粗疏简略。“爱敬之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基于对象之不同、具体情况之不同,孝行的形式和样态也是不同的。船山以“质”与“文”解释爱敬之同异,外在的“文”以“质”为基础,行孝之事必然不能背离诚孝之心的基础;同时内在的“质”也需要通过“文”得以呈现,二者应相互匹配。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若一味追求孝之本质,按照惯常的行为规范行事,虽然在道理上并无疑虑,但在结果上反而会背离诚孝之心。因此,在用心时需要积极发挥心的主体作用,对“一而不执”多加权衡,将孝心与孝行相贯通,同质异文,知常达变,才能更好地事亲行孝。
船山有言:“唯夫事亲之道,有在经为宜,在变为权者,其或私意自用,则且如申生、匡章之陷于不孝。”[4]450以申生、匡章为例,船山论述了何为“执”于己意,以诚孝之心行不孝之事。申生作为晋献公之长子,被献公宠妃骊姬陷害却不辩解,为让父亲心安,顺从自己忠君孝父之心,最后选择了自尽;匡章不愿未得先父的命令而改葬其母,还因得罪于父未能奉养,而出妻屏子,终身不用他们奉养。船山对二者的“孝行”不敢苟同,他批评申生道:“申生以君安骊姬之故,不忍辩而死,君德失,宗社危,而以不忍君失其宠嬖之情,任其煽惑,瘖死无言;臣而若此,则非臣也,臣以责难为敬者也。子之事父,爱敬并行,而敬由爱起,床笫之欢,私昵之癖,父安而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3]869可见在船山看来,申生不忍明见谤之由而死于骊姬的行为,不仅不会让其父心安,反而会致使父子相杀,让父亲陷于不义。作为人子,申生有爱敬之心,却并未做到爱敬并行,才会背离了孝之初心,其行为应归为不孝之举。船山认为申生、匡章等人将诚孝之心私意自用,最后陷于不孝之境地,都是用心“一”且“执”带来的危害。船山曰:“执以一,不如其弗一矣。用一而执之,不如其弗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异端之诐而贼道,无他,顺心之所便,专之而据为一也。”[2]273对船山来说,相较于无有孝心,执于自己所认定的孝心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迷而忘返,异端贼道均由此而起,故而“用一而执之”不如不用。
那么如何才能充心之用“一而不执”,既有诚孝之心,又兼具事亲之才呢?对此,船山以舜与文王作为“孝德之优”的典范:“假令一人有孝德以事亲,而无事亲之才,则必将欲顺而反得忤。申生之所以仅为恭,而许世子且不免于大恶,其可谓孝德之优乎?必能如大舜、文王,方可云优于孝德。”[4]720舜事瞽瞍、文王问孝,都是充心之用“一而不执”的典范。《家语》载:“舜事瞽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15]《礼记·文王世子》载:“文王之为世子……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5]551二者在行孝方面有心亦有才,舜虽忠孝而不愚孝,文王敬爱而不繁缛。虽然申生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牺牲,但牺牲本身并未尽其孝道之优,甚至让践行孝道更加困难烦扰,“令天下之父子许多疑难处依旧不得个安静在”[4]1010,而舜之孝行变通得恰到好处,其行为看似对孝道之偏颇,实质上是以权宜的方式合乎孝的要求:“依旧父爱其子,子承其父,天下方知无难处之父子,何用奇特张皇,不安其所而强有事也!”[4]1010-1011舜将诚孝之心与行孝之事融会贯通,其行为既不过分执着,也无丝毫违背诚孝之心,如此才能称之为用心时“一而不执”。
总而言之,申生、匡章用心“一而执之”,故流入歧途;舜、文王用心“一而不执”,故能知权达变,以诚孝之心行事亲之事。尽孝之道的手段在于对诚孝之心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对象和现实情况进行变通,以心行孝的手段便是守爱敬之“一”,行孝之“不执”。
四、“自然生乐”的行孝之境
船山以诚孝之“心”为核心来建构孝道实践系统,其旨在于推扩心之“诚”,使人子以“事亲”为“乐”,达到自然而乐的状态。船山认为,“事亲方是仁之实,从兄方是义之实,知斯二者方是智之实,节文斯方是礼之实,乐斯方是乐之实”[4]1008,“乐”与仁义礼智之德一样,有表之形,也有里之实,而乐之实就是事亲从兄时没有苦难勉强,而是自然而生的“乐”。船山曰:
唯能以事亲、从兄为乐,而不复有苦难勉强之意,则心和而广,气和而顺,即未尝为乐,而可以为乐之道洋溢有余;乃以之为乐,则不知足蹈手舞之咸中于律者,斯以情益和乐,而歌咏俯仰,乃觉性情之充足,非徒侈志意以取悦于外物也。此乐孝弟者所以为乐之实也。[4]1008-1009
船山此处说“乐之实”是“觉性情之充足,非徒侈志意以取悦于外物”,其实就是心之“诚”而不自欺的状态,船山释“毋自欺”为“所知者意必于此而发,所志者意必不与相违;则自知之,自欲之,而还自遂之,此之谓自快足其心”[8]66,指的就是“意”由“心”生发,不与其相违背、和顺不妄动的状态,此时的“心”是“自知、自欲、自遂、自快”的,不会因为取悦于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心意。这个时候事亲行孝才是全然发自本心,无一丝勉强之意。如此,以事亲、从兄为乐的“乐之实”才能被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
船山在孝道践行领域中所说的“乐”的含义与其原始本义不同:“缘乐之为教,先王以和人神,学者以治性情,似所用以广吾孝弟者,而非孝弟之即能乎乐,故孟子又推出学乐者一段真情真理来。”[4]1008最初的“乐”是先王为教之方,学者以“乐”陶冶情操,此时的“乐”并未与事亲行孝产生因果上的联系,而后孟子提出将“乐”作为事亲从兄之乐:“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船山便在孟子之意的基础上进行发挥,认为孟子之旨在于强调“乐孝弟者所以为乐之实”,虽然娴于音律舞蹈也可以为乐,但这种乐并未发自内心,容易受到外物干扰,导致心志意念之放纵,所以并非“乐之实”,真正的“乐”是在事亲从兄之道中体会到的“乐”,归属于人心之德,其手舞足蹈的结果是诚孝之“心”综合发用的外在表现形式。
在此基础上,船山提出了以诚孝之“心”达“自然生乐”的孝道实践之理想,以“乐”作为事亲、从兄的极顶位次。船山言:
“乐斯二者”一“乐”字有力,是事亲、从兄极顶位次。孔子所谓“色难”者,正难乎其乐也。故朱子曰:“要到乐处,实是难得。”不是现成乐底,须有功夫在。其始亦须着意,但在视无形、听无声上做去,调治得者身心细密和顺,则自然之乐便生。自然之乐,是“生”字上效验,勿误以解“乐”字。始乐时,一须加意去乐,此圣贤一步吃紧工夫,不可删抹。[4]1009
对于船山来说,“自然生乐”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在事亲、从兄的过程中下功夫的。首先,此乐“始亦须着意”,故船山行孝之实践以“意”作为“心”与“身”之关窍,关注“意”的变动迁流,并用“心志”对其加以控制;其次,此乐要“在视无形、听无声上做去”,故行孝之法须得“内有爱敬之实,外有事亲之礼”,将诚孝之心化为日用伦常之礼,看似无形无声,实则早已化入了行孝的各个行为细节之中,成为孝心自然流露之常态;最后,此乐使人“身心细密和顺”,便是用心“一而不执”,积极发挥“心”的主观能动性,恰到好处地处于“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状态,将心之用与身之形融会贯通,细密和顺。如此一来,明晰了行孝之基、行孝之方、行孝之度,行孝之“乐”便自然而生,成为船山以心行孝的最终目标和理想状态。
结 语
诚孝之“心”是船山孝道思想由本体领域向实践层面展开的逻辑转承点,上通而下达的特殊位置赋予了此“心”两重作用,它不仅是认知孝道的心性基础,也是现实中人子事亲行孝的动力核心和根本依据。首先,心之“诚”作为合天理、不自欺的为善状态,对孝道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子诚能孝,臣诚能忠”[6]360,正如后世郭嵩焘所言:“自谓父子兄弟、尊卑上下,所处各有攸宜,以至诚行乎其间,而孝、弟、慈之谊油然自生于其心。”[16]因此,诚孝之“心”以其合天尽性的特点,成为孝道思想在实践领域展开的根本前提。船山为了解决实践领域中“身”与“心”的贯通问题,选择将“意”引入孝道的逻辑体系之中,但“意”之发用并非只由“心”决定,还会被身边的事事物物与所见所闻干扰,所以船山强调“心志”对“意欲”的控制作用,坚守心之定向,遏制意欲迁流。其次,在此心性基础上,船山以爱敬之心和事亲之礼作为行孝之法,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得出“以无违而中礼”和“以礼而得无违”两种可能性,并强调在“以礼而得无违”的情况下,需要格外关注和发挥“心”的主观作用,不能让事亲之礼越俎代庖,最重要的行为衡量标准还是诚孝之“心”。再次,因为“心”的作用是无尽的,为了让心之用发挥其最大效力,且不误入歧途,就需要遵循“一而不执”的用心尺度,坚守心之所向,同时知常达变,以舜与文王作为典范,将诚孝之心与行孝之事融会贯通。最后,“持志以诚意”的行孝之基“始亦须着意”,知爱知敬、事亲以礼的行孝之方“在视无形、听无声上做去”,“一而不执”的行孝之度使得人“身心细密和顺”,此三重诚孝之“心”的逻辑展开与“自然生乐”的功夫一一契合,行孝之乐自然而生,船山以诚孝之“心”展开的孝道实践思想体系由此卓然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