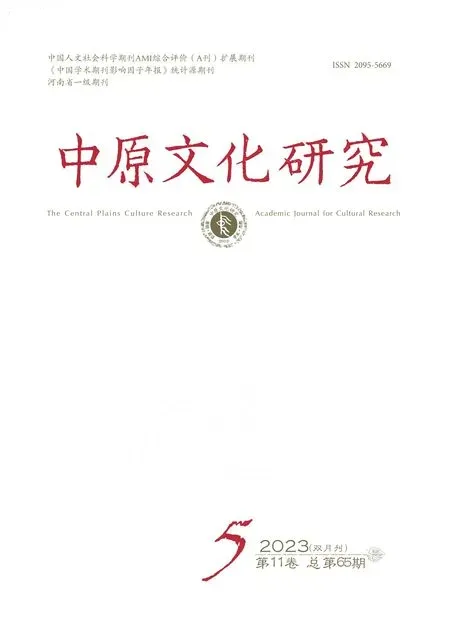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赵永春
古代“中国”一词内涵较多,既有用来指称华夏、汉族的民族内涵,也有用来指称一国之中心“京师”(包括“中央”“中央之城”“都城”“国中”“王畿”等)的国家中心的内涵,指称中原的“地理中国”的内涵,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中国”的内涵,指称国家政权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中国国家”的内涵,等等。在“中国”的多种内涵之中,到底哪一种内涵是“中国”一词的主要内涵或称核心内涵,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新清史一派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一词的主要内涵是用来指称华夏族、汉族及其政权。其实并非如此,用以指称王朝国家(不仅用以指称以华夏族、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也包括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①的“中国”内涵,才是古代“中国”一词的主要内涵。
一、“中国”国家观念的起源
学界普遍认为,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和《尚书·周书·梓材》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现文字记载“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
1963 年陕西宝鸡贾村镇出土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其内底铸有铭文122 字,记载了西周成王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之语,内容涉及周武王克商以及营建成周(洛邑)等史事,其中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1]。意思是说,周武王攻克大邑商后,曾廷告上天说:我要在“中国”建宅居住,在这里统治人民。《尚书·周书·梓材》中周成王曾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②即皇天已经将“中国”之民交给西周武王治理,武王远拓疆土,光大先王之道。今王(成王)应该继承先王之政,惟明德是用,以和悦天下迷愚之民,不负先王受命。学界多认为这两篇文献中所说的“中国”是指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即后来所说的中原地区)。其实,这两篇文献所说的“中国”,已具有多重内涵,除具有用以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一国之中心的京师以外,也具有用以指称“中国”国家政权(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内涵。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是武王克商后廷告上天时说的话。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曾在故商京师朝歌的国家社坛举行隆重的祭天大典,武王宣布“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2]126,宣布西周王朝取代商朝,正式建立国家。田广林等认为,这一记载与何尊铭文“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3]。据此可知,何尊铭文所说的“宅于成周(洛邑)”与“宅兹中国”并非完全相同的同义语。成王“宅于成周”(洛邑)是指在今洛阳建宅居住,武王在故商京师朝歌的国家社坛所说的“中国”,似指故商京师朝歌,即用来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有国家才会有京师,恐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有指称商朝的意思。因此,田广林等人认为,何尊铭文所说的“中国”与“大邑商”相对,恐也有指称商王朝的意思[3]。也就是说,何尊铭文所说的“中国”,除指称京师以外,也具有指称国家政权的内涵。
《尚书·周书·梓材》所说的“中国”,用以指称国家政权的意思更加明显。陈连开认为《尚书·周书·梓材》所说的“皇天既付中国民”,应该是“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付与周武王治理”[4]的意思。顾颉刚、王树民认为,这里说的“中国民”,就是指“周本国及其人民”[5]。曹音则认为,“皇天既付中国民”的意思是“上天既已将殷人殷地付于先王”,即将《尚书·周书·梓材》所说的“中国”释为“殷人殷地”[6]。罗蓓等也认为“在周人心目中,最初的‘中国’是指商人故地,‘中国人’则是指商朝人”[7]。田广林等进一步认为,“中国民”及其“疆土”,“无疑是指原属商朝直接治下的民众及其旧有疆土”,“中国”一词本身,“指的是商王朝国家政权”[3]。也就是说,“皇天既付中国民”中的“中国民”,虽有指称“周本国及其人民”的意思,但主要还是指商朝人民或谓商朝遗民,所说“越厥疆土”,用以指称商朝的疆土也是很清楚的。这说明,西周初年出现的“中国”一词,具有用以指称商朝国家和西周国家的内涵。
实际上,用以指称国家政权的“中国”观念,可能出现得更早。《孟子》记载,唐尧时发生洪水灾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中国”之民无以为食。后来,尧、舜任用大禹治水,最终平息水患,“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8]。此所说“中国”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地区。学界一般认为夏禹时期已经建立夏王朝国家,尧任用大禹治水时,虽处于国家建立前夕,但到大禹治水成功后,夏王朝应该进入国家形态,“中国可得而食也”的“中国”,应该具有指称夏朝国家管辖地区的意思。如是,孟子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一词,应该具有指称夏朝国家政权的意思。唐孔颖达为《礼记·檀弓上》作疏称:“禹爱乐其王业,所谓由治水广大中国,则乐名《大夏》。”大禹通过治水工程,扩大了“中国”范围,因定乐名为《大夏》[9]。其所说“中国”,无疑也是指夏朝国家政权。这里的“中国”,虽为唐朝人孔颖达所说,但为追述夏禹时《大夏》乐曲名称之由来以及禹平水土等事,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夏朝的一些史事传说,当符合夏初历史实际。如是,则可以进一步说明,夏朝已经出现了“中国”观念,夏朝在用“中国”一词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以外,也用来指称夏朝国家政权了。这说明,早在夏王朝时期,“中国”国家观念就已经出现了。
二、“中国”国家观念的确立与初步发展
春秋时期,人们在夏商周时期出现的以中原地区所建政权为“中国”的基础上,继续称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周、卫、齐、鲁、晋、宋等国家为“中国”,又因为这些国家主要为华夏族所建立,开始出现“华夏中国”的观念,而不认同在中原以外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秦、楚、吴、越等国家为“中国”。但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观念出现变化。《史记·天官书》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2]1328,又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2]1348,即称西方秦人建立的秦国为“外国”,而称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为“中国”,将楚国划分为东方六国之一,也有了认同楚国为“中国”的意思。这时期,秦国虽仍被视为“外国”,但出现了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如《史记·秦本纪》载,秦缪公时,西方的戎王派遣从晋国投奔到西戎的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曾对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2]192秦缪公在这里说的“中国”,很是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中国”释为东周和中原各国的话,只能说明秦缪公没有承认自己属于西戎,而是视秦国西边戎王为戎夷。但从当时秦缪公与由余对话的语境来看,秦缪公所说的“中国”,不像是在说与双方谈论话题无关的第三者东周,似有自诩秦国既有文化又富有,且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意思。如是,秦缪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有指称秦国的意思了。由余听了秦缪公的话,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由余在这里所说的“中国”,虽有指称中原华夏王朝的意思,但由余是针对秦缪公的话进行反驳的,似乎也没有谈论与双方无关的第三者的意思。所说“中国”,也应该是指秦国。秦缪公听完由余的议论以后,感觉由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害怕由余为敌国戎夷所用,对秦国构成威胁,遂问策于内史廖,内史廖说“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再通过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使由余为我所用[2]192-193。内史廖在这里先说戎王“未闻中国之声”,然后就让秦缪公“遗其女乐”,无疑是视秦朝“女乐”等为“中国之声”的意思。所说“中国”,就是指秦国。这就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虽然仍被中原诸国视为戎夷,但已经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思想观念。
秦统一六国后,更是以“中国”自居。如李斯曾就攻打匈奴之事谏称,如果进攻匈奴,将会出现“靡毙中国,快心匈奴”[2]2954的局面,所说“中国”,就是指秦朝国家。秦始皇在秦朝以“中国”自居的基础上,进一步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他采纳邹衍有关“终始五德之运”的学说,按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的关系排列出黄帝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秦朝为水德的中国正统传承序列,明确标榜秦王朝是继承周朝的“中国正统”王朝。秦王朝以“中国”和“中国正统”自居,在后世得到认同。如隋唐时期的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就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10]3914,宋末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11]1518,明人于慎行也说“汉初,朔方匈奴亦称中国为秦人”[12],清人王士禛也说“谓中国人为秦人”[13],等等。甚至有人将获得秦始皇用蓝田山玉制成并由李斯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传国玺,作为受天命而为中国正统的标志,形成了“以得玺者为正统”③的历史传统。
西汉和东汉的国号虽然都称作“汉”,但汉人一直称其所建政权为“中国”。如西汉武帝时,朝臣讨论是否对匈奴用兵,王恢曾说:“今边竟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臣故曰击之便。”韩安国则“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不同意对匈奴用兵。王恢又在反对韩安国的观点时说“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10]2400-2402,坚持对匈奴用兵。汉武帝曾派遣司马相如檄告巴蜀太守曰:“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2]3044上述史料中所说的“中国”,都指西汉王朝。东汉杜诗曾针对匈奴入侵河东之事,说匈奴“陵虐中国,边民虚耗,不能自守”[14]1095,所说“中国”则是指东汉王朝。西汉宣帝曾对黄霸说“如国家不虞,边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将率也”[10]3634,称西汉王朝为“国家”。东汉章帝时,耿秉曾针对“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等事说“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14]2953,所说“国家”则是指东汉王朝。两汉既称“国家”,又称“中国”,“中国”国家观念有了初步发展。两汉“中国”虽然主要表现为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但境内也包含受两汉王朝国家管辖的少数民族。东汉大思想家王充曾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15],原来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在汉朝建立以后,接受两汉王朝国家的管理,被纳入“中国”之中。这说明两汉王朝国家,也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
三、“中国”国家观念的多元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以汉人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自我认同为“中国”④,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也自我认同为“中国”。
十六国时期,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认同司马迁等人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2]2879的说法,以“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16]2645,“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11]2391。因此,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政权之时,拒绝其叔父刘宣恢复“呼韩邪之业”的建议,特定国号为“汉”,声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16]2649,就是以汉高祖刘邦的继承人自居,宣称要继承两汉之统,光大两汉之业,将自己建立的汉政权纳入到两汉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政权之时,也“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特定国号为“大夏”。他曾明确表示“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建立大夏政权,目的就是要“复大禹之业”[16]3202-3205,将自己所建政权排列到继承夏政权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
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也以“中国”自居。据《晋书》记载,石勒曾担心“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说出了他意欲为“中国正统”的担心。徐光趁机劝慰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明确表示石勒没有完成全国统一,也可以称“中国帝王”[16]2753。后赵政权“据赵旧都”[16]2721,是以战国时期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为继承对象⑤,并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继承西晋金德,以水德自居,将后赵政权排列到西晋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
建立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声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16]2803。《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则更加具体地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17],慕容鲜卑即是东胡的后裔,也就是高辛氏帝喾少子厌越之后。以“炎黄子孙”自居的慕容鲜卑后来建立燕国,声称“远遵周室,近准汉初”[16]2811,即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的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的燕国为继承对象。前燕皇帝慕容儁曾“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并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11]3131,明确称自己已经当上了中国皇帝。后来他又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继承后赵水德,以木德自居,也希望跻身于“中国正统”行列。
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也声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16]2867,有扈氏为大禹之后,也就是说氐人也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苻坚曾针对西边的氐、羌说“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11]3280。他听说天竺佛教徒鸠摩罗什很有才学:“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16]2500苻坚在派遣吕光率兵进攻西域时曾嘱咐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16]2914,明确称前秦为“中国”。史书又记载,前秦建立后,也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慕容燕木德为运,确立前秦王朝为火德,标榜自己建立的国家政权为“中国”正统。
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称“其先有虞氏(即帝舜)之苗裔”,他们认为“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6]2959。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也说,羌人“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16]3198。他们都认同羌人为“炎黄子孙”,认同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为“中国”。
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同样以“炎黄子孙”自居,标榜自己是“中国”正统。《魏书·序纪》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18]1。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人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祖先,他们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18]1,故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北魏孝文帝曾说“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18]2242,称北魏国家政权为“中国”。拓跋鲜卑建立以“魏”为国号的国家,是因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胡三省为之作注称“战国之时,魏为大国。中国谓之神州”[11]3471。显然是以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魏国和三国时期汉人建立的曹魏为继承对象,是北魏试图将自己所建国家排列到魏国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的一种表现。何德章认为拓跋鲜卑以“魏”为国号,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先以继承苻秦火德以土德自居,后改为承晋金德为水德,都是为了与晋争夺中华正统[19],所论甚是。
由以上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曹魏、西晋、宋、齐、梁、陈等国家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也都称自己所建国家政权为“中国”和“中国正统”,“中国”国家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四、“中国”国家观念的升华
隋唐时期,“中国”一词虽然也用来指称中原和华夏汉族,但主要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既用来指称历史上以华夏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也用来指称历史上一些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如北魏、北齐、北周等),其中以指称隋唐王朝国家为主要内容。
用“中国”一词指称隋唐的王朝国家,并非是由汉民族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包括境内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隋唐王朝国家是在直接继承北朝以鲜卑人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文帝杨坚长期生活在鲜卑人之中,并娶匈奴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所生之子隋炀帝起码有一半胡人(匈奴人和鲜卑人)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也娶匈奴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其父李渊则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为妻,自己也娶鲜卑长孙氏为妻,到了其子唐高宗李治时,汉人血统已经很少了。无怪乎有人不认同隋唐为汉人建立的国家政权,称“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20],“唐源流出于夷狄”[21],等等。他们称隋唐王朝国家为“夷狄之裔”,虽不完全正确,但也反映了被人们称为隋唐王朝国家的“中国”,并非是由汉人单一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而是包含多个民族在内的王朝国家的历史实际。
隋唐“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性质,从隋唐君臣的有关论述中也能看出来。史称唐高宗李治不喜欢天竺“自断手足,刳剔肠胃”等杂技,曾“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⑥。意思是说,唐高宗曾让西域关令把好国门,不让天竺的杂技传进来。所说“中国”,即是包括西域少数民族在内的用以指称整个唐朝的“中国”国家的概念。《新唐书》称,党项拓拔赤辞内属,唐朝“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22]6215。即认为包括积石山以东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属于唐朝“中国”。武则天时期,王方庆曾“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23]2897。称“昆仑乘舶”赴广州“与中国交市”,即是认同“地际南海”的广州属于唐朝“中国”⑦,“中国”国家自然包括生活在广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韩愈在其所作《送郑尚书序》中讲了“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等“海外杂国”之后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4]284。称“海外杂国”的货物运至与“海外杂国”接壤的“中国”等地,即是将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地区少数民族在内的唐朝说成是“中国”的意思,“中国”国家自然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地区的少数民族。
隋唐时期,在按地理中国的观念称包括境内少数民族在内的隋唐为“中国”国家的同时,又按文化中国的观念区分“中国”和“四夷”,“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和提升。唐朝韩愈将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思想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4]17。皇甫湜提出了“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25]等观点。陈黯又作《华心》说:“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辩在乎心,辩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26]程晏也作《内夷檄》称四夷“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27]他们都认为,不论地域和民族,只要其行为合乎礼义,就是“华”,就是“中国”,如果毁弃仁义礼智就是“中国之夷”,四夷的行为合乎仁义礼智,就是“四夷之华”。他们都主张按文化区分华夷,不论原来的民族如何,只要懂礼就是“华”,就是“中国”,属于“中国”国家;不懂礼就是夷,就不是“中国”,不属于“中国”国家。
可见,隋唐时期的“中国”国家观念,并非一种仅仅指称汉民族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而是一种包括隋唐境内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观念。隋唐王朝又在多民族“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按文化区分“中国”和四夷的“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的“中国”观念,多民族的“中国”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
五、“中国”国家观念的多元一体化
辽、宋、西夏、金时期是“中国”国家观念由多元化向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辽、宋、西夏、金都称自己所建国家政权为“中国”,并标榜其政权是“中国正统”。
北宋一直以“中国”自居,并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五行相生“木生火”的关系确立北宋继承后周木德为火德,通过继承后周正统进入中国正统发展序列。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虽然离开“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但仍以继承北宋“中国”的优势而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南宋后期,大臣乔行简曾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28]12489真德秀也曾在上疏中称:“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28]12958他们都称南宋国家为“中国”。南宋“中国”仍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与北宋相同的火德自居,继续标榜南宋“中国”是后周“中国”的合法继承者,是“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中的重要一员。
以契丹族为统治者建立的辽王朝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辽天祚帝时期刻写的《鲜演大师墓碑》中有“大辽中国”[29]一语,即是称大辽国家为“中国”。辽王朝用契丹文字书写自己所建国家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或“大中央辽契丹国”⑧,所使用的“大中央”一语就是“大中国”的意思,也是称辽朝为“中国”。辽王朝还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承五代时期石晋(后晋)的金德自居,按金生水的关系确定辽朝为水德,即是标榜契丹所建国家政权是接续后晋的“中国”正统王朝。
金朝也依据中原即“中国”以及“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0]等思想观念,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如海陵意欲伐宋,其嫡母徒单氏不同意,特劝谏说“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31]1506,即是用“中国”指称金朝;金世宗时,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31]2175,也是称金朝为“中国”;金章宗时期,在讨论宋人韩侂胄是否有意北伐时,完颜匡曾说“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31]2167;金朝末年,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军交战,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将士曾说“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32],都称金朝为“中国”。金朝也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但在应该通过继承唐朝、辽朝还是北宋正统的基础上进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金章宗一度下诏“更定德运为土”[31]259,试图通过继承北宋(火德)正统进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虽未能完全统一认识,但在称金朝为“中国”正统国家的问题上则不存在丝毫分歧。
西夏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即称其先祖为北魏拓跋氏,也以“炎黄子孙”自居。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早已明确自称“中国”⑨,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并效仿北魏建立国家政权,也具有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意识。史金波曾依据榆林窟第15 窟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4 年)的汉文题记“愿惠聪等七人……并四方施主……免离地狱,速转生于中国”[33]的记载,谓“这也直接表明当时西夏人认为西夏属于中国”⑩。西夏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基础上,也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王炯、彭向前认为,西夏文献中记载的西夏国号“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即是西夏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唐王朝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的意思[34],表明西夏也希望通过继承唐朝正统进入“中国”正统发展序列。
辽、宋、西夏、金在当时分别为不同的王朝国家,具有多元性质,但它们在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的问题上,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一体性,“中国”国家观念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
六、“中国”国家观念走向定型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国家观念走向定型的时期。
元朝时期,不仅境内汉族称元朝为“中国”,蒙古等少数民族也称元朝为“中国”。如蒙古人完泽和蒙古化的西域康里人不忽木,在元世祖欲发兵征伐安南时曾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35]3917成宗时期的蒙古人哈剌哈孙在有人主张出兵征服八百媳妇国时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35]3293蒙古人完泽、哈剌哈孙等人所说的“中国”,都指元王朝,可见,元人一直称元朝为“中国”。元朝还按照辽、宋、金“各与正统”[36]的思想观念,修成了中国正史《辽史》《宋史》和《金史》,表明元王朝是继承辽、宋、金正统的“中国”正统国家,将元朝纳入辽、宋、金之后的“中国”正统发展序列。
明人也称明朝为“中国”,但并非汉族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包括多民族的“中国”国家。如洪武十四年(1381 年),明太祖朱元璋曾针对安南出兵侵犯明朝思明府(治所在今广西宁明县东明江镇)永平寨等地却反诬明朝思明府侵犯安南等事时,谴责安南国王“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之罪[37]2169,称安南欺诳明朝为“欺诳中国”,即是称明朝为“中国”的思想观念。朱元璋在谴责安南侵占思明府管辖下的“丘温以北之地”时,对安南国王陈日焜说,其地自汉朝至宋朝,一直“为中国所有”,“元世祖时……其属思明亦明矣”[37]3621,令安南将“丘温以北之地”退还明朝思明府。明成祖朱棣在谴责安南侵夺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时也说,“此乃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37]583。他们都称明朝为“中国”,包括与安南接壤的思明府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朱元璋在高丽提出“文、高、和、定等州”领土要求时,曾回答说“数州之地……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指明朝控制的辽东地区)”[37]2867,即认为“文、高、和、定”等东北边疆地区,原来为元朝所统领,现在就应该归属于明朝。这表明明人所说的明朝也是一个包括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国家。明太祖朱元璋在起兵反元之时,曾提出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37]402的口号,不认同元朝为“中国”国家,但当他灭亡元朝以后,很快就转到认同元朝为“中国”以及明承元统的立场上来,他曾说“天更元运,以付于朕”[37]2946,明确表达了明朝是继承元朝正统的“中国正统”国家的思想观念。朱元璋又依据为前朝修史就是本朝对前朝法统的认同,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中国”传统观念,下诏纂修《元史》;又列元世祖和一些大臣于历代帝王庙之中,与“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的帝王、大臣一并祭祀和陪祀。这明确表达了明朝“中国”是继承元朝“中国”以及上承各个王朝的“中国正统”国家的思想观念。
与明朝并立的北元政权,也声称自己是大元“中国”的后裔,是大元“中国”的继承者。他们一直以“大元”为自己所建政权的国号,并遵循自秦朝以来即形成的得传国玺者为“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十分珍视他们从元顺帝手中获得的传国玺,甚至以他们手中握有元朝传国玺而炫耀他们所建政权比明朝更具正统性。明朝和北元都声称自己是大元“中国”的继承者,表明“明朝与北元正是在元朝遗留的版图上形成的两个政权”,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一次南北朝对峙时期”[38]。因此,明朝时期的“中国”国家观念既包括明朝的国家观念,也包括北元的国家观念。明朝和北元虽然分别为不同的国家政权,但在称“中国”的问题上则是一致的。
清朝更是称自己建立的政权为“中国”,并对“汉”和“中国”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分。史书记载,清朝大臣在与缅甸往来的文书中曾写有劝缅甸“归汉”的词语,乾隆皇帝看到后,十分不满,训斥这些大臣说:“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39]643他将“中国”和“汉”作了明确区分,认为“汉”仅仅是一个指称“汉族”或“汉文化”的单一民族或单一民族文化的概念,而“中国”“大清”或“天朝”则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概念,因此,不能用“汉”一个民族代表大清王朝国家或“中国”国家。清王朝在强调自己是“中国”国家的同时,也标榜自己是继承明朝和北元以及上承辽、宋、西夏、金、元等王朝的“中国”正统王朝,并按照这种“继承性中国”的思想观念,不允许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分离出去,也不强行将原来不属于自己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纳入进来⑪,并按照这种“继承性中国”的原则,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平定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罗卜藏丹津、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等变乱,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管理,“中国”国家观念发展成为一个包括“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40]以及境内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国家观念,“中国”国家观念走向定型。
综上所述,文字记载的具有国家内涵的“中国”一词虽然出现在西周初年,但据后人记述的相关文献记载分析,“中国”国家观念早在夏王朝建立时就已出现。春秋时期,人们在夏商周出现的以中原地区所建政权为“中国”的基础上,继续称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周、卫、齐、鲁、晋、宋等国家为“中国”,又因为这些国家主要为华夏族所建立,开始出现“华夏中国”观念,不认同在中原以外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秦、楚、吴、越等国家为“中国”。战国时期,人们称楚国与韩、赵、魏、燕、齐关东六国为“中国”,开始认同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楚国为“中国”,并出现了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秦统一六国,明确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将秦王朝排列到黄帝、夏、商、周之后的历史发展序列之中,“中国”国家观念正式确立。两汉既称“国家”,又称“中国”,用以指称两汉境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观念有了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自我认同为“中国”,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国家也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国家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鲜卑等少数民族具有渊源关系的隋唐“中国”,在强调隋唐“中国”境内包括少数民族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按文化区分“中国”和四夷的“礼别华夷”和“华夷互化”的“中国”观念,多民族的“中国”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辽、宋、西夏、金分别是以契丹、汉、党项、女真为统治者建立的不同政权,具有多元性质,但他们又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和“中国正统”,在“中国”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体性特征,“中国”国家观念呈现出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元朝时期,不仅境内汉族称元朝为“中国”,蒙古等少数民族也称元朝为“中国”,将元朝纳入辽、宋、西夏、金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虽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不认同元朝为“中国”国家,但灭亡元朝以后就转到“承元建国”的立场上来,认为明朝是继承元朝的“中国”国家,将明朝排列到元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之中。与明朝并立的北元政权,也自称是大元“中国”的继承者,甚至以自己手握元朝传国玺而炫耀自己的政权比明朝更具正统性。清朝也自称为“中国”,并对“中国”和“汉”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分,在继承明朝和北元等历史“中国”的基础上,将清朝“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包括“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以及境内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国家,“中国”国家观念走向定型。
注释
①有关国家概念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国家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古代没有国家。本文认为古代也有国家。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 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本文认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中国古代各民族所建立的以国号为代表的王朝和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有国王,有人民,有领土,具备国家形态,虽与近代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但与近代欧美诸国所倡导的以主权、人民和领土三要素判断“国家”的主张也相去不远,仍然可以称之为古代国家或王朝国家、王权国家、帝制国家等。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为王朝国家类型。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08 页。有人认为这段话是周公对康叔说的。也有人将“肆”字断至下句,即将此段话释为“老天既然把中国的人民和疆土付给了我们的先王,所以王要照着美德去做,使迷惑的人们和悦,而领导他们以完成先王所接受的使命”,参见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0 页。本文据《十三经注疏》本及孔传释文,将“肆”字断至上句。③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明万历三十年刻本。④三国时期的吴国、蜀国以及两晋时期的东晋,因为没有在中原地区建国,一度没有自称“中国”,但后人一致认为它们属于中国。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8 胡三省在为“赵人”做注时称“赵人,谓中国人也”,虽非为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做注,但所论“赵人”为“中国人”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⑥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29《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073 页;《新唐书》卷22《礼乐志》记载相同,见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79 页。⑦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安边御寇·南蕃呼中国为唐》称“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参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09 页。⑧参见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 年第2 期;《从契丹文字的解读探讨辽代中晚期的国号》,《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6 年第2 期。⑨北魏自称“中国”的史料很多,如北魏太和十六年(492 年),宕昌王弥机朝于北魏,“殊无风礼”,朝罢,北魏孝文帝对大臣们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魏收:《魏书》卷101《宕昌羌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242 页),等等,都称北魏国家为“中国”。⑩参见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 年第4期。⑪郭成康通过对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军追击阿睦尔撒纳叛军至哈萨克,哈萨克愿意臣服,但乾隆皇帝仅仅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之例,将哈萨克作为“藩属国”对待,并未将哈萨克如同漠西蒙古和西藏一样,纳入清朝版图等史事的讨论,指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