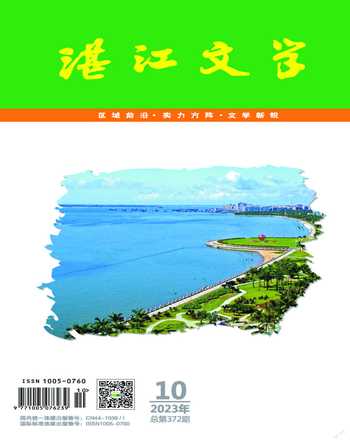好茶需要分享(组诗)

煤矿洞前
普通一座山因蕴藏火焰
从而有了底气
洞口只让你看点灯火
轻易不亮真金
山上怪石嶙峋,草木稀疏
即使是山
能够活下来也算奇迹
更别提幽暗中还要坚守
燃烧的部分
站在矿洞前我犹豫了很久
也许看到好风景
也有可能从此不见光阴
只见走出来的人
煤炭一样乌黑
眼光却像闪电,比外面阳光强烈
新房开工
面对东方,我拿起了榔头
对即将装修的新房
找出最坚硬部分,重锤敲击
这是师傅要求主人所做功课
我活得并不坚强
像敲钟一样敲响新房
只祈祷能遮风挡雨
装修者将泥土翻来覆去
需要心理安慰
我不能埋雷,不能用力过猛
毕竟高楼还没住人
轻重间得平衡呼吸
必须在墙上划出一道伤痕
让火星迸发,让我今后日子
哪怕灯火辉煌
也得记住这里曾是一片空白
同时也是崭新开始
好 茶
对茶山的要求不算高
可以海拔千米以下
不需要艳阳永远高照
偶尔云雾缭绕
能让心事静静发芽就好
茶山最好有一座老寺庙
好茶听着经声长大
哪怕一言不发,打坐于枝上
也会长成鸟舌一样
许多茶树挨过千刀万剐
枝叶经历高温高压
即使这样还算不上好茶
好茶必需分享
需要众人把茶话桑麻
如果某天只有我俩雪中煮茶
那将是另一种味道
路过此山
飞机上撒下的树种
落在坡顶因阳光充足
会长得茂盛,凭借位置
还能视野开阔
运气差的滚向坡底
就算长势良好,最终还是要比山顶的树
矮一长截
我远远望去,其实就是一座山
树们靠山成林
置身其中后
发现有几棵树密集某个区域
明显都要矮小一些
当一阵风吹来,却响动最大
我只是看风景的人
没兴趣听争吵,也不想比较
天已黄昏,我再不下山
也许会迷路于夜色
风 电
站在高山平原,或者江湖
风力发电机都可以
最先晒到太阳
呼吸到最新鲜空气
高大并吸引眼球
我承认偶尔会心生羡慕
可随便给点风
就要舞蹈的德行
还是令我迟疑,从而缺乏
坚决跟风的勇气
况且先得有风,后才是自己
并非所有的风都是东风
也有风沙、风暴和阴风……
最大风险还在于
高举的手臂不能放下
一旦不动,就要被修理
高 度
珠峰南坡从山脚到山顶
植物群依次为:
常绿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针叶林……
也就是说,一棵树想活在高处
就得减少枝繁叶茂
留下骨头和针刺
一些往高处爬的人
也在发生变化
外表却与树木相反
骨质开始疏松,脂肪愈来愈厚
最后变成白胖子
我在山脚徘徊多年
日渐消瘦,见过太多下山之人后
攀高愿望已经消失
过 程
时间的通道上
我们站在各自家门
小心说着现在才敢大声说的话
有时你脸红一下
配合我假装的老成
距离限定在两道门
不靠近也舍不得远离
偶尔望望窗外蝴蝶花
便像嗅尽了人间香气
即便不说话
就可以站成地老天荒
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
只当风吹了一下
那时我们还没门框高
却自认为知晓了天下
不像现在真正老了
只剩回憶,几十年只需几秒完成
在高原听歌
拉萨的出租车上
藏歌也在奔跑
之前听过这些旋律
身临其境,气场却明显变化
仿佛只有海拔3000米以上
才配得上这种悠扬
晚上还去听了
藏族歌手的演唱
歌声中草原以及牛羊
即便没有背景墙
我也知道就在身旁
而冰雪上面天籁之音
雄鹰也能听到
唱歌的人都该去高原吊嗓
特别是美声,经过雪山荡漾
腔调会不一样
公 海
站在南海一块甲板上
突然听到广播船已至公海
我慌忙抬起头来
看到万物可以共存的地方
却什么都不存在
只有船舷划破的海面
在我们离开后重新海天一线
除了苍茫与好奇
剩下的公海时间
像没有皱褶的蓝纸片
我紧紧攥在手心
以至于后来对公海的认识
我只停留在一张船票
各人找到既定的地方上岸
沙滩上的帆船
在沙滩上航行久了
带着一身沙尘
愈陷愈深,哪怕看到浪潮
听到了大海呼唤
努力想行,却无法甩开自己
有着帆船完美造型
铁锚链条也绷得很直
风帆弯成了弓形
却一箭未发
更无水手影子
只有游客不会看成木头
欣喜认作大海征服者
与之握手合影,
摆出乘风破浪姿势
命名帆船,以船长自诩
只有在夢中,夜色下
或者暴风骤雨中
帆船才真正融入大海
兴奋喊叫,却无人喝彩
也没人想过,船只想活在水中
裁缝铺
我家对面有一个裁缝铺
一群人天天努力地
想让棉布不只用于御寒遮羞
千万朵棉花汇聚这里
带着阳光和雨露
被裁剪、缝合、熨烫……
像春天的花园
然后就有一个人形,重新站起
多年后我写诗
一个人将白纸交给笔墨
也想踩动针线
缝补阳光,连接笑容
可许多时候都只剩一张废纸
也许要再过许多年我才会明白
裁缝铺留下的不仅是布衣
也有他们的剪刀尺子
过高桥
即使世界最高桥
如果我不仰视,也仅仅是道
从桥上经过
车辆呼啸,不见人影
高速世界容不下停顿
也不可能有回头机会
只有建桥人
才掂量得出钢铁重量
也只有站得比桥高的人
才一览了桥与众山小
我仅是路过,只能带走一阵风和一座桥响亮的名字
作者简介
涂拥,中国作协会员。有组诗发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作家》《诗歌月刊》等刊,诗作入选多种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