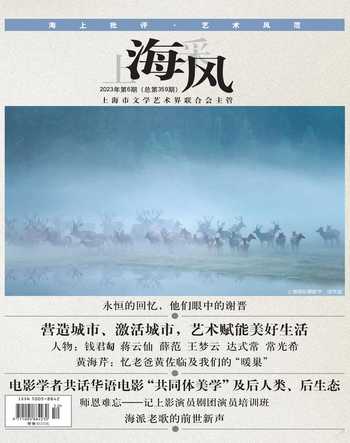忆老爸黄佐临及我们的“暖巢”




秋风送爽,金桂飘香。空气都是清清甜甜的。
十月,老爸(黄佐临)的生日到了。
今年,他应该117岁。
妈妈出生在1912的新年新春,她应该111岁了。
两个纯粹的人,相识、相知、相爱、结婚,生下了我们五个。1941年,爸爸与他的岳父金峻轩,合资买下卫乐园一号,就是那栋卫乐园后弄堂走到最后,偏僻矗立的二层小洋楼——我们的家。
人人都羡慕我,出生在名门世家。
有同学说,你多好啊,出身好,又有钱,又荣耀;学校组织我们去机场欢迎外宾,爸爸妈妈作为贵宾,并肩缓缓走过我们的列队,这个时候,同学们的羡慕,想必达到极致。名与利,光鲜的外表,过于炫目,遮挡了一些人的目光。我想,我幸运地出生在这个家,最最引以为傲的,绝对是它的内在,它的诚实,它的质朴,它的率真。
若说爸爸妈妈是名人,不如说他们是“忙”人,忙碌至极。他们以全身心投入热爱的戏剧、电影艺术,竭尽全力。他们没有参加过一次我们的家长会,我们除了自己的生日,不知道所有的节假日,例如中秋、端午乃至元宵,因为,他们每逢佳节倍忙碌。
可是,他们又非常爱我们,非常爱我们这个家。
他们会挤出时间,带我们全家出游。有一次,盼了好久的中山公园终于成行,才走到弄堂口,爸爸的朋友鲁韧先生来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那个丧气就不用说了。最后,五个小人唱起了《达坂城的姑娘》泄愤,因为,鲁韧先生曾经在跳这个新疆舞的时候,裤子松了。一次去漕河泾的冠生园,调皮的弟弟爬在大金鱼缸上捞金鱼,竟然掉了下去。自此,弟弟黄学良有了掉入金鱼缸的黑历史。暑假,我们举家去了依山傍水的乍浦,学会了在大海里游泳,一岁多的弟弟学会了在沙滩上走路。回上海,弟弟在打蜡地板奔跑,一步一滑,跌跌撞撞,撞碎了阳台门的玻璃。1947年暑假,我们乘船去台湾探望三姑姑,台湾刚好放映黄蜀芹参演的电影《不了情》,热情的观众把黄蜀芹围了起来要求签名,最后,9岁的黄蜀芹被吓哭了……
炎炎夏日,累了一天的妈妈下班回家,跌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由衷地叹道:“走到哪儿,还是家里好啊!”妈妈在日夜两场的演出间隙,骑自行车从卡尔登戏院赶回来,给孩儿们喂奶,每天每天,匆匆忙忙,终于得了严重胃病,但是她坚持母乳喂养,让我们五个得以健康成长。
等我们长大一些,爸爸带我们练习骑自行车,第一次上街去,他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出了弄堂,越加紧张。才到泰安路小菜场,姐姐就撞翻人家一个竹篓子,绿豆芽撒了一地。爸爸赶紧下车,拙嘴笨舌赔礼,诚心诚意赔偿。我们在弄堂里闯了祸,爸爸就带我们上门道歉,回家以后,不打不骂,只是说:人家讲,你们父母都是文化人,孩子们怎么那么没有教养(我想,他是让我们自行惭愧)。妹妹崴了脚,爸爸把她背上背下。我过生日,爸爸会送我一个景德镇的猫咪瓷壶,因为我的小名叫毛毛,等等。所以,我们的名人爸妈,也面对各种家庭琐事,和别人家的爸妈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的爸妈,也有他们自己的教育方式。对待我们最大的独特之处,就是很尊重我们的意愿。弟弟拉小提琴很有天赋,可是他自己没有兴趣,爸妈就同意他放弃。弟弟喜欢上了京剧老生,爸妈就支持他每周去天蟾舞台看京剧演出。老五黄小芹,耳朵特别灵,就支持她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钢琴。老三黄汝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被内招进刚成立的上海计量局,一个保密单位,这说明老三不能读大学了。去还是不去?老三想去,爸妈就同意她边工作边读夜大学。事后,爸爸还老爱逗她:“老三,今天都干些什么了?”老三照例一瞪眼说:“保密!”大家都笑了。挺严峻的问题,就这么轻松解决。老大中学毕业放弃高考,班主任老师追到家里,请家长说服她不要放弃,太过可惜。结果,爸妈同意了老大的意愿。老大为此下乡两年,等电影学院招生,才再去追考自己喜欢的电影导演专业。我呢,偶尔说起,喜欢心理学,第二天,桌上就堆了一叠巴甫洛夫学说;说起一个学校发生的小故事,爸爸就会有意无意地说,可以试试写个小电影,等我真的写好了,爸爸竟然拿去请电影厂的叔叔看,请人家提意见,像真的一样。
记得我初中毕业,爸爸去北京拍《鲁迅传》,我就跟去了北京。他忙着拍戏,我一个人玩,在故宫后门一条小街,迷上了外壳珐琅质的、五彩缤纷还会打鸣的怀表。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把你写的小诗拿去投稿,我就给你买怀表。”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有感而发,大约的意思是:让我们把脚步放得轻轻,不要把辛劳的领袖惊醒……听了爸爸开出的条件,我想了许久,终是没有胆子把稿件投出去,当然,怀表也没有得到。
长大以后,姐姐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回上海电影制片厂。老三本来就在上海计量局。弟弟中学毕业,正逢上山下乡,因为他劳动卖力,老师傅喜欢,留在上钢三厂当电工。老五音乐附小毕业,正是特殊时期,无法考入音乐附中,分去上海图书馆书库工作。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福州军区。爸妈有些不舍,专门去问了南京军区的朋友,回来以后,郑重地对我说:“部队对女同志而言,比较局限,有的地方连女厕所都没有。”然而,我年少气盛,自信满满,爸妈只好为我准备行装,送我从军。
这一走,就是18年。
家里五个孩子,就我一个离家远行,那么,所受到的呵护,也必定是最多。朋友们好奇,家里给我带什么行李?爸爸趴在饭桌上,把一条绿缎子面的鸭绒被一剪为二,一半给姐姐,一半让我带走。我不肯带,绿缎面,太奇怪了。爸爸说,带吧,行军背着,可以轻一点。然后,他用白被套套上。我勉强说:“好吧。”下部队,我的被子鼓鼓囊囊,在一堆四四方方的被子里,尤其突出。老同志说,来,你个新兵蛋子,我教给你怎么打背包!他打了半天,不是东突就是西翘,愣了好一会,说:“我的个妈呀,你这是什么被子?鸭绒被?”战友们都向我看来,像看外星人。当时能拥有鸭绒被,有如天方夜谭,我羞得恨不得钻地底下去。
18年中,家里给我寄些什么呢?不是吃的,不是穿的,也不是什么化妆品。1960年代中,他们给我寄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是稀罕物,大概连部队首长都没有吧。害怕過于特殊化,我只敢半夜偷偷听。1970年代中,我收到爸爸寄来的带轮子的旅行包,让我下生活的时候,可以省力些。那时候旅行包有轮子,也是很稀罕的。我拉来拉去的风光了好一阵。最叫我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件爸爸自行设计的“防蚤服”。这是一件白纺绸的套头睡袍,袖口和裤腿,都是全封闭的,唯有脸部是一方深墨绿的蚊帐布,用以透气。我试着穿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因为我曾说过,福建乡下跳蚤多,把我咬得体无完肤。可是这件奇装异服,虽是防了跳蚤,夜半三更,穿了会吓死人的,我把它又寄了回去。我安慰老爸说,这个创意,可以得诺贝尔奖,可我们是前线,民兵看见会以为是对过偷渡过来的特务水鬼,要把我抓起来的。这样,他老人家才算作罢。
在离家的18年中,爸妈没有以任何借口让我回家看看。连外公过世,都没有及时告知。可是,仅有的一次,说要陪妈妈看病,把我叫了回去,实质上,是携妈妈去北京观摩爸爸导演的《伽利略》。我看过《伽利略》译本,晦涩难懂。而爸爸导演的舞台剧,引用了古希腊的幕前说唱,生动顺畅,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爸爸倾注的心血,难以估量。我知道,爸爸是要和我们共同分享演出的成功和喜悦。我和妈妈连看三场,其中,伽利略恳求神父们看一看望远镜,看一看天体的真相,他求一次,神父们往后退一步,求一次,神父们再退一步,再求,再退……我看得热泪盈眶。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哇!当时朋友们评论,让你们坐飞机来回,就为了看一个戏!
哇!是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那些“哇”,那些“匪夷所思”,那些潜台词,那些爸妈胸中默默的涌动,我懂。
顺境中,爸爸妈妈忙着、累着、努力着、奋斗着,对我们呢,牵挂着、关心着、注意着。殊不知,逆境中的爱,才是最直击心窝的。
特殊时期,我们抱团取暖。
我回上海探亲。每天,和家人一起,喝三分钱的冬瓜汤。当时,爸爸每个月工资15元。有一天,爸爸下班,他找到我,塞给我一个咸鸭蛋,悄声说,革命群众偷偷给他的。我傻站着,不知所措。这个鸭蛋太沉重,我怎么能够接受?又怎么能够拒绝?
又一次,路过上海。爸爸忽然问:你的手表呢?那还是考上初中,他给的奖励。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直到工作,近20年我一直戴着这块半钢的小女表没有换过。我实话实说,表太老了,九江(我们已经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1团,在九江庐山脚下)修不好,我托人带到南昌去修了。说完,我立即后悔。果然,离沪前,爸爸非要带我去静安寺旧货店买手表。那时候,手表要券,所以,爸爸只好买二手货。他一定要买一块东风表(天津出的,他的第二故乡)。当时,他每月只有15元,经年累月,他哆哆嗦嗦地积攒了100元。革命群众问:“你哪儿来的100元?攒钱做什么!”他说:“我担心我的孩子们。”
于是,这块普通的东风二手表,绝不普通。对我来说,压在心头,重过千斤……
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决心替我带我的二女儿郭茅。在我们小时候,妈妈就宣布,带你们五个就够了,将来,我决不帮你们带你们的孩子。可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硬是留下了郭茅,给了她最真挚的爱。茅和她外公,成了忘年交,一老一小,有说不完的话。姐妹们开玩笑,说她排行老六。于是,郭茅得了個“阿六头”的雅号。
我给家里写信,收信人是“黄全家”,爸爸妈妈给我写信,署名是“马巴”,一个自创的、所有字典里没有的字,以示他们不连累子女,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爸爸妈妈的爱,有如黑夜的繁星,数不胜数,又如冬日的暖阳,环绕在我们身边,默默地、无声地、又无时不在。
爸爸去世后,一位哲人来到我们家,说:你们爸爸走得急,来不及交代,家里有三件宝,要珍惜哦。于是,我们五个面面相觑,哪三件宝啊?一件,大概是萧伯纳先生送的相册,萧伯纳先生的亲笔题词,以及爸爸的藏书,我们捐给了上海图书馆;第二件,大概是爸爸的房子。我们遵循他的意愿,没有作为纪念馆;第三件,是什么呢?猜来猜去,不知所以。
我自己想,第三件,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这个充满爱的家,无价之宝。1950年代初,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高高兴兴带回来一张白石老人的画,这不是一幅普通的画,是白石老人根据爸爸的意愿,构思而成。画面由一只雄壮的公鸡(象征爸爸)、一只温柔的母鸡(象征妈妈)组成,左上方是三只小鸡(应该是黄蜀芹、黄海芹、黄汝芹三个姐妹),左前方是一只啄螳螂的小鸡(是弟弟黄学良,男孩子,1952年左右,正是“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时候)。最后,拖在后面在奔跑的小鸡,一只小脚还跷着(那是小老五黄小芹,我们最小的妹妹)。
无疑,这是我们家的缩影。
爸爸把画挂在大厅里,凡有国内外贵宾来访,他总要兴致勃勃地讲解一遍,介绍这一幅画,介绍白石老人,介绍他喜爱的家。这是怎样一幅和睦的景象啊,主人讲得喜气洋洋,客人听得津津有味,每个人的心里,都呈现一个美好的家。
可惜,动乱中,这幅画不翼而飞,至今无有音讯。
我们失去了白石老人的画,很难过,很惋惜。但是,我们心爱的家还在,我们之间的爱还在。爸爸妈妈做人的榜样还在。温暖的情谊,有如清澈的小溪,源源不断地流淌,流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还是在九江的时候,我想要添加一件棉袄。星期天,“黄全家”们骑着自行车全体出动,帮我在大街小巷寻找。当我重新回到写作岗位,姐姐黄蜀芹想方设法搞到内参电影票,给我补课。那时候很严格,要凭工作证和电影票才能进。于是,姐姐看第二场,我看第三场,我们在新光电影院对过的上海食品商店碰头,姐姐把工作证借我,我冒充她进去观摩,竟然一次也没有“穿帮”。我们的孩儿们,聚在一起,拍起了小电影,于是,有了《泰安路的星期天》:白发的外公,开着老人车,和他的儿孙们嬉戏;远赴海外的堂弟们,至今心心念念的,就是星期天的家庭聚会。我们没有满汉全席,我们吃面条,或是馄饨,再不就是一大锅沙拉,大家喜欢的不就是聚在一起,不戴面具,赤诚相待吗?家,家风,让每个人挺起胸膛,让每个人骄傲。
我们失去了白石老人的画,也可以说,没有失去。我们的家还在,我们的爱还在,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盗画的人得到了画,但也可以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画的灵魂是无法盗走的。
每每忆起往事,更加怀念温暖的家。
我爱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