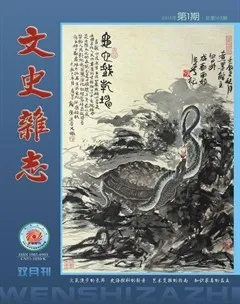今文经、古文经的前世今生
付雨欣
摘 要:一直以来,学界似乎沿袭着一个不甚准确的观点,即认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存有泾渭分明的壁垒,并用这种理论试图分析历史上各位经师及其学说呈现出如今所见样貌的背后原因。实际上这完全是在用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论作前提,那么可想而知以往的不少看法,甚至认为是定论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皆有加以重新审视的必要。
关键词:今文经;古文经;嬗变;源流
今文经与古文经,实际上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自此二者产生之时便是如此。今文,本来没有这个概念,只是在与之不同的较古文字面世之后,为示区分,方才称原来流传于世的用隶书写成的经书文本称为“今文经”,而将后出的这批用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征诸史籍,对此有详实的记载。
《汉书·楚元王传》: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1]
《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2]
《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3]
鲁恭(共)王坏孔子宅,推动了这一波古文经的涌现,其中包括《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文献。除此之外,河间献王亦得到一部分古文字之书。《汉书·河间献王传》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4]
这一批用古文字书写而成的书籍,则包括《周官》《尚书》《礼古经》《礼记》《孟子》《老子》之属。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个“古文字”的界定尚未形成较一致的看法,本文暂采用将之视为秦统一之前齐鲁等地所用古文文字的手写体这种观点。其实,这批古文书籍在面世没多久就不再是以“古文”的形态流传了,“古文”只是其最初面貌。由于一般人并不能识得古文字,要想让这批古文经能够被一般人学习,以促进其传播,必有一批能识古文字的经师致力于将之“今文化”。“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便是其例。这仅仅是文本面貌上“古文”“今文”的合流,其后共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形式流传;此外,尚有经义上的今古文分别。一般认为,古文经学派解经风格较为平实,注重从文字、音韵、训诂等角度进行名物制度的阐释,而不过多进行思想义理的发挥;而今文经学派则注重从经书中寻找圣人的“微言大义”,从经书的字句中寻找能够与现实政治相联系的内容,从联系现实的角度为之阐释,并且进一步发挥,由经书而导向指点时政之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文经学派的这种特点,究竟是其文本本身所致,即新面世的这些古文字经书已是前人作过注解的,这些典籍中本含有先秦经师所作的阐发;抑或是汉代经师的阐释所致,即这批经书本身不带有前人的注解,而是由汉代的经师按照名物训诂的原则为之注解?换言之,这种重名物训诂而不重思想阐发的特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特点是由汉代经师首创其例,还是先秦早已有人在这些“古文”之经书上留下了他们的平实而疏于义理阐发的注解而汉人仅仅是继承并加以发展?从这种溯源的角度出发,即从逆流而上的思路方向考虑,或许这个疑问在目前尚不能得到解决;那么顺着历史演进的方向来看或许有所裨益。
先秦时期,名物训诂的这种学风,如所周知,子夏是其代表人物。不少典籍皆记载了子夏对于章句训诂、名物考索的追求。例如《后汉书·徐防列传》所载:“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5]
尽管孔子认为这是汲汲于名物训诂不过是“小人儒”的行径,并劝子夏“妆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然而在众多孔门后学之中,子夏传经之功又是最为突出的。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史记索引》: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而此史并不论,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6]
从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子夏对于后世学术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马宗霍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说“是故孔门高弟之学,其流被于后者,要以子夏、曾子为最可溯”,正是此理。
然而,子夏的后学所传并不完全是传统所认为的古文经学。南宋学者洪迈之《容斋随笔》载: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它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7]
子夏所传之经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诗》与《公羊春秋》。此二者中很明显一个属于古文经学,而另一个则属于今文经学。这种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为何从一个老师传承下来的学术谱系至汉代会有如此巨大的分歧?其实我们应当注意到,今文经与古文经在其学术思想或者说学术旨趣方面,并未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从学理上说,要想阐释经书的“大义”并借以联系现实政治,基本的文字章句训诂是无法避免的;若是经师连句子的意思都讲不明白,又何谈先王、圣人的垂世大义?反过来亦是同样的道理:若是古文经学的经师们无法在文词训释的基础上贯通经书作者(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王圣人)的基本思想,那么经书也仅仅是支离破碎的一个又一个语词罢了。这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经书的本来功用而走向故步自封的一隅,因此适当的经义疏通与思想阐发是不可缺少的。以是观之,从名物训诂与义理阐发为切入点以区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是欠妥的做法。实际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论是在文本层面还是在解经层面皆是如此。举例而言,春秋三传之中,《穀梁传》实则是介于《公羊传》与《左氏传》之间的,其义理阐发的倾向不如《公羊传》,而字词名物的训释方面又不如《左氏传》。尽管传统的观点是将《穀梁传》归诸今文经,但是显然它并非极纯粹的今文经。不论是先秦时期,抑或是汉代,经师们解经皆需同时注重经义思想的阐发与文词的训释。学界传统上所认为的汉代的今文经、古文经学派或许呈现出在思想、文句两方面的分野;但這种倾向并非是绝对的,而仅仅是一种侧重或者说偏向。从子夏本人的学术倾向来看,他是更重视做一个“小人儒”的,即更注重从“小学”角度对经书进行阐释。然而需要注意一点:子夏尽管更重视小学,但他并不会也不能完全忽视思想义理的挖掘与发挥;否则就只是流于表面功夫,甚至可能致使连“小人儒”都做不好。因为“小学”与“义理”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此二者尽管有区别,但谁也离不开谁。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导源于子夏的汉代经学,为何会在存有“小学”与“义理”之流派分殊的同时,很多时候难以将其区分开来,原因就在这里:“小学”与“义理”本身就是紧密联系的治学手段,不论古文经学家还是今文经学家,离开其中一者,则无法治学。具体到某一位经师身上更是如此——他可能在自身整体的治学旨趣上呈现出一种倾向于“小学”或“义理”的风格,但落实到其具体学习或传授经书的过程中,则不可能离开“小学”或“义理”之中任何一种治经工具。
近来亦有学者注意到目前学界通行的某些对于今古文加以区分的标准不甚符合历史实际。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研究者所感知到的这种存在于今古文之间泾渭分明的壁垒是由后世之人回顾两汉之际的学术走向时,一层一层地叠加上去的;就如同“层累的古史说”,它并不贴合汉代的历史原貌——尤其是具体到经书中某处文句的解释上,并不一定有着如此严格的学派划分。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云:“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8]而彼时因不守师法而黜用的例子并不鲜见,例如《汉书·孟喜传》载:“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9]可见汉代是极其重视师法的。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尽管笼统地说“汉代重师法”并无甚错处,然而这个“重师法”的程度却并非在整个汉代始终保持一致。在西汉初期古文经尚未得到广泛传布之前,虽然经书文本有今文、古文的字体差异,但学说上却并无所谓今文、古文之分别;然而在今文经内部各家学说之间可能已有师法的区别,但尚未严格区分。自从汉武帝时期公孙弘将经学与功名利禄相联系以后,这个“师法”才越发受到重视。如所周知,到了东汉末期,尤其是郑玄这样兼通今古文的大家为诸经作注以后,今古文实则已然没有区分的必要了。而从郑玄所处的时期往上逆推,即可知晓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今古文之间的壁垒已然不甚突出,遑论“师法”的隔膜,其自当已消弭殆尽耳。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何汉末能够出现郑玄这样一个学识广博的学者;否则在一片“师法”森严的环境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打破今古文壁垒的郑玄,岂非因太过突兀而成为时代之“异端”?唯有将郑玄作为突破口,以此进一步地深入考察那个时代的学术动态与整体走向,才能更贴近历史的真相。实际上,今古文之间的壁垒在东汉章帝时期已有松动的迹象,尤其是“师法”的禁锢在这一时期彻底瓦解。《后汉书》记载道: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10]
汉章帝继位之初即“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令古文经学者贾逵进讲,使其比较《公羊春秋》《左氏春秋》异同;而贾逵上《左氏》优于《公羊》三十事,受到赏赐。此后没过几年,古文经即得立学官,《后汉书》曰: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11]
由是,章帝时期推进的一系列举措打破了东汉前期官方经学墨守师法的传统,自此以后,兼习不同经学、兼通不同流派成为学术之风尚。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说,今古文经之间的壁垒或许存在过一段时间,但并非贯穿了整个汉代;“师法”之守亦复如是,只是在汉代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比较突出而已。
实际上,不仅是今人对于汉代的学术一直以来沿袭着这种有失偏颇的观点,古人亦是如此。这种存有一定偏差的感知实则是从那些开始思考与反观汉代学术走向的学者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的,因此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从而缺少一种反思的精神。那么在这种僵硬且脱离实际的观点指引下,学者在挖掘汉代经师解经的内在机理时往往陷入强而为之的境地,甚至于对汉以后的学术亦无法作出准确评断。举例而言,清儒朱彬《礼记训纂·礼运》载:
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说文》:“麒,麒麟,仁兽也。”段氏玉裁曰:“公羊传曰:‘麟者,仁兽也。’《毛诗传》曰:‘麟信而应礼。’《左传》服虔注:‘麟,中央土兽。土为信。’《五经异义》许慎谨按:‘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是《异义》谓麟为信兽,从左、毛说,而此云‘仁兽’,何也?《异义》早成,《解字》晚定,从《公羊》说。”[12]
此处朱彬引《说文》中“麒,麒麟,仁兽也”的说法以解释“凤皇麒麟皆在郊棷”之“麒”,下又引段玉裁语“是《异义》谓麟为信兽,从左、毛说,而此云‘仁兽’,何也?《异义》早成,《解字》晚定,从《公羊》说”。根据段玉裁的说法,对于麒麟究竟是“仁兽”还是“信兽”这个问题,许慎在早年写定的《五经异义》中采用《公羊传》的“信兽”观点,而在晚年写成的《说文解字》中采用《毛诗》《左传》“仁兽”的观点。这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许慎早年接受古文经学的观点而晚年改从今文经学。然此与学界一般的看法相违悖。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东汉是一个由今文经占主导地位转向古文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即时代的大趋势是古文经逐渐盛行起來。那么许慎又怎会从势头大好的古文学派转向逐渐式微的今文学派?这岂非“弃明投暗”之举?此尚需结合时代背景见微知著地深入挖掘彼时的学术特点,其唯一的解释是当时已然不甚注重今古文之间的壁垒。经学在当时是否仍有今古文的区分?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原先阻隔于今文、古文经学之间的壁垒,换言之,即两派之间水火不容的争斗态势,已然消弭,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还需进一步考虑,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学随术变”似乎是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答案——汉章帝喜好古文。东汉立国之初,光武帝自然需要表明自己继承西汉的正统地位,那么他就不得不做出支持今文经学的姿态;因为西汉时期只有今文经学得立学官,而古文经学则始终在野。到了章帝时期,东汉的时局已经稳固下来,章帝也就不需要为了巩固统治而特意在学术上支持哪一派,因而他从己所好,扶持传播古文经学。在官方引导下,学习古文经学自然形成风尚;但同时今文经学仍是自西汉以来被官方承认的学术,是故不便于此时废除。正如后来宋代的“祖宗之法”,今文经学是有汉一代的“祖宗之学”,仍应推行。自此,今古文经学成为官方正式推行的、并行不悖的两股学术思潮。从这个视角出发,许多看似抵牾之处也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为何许慎早期采用古文经学的说法而晚年改从今文经学之观点?因为许慎所处时期亦是扶持古文经学的举措推行得较为深入的阶段。彼时今文、古文之间已经没有森严的壁垒,是故他能够依据实际情况,对于具体文句的解说或采今文经之说,或取古文经之说。对于许慎在《异义》与《说文》中说法的变动,不可直截视为其早年、晚年两个时期所从学派发生变化,而应理解成他针对具体文句的解说择善而从,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
除了以上所论,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展现汉代今古文经并不完全对立的学术特点。许慎撰有《五经异义》一书,“盖亦因时而作,忧大业之陵迟,救末师之舛陋也”[13],分别叙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目的在于刊正各经。此是许慎有感于五经传说臧否不同的现实所撰通经之作。而后郑玄著《驳五经异义》一书,反驳许慎在《五经异义》中的看法。一般认为,郑玄与许慎一样,尽管兼通今古文经学,但总体上是归于古文学派的学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许慎、郑玄所处时期今古文之间的壁垒仍旧那样森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他们这样的通儒产生,更不会有《五经异义》《驳五经异义》之问世。
注释:
[1][3][4][9](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9页,第1706页,第2410页,第3599页。
[2][6](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5页,第2203页。
[5][10][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00页,第1236页,第1239页。
[7](宋)洪迈:《容斋随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8](汉)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页。
[12](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56页。
[13](清)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自序》,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