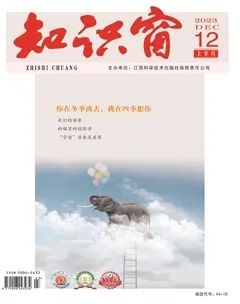教授的粉笔
彭妤
关于粉笔,北京大学的程郁缀教授有一段关乎学识境界的趣论:“作为北京大学教授,都要能够一支粉笔讲一天;比较优秀的教授,要能够一支粉笔讲一周;杰出的资深教授,要能够一支粉笔讲一月;只有一支粉笔讲一年乃至一辈子的教授,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师。”
初见这段文字,我并未真正读懂。后来,我读到一篇追忆钱玄同先生的文章。文章中写道,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文字学时,上课从来不带书本,只需一支粉笔,手写口谈,口讲指画,追溯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到大小篆、隶……把字的流传演变经过讲得清清楚楚,同时旁征博引《说文解字》《尔雅》等,原原本本,绝无差错。一个字的含义,他往往要解释好几个小时。此时,我猛然想起程郁缀教授的话,明白了真正的大师正是钱玄同这样的人。
其实一支粉笔,见证的不仅是学术学问的青蓝相继,还有大师的神采和风仪。钱理群教授在讲课时的感情投入之浓,在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讲热爱的鲁迅时,你必定能看到他眼中闪亮的泪光和头上闪亮的汗珠。泪水和汗珠都源于激动,這激动还会直接影响到板书。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来不及找手帕,他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
在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既然有用粉笔的教授,就一定有不用粉笔的教授,比如梁实秋。梁实秋上课,从不使用粉笔,黑板上也从不写一个字,理由是“我不愿吃粉笔灰”。虽无板书,但他讲课功底十分深厚,极具感染力,深得学生喜爱。据说有一次,他以个人风格解读英格兰诗人彭斯的一首诗,讲了没多久,课堂上有个女生为情所动,泪如雨下。他继续往下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实秋向家人提起此事,儿子问他:“您是否觉得抱歉?”梁实秋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这样看来,梁实秋的课确实也不用借助粉笔板书,凭他一张嘴足够了。
三尺讲台,一支粉笔,用或不用都没关系。用,是要书写乾坤天地;不用,是要留白,浓淡相宜。或用或不用的粉笔里,有丰标不凡的精神风度,有桃李无言的师者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