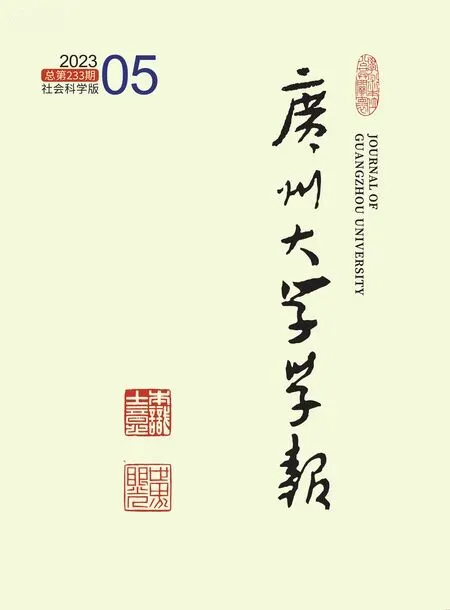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
——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王子威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从2014年的《强制阐释论》[1]、2017年的《公共阐释论纲》[2]再到2022年的《公共阐释论》[3],张江立足于挖掘中国阐释学传统资源,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阐释学一脉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分析,尝试建设一条结合中国传统、符合中国当下的中国阐释学理路。他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所强调的阐释的公共性以及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的关系问题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若论及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的关系,无法绕开阐释学循环(Der hemeneutische Zirkel,还译为诠释学循环、解释学循环)这一概念。因为文本意义产生于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之中:理解者在理解作品时会在文本、作者、自身、历史、时代等多重因素之间产生出多种解读,同时在这些因素之间交融这些一致或冲突的解读进而产出文本意义,这一过程呈现为一种动态的阐释学循环。可以说,阐释学循环是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无论是个体阐释还是公共阐释,二者的产生都源于不同类型的阐释学循环发生作用。当阐释学循环分属不同类型,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从意义产生的动态过程——阐释学循环入手,区分三种阐释学循环类型,明晰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二者关系,突显阐释必须拓展出公共性这一特征的必要。
一、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
在阐释学①中很早就有一种存在于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循环结构,也就是阐释学循环。阐释学循环涉及整体和部分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伽达默尔称“整体和部分循环的内容意义是所有理解的基础”[4]79。但整体指什么?部分指什么?整体和部分的所指并不是固定的,随着阐释学的发展,整体、部分及二者关系的内涵始终存在着变化。
为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文本的内在意义和作品思想,从古典阐释学到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近代阐释学理论关注阐释学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以文本对象为重心的理论路径,同时也产生了对文本对象内整体和部分循环关系的探讨。在这里,按是否包含创作文本的作者在内,整体和部分的内涵可分为两个层面来讲,本文将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细化区分为仅内在于文本语言中的阐释学循环和内在于包含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其生命精神的文本中的阐释学循环两种②。
其一,在仅涉及文本语言的阐释学循环中,整体指的是一部作品的全文,其中的部分按层级分别指文本内部的章节、段落、语句和语词。要理解全文的意义,就要先理解其中的章节;要理解章节,就要先理解其中的段落;要理解段落,就要先理解其中的语句;要理解语句,就要先理解其中的语词。而在每一次深入文本部分去获取对语言的理解时,也同时会回到文本整体去寻求上下文的意义交融,从而获取贯通前后的一致性意义,即在多个层级的部分和整体间交流、循环和更新理解。可见这里的整体和部分是包含和被包含的一对概念,指全文和章节、章节和段落、段落和语句、语句和语词的关系,更指从小的语词层层递进至大的全文这一理解循环过程。
在近代西方阐释学产生之前,宗教改革派代表人物马丁·路德主张的“《圣经》自解原则”(Schriftprinzip)较有代表性地呈现出这种阐释学循环特征。伽达默尔曾评价“《圣经》诠释学作为现代精神科学诠释学的前史”,其前提是宗教改革派的“《圣经》自解原则”,即“《圣经》是自身解释自身(sui ipsius interpres)”。[5]259他总结道:“我们既不需要传统以获得对《圣经》的正确理解,也不需要一种解释技术以适应古代文字四重意义学说,《圣经》的原文本身就有一种明确的、可以从自身得知的意义,即文字意义(sensus literalis)。”[5]259
马丁·路德认为《圣经》具备这种自己解释自己的能力,《圣经》文本才是意义的权威来源,从文本的字面意义就可以得到对《圣经》正确清晰的理解。那么,如何去获取文字意义?马丁·路德认为,“即使有些文句在某一处是模糊难解的,但在另一处却明了易懂,并且具有同一主题,对全体世人公开发表”[6]310-311,也就是说,在对《圣经》这一经典文本的意义阐释过程中,对字、词、语句的理解有赖于对《圣经》文本整体的把握,同时要想把握文本整体的意义也必须依靠对字、词、语句的具体理解,这就体现出一种内在于文本语言内部的阐释学循环。
因为正是《圣经》的整体指导着对个别细节的理解,反之,这种整体也只有通过日益增多的对个别细节的理解才能获得。整体和部分这样一种循环关系本身并不是新的东西。古代的修辞学就已经知道这种关系,它把完满的讲演与有机的身体、与头和肢体的关系加以比较。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把这种从古代修辞学里所得知的观点应用到理解的过程,并把它发展成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contextus)即从前后关系以及从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即从目的(scopus)去加以理解。[5]260
路德宗教改革坚持的“《圣经》自解原则”,力求使解读宗教经典文本《圣经》的权力逐渐脱离教会独断论的禁锢,这一主张也使得人们逐渐将《圣经》与历史流传的古典文本等同而视。因此,为适应当时对一般阐释方法的研究趋势,阐释学逐渐从一种应用性技艺向一门研究解释方法的学问发展。但在这里会产生一个疑惑,就是对于文本内具备自明性的东西,理解者可以清楚地通过上下文来理解,但文本中的那些不具备自明性的东西、模糊的部分又要如何来理解?
因此会引出其二,内在于一种广义文本(包含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其生命精神的文本)的阐释学循环。在这里,整体指的不再仅仅是语言文本,并非是与创作者分离的文本,而是承载创作文本的作者、作者的生命精神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各种内容在内的文本。理解的对象拓展到了依托于文本之上的一切具有语言性、文本性和思想性的东西,从文字到话语,从生活到历史,从思维到心理,而部分则指的是以上所有内涵的某一个方面。正如弗里德里希·阿斯特③认为,“文字、意义和精神是解释的三要素。文字的诠释(hermeneutics)就是对个别的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意义(Sinn)的诠释就是对它在所与段落关系里的意味性(Bedeutung)的解释,精神的诠释就是对它与整体观念(在整体观念里,个别消融于整体的统一之中)的更高关系的解释”[7]12-13。
检验检测中心要努力探索,找问题、挖隐患,消除监测抽检风险。在制定抽样监测工作方案时,以查找问题为主导,多抽检基层市场的散装食品,在采样时,多采“三小”行业生产的食品,特别注意把群众消费量大的食品品种、高风险品种、新批准原料生产的品种、通过其他渠道已经发现问题的品种等作为抽检监测的重点。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抽检监测方式,集中力量确定若干重点食品品种,有针对性地加大抽检频次,并定期跟踪。同时,强化监管整改措施,倒逼企业加强自检送检,集中精力解决了一批风险隐患问题,树立一批放心食品品牌[2]。
当文本对象不再受限于语言文字,而是拓展至语言背后的作者、时代、生命等,文本随之具有了历史性。具体而言,整体除了指作品全文之外,还包括同一作者的全部作品,同时代的作品集合,过去时代的所有作品、作品内容所代表的生活体验以及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甚至是整个过往时代的生命体验等,这就使阐释学具备了向生命性和历史性发展的可能。因此承接沃尔夫④和阿斯特思想的施莱尔马赫认为,“每一话语总只是通过它所属的整体生命而理解,这就是说,因为每一话语作为讲话者的生命环节只有通过他的一切生命环节才是可认识的,而这只是由他的环境整体而来,他的发展和他的进展是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所以每一讲话者只有通过他的民族性(Nationalitaet)和他的时代才是可理解的”[7]51。他还提到,“作者生活和工作的时代的词汇和历史构造了他的著作所有独特性得以被理解的整体”[7]62,这都表现出内在于广义文本(包含作者时代背景和生命精神的文本)的阐释学循环特征。由此,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近代阐释学理论寻求舍弃理解者自身的视域,努力与作者处于同一视域,要求“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追求“对某个创造所进行的重构(den rekonstrucktiven Vollzug einer Produktion)”[5]283。
而后狄尔泰更表示“个人所理解的生命表现对他来说通常不只是一个个别的表现,而且仿佛充满了一种对共同性的认识”,提出“客观精神”概念,将“个别的生命”纳入公共的东西之中。[7]98如此一来,理解文本意义就不仅限于语言文字,更包含了对创作者甚至是生活共同体的精神的领会。同样在现代阐释学的发展中,贝蒂融作者和文本为一体的文本中心阐释学理论也体现着这种阐释学循环。贝蒂延续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阐释学思想,认为文本对象是独立自主的,提出整体规则和意义融贯性规则,认为整体可被视为个人的整体生命和文本所隶属的文化体系,主张“整体的意义必定是从它的个别元素而推出,并且个别元素必须通过它是其部分的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进的整体来理解”,而“每一讲话和每一写下的作品都能同样被认为是一链条中的一环,而这链条只能通过它在更大意义语境中的位置才能被完全理解”。[7]132
由此可见,在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对象之内时,理解者完全抛却自身,将自我置于文本和作者的境遇内进行意义的还原性重构。当这一种阐释学循环类型起主导作用时,个体阐释并不具有当下性和时代性,反而是理解者全部回到旧纸堆和作者时代去挖掘一种所谓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以说服其他理解者来认同这种“权威”的文本意义。在这一阐释学循环的指导下,公共阐释的诞生更取决于历史史料和语境重构的客观性,而非理解者的阐发能力或多个理解者的共通感。那么,个体阐释在上升至公共阐释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其他理解者对意义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质疑,即一个理解者抛却自身所进行的历史性重构是否具有广泛的说服力。
二、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
通过前文对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类型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类阐释学循环是仅处于文本对象、理解对象一方之内的循环,也就是说,阐释学循环始终在文本的语言内部或在文本和作者之间进行。这种循环倾向于在过去中“历史地”重构过去,试图寻找一种最贴近过去的客观性。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被重构的这个历史性的过去是通过当下理解者来阐释的,这种阐释究竟可以达到多大程度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伽达默尔指出,施莱尔马赫需要“作为解释者的人把文本看成独立于它们真理要求的纯粹的表达现象(Ausdruckspänomene)”[5]290,即便在狄尔泰那里,文本意义整体也与理解者相分离。但无论文本如何与理解者相分离,无论其如何将意义封闭为一个过去的整体,无论理解者可以比作者还多么更好地理解作品,文本意义的阐释都是通过理解者做出的。“我们自身是作为理解者本身立于历史之中的,我们是一个连续转动的链条中的一个有条件的和有限的环节”[5]294,所以我们无法做到完全抛却自身、完全从当下视域抽离而置于作者的精神中去消除那些文本之于我们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将文本完全视为客观对象而追求客观意义的做法看似具有至高的历史感,实则却最欠缺历史性,也无法达到其所追求的客观性。
因此,在阐释学的发展中出现纳入理解者维度的第二种阐释学循环不是仅停留在文本对象内,而是在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之间的循环,即文本意义产生于理解者和文本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整体在这里指理解者的前见(Vorurteil)和文本以语言为中介的相遇、交流空间,部分则指前见和文本所分别占据的两个视域,同时,整体也可以指在阐释学循环中不断产生的一致意见,部分则可以指理解者在与文本意义达成交融一致之前的多次意义筹划。具体来讲,在理解者阐释文本意义时始终提前带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期待”,并做出“预先的筹划”[5]388。海德格尔认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8]215。因此理解者总是带有自身的前见去理解陌生的文本,即不可能抛弃自身投入文本对象,也不可能作为主体对客体进行占有和还原,而是置自身于文本对象内,带着自身与文本对象相遇。在这一相遇过程中,理解者的前见“不断地根据继续进入意义而出现的东西被修改”[5]388,循环始终继续,而不像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会在文本全部意义被获取之后走向消失的命运。纳入了理解者维度的阐释学循环,“在本质上就不是形式的,它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而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传承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Ineinanderspiel)”[5]425。
存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坚持阐释真正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提出“效果历史”概念,在辩证性的阐释学循环中始终主张“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的历史性”[5]434。
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将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5]434
也就是认为理解者身处的当下是历史性的当下,理解者无法将自身与经验、事物相分离,无法把过去仅作为客体来审视。历史主义在与过去的接触中保持着一种对象性视角,将自身从历史长河中独立出来,认为理解者可以完全地反思并超越自身的前见从而达到真理性的理解,这恰恰忽视了理解者自身也存在于历史之中,实则是“丢弃我们本身历史性的非历史性的理解”[9]。
其二是承认个体阐释的有限性。正如前文所述,伽达默尔对客观历史主义进行批判,认为理解者应首先具备效果历史意识,明确自身也是延续性的历史存在。理解者无法完全屏蔽或超越自身的前见,无法脱离当下处境,因此必须承认个体阐释具有有限性,“一切有限的现在都有它的局限”[5]437。也正是这种有限性前见才是开启阐释的前提,因为当理解者将自身置于与文本对象相同的地位时才会建立起自身前见和文本对象的平等对话,才会在不断修正和更新的阐释学循环中产生丰富的个体阐释。如果仅仅将文本视为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认识对象,会将文本完全变成封闭性的客观对象而导致主客体的绝对对立,暴露一种可把握绝对规律和真理的主体性哲学倾向,从而大大限制文本意义的丰富阐释。同时,承认个体阐释的有限性还意味着理解者明了自身前见存在真假之分,当与文本对象相遇并对话的时间越久,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假前见和推进理解的真前见就会逐渐分离开来,理解者就此可修正自身,从而于阐释学循环中获得一种更新意义并趋近一致意见的可能性。
其三是视理解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将阐释学导向本体论哲学。如果说上一种阐释学循环类型仍旧属于方法论和认识论范围,那么纳入理解者视域的阐释学循环则具备本体论哲学的意味。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路径,认同其关于理解的时间性分析,并不视文本对象为孤立的历史客体,反而将文本对象和理解者同置于历史之中,将理解者经由语言这一中介和文本相遇的过程用前见、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概念完整串联起来,即“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5]443。在此意义上,理解者的前见和不断更新的理解也一并被纳入了历史,从而呈现出将理解作为一种此在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特征。在封闭于文本对象内部的阐释学循环类型中,理解者独立于文本作为主体审视客体文本,不同于此,当理解者总是处于与文本对象相互了解的动态过程中时,视域并非是异己的、封闭的。在这种理解者和文本视域相互交融的阐释学循环中,理解者会意识到自身在阐释学循环中不断生成新的理解,意识到自身在这些不断积累的理解中存在。
由此可见,在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时,个体阐释显得尤为重要。当理解者不再追逐文本和作者所处历史的虚幻魅影,反而将自身和文本相等同来进行理解性的相遇,来进行意义阐释,理解者在这里格外展现了其阐释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在这一阐释学循环的主导作用下,阐释学理论更为关注理解者的个体阐释,并关注不同个体阐释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更追求自然而然的视域融合,而不求必须走向公共阐释。也就是说,在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而更重视个体阐释的阶段,理解者之间的交流更看重对话的开启而非对话的结果。
三、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
通过存在论意义上的视域融合可见“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Überlagerung),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5]444。由此能够发现无论是效果历史还是视域融合,哲学诠释学更多将关注重心集中在某一个理解者和文本对象的相遇过程上,更加突出个体在阐释中的存在状态。虽然伽达默尔在追问“理解何以可能”的过程中通过对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追溯为阐释学增加了伦理—政治性的人文传统深度,但这种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共通感却与个体阐释文本的阐释学循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游离。
在这里突显的问题是,阐释学循环既存在于隶属于文学的文本阐释内,也存在于隶属于伦理—政治学的他者理解内,如何来辨析和理解这种置于学科交叉地带的概念?而这也呼应了在阐释学循环概念发展演进中出现的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公共阐释论纲》一文中,张江提出“阐释本身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的讨论,主张“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定义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2]。由此发现,公共阐释论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与阐释学循环概念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谋而合。
本文因此基于公共阐释论的启发提出阐释学理论中存在着第三种阐释学循环,一种更带有公共性特点的阐释学循环,即存在于文本对象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这种循环指多个理解者分别与同一文本对象进行交流并产生多种个体阐释后,在不同的理解者之间进行意义的交流、循环和更新,最终或可形成有认同的公共阐释的动态过程。在这种阐释学循环中,整体指的是从个体阐释最终上升达成的公共阐释,而部分指的是多种个体阐释,同时在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循环是基于同一文本的。具体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解析这一阐释学循环类型:其一是阐释学循环始于具备公共性的个体阐释;其二是个体阐释经由淘炼向公共阐释转换,这是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的关键环节;其三是公共阐释具有反思性和历史性,体现出同时于横向空间和纵向历史中都有循环的特征。
首先,阐释学循环始于个体阐释,而个体阐释是具备公共性的个体体验。个体阐释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其一是人的社会性,“任何理解与阐释,最终归约、受制于人的公共性与社会性”[2];其二是此在的共在,“此在的理解和阐释的出发点及落脚点都是公共性的共在”[2];其三是集体体验和民族记忆,“非自觉的、无意识的前见,即阐释者认知框架中的文化、历史与多种社会规范的集合,并非私人构造,以此为起点的阐释期待,集中展示出个体阐释的公共基础”[2];其四是语言,语言决定个体的思维方式,“语言是公共思维活动的存在方式”[2]。不仅公共阐释论对于这种个体阐释的有限性和公共性有所论证,伽达默尔在追溯“共通感”概念时也将这种具有公共性的个体体验作为哲学诠释学普遍性的论证基础。公共性是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得以开始的基础,并非公共性压倒性地占据个体体验,而是公共性和个性平等存在、共同存在于个体阐释中。产生于前两种阐释学循环中的独特的个体阐释尤为重要,但这种个体阐释的内部也存在着可向公共阐释转换的公共性特征。
其次,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的关键环节,是个体阐释经由淘炼向公共阐释转换。阐释学循环从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上升和拓展的类型发展,与公共阐释论提出的一种个体阐释向澄明、公度⑤和超越趋势的路径不谋而合。即将个体阐释置入“公共意义”领域,向公众敞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晦暗文本”,“释放文本的自在性”,当个体阐释进入公共空间,“以独立方式表达意愿与见解,争取他人承认”,借由公共理性的作用,阐释得以公度而最终形成基本共识,“个体阐释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在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规约中,实现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升华为公共阐释”。[2]阐释学循环从一个理解者向多个理解者的范围拓展正推动了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阶段性上升。
这种推动作用体现为个体阐释的淘炼性的转换,张江在与约翰·汤普森的对话中提到,阐释空间中的确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存在着思想的斗争,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阐释中,最终会脱颖而出一个公共阐释,是经由“淘洗过滤”而出的理性的、澄明的公共阐释。[10]通过个体阐释经由淘炼转换为公共阐释的环节,阐释学循环真正从单独个体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进入更为宏大的人与他者、人与社会的阐释交流空间,从一种拘于文本对象的、个体经验的循环拓展为多个理解者之间基于同一文本对象的多向复杂循环。
这一阐释学循环中最终产出的公共阐释具有反思性和历史性。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体现为由个体阐释上升而来的公共阐释与文本之间的意义循环,体现为公共阐释(多个理解者的共识)与个体阐释(一个理解者的认识)之间的意义循环。即“公共阐释与文本对话交流,在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同时,“公共阐释与个体阐释对话交流,在个体阐释的质询中反思自身,校准和增补自身”。[2]如果说以上是公共阐释横向的反思性循环展开,那么公共阐释同样具有纵向的历史性循环展开。在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中,张江指出,“随着历史、文化及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阐释的标准、阐释的结果或形成的共识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它们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时代或一个历史阶段,变成一种声音,永远地传递下去”,因此公共阐释“总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得到修正的”。[11]也就是说,在第三种类型的阐释学循环中,不仅存在一个理解者阅读文本时所延续出的自身存在的历史性,更存在着多个理解者之间共识、一致意见、公共阐释的历史性,也正是这种阐释学循环支撑并体现着公共阐释论对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上升进路的价值和意义。
以上三个方面完整呈现了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过程,这是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的循环过程,也是从己到众的循环过程。一个理解者在审视文本对象时,在与文本对象对话时在阐释学循环中生成个体阐释,个体阐释不仅具备一定的客观性,也具备修正前见的历史性。当个体阐释进入冲突和竞争的公共视域会面临被淘汰或被承认的结果,个体阐释不被承认则被淘汰,个体阐释被承认则转化为公共阐释,公共阐释再进入与文本、与其他理解者的对话中进行阐释学循环,经由这一过程所形成的公共阐释具备反思性和历史性特征,始终于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循环地被检验和被更新。因此,从这一阐释学循环类型中可见阐释学循环概念演进与公共阐释论内在的理路契合。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和演进不仅拓展了阐释从个体向公共的阶段性上升,更促使包容了公共阐释论的阐释学理论愈加适应当下时代的发展。
四、余 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从古典阐释学到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近代阐释学,到承接海德格尔思想流脉的哲学诠释学,再到如今的公共阐释论,在最基本的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上主要展现出三种不同的阐释学循环类型,分别为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以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阐释学循环在此三种类型间的转换和演进不断推动着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相互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本文在分析阐释学循环这一概念的发展演进时发现阐释学循环逐渐拓展其内涵,逐渐不再拘于文本对象、理解者个体而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发展的趋势。由此呼应前文提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定义:理解者在理解作品时于文本、作者、理解者自身、历史、时代等多重因素之间交融那些一致或冲突的理解并产生意义的动态过程。如今阐释学循环的这种动态发展趋势恰与公共阐释论对阐释公共性的强调契合共通,体现着公共阐释论在推动当下阐释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虽然这三种阐释学循环类型存在着一定的线性递进关系,但并非新的类型产生,旧的类型就被淘汰,而是这三种类型一直且仍旧共同存在于阐释学的发展中,每一种循环类型都仍然保有其在阐释学理论中的存在价值,是理论始终需要关注的不同侧面。二是要注意阐释学循环的内核仍旧是文本,无论如何循环阐释最终仍要回到文本上。在阐释学循环向读者、向公共性发展的趋势中,无论整体、部分和二者关系的内涵如何变化,阐释都是生发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再回归至文本意义的阐释。正如艾柯所讲:“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12]三是在关注阐释公共性的同时要强调阐释的反思性。阐释学循环概念之所以重要,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僵化的共识和强取统一的公共阐释。要注意阐释学循环始终是动态的、演进的过程,这提醒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对自身阐释的修正和对公共阐释的反思。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使阐释学理论更加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更多的理论价值。
【注释】
① 阐释学(Die Hermeneutik 德,the Hermeneutics 英),国内学界还译为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关于西方阐释学的译名问题在国内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本文不对翻译问题做深入辨析,统一使用“阐释学循环”指称Der hemeneutische Zirkel,引用他人论述时保留原译。
② 本文之所以将作者纳入内在于文本对象的这类阐释学循环,是由于文本中既包含着作者书写下的语言文字,也承载着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生命精神。实际上,作者通过文本这一历史流传物同其中的语言文字共同呈现在理解者面前,在此意义上讲,作者和文本密不可分。在阐释学理论的后期发展中并不过度地、绝对地区分作者和文本。另外,作者和理解者处于同一个时代并共同阅读作品进行交流的情况在19世纪之前并不多见,这种作者和理解者同时就文本进行阐释和交流的情况可以放在公共阐释所推进的第三种阐释学循环中去讨论,即实际上作者在文本创作完成后也可作为一个文本理解者。这里,在对第一种阐释学循环类型的讨论中仅关注阐释学早期发展以文本对象为重心的意义阐释模式。
③ 弗里德里希·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1776-1841),德国语文学家、哲学家,著有《语法、诠释学及批评的基本原理》和《语文学大纲》,对施莱尔马赫一般阐释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④ 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德国语文学家和古典学者、近代语文学奠基人,著有《荷马导论》,率先用18世纪欧洲学界新兴的、用于研究《圣经》的文本分析法来对荷马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
⑤ 公度是一个几何学概念,对于两条线段a和b,如果存在线段d,使得a=md,b=nd(m、n为自然数),那么就称线段d为线段a和b的一个公度。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指出,“公共阐释是公度性阐释。阐释的公度性是指,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这种概念的转用引申是指从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上升的过程正是寻求共通、可被共同认同的过程,是“寻求阐释的最大公度”的过程。
——意象阐释学的观念与方法》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