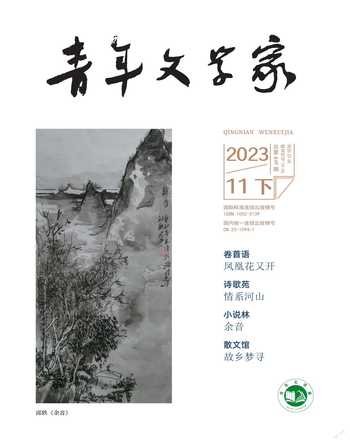论沈从文湘西小说《边城》的抒情性
付新荔

在湘西题材的小说《边城》中,作者沈从文描绘了湘西人性中的美与善的悲剧,把浓郁的抒情性表现到了极致。抒情性是沈从文小说的特色。沈从文认为作家应“习惯于情绪体操”。在湘西小说创作中,他或是直接把主体情绪灌注到形象和物象之中,使之带上鲜明的情绪色彩;或是借助于记梦和象征的写作手法曲折地表达主体情感,酿造出浓郁的抒情性。关于乡村与底层阶级是沈从文小说的一大题材,在这类题材中,沈从文的健康人性观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从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他对这种人生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也表现了其浓郁的抒情性。
一、《边城》的湘西情结
《边城》是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1934年。沈从文在《边城》里描写了湘川交界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中的波澜曲折、打动人心的故事。天保和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一个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但是两兄弟都互敬互让、真诚善良,彼此都为对方着想,二人相约以唱山歌的形式争得翠翠的心。然而,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天保因遇难而离世,傩送因愧疚而出走,而翠翠可能会面对孤独终老、孑然一身的悲惨境遇。在这里,翠翠的哀乐、梦境,与湘西茶峒的自然景物叠印在一起,意象新颖、美妙、繁多,含蓄地写出了傩送歌声之美妙动人,但无跳跃感,没有“隔”的感觉,而是缓缓流出,委婉诱人而不晦涩难解。哥哥自知不是弟弟敌手,主动退让,乘船离去,途中失事,不幸淹死。傩送在暗中爱着翠翠却得不到她的积极回应,家中又逼迫他接受新碾坊,于是赌气之下就离开了茶峒。沈从文在作品中表现了社会底层百姓的多种生活面貌及其形形色色的悲欢哀乐,其中寄托了他对“人性心灵美”的向往之情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充分表现出那个具有原始习俗的、自给自足的湘西世界遭受的具体的历史哀痛。事实上,小说中的人与环境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他对当时的现实社会感到不满,为了拯救人性的堕落,唤起原始的美好的人性,就创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环境,虚构了几个具有原始的朴素的人性美的人物,表达他的那种“返璞归真”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他自称《边城》的创作,“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沈从文:梦想与现实疏离的意义》)。在沈从文的思想世界里,湘西乡下确实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象征着勤劳、安宁、朴素、可亲。那里没有喧嚣、诱惑、不安、痛苦与虚空,和充满紧张、危险、迷茫、恐惧的城市截然相反。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浓郁的湘西情结和深切的情爱体验的艺术结晶,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心灵支撑,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朴素正直的人性美。作者将审美的人生形式和朴素纯真的湘西风情相互交融,用富含诗情的语言和充满灵气飘逸的笔触勾画出“边城”这个净化、理想化的世界。《边城》中的湘西山城茶峒,僻远秀丽。这里民情淳厚朴实,古风犹存,人人从善如流、重义轻利、遵守信约,几乎人人都是美和善的化身。老船夫忠于职守,慷慨豪爽,忠厚善良。他五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不停地为过往行人摆渡。过渡人出于感激,特意留下“渡钱”,但他分文不取,如数归还。不得已接受别人一个铜子,他也必以烟草回敬,或在酷暑时置办些凉茶,给过路人随意解渴。船总顺顺,豁达洒脱,公正廉洁,慷慨好义,备受人们尊敬。老船夫死后,他热心料理后事,尽力关照孤女翠翠的生活。其他人物如杨马兵、过渡客人、商人、水手等,无一不是那样热忱、质朴、善良……这简直是一幅民性淳朴、和谐恬淡的“世外桃源”图。沈从文说《边城》这部中篇小说是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他为小说已经消失的蛮荒历史、人类的记忆和梦幻里的世界辩护:“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沈从文批评文集》)沈从文通过湘西小说创作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伦理世界,期待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是满目疮痍与凋敝,而是充满温馨与牧歌。沈从文通过乡村儿女爱情形态的描绘,表现出乡村世界中自由的情爱关系,由此显示出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出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
二、《边城》的牧歌情调
《边城》还将人物和环境都做了理想化的处理,可以看出作者主观理想的张扬和抒情性的表达。他把浓郁的自我情感灌注到边城子民身上,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这一形象。但是,沈从文写作《边城》,“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而是要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文集》)。这种人生形式主要是通过其中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及其演变体现出来的。傩送的勤快、热情、大方、勇敢,翠翠的聪明灵秀、纯朴、善良,以及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相貌与形体,造成了他们灵魂的相互吸引和心灵的相互沟通。翠翠信守自己这种爱的选择,婉言回避和拒绝了天保的托媒提亲。而傩送在要渡船还是要碾坊的选择上,认为自己“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两个人都不愿被环境支配,而是坚定地把握命运,信守着自己的本来。这正是一种生命的神性,一种属于自为状态的生命形式。特别是翠翠,当明白了爷爷猝死、傩送出走的前因后果后,“哭了一个夜晚”,最后孤寂地守在渡口,一边与爷爷的坟墓做伴,一边默默地等待着那个或许永远不会回来,或许明天就回来的梦中人。曲终奏雅,《边城》遂成为一首优美动人的人性抒情诗。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湘行散记》)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
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是一个美好的艺术世界,是传达善良人性美與人情美的载体。在湘西世界中,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百姓之间都是将心比心、互相帮助的。这里好似一个大同世界,每一个受伤的人都会得到慰藉,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都会得到援助。这里充满了人情美和人性美,比如乡下老太太,即叔远母亲的体贴善良;卖梨老妇人从不斤斤计较,待买主如客人的真心实意。尽管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不追求迷离曲折,也不刻意地去塑造人性的复杂意义,但是他的湘西小说总是充满故事性,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容易与读者建立起情感联络的桥梁。沈从文以散文化的笔调勾画出一个个美丽哀婉的故事,给人一种清新迷人的感觉,具有激发读者思考、陶冶情操和洗涤心灵的作用。很明显,《边城》是沈从文对理想的生命形式的一种抒发,这种抒发一方面是基于作者对当时社会黑暗,特别是对人性的扭曲和堕落的不满;另一方面是作者对人性中优秀美好品质消失的忧虑,这种由现实而生发的忧患意识很容易促使作者对这种人生形式进行热情的抒发,来表达自己对这种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和渴望。
三、《边城》的悲剧意蕴
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幕悲剧,构成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天保的失恋。翠翠为什么不爱天保而爱傩送的呢?其实是因为天保的性格是实际的,而傩送的性格则是诗意的。在《边城》中,婚恋的“不凑巧”以及因此而生的憾恨与希望并存的复杂情感,源自沈从文自身的生命体验,因此小说也就成了作者寄托情感的载体。李健吾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在《边城》中,每个主人公的身上似乎都有着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忧郁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湘西世界的生存环境也是密切相关的。沈从文写《边城》的灵感是源于他个人的情感生活,他在《边城》中创造出了一个凄美的传奇—一切都因善与爱而不凑巧。这种不凑巧有两种,一种是翠翠与两位年轻人都不凑巧,一种是两位年轻人之间也不凑巧,进而导致良缘错失,成为凄美的悲剧。沈从文先生于是借这首牧歌,把他过去经历的痛苦的挣扎借人物展示出来,他受压抑的、无可安放的对于爱情的渴求得到了宣泄与弥补。同时,书中的人物们也似乎听到了作者要求“生命”摆脱这种自在状态的沉痛的呼喊,呼唤乡村儿女的生命和灵魂摆脱这种种限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生命的自由。
在《边城》中,沈从文把这种自我情绪灌注到翠翠身上,使之均着“我”之色。翠翠所处的社会是比较原始的,她是一个拥有许多原始的朴实的特质的人,她善良纯真、热爱生活、勤于劳动。但是,由于各种落后的习俗和理论偏差,她遭受了诸多不幸,幸运的是她依然保留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质朴之心。夏志清认为,“对土地和对小人物的忠诚,是一切更大更难达到的美德,如慈悲心、豪情和勇气等的基础”(《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沈从文心中,他认为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应该存在于生命之中,他在创作中着力于为笔下的小人物保留完整人格。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时候时刻贴着故事主人公和湘西世界去写。他既写他所感受的真实的湘西世界,又写他所感受之外的湘西世界;既细致地表现出真实的湘西世界,又能跳脱出这个世界去看到一些身处这个世界之中的人无法意识到的悲哀的一面。湘西世界中的人们往往蒙昧而不自知,意识不到自己的悲哀,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丝毫不在意。面对这样的局面,沈从文的内心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他希望向读者去展示一个朴实纯真、远离世俗的原始而美好的湘西世界,却不得不揭露这个看似美好的世界背后的劣根性的东西,他不希望这种劣根性和愚昧麻木一直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渴望去打破这种局面,去唤醒这些人,这就常常让他清新的文字流淌出悲剧意蕴,充满了抒情性。
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启迪着沈从文的灵性,陶冶着他的情趣。光怪陆离的生活经验,让沈从文提升了精细观察和丰富想象的能力。这种想象,附着在家乡优美的山川风物上,又赋予沈从文以独特的抒情气质。行伍生活以及漂泊经历,使他看到了社会对人民生活的肆意蹂躏,并引发了他对人生、社会、生命、生活的精细观察与哲学思考。都市生活的坎坷与丰富的人生况味,让他形成了完整的“乡下人”的基本心理素质和以“生命学说”为核心的人生观,以及“美在生命”的艺术观,从而在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中,他展开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乡村世界,弹奏出一曲曲“生命”的乐音。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世界,与其笔下的都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沈从文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便是抒情性,他的湘西小說都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性,让读者沉浸在这个世界之中,切身感受湘西世界的传奇色彩和一个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充满了人性的颂歌和道德的庄严;他笔下的都市社会,充满了庸俗、虚伪、卑劣和污浊。这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构成了作家所建造的文学世界的完整轮廓。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一完整的艺术世界,沈从文在所展开的一个延伸得寥廓而悠远的人生视野里,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连贯的思考和艺术的表现,从而寄托了自己的人生审美追求,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未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