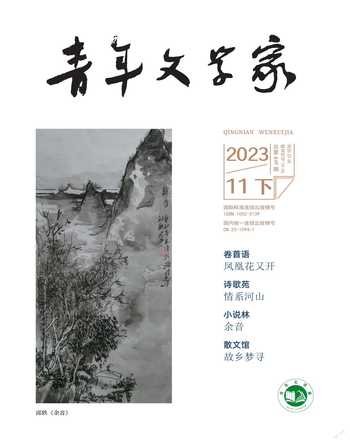白菜飘香的冬天
马玉涛
冬日的一天傍晚,下班赶回老家。推门进屋,一股熟悉的饭香迎面扑来,原来母亲已做好晚饭,正在饭桌边等我呢。此刻温馨明亮的客厅内,饭菜的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一大盘辣炒白菜所散发出的味道,融合了浓浓的亲情与母爱,宛若暖阳笼罩,让我如沐春风。
和父母围桌而坐,边吃边聊,那种香甜的惬意和满足,让我回忆起儿时的一幕幕场景。
我的老家桓台县城周边是早先种植大白菜的几个村子之一,也是白菜种植的重点村庄,这里种植的白菜品种好,产量高,收益多,在当时远近闻名。改革开放后,村东的小片地上有我家的八分自留地,父母在这块地上全部种上了白菜。那时候没有卖白菜种子的,家家户户大多是自留白菜种。白菜在收获后,人们总会留下几棵大的、好的作菜种。这种品种叫作“包头白”,产量高,外形也是又大又圆,一棵白菜能生长到十多斤。母亲说,她收获过的最大的白菜,竟重达十八斤,像一颗青白镶嵌的翡翠玉球。
清明时节,春暖花开,正是栽植留种大白菜的好节气。此时留种的白菜只剩下根盘和几片含苞的小芯叶了,但它们像是母亲的宝贝一样,被母亲一棵棵温柔地栽到地里。母亲给它们浇水、施肥,呵护备至。“五一”一过,白菜终于开花了,此时的菜地宛若一幅绚丽多姿的油画。那四片金黄的小花瓣,围着花蕊,竞相绽放,一簇簇金黄的花海,仿佛母亲慈祥欣慰的笑脸。花开花落,白菜打种的时候,麦子也成熟了。白菜种和麦子在这个时节一起收获了。
立秋节气,母亲播撒下一粒粒白菜种子,一个个新芽竞相破土而出。待到处暑时节,栽植的一棵棵白菜秧,很快就能长成了一片绿油油的小小的白菜。这些小小的白菜着实惹人喜欢,伸出头沐浴着阳光和雨露茁壮生长着。白菜田里的水井都是洞子井,井底的水洞与乌河水连通在一起。乌河水质甘洌,用这水浇灌的白菜,品质可想而知。那时化肥还没有普及,地里全部使用有机粪肥。地里不打农药,也不会生虫子。霜降节气一过,母亲就用草绳将一棵棵白菜捆起来,这样有利于白菜长得结实丰硕。此时距离收获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转眼就到了小雪节气,也到了最终收获的日子。这时,母亲就会带着菜刀去白菜地里采摘。她先是摁着大白菜,然后左摇右晃,向上一扽,就把它拔出来了。拔出后,她用菜刀把菜根上的泥土及亂根砍去,只留下短短的主根,这样有利于贮藏和保鲜。收获的季节,会有大批的外地的解放牌大卡车来收购白菜,地里人来人往,收购、过磅、装车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
俗语说得好:“百菜不如白菜。”白菜是北方农村的第一主打菜,更是北方人民冬天的家常菜。白菜寓意“百财”,更是年夜饭不可或缺的菜品。作为一名北方的农村后生,若是没在入冬前窖藏上一些白菜,年都过得不舒坦。窖藏起来的白菜,不损失水分和营养,随时吃,随时取,是农村最天然的冷库。记忆中,母亲总会把出售完剩余的几十棵白菜拉回家中窖藏起来。那时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有地窖,贮存冬天的主菜:白菜和萝卜。所谓“地窖”,就是在院子里开挖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坑,坑的最上面摆上圆木,铺满玉米秸秆,然后再敷上厚厚的土,留一个进出地窖的洞口,用来搬运白菜。
常言道:“萝卜、白菜保平安。”我的记忆中常会闪现出一幅幅画面来:祖母在老宅的土坯房里,把白菜剥去菜叶留着炒菜吃,然后把剩下的菜根泡在罐头瓶子里,过不了多久,白菜便会绽放出金黄的小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屋里的土炕头,被烧得温暖如春。祖父在土炉子上翻动着铁锅,炒着白菜,满屋热气,香气氤氲。屋外院子里那腌渍白菜的坛缸,还有祖母从缸中捞咸菜的场景,都像是一场久久不肯散去的梦……
如今,母亲依旧种着几分地的白菜。白菜收获后,母亲总会分一些给亲戚们品尝,偶尔也会拿一些到集市上去卖,挣点儿零花钱。我始终记得一家人在白菜飘香的冬天,感受浓浓亲情与恩泽的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