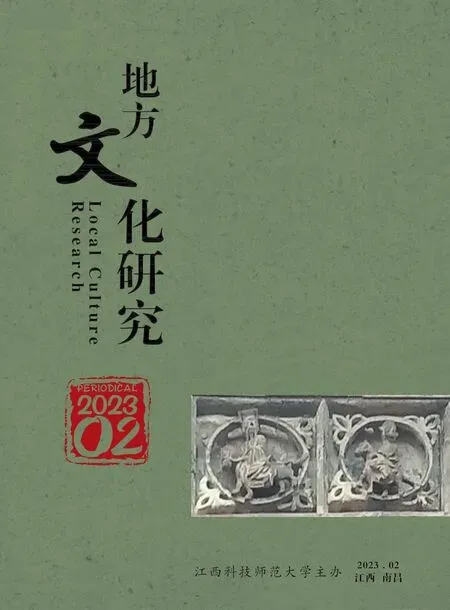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婚礼风俗的变迁
——基于陕西方志文本的研究
白中阳,刘思雨
(1,2.延安大学历史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从古至今,婚姻一直都受到社会和个人的重视。事实上,婚姻与人类繁衍息息相关,是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婚姻风俗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随着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的运动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生移易,能够体现出一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变迁。陕西关中地区即是如此,该区域历史文化深厚,曾有13个王朝定都于此,辉煌的文化成果曾经影响全国。进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较为滞后,明显逊于沿海地区和其他大城市,更多的传统文化和观念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中得到了新的塑造与重构。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婚俗文化的变迁,烛照出该区域广大民众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下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对该时期关中地区婚俗文化的梳理,可以从侧面展现出民国时期关中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变革。
近年来,学界关于关中地区婚礼风俗演变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首先,针对关中地区婚俗情况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如张建忠《陕西民俗采风》①张建忠:《陕西民俗采风》,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第31-33页。中对婚姻风俗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在关中各地的民谣里有大量关于婚姻风俗的描述,但整体上对婚俗的研究不够深入。郝明丽《民国时期关中传统婚俗研究》②郝明丽:《民国时期关中传统婚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43页。对民国时关中传统婚俗进行了一定论述,阐释自然、社会条件、文化传统方面对关中地区婚俗的影响,总结了民国时期关中传统婚姻形态和婚俗的特点。整体而言,该文既梳理了传统婚俗现象,又分析了婚俗演变的原因,很有借鉴意义。其次,针对关中个别县区的微观研究成果也有所出现。如马之骕《中国的婚俗》③马之骕:《中国的婚俗》,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02-212页。中用口述史料描述陕西婚俗,内容为陕西三原立法委员陈顾远的口述,相关内容虽局限于对三原地区婚俗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的相关介绍,但仍具有一定的学术借鉴意义。赵宇共《关中农村婚俗中的母系情结》①赵宇共:《关中农村婚俗中的母系情结》,《浙江学刊》1999年第4期,第75-82页。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结合中国上古礼仪文化分析陕西关中临平村婚礼习俗,并对“婚夜压炕”这一罕见的风俗进行介绍和阐释。通过研究,该文得出“陕西关中农村嫁娶仪式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婚礼风俗是女性和男性历史性互动抗争的产物”这一结论。该文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为本文创作提供了一定借鉴。
此外,还有一些在研究陕西民俗时涉及关中地区婚俗的学术成果。如杨景震《陕西民俗》②杨景震:《陕西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6-253页。叙述了陕西民俗发展的概况,其中用数个独立章节细致梳理了婚礼过程中相关风俗,但只描述了婚姻风俗现象,未能深挖现象背后隐匿的深层次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关中地区传统婚俗的学术成果。如郭宁的《关中地区传统婚俗传承问题调研分析》③郭宁:《关中地区传统婚俗传承问题调研分析》,《智库时代》2020年第5期,第211-212页。一文,该文运用问卷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关中传统婚俗的传承状况,并细致论述了传统婚俗继承困难的原因,其中着重对关中地区的传统婚俗的演变进行了概述。整体而言,该文虽研究方式新颖,但仅侧重于考察关中地区传统婚俗的传承情况,并未对关中地区婚姻习俗的变迁有充分的论述。
综上,民国时期关中婚俗的相关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日益丰富,有对陕西婚俗进行整体研究的学术专著,有针对关中个别县、村进行微观探讨的专题研究,亦有针对民国时期关中传统婚俗全面整理的相关成果。但透过梳理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只将关中婚俗视为中华婚俗整体研究中的很小一部分,缺少对关中婚俗的专门探讨。此外,多数研究忽略了婚俗变化的过程,只对婚俗现象进行论述。再者,某些研究成果缺少集中性的关于关中地区婚俗演变过程及其原因的探究。鉴于此,本文搜集相关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史料分析法,探究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婚俗的存续状态与演变过程,期望能够理清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婚礼风俗的变迁历程,以此推动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一、关中地区的传统婚俗及其演变
(一)婚礼的前奏:“三书六礼”
1.“媒妁之言”
关中各地婚前礼仪虽多承袭传统社会“六礼”的传统,但根据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整体上看,民国时期关中一带婚礼仪式中“问名、纳吉,久已不行”。④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这时传统婚嫁时兴的“六礼”已开始简化。尽管如此,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为宗法制服务,维系着社会稳定、经济建设、人口资源等重大问题。加之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的当事人在订立婚约时缺少自主性,与何人结婚的决定权掌握在父母手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婚姻规则,这样带有包办色彩的婚姻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深深扎根于关中。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多数青年人结婚仍然要遵循父母安排,父母挑选结婚对象要通过媒人说合。某种程度上,“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是相辅相成的。“婚为令媒氏议婚”⑤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只凭媒妁之言”⑥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1页。、“始聘,继娶”。⑦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4页。由此可见,媒人说亲是民国关中人结婚的“合法性”因素,没有媒人说亲的婚姻是不合当时社会规范的。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关中青年结婚只得服从父母安排和媒人说辞,在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上缺乏个人意志。
媒人是选择结婚对象中不可或缺的中介。说媒者通常是同乡妇女或医生,⑧马之骕:《中国的婚俗》,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03页。受男方或女方父母所托寻找亲事亦或主动为人物色对象。媒人在男女两家间牵线搭桥,从最初时的介绍对象到之后赠礼订婚环节,均由媒人传递消息。但因男女不相见,只能参考媒人一人之言,媒人常有意或无意把对方的优点夸大一些以促成婚事。但由此也造成了新人婚后的不满与不快,埋下了婚姻矛盾的隐患,甚至最终造成了男女双方婚姻的不幸。由此可见,传统包办婚姻导致年轻人无法掌控自己的终生幸福。
民国时期的关中虽仍保存说媒的风俗,但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俗在某些地区有所松动。如陇县的男女在婚姻大事上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经媒人说亲、家长合婚、压庚帖后,双方会见面议定。当事人在订婚过程中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媒人说媒男方看中后,男方父母会择定吉日由父母和媒人领着儿子到女方家拜访,男方会带上酒、肉等“四色礼”并用红纸包双数的钱作为礼物。如果男女双方不同意亲事,就不作表示;如果男女双方同意婚事,女方会收下所赠之物,这样就算定亲。①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陇县志》卷2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24页。陇县虽地处山区,但婚前相亲的新风俗对破除该地区传统婚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模式有重要意义,使得关中地区在婚姻习俗变革方面涌现出了一股新风气。
2.“相合八字”
经过说媒议婚后双方都认可婚事,媒人便会将女方的生辰八字要来送去男方家,这种仪式叫做“合八字”。合八字意在推算两人命中相生还是相克,具体操作时由媒人将女方的八字用红纸写帖子交给男方,再将男方八字送去女方。两家人互换获得对方八字,而后请来阴阳先生测算两人八字是否和谐后决定是否订婚。②白水县县志编纂员会:《白水县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650页。关中也有其他合婚方式,如长安县、周至县是将女方开出的庚帖,交由男方压在自家供奉的香炉下,三日内没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再请人测算八字,如结果显示八字相克便作罢婚事。③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整体而言,关中人合八字方法不尽相同,一些地区看八字时兼看双方属相,如长武县流传的民谣中记录看属相流行的方法是:“鸡猴不到头,白马犯青牛,虎蛇如刀锉,羊鼠一旦休。”④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从歌谣中可见看属相时还有“犯月”之说。事实上,看犯月有一套具体的标准,如属蛇的犯正月,属牛的犯四月,属兔的犯五月,属羊的犯九月等。⑤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信奉犯月规则的人认为如果犯月会使对方家变穷,这时父母会重新考虑是否同意成婚。
相合八字是关中人正式确定婚姻关系前不可缺少的环节。合八字的风俗表达了关中人希望婚姻幸福美满的心愿,但把人生命运寄托于测算八字这样的迷信之术,说明封建迷信的思想仍深植于民国的关中社会和广大人民内心。合八字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结婚双方的命运和婚后生活能否幸福寄托于毫无科学依据的封建迷信的说辞之下。这一过程中的“伤夫克子”“旺夫益子”的评价反映出女子社会地位的低下,妇女在父权制下可以任意被指为不吉利,并被视为造成家庭不幸的根源,而其命运同时在封建迷信定义下被牢牢束缚。但在关中的高陵县,合婚这一带有封建迷信的风俗较为薄弱,合八字的习俗因经济贫困被高陵人略过。⑥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卷24,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第659页。无论是交换八字请算命先生测算,还是验证婚事是否吉利的祭祀环节,亦或是请媒人在两家间传递信息,对贫困之家来说繁琐且花费巨大,因此,他们乐于省去合八字的习俗。事实上民国以降,因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文明的开化等原因,讲究命运的“合”与“克”这样没有科学依据的婚俗在关中部分地区开始逐渐消失。
3.“纳征之礼”
合婚后若双方再无其它异议,择吉日便会正式订婚,商定彩礼金额是订婚的关键环节。彩礼是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关中遵循传统婚礼中“纳征”后婚约成立的风俗。彩礼从纳征中脱出,彩礼的交付在缔结婚姻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意味着婚约能否定成。
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结婚看重彩礼“惟乡民不分贫富,聘多论财”。①咸阳旧志稽注编纂委员会:《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10,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64页。彩礼包含首饰、衣物、聘金。②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6页。如民国渭南地区彩礼构成为一份银元24枚,并有衣料、被褥、首饰、棉花、丝线等礼物。③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渭南地区志》卷22,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774页。因家庭贫富程度彩礼具体金额有区别。以眉县为例,中上之家彩礼送银50两,贫穷之家为铜钱30串。④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眉县志》卷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9页。特殊时期彩礼的支付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抗战时期民生凋敝、通货膨胀加剧,彩礼逐渐从金钱变成了实物。宝鸡千阳彩礼一般为4至6石小麦,个别人家索要10石。⑤千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千阳县志》卷27,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咸阳武功彩礼支付内容为小麦或玉米,数额5石到10石,个别高达36石。此时除以粮食为主的彩礼,另有“押彩钱”。通常为10至20公斤的棉花、布匹、鞋、衣料钱、首饰钱等。⑥武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功县志》卷30,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0页。综观彩礼的构成及彩礼习俗的发展,关中人民越发在意彩礼带来的物质价值而非礼节仪式。这实际上是社会因素对关中人生活面貌产生影响的具体展现,正是因为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崩溃人们才会索要高额彩礼,把彩礼转化成更为实际的粮食。
在订婚过程中,经济状况的优劣是缔结婚姻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周至县志》记载,民国时“世俗之辈,好尚奢靡,又有较量财帛,以致男女失时。”⑦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7页。巨大的彩礼数额成为结成婚姻的阻碍。贫穷人家的男子或负担更重的礼金,大荔县便有“男家愈贫,礼银愈重”的状况。⑧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6页。另有《兴平县志》记载有索取巨额彩礼以致到适婚年龄却无法成婚的现象,“今则公然鬻女矣。其索取金帛,不置男家之贫富,而过事索求,至有嫁不及时,壮而无偶者”。⑨咸阳经典旧志稽注编纂委员会:《民国校订兴平县志》卷8,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08页。彩礼成为一条横亘在青年人之间冰冷的银河,终结了许多良缘。即使关中有“婚不论财”⑩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的说法,但女方把彩礼看得很重,大多有买卖婚姻之嫌。对此,陕西十大怪中的“姑娘高价卖”,11○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卷7,西安:西安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描述的就是这种结婚时男方需要花费巨款,有卖女现象的风俗。在如此的社会风气中,谁家女儿出嫁得到的彩礼多,便会被称为值钱。虽然彩礼形式从银元转换到实物,是因战争和关中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战争和灾害也导致了货币贬值,农业欠收,民生艰难,上述恶果继而又反作用在彩礼的索取上,由此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对此,关中民众因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突变,越来越多的父母把女儿作为缓解饥贫的工具,婚姻愈发带有明显的买卖性质。
在订婚环节中,当事人少有掌握自主性的,只有前文宝鸡陇县和凤翔县偶有在双方父母同意下男方到女方家“相看”等类似相亲的环节。此外,民国关中地区男女结婚几乎缺少自主选择配偶权,只有宝鸡地区的新人在订婚中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但这并非真正的两厢情愿,因早婚的习俗订婚者大多只有十五岁左右,这样年龄的孩子尚不懂婚姻及其重要性,多数在相亲时观察父母对这门婚事的态度并顺从父母意愿。整体而言,“父母之命”的压力虽在关中一些区域有所松动,但长久沿袭的结婚前不相见的传统还是订婚过程的主流。整体上看,关中地区男女青年在订婚时没有个人抉择自由的情况居多。
(二)婚礼进行时:迎娶之礼
1.“亲迎之礼”
婚礼中重要的环节是六礼中的“亲迎”,迎娶的礼仪最为隆重。但亲迎在关中不兴,只是富绅家讲究亲迎。民国之初,富绅家用轿子迎亲,平民常用牛车。之后迎亲时的鼓乐逐渐减少,婚礼迎娶仪式逐渐简化。①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眉县志》卷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9页。婚礼迎娶的规格由个人经济条件决定,但都会备轿或车迎娶新娘。总体上,民国时期关中亲迎礼较为简洁。对此,关中方志记载:“城中无肩舆,无鼓吹音乐,更喜无优人。惟赛神招自邻县,则间行之。”②淳化县志编纂委员会:《淳化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迎娶时用花轿迎亲者,按关中的习俗,花轿去新娘家时轿不能空着,轿里要坐个“押轿娃”。③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婚礼当天,新郎往往穿礼服,戴礼帽,披红插花。④陕西省临潼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潼县志》卷3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4页。新娘出嫁时穿凤袍,头盖盖头。⑤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2页。而且新娘出嫁要用哭嫁表示对离开父母的悲伤。出嫁若不哭则会引来人们议论。不少新娘哭嫁以唱歌谣的方式来表达不舍,如“前年订婚刀割肉,今日出嫁火烧心。这根铁链谁制造?紧紧锁我身!”⑥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咸阳县志》卷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84页。由此可见,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婚俗中仍保留着传统风俗的痕迹。
到达男方家后新娘不能随便下轿,新郎家会举行“打醋坛”的仪式,这是一种祈福驱邪的巫术。新郎家在接到花轿后派出一人手持火把,在花轿周围绕一圈,称为燎轿,意在驱走邪祟。之后由一名披红布的男性长辈,一手举烧红的铁铧,一手端醋,绕着轿顺时针走三圈,再倒转方向走三圈。边走边往铁铧上浇醋,这种仪式称作“打醋坛”,起驱散邪恶的作用。关中人认为打醋坛是请来姜太公驱散不洁之物,以免迎亲路上招引来的鬼怪进入家门危害家庭生活。⑦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新娘下轿后行走,脚不能沾土,即将走过的路上会提前铺好布。新娘脚不能沾地也是关中婚俗中压胜仪式的一部分,意在防止土地中隐藏的鬼怪附身。新娘下轿后在两个伴娘的搀扶下继续前行,身后有男方家人撒麦草、豌豆、红枣、核桃到新娘身上,这称为“刘海撒金钱”。这一过程中,男方家人口中念念有词道:“一撒麸,二撒料,三撒新媳妇下了轿。一撒金,二撒银,三撒新媳妇进了门。新媳妇,好手脚,走路好像风摆柳。今年娶,明年抓,生个胖娃叫大大。”⑧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咸阳县志》卷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85页。关中婚礼上撒五色粮食寓意丰衣足食,祝福今后的新家不缺粮食。
新娘入门后,新人要进行拜堂仪式。新人并排站立在祖宗牌位前,听唱礼人指挥,先拜天地、祖先,再拜高堂,最后夫妻交拜。拜堂即宣告新人的姻缘由天定。拜堂后入洞房,这是婚礼仪式的最后一项。新郎、新娘在洞房进行合卺礼,两人各取一杯酒,喝掉半杯后交换酒杯饮尽。合卺有时不饮酒而是吃面条,“晚间交盏换杯,换吃面条,曰‘换碗面’,即古合卺礼也。”⑨铜川市印台区史志办公室:《民国同官县志》卷26,铜川:铜川市印刷厂,2006年,第420页。合卺蕴含着夫妇平等和睦的祝愿,寓意新婚夫妻永结同心。新人入过洞房,婚礼仪式便完成了。
入洞房后,便布置宴席招待宾客。婚宴结束后部分亲友会留至晚间闹洞房,关中地区俗称之“耍媳妇”。闹洞房时无论性别和年龄,亲朋好友一起唱歌、说绕口令。但有人在闹洞房的氛围中会说些让新人害羞的话,并要求新人做一些低俗的动作。⑩马之骕:《中国的婚俗》,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10页。闹洞房习俗本意是让新人互相熟悉,但该习俗带有作弄性质,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部分人的低俗闹剧。民国时期一些有文化的关中人认为闹洞房的习俗不文明、不健康,“至所谓闹房者,则大伤风化,宜亟革之。”11○ 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整体来看,尽管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婚俗中融入了某些现代文明婚俗的元素,但主体上仍保留着传统风俗的痕迹。
2.新婚饮食
关中地处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小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业生产和地域环境使关中人偏好面食,日常饮食主要是面条、蒸馍、锅盔、搅团等。关中面条种类繁多,常吃的有捞面条、油泼面、浆水面等。陕西关中有以面条待客的习惯,一些面条在做法和食用的时间节点上,通常代表着关中人某种特殊的情感或人生祝愿,例如面条在婚宴中即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关中地区婚宴往往有两场,这种婚宴被称作“一汤”“一席”。“汤”指吃臊子面或饸饹面,“席”是吃完面后的正式酒席。①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页。例如,新娘下轿进门后男方要布置早饭请宾客吃臊子面。拜堂仪式在中午,拜堂结束后吃午饭,即酒席。②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页。第二次酒席俗称转圆,③铜川市印台区史志办公室:《民国同官县志》卷26,铜川:铜川市印刷厂,2006年,第420页。新郎、新娘此时需一起给客人叩拜和敬酒。整体而言,关中地区婚宴的规格依主人贫富而有所差异,普通人家办酒席多数是一荤八素,富人家酒菜荤素各四种,贫穷人家办婚宴多是两顿饸饹或小米饭。④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川市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08页。但整体上来看,面条在关中人的人生重大仪礼中依旧是餐桌上的主角。
婚后第二天早晨,女方家送馄饨到女婿家,名曰“开门汤”。男方家要招待送饭的人,端来“四小吃”,即一碗面配四种小菜。⑤马之骕:《中国的婚俗》,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01页。在关中的农村,婚礼后的第二天上午新媳妇必须下厨擀面,目的是检验新媳妇的厨艺,俗称“考媳妇”。因关中人喜爱面条,擀面便是关中女人必备的技能。烹饪一碗诱人的手擀面要做到把面擀得薄如纸,切出的面细如丝线,面条下锅很难煮断。达到这个标准的才算得上是“巧媳妇”,否则便是“笨媳妇”。⑥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考媳妇”必须邀请亲戚和乡亲来家中做客,客人是新妇的考官,客人们要一起品评面条的味道。若新娘厨艺不彰则会被宾客嘲笑笨拙,而可口的面条会得到褒扬。关中民间有赞美新娘擀面技艺高超的歌谣道:“树上喜鹊叫喳喳,新娘入厨做茶饭,擀得面儿细又薄,下在锅里莲花转,盛在碗里摆牡丹,挑上筷子打秋千,吃在肚里缠线线。”⑦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整体而言,以饮食为载体的婚礼食俗,其本质上仍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一套特定的仪程完成婚礼仪式的实践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起了生命个体的社会属性。换而言之,上述以饮食为载体的婚姻仪礼不仅是对个体生命婚姻过程的仪式化认可,更是对关中地域民众的家庭及其社会关系起着建构和整合的作用。
二、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婚礼风俗演变的特点
(一)传统陋俗的延续
从上述传统婚俗的现象中可以看出民国时的关中婚俗保存有许多传统元素。虽“六礼不能备”,⑧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8页。但是古礼的纳采、问名、纳征、亲迎的程序演变发展为重媒人说媒和父母之命、合八字、重彩礼、男方用车轿迎娶。民国关中婚礼继承了“六礼”基本仪式,表现形式虽与“六礼”不一致,但基本模式未变。因此,从上述继承传统的婚俗现象中可以总结出关中地区婚礼风俗演变的以下特点:
1.流行早婚
关中盛行早婚。陕西各地盛行早婚,谚语“庄稼长到寒露,女儿养到十六”,⑨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1页。描述的便是这一现象。民国时期,一般女孩到十三、十四的年纪,父母就忙着给女儿找媒人说亲事,若是女孩到了十六岁还未结婚,会被人嘲笑。对初婚年龄《同官县志》⑩历史地名,今陕西铜川,原名“同官”,因与“潼关”同音,治所又设在铜水之川,故更名铜川。有记载,当地成婚年纪普遍均在十七八岁上下,贫家男子有在二十至三十岁者;女子则不曾有超过二十岁者。①丁世良,赵放:《中华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2页。《陕西妇女志》统计显示,1930年陕西男子初婚年龄在15.6岁,女子为16岁。②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页。女子在二十岁前结婚,十六岁没结婚的女孩会被议论。男子结婚年龄贫富有别,家贫的男子结婚在二十岁以后,比富人家晚。整体而言,关中地区流行早婚习俗,平均婚龄十六、十七岁左右。
首先,早婚习俗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并不显著,小农经济还是主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下家庭是生产和创造收入的重要载体。此时的婚姻重点聚焦在繁育子嗣的功能上,为了维持家中的劳动力,父母会早早为儿子张罗婚事。对父母而言结婚意味着添丁、绵延子嗣。婚后生育孩子为家里增加的帮手既有利于繁荣家庭经济,并且媳妇也能照顾家中儿子生活,分担家务。因此,为了保证生产和生活就需要早婚早育为家庭增添劳动力。
其次,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婚姻与家庭经济相关,早婚的风俗便有生存空间。同时早婚也与男女人口结构有关,《西安市志》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西安居民中本籍男性占比63.06%,女性占36.94%;民国三十四年(1945)西安本籍男性占比51.95%,女性占48.05%。③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卷7,西安:西安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从上述数据可见,民国关中男女比例失衡,女性人数偏少造成男方父母在男性童年时说媒的习俗,因此初婚年龄保持低位便不难理解了。
最后,民国时期的关中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诚如上文所言,人们期盼多子多福,这很大程度上缘于能够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之中,以此来维持日常生计或创造财富。但早婚者年龄尚小,缺少对事物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婚姻全由父母操控,没有感情基础的家庭生活往往会产生矛盾,且早婚早育会损害女性健康。对此,有不少关中民间歌谣控诉早婚,表达青年男女心中的怨愤,如“十七岁姐七岁郎,夜夜睡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岁小,说他儿来不叫娘。等到郎大姐已老,待到花开叶已黄。”④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咸阳县志》卷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81页。由此可见,早婚习俗造成不幸的家庭生活,这种不稳定的婚姻很大概率会产生家庭与社会纠纷,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事实上,早婚中所存在的诸如上述男女之间在年龄、体格、权力上的较大差距,极易导致女孩婚后家庭自主权的丧失和家庭地位的低下。
2.结婚重财
结婚前女方家收取彩礼数额较大,人们更多地关注彩礼为家庭带来的财富。关中的男女在婚事上,都是由父母来操持,婚约正式落定前要先论彩礼,而在彩礼问题上是能否达成一致是订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彩礼数额多是由女方家长开具,男方为了成婚只好被动接受。事实上,因结婚重财,民国时期的关中女性一直饱受买卖婚姻之苦。
具体而言,民国时期关中人结婚尤为看重彩礼。民国二十一——二十五年(1932—1936)西安的彩礼钱为50—160元,个别多达220元;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左右,因物价暴涨彩礼变成了实物,大约是小麦20石或棉花40捆、面粉500公斤;民国三十五年(1946)为法币65~100万元,翌年增长到500万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彩礼涨至2.8亿元和33公斤棉花,折算银元100元以上。⑤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卷7,西安:西安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关中结婚论财现象愈演愈烈。
再者,该时期关中地区结婚重财,买卖婚姻盛行,适龄的女孩是封建家长制和男权社会可随意支配的物品,家长看重嫁女而得的财物而不是女儿或姐妹未来婚姻的质量。关中歌谣《怨大(爸)妈》生动地展现了包办婚姻之下关中女性婚嫁的凄惨样态,歌谣描述了因婚前不能见面,女子婚后才发现丈夫面貌丑陋的情形。歌谣尽显女子无法支配自己婚姻命运的哀怨,“女子今年一十三,我大我妈急得给我寻老汉。拜了地,拜了天,揭开盖脸子偷眼观,呀呀妈!茬茬胡子一只眼,黑得像个叫驴脸。大、妈八辈子没见过钱,叫你女儿死都蒙不合眼。”①张建忠:《陕西民俗采风》,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由此可见,没有婚姻自主的妇女早早嫁给了丑陋的、不喜欢的丈夫,而她出嫁的原因是父母对高额彩礼的贪欲。事实上,买卖婚姻导致女孩被父母任意摆布失去人权,葬送大半人生的现象,在该时期的关中地区已屡见不鲜。
此外,小农经济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生活分工方式,使女性经济上的地位低于男性,只得依靠男性供养。男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逐渐形成了父权、夫权体制下传统的“出嫁从夫”“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女性出嫁成为男方家的劳动力,从夫居,生子从夫姓,在这样的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下,收取或支付高额彩礼的行为,即视同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将女性看作商品的买断性交易过程。彩礼被看重,成为订立婚约不可或缺的条件。另外,男女比例失衡也提高了女方父母在婚姻市场的要价能力,使彩礼愈演愈烈。再者,天灾人祸、军阀横行导致民不聊生,女儿越发被当作缓解家庭困境可议价的商品。
3.其它陋俗
首先,媒妁之言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极大的婚后隐患。传统婚姻流程中说媒、合婚、订婚环节要靠媒人在两家间传话,说媒时对方家庭、外貌等条件凭媒人介绍,媒人或多或少会将对方的优点放大并遮掩缺陷以尽可能多的促成婚姻。关中有妇女所唱民谣《媒人真是没良心》来控诉说媒和包办婚姻中的丑恶现象:“我大(爸)爱吃山核桃,把我卖到山屹崂。桌子擀面太得高,板凳擀面折断腰。半截擀杖没牙刀,漏气风箱要我烧。我妈只图把我卖,我受的难过谁知道?天知道,地知道,剩下就是我知道。拄擀杖骂媒人,媒人真是没良心,说下这媒烂舌根!”②张建忠:《陕西民俗采风》,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第254页。不难发现,挑选结婚对象只听媒人一面之词的习俗,使得部分新婚男女婚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理想中的意中人。而且,上述媒人说媒中的随意性也造成新婚夫妇心中的怨愤,埋下日后家庭矛盾的隐患。
其次,民国时期还有区别于正常婚姻的特殊婚姻。特殊形式的婚姻即一些非正常的婚姻,这些非正常婚姻多属旧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迷信思想。如“冲喜”,民间认为患宿疾的订过婚的男人,把没迎娶的媳妇接来办个婚礼,病就会因喜事好转。冲喜时婚礼随意准备,有时因新郎病重,新娘只能抱着公鸡拜堂结婚。③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冲喜令许多妇女成为了愚昧迷信风俗的牺牲品。除此之外,“冥婚”也是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具有迷信色彩的特殊婚姻。“冥婚”意为给生前未婚的死人办理婚事。旧社会奉行“无妻不继子,无子不继孙”④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的观念,认为未结婚的男子死后将无人供奉灵位。因此未婚男人去世后,其父母常常要找一个近期身故的未婚女子与儿子同葬。冥婚形式同正常婚礼相似,男方要交彩礼,用轿和棺接女方的尸身和牌位。于是有人觉得冥婚有利可图,以此牟利,甚至盗挖尸体。⑤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冥婚不仅充满愚昧迷信,还扰乱社会秩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冥婚习俗才逐渐尽绝。
再次,民国关中地区的许多年轻人因贫困而被当作奴仆或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如广泛存在于关中的“童养婚”即是如此。童养媳出身贫苦人家,父母无力抚养就从小找好婆家送养。童养媳被婆家买来成为类似佣人、女仆的角色,家庭地位很低,且从小要负担家务和农活。再者,还有“倒插门”招女婿的入赘式婚姻。入赘女婿的境遇与童养媳相似,被招入赘者因为家庭贫穷而娶妻困难才选择这样的婚姻。他们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日常生活要顺从媳妇及长辈,有的还因为更改姓氏受到歧视。倒插门的婚姻多数不长久,男方常常受入赘之家的虐待或亲朋、邻里的取笑而出走,或因女方不满意而被赶走。⑥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总的来说,许多“倒插门”者遭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最后,“换亲”式婚姻也令许多关中青年深受包办婚姻之苦。通常情况下,换亲的都是贫穷人家,两家的儿子娶不到媳妇恰好双方均有未婚的女儿,于是双方家长协商互换女儿为儿子成婚。①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俗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换亲式婚姻往往年龄差距较大,或者一方有身体残疾。换亲结婚者因家长命令不敢违背,酿成不少悲剧。被换的女儿在这场婚姻中沦为父兄获利的交易物品,全无半点个人意志。
整体而言,上述特殊的婚姻形式大多是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观念催生出的畸形婚姻,这些婚姻陋俗也造成许多关中男女婚后生活的痛苦与不幸。
(二)新式婚俗的诞生
传统婚姻陋俗虽然顽固,但随着社会风气的日渐开化,移风易俗的潮流使传统婚俗开始发生变更,进步人士更主张男女恋爱自由。尤其是随着新的婚姻观出现与传播,文明婚礼、平等婚姻逐渐在关中大地流行。尽管关中深处内陆,但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打破传统,在自由、民主的口号下自由恋爱,在妇女解放和权利平等的浪潮中勇于提出离婚诉求。虽然,民主自由的思潮冲击着封建礼教,但婚姻习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大部分传统婚俗仍然被继承下来。当然,转变是有过程的,即便在相对闭塞的关中地区,也不乏有追逐现代化潮流,接受婚姻自由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新式婚俗的实践者。
1.自由恋爱和文明婚礼
民国初期西安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自由恋爱。随后,西安市民掀起了一股妇女婚恋解放的浪潮,自由恋爱是这场妇女运动的口号。同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让部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和社会实践,逐渐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其中不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文明结婚在订婚时,由订婚人、介绍人和家长说亲并立下婚约,结婚双方签字盖章。相比传统婚礼,文明婚礼仪式简单,新人请亲友中德高望重者做证婚人,证婚宣誓后代表婚礼完毕,之后会设宴庆祝。
对于关中地区的文明婚礼,民国时期该地区的方志中多有记载。如《白水县志》曾记载当地知识分子提倡文明婚礼,反对旧式婚俗,但新式婚礼只存在于少数士绅、富人家,举行婚礼时新郎着西装,新娘穿旗袍,不行拜堂礼而行鞠躬礼。②白水县县志编纂员会:《白水县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651页。此外,韩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城市和乡村都有举行新式婚礼的现象出现。婚礼上新郎着中山装或西装,新娘穿旗袍,头蒙白纱。婚礼仪式上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男女双方主婚人致祝词,来宾代表致贺词,最后夫妻交换戒指代表礼成。③韩城市志编纂委员会:《韩城市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882页。另外,凤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士绅、豪富之家和知识分子中亦出现被当地人称其为“文明结婚”的新式婚礼。婚礼上新郎穿长袍,插金花;新妇穿旗袍,身披薄纱,穿高跟鞋;举行婚礼时邀请当地名人做证婚人,双方家长做主婚人;仪式上,证婚人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致辞祝福,亲友宾客在宴席间祝贺;新式婚礼由专业的司仪主持,新人不行拜堂而互相行鞠躬礼,婚礼后设宴答谢宾客。④凤县志编纂委员会:《凤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2页。总而言之,民国时期的文明婚礼并不普及,只有家境富裕的才会举办。文明婚礼的仪式摒除了传统婚礼中的巫术、迷信元素,仿照西式婚礼将中西婚礼仪式相结合,既简化了传统婚礼仪式又保留了一部分中国传统风俗。
关中的婚礼新形态之中还有陕西政府倡导举办的集团婚礼。集团婚礼旨在推行简朴风尚及促进节约运动。1947年西安市在陕西省“新运会”的主导下举办了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共有21对新人登记参加。此次集团结婚中新郎最大者33岁,新娘最大27岁,年龄最小的新郎21岁,新娘16岁。陕西人参与最多,兼有豫、晋、鲁等籍人士,报名者有商界、军界、学界各界人士。婚礼由西安市长证婚,亲礼者与新人都情绪高昂。⑤佚名:《陕西集团结婚:五月十八日举行参加者二十一对》,《新运导报》1947年第3期,第44页。不难看出集团婚礼的适应人群广泛,包容度很高,并且简单节俭、秩序整齐的新结婚方式容易博得群众的喜爱。事实上,陕西关中的集团婚礼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中诞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引导的成果。集团婚礼有利于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新风,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婚俗和固有的婚姻观,对除去关中婚俗陋习颇为有益。
须承认,虽然民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出现了模仿西方婚礼的新式婚俗,但新式婚礼只流行于个别市、县和个别阶层,大部分农村仍然举行传统婚礼。豪绅和知识分子最先接触西方婚礼习俗并模仿,但广大关中民众仍沿袭旧俗。
2.离婚日渐趋于自由
民国时期的关中地区曾有妇女采取法律手段解除父母包办的婚约,争得婚姻自主权的现象出现。民国二十五年(1936),关中人士樊绒花在给法院的状书上写道:“八岁父母将我与水重华订婚约,誓不从父母之命,今如有威胁成婚,惟有决心自杀以尽人道,万难从父母之命。”①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法庭当庭依法宣判婚约无效,樊绒花成功为自己取得自由恋爱的权力。事实上,民国颁布的法律中制定了很多限制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现象的条文。例如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颁布了《民法》,其中第972条至第1058条,明确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不得结婚”;“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结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2人以上之证婚人”等,②陕西省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7页。这些法律条文成为思想解放人士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重要武器。
尽管保障婚姻权益的法律条目日渐增多,但也须承认,民众婚姻观念上的陈旧与保守一直是关中地区婚俗变革的重要阻力,多数关中人始终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因此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和法庭判离的都较为鲜见。千百年来传统社会和家庭共同教育妇女顺从,妇女遵守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的规训,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及意识。即便有离婚现象,也多数是由丈夫或父母来决定,妻子只能被迫顺从。对此,民国立法部门制定离婚法条,离婚一是“两愿离婚”,即签订离婚协议,并有两名以上证人签字;二是“裁判离婚”,即由法院判决婚姻撤销。法律规定如有一方犯以下罪行的可向法院提出离婚:重婚、与人通奸、一方受他方虐待、图杀、不治之顽疾、不治之精神病。③陕西省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8页。由此,立法规定了男女有平等的离婚权,让深受包办婚姻、家庭暴力等压迫的妇女能够用法律反抗封建礼教,脱离不幸的婚姻。
此外,随着西方民主、女权思想的传入,关中地区青年男女的传统婚姻观念逐渐开始动摇。其中,清末以来关中民间天足会等组织所开展的反缠足运动,就为女性的身心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反缠足不仅颠覆了妇女依附男性审美、依靠男性供养的心理和行为,在现实上和心理上解放了受封建规则压迫的妇女,而且也使得妇女们以新姿态自信地立足社会,与男性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从事喜爱的职业,享受平等的待遇。同时日渐开放的思想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令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学堂学习文化知识。例如,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八年(1919)间,西安、富平、宝鸡等地陆续创设女子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创建的女子小学有112所。④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页。新式的女子教育使她们学习到了新知识和新思想,产生对旧习俗的反叛精神和女性自觉,从而逐步实现了自立、自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西安有史以来的第一起离婚案曾引起当时社会的震动,这起离婚案说明关中社会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民国十五年(1926),西安简易师范学校女学生萧桂藩与朱子愫结婚。因实为包办婚姻,婚后二人感情不合,并且朱家常虐待萧桂藩,萧不堪忍受向“西安妇女协进会”求救。经过调查西安妇协认为两人婚姻破裂,支持萧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朱凭借其军官身份带来的特权驳回离婚起诉,并且有恃无恐地打骂萧并约束其自由。萧寻找机会逃出,妇协向各报投稿并向社会揭露事件始末,呼吁社会给予萧同情和支援。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院不得不重新判决了两人离婚。⑤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此外,根据《西安市志》中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离婚原因统计调查显示,离婚多是由女子提出,原因有丈夫打骂、妻子不愿做妾、妻子发现丈夫另有姘居等。①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卷7,西安:西安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不少妇女已懂得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在心理层面上逐渐改变了旧有的传统婚嫁观念,敢于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幸福。
然而,该时期陕西各级政府中并没有专门的婚姻维权机构,各地包办买卖婚姻、早婚现象依旧普遍存在。对此,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省政府曾试图统一全省婚丧礼仪,颁布了《婚丧仪仗暂行办法》作为规范,但收效不佳。②陕西省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7页。整体而言,时至民国政权结束,法律也没能完全有力地影响关中人的婚姻习惯和观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等封建婚姻观、伦理观仍然束缚着广大关中民众。但政府和民间进步势力争取婚姻自由、离婚观的转变,以及政府立法支持改变传统婚姻中的陋俗等社会新风气的出现,均说明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妇女权利和自由婚姻的理解。虽然不少婚姻陋俗或畸形婚姻形态仍然存在,且封建婚姻观念仍旧根深蒂固,但在恋爱观、离婚观的转变上也真实地体现了关中社会的进步。
三、关中地区婚礼风俗演变的原因及时代意义
(一)关中地区婚礼风俗演变的原因
1.地理因素
一个区域特有的自然条件影响地域文化的形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养成了该区域内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理解关中地区自然条件是理清关中婚俗变迁原因的基础。
具体而言,关中地区拥有土壤肥沃的广大平原,气候温和无霜冻。同时关中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因较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关中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孕育了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进而造就了关中地区长时段的政治中心地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关中地区长期受传统中国文化的浸润,并且拥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在关中平原庇护下生长的关中人深受农耕文化影响,习惯安逸的生活,朴实勤劳地经营着土地。与此同时,关中人形成固守的心理。因此,在面对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的新变化和新事物的涌现时,关中人的行为偏向于保守,心理上求平稳,安于现状。此外,关中位于中国中西部,深处内陆,南北有山脉或高原,地理位置较为封闭。民国时期西风在沿海徐徐吹拂,传播到内陆的关中地区需要较长时间。关中因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保留较多的传统因素,在变化日新月异的民国时期,该地区虽然发展节奏缓慢,却也出现了不断变化的新气象。体现在婚俗上,便形成了传统习俗与摩登行为并行的特点,尤其是在对传统文化及观念的反叛行为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
同时,自然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民国时期,陕西自然灾害频发。如民国十七年(1928)至二十一年(1932),陕西旱灾持续五年,暴风、冰雹、蝗、洪等各类灾害并发,继而又突发鼠疫。灾情以民国十八年(1929)最为惨重,全省92县,县县有灾。③陕西省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9页。据西北灾情视察团的报告《陕人无唯类矣各县人民死亡逃难者过半武功县设有人市贩卖妇女》来看,“关中武功县人口原有十八万,在此次灾情中七万余人饿毙,五万多人逃荒,县城四十里内荒绝人烟。因连年受灾当地人民求生无门选择自尽或卖儿卖妻。当地有人市,妇女价高者八元,低者三四元。妇女被典卖,无人看顾的小孩流落街头巷口。”④西北灾情视察团:《陕人无唯类矣:各县人民死亡逃难者过半,武功县设有人市贩卖妇女》,《大公报》,1929年10月25日,第7版。由此可见,因天灾频繁、民不聊生,妇女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
再者,关中的农民往往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只能依靠政府救助。在生存危机下农民先变卖生产资料,再伐木卖树。于是在接连的大灾过后,土地荒芜、人去楼空,农民失去生产资料致使农业生产无法重新恢复。关中人受连年旱灾和疫病影响生活艰难,受灾饥民皆食草根、树皮度日。而且旱灾之外还时常出现极端天气,冰雹和雪灾使灾民饥寒交迫。因此,在极端惨烈的自然灾害下关中灾民为了生存不惜卖儿鬻女。连年旱灾,饿殍遍野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催生出民国时期关中人结婚的高昂彩礼及买卖婚姻的现象,致使父母用未婚女儿换取钱财或粮食的行为常态化。由此看来,关中人结婚论财的习俗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便不足为奇了。
2.文化因素
首先,社会风俗的演变过程中,文化因素是重要的推动力,文化水平影响着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民国以来,关中各地陆续开办新式学校。日渐开放的文化思想及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令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学堂学习文化知识。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八年(1919)间,西安、富平、宝鸡、岐山、陇县等地陆续开始兴办女子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民国时期关中创设的公、私学校众多有112所。①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页。教育使她们获得新思想,产生对旧习俗的反叛精神和女性自觉,从而自立、自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们反对包办婚姻,践行自由恋爱,改变了以往嫁鸡随鸡的婚姻观念。
其次,民国时期陕西有进步的、革命的教育宗旨,以求培养一批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革命人才。民国十六年(1927)左右,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以第四号命令宣告的陕西革命教育宗旨为:“教育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人才,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达到世界革命”。②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教育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从政府规定的办学宗旨中可以看到,陕西的教育以继承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民权基础为目的。新式学校传播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培养了有革命意识的年轻人。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层面的落后,因此把矛头对准了封建文化和道德。传统婚姻风俗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表,自然受到革命者的抨击。秋瑾曾说:“吾谓革命当自家始,所谓男女平等权是也。”③秋瑾:《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陕西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培养了有民族意识、民主意识的有识之士,他们将目光首先投向自身,在革命活动中他们积极反对家庭中的男尊女卑现象,并大力反对包办婚姻、早婚、童养媳等传统婚姻中的陋习。先锋者们掀起的反叛传统礼教的风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中青年加入其中。在先进人士的号召下,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不断有关中民众意识到传统婚俗中的弊端及其严重危害,并且协力反抗。
最后,在先进思想文化的大力推动下,女性社会组织的相继涌现也推动了关中地区婚礼风俗的演变。例如,清末以来关中已有民间天足会组织进行禁止缠足运动,他们积极宣传放足的益处,并向关中女性普及卫生、健康及生理方面的知识。对此,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2日《新秦日报》曾报道:放足处立刻派专员复查放足情况,并与公安局和县政府一同办理,逐户详查,若有仍坚持缠足,依法律惩办。此举显示西安政府禁止缠足的决心,意在令惨无人道的缠足恶习禁绝。④陕西省妇联志办:《新编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政府力行的缠足禁令利用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加速了缠足恶习的灭绝,并令妇女以健康的状态投入社会生产生活,心理上帮助妇女脱离对男性的依附,从而帮助广大妇女能够自立于社会,参加劳动,进而加速了关中青年从旧的婚姻习俗中解脱。由此可见,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对于关中地区女性的自由与独立,以及改变关中地区传统婚俗和婚姻观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3.政治因素
尽管传统的礼教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并同民间习俗相伴生。但政府行政力在婚礼风俗变革中的引导与宣传作用更是不容忽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均发生了剧烈变化,政府在移风易俗方面实施了许多新的举措。对此,民国政府运用法令的强制性推动社会风俗改革。譬如1930年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婚姻中的诸多陋俗。
再者,为了响应中央政府改良风俗的政策,推动陕西旧式婚俗的更易,陕西地方政府根据省情颁布了《陕西暂行婚姻条例》。条例对结婚自愿、结婚最低年龄、婚姻预约的绝对效力、婚姻双方资产、撤销婚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并附有为何作此规定的具体解释。①佚名:《重要法令及公文:陕西暂行婚姻条例》,《法律评论》1928年第235期,第14页。法条简明易懂,利于推广普及,为陕西婚礼风俗提供一个清晰的改革方向,此法对关中婚礼风俗改良至关重要。此外,民国新生活运动也对关中地区的婚俗产生了显著影响。新生活运动倡导集团结婚,集团婚礼成为关中区域新鲜的婚姻行为,有益于抑制关中婚俗中奢侈尚财的陋俗。不过关于关中地区集团婚礼的文字记录不多,这种婚礼新形式在关中较少见,但是关中地区集团婚礼对推行文明结婚的意义不容否认。
另外,陕西民政厅因省内实情于民国十七年(1928)发布训令,令陕西各县长禁止买卖婚姻。因有在缔结婚姻时勒索金钱而耽误婚嫁的极端之举,令各县县长张贴布告并口头宣传,禁止结婚中穷奢极侈的行为,防止买卖婚姻。②邓长耀:《陕西省政府民政厅训令:令九十一县县长禁止买卖婚姻以挽风文》,《民政周报》1928年第45期,第6页。此训令为挽救陕西婚礼中论财争物的颓风,齐男女平等之权颇为有益,同时在宣传人权平等思想、杜绝买卖婚姻方面更有重要意义。
然而,民国时期关中军人主政,权力更迭频繁,战乱连连,社会秩序混乱,政府政策无法得到良好的实施。关于婚姻问题的法律政策同样没能得到预期效果。陕西省民政厅在冯玉祥主陕时期,曾两度公布关于婚姻问题的通令,致力于更正关中盛行的早婚习俗和禁止买卖婚姻。此法明确限定:未达到男满20岁,女满18岁的法定初婚年龄,不能成婚;严厉禁止买卖婚姻。③陕西省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新编陕西省志民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但因政权更迭,政随人转,该政策难以达到成效。此外,因为局势动荡及政府执政能力不佳,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省民政厅发布的《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同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足见,民国时期,政府颁布的政策、法律没能发挥应有的效力,关中各地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陋俗没有得到有力约束,畸形的婚姻形态依然流行。而且,政令不达使男尊女卑、从一而终、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观念仍未被拔除,传统婚姻观和旧婚礼习俗依然有其存在空间,没有得到应有限制。
(二)关中地区婚礼风俗演变的时代意义
首先,关中婚礼风俗的演进中陈规陋习被革新,关中地区的婚礼风俗完成了一次吐故纳新。新式婚礼与集团婚礼一改传统婚礼中铺张浪费、流程繁琐的弊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传统婚礼中常有的迷信色彩和庸俗行为。部分地区不再遵守男女青年婚前不相见的传统,父母会考虑子女对亲事的态度,包办婚姻对年轻人的约束有所松动。婚礼仪式简约,集团结婚流行,婚服西化。整体而言,关中地区婚礼风俗的发展与演变,使得民国时期的关中婚礼风俗呈现中西文化交融、新旧交织的新气象。
其次,关中婚礼风俗的演变使得关中地区文明风尚盛行。关中部分市县结婚时简化传统婚礼流程和亲迎仪式,减少了传统婚俗中的巫术遗留,一定程度破除了封建迷信。新式婚礼的出现为关中婚俗注入了活力,有利于促成节约的社会风气,令婚俗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婚姻中逐渐注重个人意愿,关中的婚俗逐渐展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权平等。
再次,关中地区婚礼风俗变动中潜藏着婚姻观的变革。第一,婚姻的目的发生转变。传统婚姻的缔结之目的更多是服从父母和家族利益,或是以繁衍后代为主维系家族发展。在受西方以人为本的文化感应之下,渐有关注婚姻当事人个人意向的相亲。第二,离婚不再被置诸高阁。妇女改变了以往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同时追求性别平等,一改封建社会的依附男性状态。第三,婚姻自主观不断发展。年轻人以逃婚、起诉的方式与父母之命对抗,谋求恋爱自由权。这样一反传统的新婚姻行为,投射出民国时期部分关中人士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已然淡薄的现实,他们结婚考虑主观的爱情和幸福。同样映现关中的青年男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愿望。
最后,关中地区婚礼风俗的演变对现实婚俗改革具有借鉴意义。一种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习俗,通常是人们长期沿袭下来的习惯,作为一种文化惯性融入大众生活。习俗拥有特殊的历史继承性,因此革除陋习在需要长期实践中实现。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社会风俗的革新至今不过短短百年,部分陈规陋习依旧残留至今。因此在当代仍需审视婚俗现象。例如,婚礼铺张浪费、闹洞房低俗等陋习依然层出不穷,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余毒尚在,贞洁观仍旧是一部分人心中的枷锁。这些婚礼陋俗仍需剔除,使得婚礼风俗在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向上健康发展。
四、结 语
民国时期是处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发展、大变局期。该时期新事物和新思潮将民主和科学渗透入各领域,婚姻观念也发生着由旧向新的转变。传统婚俗与西方婚俗发生碰撞、交融,新式婚俗从这一过程应运而生。随着近代教育的发展,青年人接触到新式婚礼,纷纷选择举办拥有自由平等理念的新式婚礼。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封建礼教受到强烈冲击。知识分子和富人最先接受男女平等和自由恋爱的概念,他们逐渐开始挣脱封建家长制和包办婚姻,继而引发平民阶层的争先效仿。此外政府积极引导促进新婚俗形成,推动关中婚俗向简约、健康方向转变。但民国时期关中社会动荡、灾害频发,婚俗的变革受到阻滞。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婚俗变革整体上较为缓慢。从全国来看,处于内陆的关中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相对落后,这样的落后给传统婚礼风俗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再者,由于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婚姻制度历时久、积淀深,这使得民国时期关中婚礼风俗有着新旧杂糅的过渡特征,这种过渡性特征是时代的特色。
整体来看,民国时期关中的婚俗以传统为主流,新式婚俗零星出现。但不容置疑的是,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婚礼风俗中的封建落后部分开始逐渐剥脱,呈现出新旧共存、中西结合的特点,并且随着现代文明曙光的照射,关中地区婚礼习俗有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发展的强烈趋势。而且在婚俗的动态演变历程中,传统婚俗里的糟粕被识别和剔除,但仍有部分落后的婚俗文化残留下来。例如,重男轻女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人仍旧被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观念捆绑,彩礼问题仍被广泛讨论,婚礼铺张浪费和低俗闹婚现象屡见不鲜。对此,笔者期望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婚礼风俗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提供历史角度审视婚礼陋俗存续至今的根源,以此帮助人们识别出传统婚俗中的优秀成分并加以继承、弘扬,并给予婚姻陋俗的革除与改良提供相关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