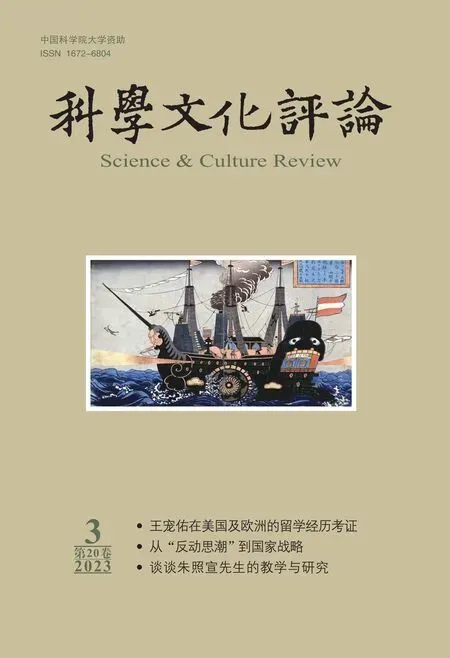多萝西·霍奇金与中国生物分子研究
郭晓雯
英国生物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1910—1994),出生于开罗一个英国殖民地教育官员家庭。1928年她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学习化学,毕业后来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跟随约翰·贝尔纳(John Bernal)从事晶体学研究,1934年回到牛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7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利用X射线晶体学技术,她分别在1949和1957年测定出青霉素、维生素B12的结构,并因此在196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2]。她推动X射线晶体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确定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被视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科学家之一。
霍奇金在国际科学界担任诸多要职,包括1972—1975年担任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主席,1976—1988年担任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主席,1977—1978年担任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此外,她担任过加纳总统顾问,多次出访苏联和越南,1987年被授予列宁和平奖,对中国蛋白质研究进展也保持了长期关注,在1959—1993年间八次访问中国。这些活动使她不仅仅因其科学成就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科学事务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促进国际科技交流都贡献了力量。
一 与中国结缘
1. 霍奇金的左翼倾向
霍奇金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为她日后关心公共事务和国际问题埋下了伏笔。她的父亲约翰·克劳福特(John Crowfoot)1901年进入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政府教育部,成为一名公务员,1916年担任苏丹的教育长官。童年时期的霍奇金便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但是这种往返于英国和殖民地的奔波生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和杀戮,使得她对科学以外的东西也有了特别的关注。而霍奇金的母亲茉莉·克劳福特(Molly Crowfoot)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一战结束后即加入了联合国的前身——旨在维护和平的国际联盟,1925年9月,她带霍奇金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第6届大会,在与埃及、苏丹和耶路撒冷的女子们打交道时也毫无种族偏见。母亲的行为、性格特点深深影响了霍奇金,令她意识到做被动的观察者是不够的,而是要主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这构成了霍奇金对国际事务最初的理解([1],页3,21,323)。
成年后的学习经历和婚姻使得霍奇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32年霍奇金来到剑桥成为贝尔纳的学生,贝尔纳加入了英国共产党,霍奇金和他保持过一段情人关系,因此接触到剑桥科学家反战团体的思想,并关心着西班牙和中国战争的进展([1],页93—94)。1937年霍奇金嫁给牛津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托马斯的研究旨趣在于非洲历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也是一名英共党员[1—2]。由于上述关系,20世纪50年代时霍奇金无法办理美国签证、被禁止入境,无法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但有别于贝尔纳,霍奇金处事低调,她十分厌恶被当作某种“楷模”,拒绝给自己牢固地贴上诸如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女性主义等标签([1],页326),也没有加入英国共产党。她在剑桥期间加入了科学工作者协会,但只是个支持者而非活动家,她不愿在自己不完全了解的话题上发表意见,也不愿让这些政治议题占用科研时间。
霍奇金最初了解中国,和在牛津就读的廖鸿英有关。廖鸿英1905年生于福建长汀,1930年被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录取,学习化学。霍奇金比廖鸿英小五岁,但高两个年级,经常为廖鸿英辅导功课。廖鸿英思想左翼,多次向霍奇金表达了自己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祖国的渴望,霍奇金深受感动,还通过廖鸿英与伦敦的英中友好组织联系,考虑过毕业后到中国去工作([1],页327)。廖鸿英活跃于英中友好协会(British-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BCFA)和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SACU),凭借和廖鸿英的交情还有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关系,霍奇金获得了首次访华的机会。
2. 霍奇金造访中国
1959年,中国希望英国组织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学术代表团,前往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英中友好协会应中国驻伦敦临时代办处之邀,帮助确定人选。友协主席李约瑟、友协艺术与科学委员会成员比尔·皮里(Bill Pirie)都与霍奇金相识。由于皇家学会会长恒兴伍德(Cyril Hinshelwood)另有日程而谢绝邀请,访华代表团名单中霍奇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廖鸿英和丈夫作为代表团的翻译。这次访问给霍奇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页328)。访问期间,霍奇金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北京大学作了关于测定维生素B12晶体结构的报告,维生素B12是当时世界上已经测定的、最复杂的晶体结构,其不对称单位含有90多个原子(不算氢原子)。霍奇金的研究小组历时7年完成了这一结构的测定,并凭借这项成果以及青霉素等重要的晶体结构测定工作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3]。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运动,我国提出要开展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并于1959年1月正式启动,霍奇金在访华期间得知了这一消息。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科技交流也陷入低潮,中方开始更多谋求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交往。1962年9月22—10月7日,皇家学会副会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率五人代表团访华,与中科院就中英科研人员互访问题展开了座谈,双方达成了科技交流的口头协议[4]。1965年,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邀请霍奇金去日本作为期两周的讲座,当时要在东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英国文化展,她的讲座是活动的一部分。霍奇金希望可以在归途中顺便访问中国。在中科院和皇家学会的努力下,她顺利获得了访华资助和邀请信([1],页331)。霍奇金抵达上海时,王应睐和同事们已经成功合成了牛胰岛素。她知道除了中国人之外,美国匹兹堡由帕纳约蒂斯·卡索亚尼斯(Panayotir Katsoyannis)领导的小组,以及德国亚琛由赫尔穆特·察恩(Helmut Zahn)领导的小组,都在尝试合成胰岛素。但三国都尚未成功取得结晶。因而她鼓励中国的研究人员再接再厉取得结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用X射线衍射分析的方法测定人工及天然胰岛素的空间结构,并提出可以在后一项工作上和中国同行展开合作([1],页332)。但她的热情并未获得积极响应,当时“阶级斗争”处于紧张状态,不难理解中国研究人员会果断拒绝与“资产阶级学者”合作,坚持独立完成相关任务[5]。
3. 霍奇金与中国胰岛素研究小组成员
在访华前,霍奇金已经和中国科学家建立了一些私人联系。1947年,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的唐有祺,当时正在美国跟随结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从事X射线晶体学等研究,他和霍奇金初次见面是在帕萨迪纳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会场成群的美国人中,他和霍奇金是仅有的两名外国人,霍奇金又是唯一的女性,因此引起了唐有祺的注意,但是彼此没有更多交流。1951年唐有祺从美国绕道欧洲回国,埃迪·休斯(Eddie Hughes)鼓励他去拜访一些英国晶体学家,因此唐有祺到牛津大学拜访了霍奇金([1],页329)。1959年霍奇金来华,随后受邀到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唐有祺担任她的翻译,两人因此建立起了联系。唐有祺不仅是我国开展晶体结构测序项目的提出者,也是日后中国参加国际晶体学大会的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霍奇金给予了他很多帮助。
同时,霍奇金也是中国晶体研究小组另一位重要成员梁栋材的导师。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65年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当年我国向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派遣了50名自然科学学科的留学生。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梁栋材被派往英国访问,起初在皇家研究院跟随查尔斯·布恩(Charles Bunn)工作,后来转到牛津大学霍奇金的胰岛素研究小组,实验室小组成员还有汤姆·布伦德尔(Tom Blundell)、盖·道森(Guy Dodson)等人。在霍奇金的指导下,梁栋材展开了蛋白质结构确定、晶体培养、制备重原子衍生物等工作,此前梁栋材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并没有基础,因而霍奇金可以称为他在蛋白质晶体学领域的“领路人”([1],页334)。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自1962年中科院与皇家学会达成口头协议以来建立起的中英科技交流关系难以为继。“文革”爆发当年,霍奇金尝试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在埃克塞特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并提出由她个人出资为中国科学家支付旅费,被中国科学院谢绝[6]。教育部于1967年1月18日发出《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在中国大使馆立刻回国的命令下,梁栋材在牛津的逗留期限缩短,于1967年初回国,随即加入胰岛素结构测定项目([1],页334;[7],页50)。这段牛津岁月令霍奇金与梁栋材建立起友谊,两人此后有很多通信往来。
我国成功合成人工牛胰岛素之后,针对下一步要进行的研究工作展开了讨论。1966年4月举行的人工合成胰岛素鉴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受霍奇金建议的影响,唐有祺提出下一步可以进行胰岛素晶体空间结构的测定,这一提议得到上级重视并最终落实。唐有祺为该项目的学术负责人,梁栋材也是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1979年以前,中国科学家不允许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由中科院主办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在“文革”开始后停刊长达7年之久,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强烈要求下,于1973年2月复刊,分中文和外文两种版本在国内外公开发行[8]。而在这段无法了解中国科研工作的时间里,霍奇金想要跟进中国胰岛素研究的进展只能积极争取访华的机会。
二 友谊的发展
1. 1972年的破冰之旅
“文革”爆发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香港爆发的“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在华英国人被当作间谍遭到关押等,对中英关系固然造成了破坏,对英国左翼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引发了其内部的一些分歧,但他们获得中国国内新闻的手段和来源也非常有限[9]。而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令中英两国改善双边关系迎来契机,皇家学会在这时也努力谋求恢复交流。1971年4月5日,国务院对外交部和中科院联合提交的有关“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人希望恢复中英科技文化交流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函中,对英方提出的互访问题原则上表示同意,“文革”以来中断的交往得以恢复,英国左派怀着对“文革”期间中国发生的变化和科研工作进展的好奇心再次来到中国,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访华的英国人。
得益于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政治挂帅,其后续的晶体结构测序项目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保留了下来。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顾孝诚回忆:政府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也要继续进行一些基础研究,以表示我们对促进基础发展高度重视”[6]。晶体结构测序使用市场上购得的猪胰岛素样品做试验,使用的第一批晶体是参照霍奇金小组已发表的胰岛素结晶条件。由于缺少蛋白质结晶经验,当时采用的是与处理小分子类似的大容量结晶方法,这批晶体在鉴定胰岛素重原子衍生物中发挥了作用。梁栋材从英国回来后,小组则改用他传授的微量生长晶体法([10],页134—135)。
霍奇金小组的胰岛素结构测定工作开始于1934年,到1969年完成了2.8Å分辨率的胰岛素三方二锌晶体结构测定工作。而中国胰岛素研究小组采取特殊的“大协作”方式开展研究,同时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财力物力支持,经过4年的努力完成了猪胰岛素结构测定,于1971年6月得到了2.5Å分辨率的测定结果。霍奇金得知这个消息时,刚结束对越南的一次访问。国际晶体学大会将于次年在京都举行,她刚被提名为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主席。她擅长最大限度利用各种官方出差机会,于是计划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安排一次北京之行([1],页335;[5])。同年11月,霍奇金致信梁栋材,附带英国胰岛素研究方面的资料,提出与中国进行交换。此时梁栋材已下放广东,信件并未交到他本人手里。1972年物理所业务组致院外事组的函中谈到以下几点考虑:由于中国2.5Å的工作成果尚未发表,而霍奇金在信中提到英国即将完成1.9Å分辨率的工作,因而决定拖延复信时间到1972年5月,等得到1.8Å分辨率的成果后再与英国交换图纸、样品。回信由外事组替梁栋材代笔,称近几个月在南方出差,未及时回信[11—13]。1972年8月,霍奇金终于得以再次访问中国。
中科院与皇家学会恢复交往对双方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皇家学会根据中科院复信的语气感觉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呈现出比以前更开放宽容的姿态,对访客人数和背景的严格限制仍然存在,这将导致真正的科技层面的交流难以进行。为得到中方的批准,恢复之初只能派出受中国欢迎的左翼科学家访华,曼德逊(Kurt Mendelssohn)、李约瑟是恢复访华后最先来华的两位英国科学家,但根据皇家学会的资料,皇家学会这一时期并不想再向曼德逊或李约瑟提供资金,因为他们更想把钱真正花在科技层面,而非政治层面上。在这种情形下,1972年5月,皇家学会会长艾伦·霍奇金(Alan Hodgkin)(1)多萝西·霍奇金为艾伦·霍奇金堂兄的妻子,下文霍奇金均指多萝西·霍奇金。等率代表团访问,多次谈及多萝西·霍奇金访华事宜,这一方面符合她本人的意愿,一方面也使得双方的交流能够真正触及科学层面,被皇家学会称为“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现有友好联系”[14—15]。
霍奇金这次访华最主要的目的是跟进中国取得的进展,在北京物理所她将自己携带的胰岛素电子密度图和中国的进行比对,之后又去往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由中方组织参观了干校、公社,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情况。霍奇金也担心着旧友在“文革”中的遭遇。在霍奇金致秦力生的函中谈到,她此次访华希望能见到梁栋材、唐有祺和周培源。但是在之后中方的访问简报中提到要求会见“唐有祺、周培源和吴世昌”[16]。梁栋材因曾先后在苏联科学院、牛津大学霍奇金实验室学习,所以在“文革”中既是苏联修正主义也是西方帝国主义,被下放到他的老家广东。这次霍奇金访华,他被临时召回与她会面,但对于自己已不再研究胰岛素一事,梁栋材回忆说“实在无法向她说出口”。8月23日,霍奇金结束在中国的行程,前往日本参加第九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在大会上向国际晶体学界介绍了她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访问,让世界首次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在胰岛素方面的研究结果[17],普渡大学的迈克尔·罗斯曼(Michael Rossmann)说:“如果不是多萝西·霍奇金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相信。”[18]
1974年,中国研究小组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l.8Å的胰岛素分子的精细结构,上海研究组则报道了胰岛素和胰岛素衍生物与其受体相互作用的文章。次年,小组成员惊讶地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读到霍奇金发表的“中国的胰岛素研究”(Chinese work on insulin)一文。《中国科学》虽已于1973年复刊,是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但在国际科学界仍鲜为人知[17]。霍奇金的这篇文章,对中国已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概述,同时谈到中国这项工作并非只是不同国家同步进行的重复性工作,而是发挥了独特作用。这种作用总结来说有两点:一方面,从两个角度来看胰岛素晶体结构有很大帮助。当霍奇金和中国研究小组比较原子坐标时,对英方的操作是一种全面的交叉检查;此外,中国的研究结果与英方相似,但添加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细节,也识别出几个完全不同的特征[19]。事实上,客观评价中国胰岛素方面的成就,可以看到它仍然是使用西方方法和仪器来解决的一个计算量极大的工程性难题,原创价值不高,而且在时间上也居于霍奇金小组之后,“大协作”科研方式的背后是国家行为,区别于国外研究小组寥寥数人的努力成果[5]。而霍奇金以一种谦逊和鼓励的姿态为世界了解中国晶体研究、打破中国与外界的隔绝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2. 霍奇金与后续中英晶体学交流
在霍奇金的带动下,更多英国晶体学家、研究人员来到中国访学。1977年12月,霍奇金再次访华,同行的还有曾与梁栋材一同在实验室工作的道森,这次访华他们参观了上海生物化学所等单位,接待人员包括梁栋材、顾孝诚、唐有祺等。在生化所,中方研究人员介绍了包括胰岛素结构功能及作用原理、多肽激素应用、蛋白质合成方法以及烟草花叶病毒蛋白外壳的合成等工作。霍奇金和道森则分别介绍了英国进行的1.5Å分辨率胰岛素晶体结构、4锌和2锌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比较及八目鳗胰岛素晶体结构。霍奇金希望中国派人去英国学习,并说虽然她要退休了,但仍可代表其他人表示欢迎[20]。道森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这次访华以及和中国的交往,文中写到:“通过对两国最新的胰岛素晶体衍射数据的比较表明,这两个独立得出的结果在细节上是相同的……从中国研究人员身上能看到他们对晶体结构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21]
1980年11月24日,霍奇金又一次来到北京,同行者是布伦德尔。此次访华由生物物理所、上海生化所、北大化学系、生物系等接待,他们的任务包括讲学和指导试验工作,围绕胰岛素结构、X射线衍射做了6个报告。根据霍奇金的建议,梁栋材还邀请了也在高分辨率上分析胰岛素结构的、来自日本名古屋的Sakabe教授夫妇,三个小组齐聚北京讨论胰岛素的精细结构[17]。中英两个实验室各自独立得到的电子密度图,通过精化和修正而达到高分辨率上的完全吻合,说明这种提高分辨率和精化结构的方法是十分可靠的,而对方法的检验也是对蛋白质晶体学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米切尔·刘易斯(Mitchell Lewis)回忆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时,霍奇金会鼓励年轻科学家去北京访学[22]。牛津大学研究生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北京梁栋材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斯图尔特在他的文章中谈到:“通过霍奇金在中国的交往,以及她和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在英国的努力,1981—1983年我得以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中国研究胰岛素结构。牛津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和中国的结构生物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一联系的建立直接归功于霍奇金。”[23]
1982年7月,生物化学学会第600次会议在牛津大学举行,同时还举办了中英生物化学学会联合学术讨论会,王应睐、张友尚等赴英国参会,霍奇金是会议的首位发言人。大会上,她以中英生物化学领域的友谊和中国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的贡献作为开场白,作了题为“胰岛素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报告[24]。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访问中国,在访华前的采访中,当问及“如何评价过去几年中英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发展”时,撒切尔夫人谈到科学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中科院与皇家学会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有益的联系,而这次访华她将前往上海的一家研究机构。这家研究机构正是霍奇金多次访问过的上海生化所。撒切尔夫人青年时代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化学并做过4年化学研究,霍奇金是她的老师。参观结束后撒切尔夫人邀请中国科学家合影留念,并欢迎他们今后到英国访问。
1985年,霍奇金在道森的陪同下第六次访华。这一次是将中国1.2Å分辨率的电子密度图与牛津小组l.5Å的图做比较,两组图再次呈现高度吻合[17]。此后,上海生化所和道森所在的约克大学在胰岛素结构研究方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如pH引起的结构变化及其形成原纤维的能力问题,张有尚和约克大学的让·惠廷汉姆(Jean Whittingham)通过合作研究在极低pH条件下生长的天然、单体和单链胰岛素晶体的结构来捕捉分子的展开;晶体结构测定方法方面,约克大学的伍尔夫森和以范海福为首的中国晶体学家开展了长期合作。这些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1世纪[21]。
三 霍奇金与中国参加国际晶体学大会(IUCr)
1. 1978年国际晶体学大会
国际晶体学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IUCr)成立于1948年,同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大会,此后每三年召开一次。霍奇金是此事的积极倡导者,成立学会的想法也得到了世界各国晶体学家的普遍支持。它的成立对战后重建科学联系、交流研究前沿提供了机遇,此后虽然冷战氛围席卷全球,但学会成立之初的国际精神仍能得到保留[25—26]。1956年中国受邀参加次年举办的第四次会议,原本已准备参会,但发现参会人员中有台湾代表而拒绝了邀请。1966年因“文革”进入高潮而拒绝参加当年举办的第七次会议,1972年“文革”尚未结束,参会邀请再次被拒绝。1972—1975年,IUCr主席一职由霍奇金担任,对她来说,中国的缺席是一个遗憾,她虽有一定影响力,但也无法说服中国加入[25]。
1978年,霍奇金再次向中国发出邀请,此时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均已好转,中国也与英国签订了正式的科技交流协议。8月2日,中国代表团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参加第十一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并在会议期间递交了由秦力生秘书长签字的“中国晶体学国家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申请书。代表团由唐有祺率领,成员包括黄金陵、章元龙、梁敬魁、顾孝诚、何崇藩、范海福、林政炯、陈创天和杨翠英([27],页62)。在中国展讲台前,中国代表团展出的科学论文和实物模型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广泛兴趣。这次大会中国代表共提交了9篇论文,3篇关于结构测定工作,1篇关于结构测定方法的研究,另外5篇介绍的是相变、薄膜、晶体生长和材料等方面的工作。中国10cm×10cm的云母单晶体,由于个体大、生长完整、结构无缺陷,尤其受到外国同行的重视([28],页190)。
8月3日下午开幕式结束,当晚第一项日程就是讨论接纳中国和埃及入会的问题。霍奇金向唐有祺解释了投票程序,还保证说中国一定会被接纳,结果也确实如此。事实上霍奇金此前在国际会议上的努力为我国顺利加入IUCr产生了很大帮助。顾孝诚回忆说:
我们都看到投票一致通过。我想如果没有她的介绍和努力,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在会上,我们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他们都向我们表示祝贺,许多人说“你们来得太迟了,早就该来,许多年前你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我们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研究小组,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最早是从多萝西那里听说的”。([1],页337)
霍奇金在把中国晶体学介绍给全世界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IUCr也成为当时中国加入的少数几个国际科学协会之一。
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于8月23至9月9日顺道赴英国访问17天。这次访问是由霍奇金委托皇家学会同中国驻英使馆安排的([27],页63)。之所以要顺访英国,唐有祺有着他自己的考虑:他到波兰后,发现波兰科学水平尚且一般,因此就想再去英国,了解英美科学发展的情况([28],页192)。代表团在英国先后访问了皇家学会、帝国学院、剑桥化学系以及英国医学会设在剑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应英方之请,唐有祺介绍了我国进行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的过程和情况。26日下午代表团一行来到约克大学,迈克尔·沃尔夫森(Michael Woolfson)和道森等来接站。沃尔夫森的一番话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他说:“在华沙刚见到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时,真的有点以为他们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但经过不断观察,知道他们与我们一样,也都是正常的人类一员。”经过十年“文革”的封闭,我国亟需恢复参与国际科技事务,重建理解与对话。之后沃尔夫森成为中国科学家的朋友,多次访华关心我国晶体学的发展,并与我国学者合作解决了直接法中的问题([27],页63)。此后,很多与霍奇金有着良好关系的实验室——牛津、剑桥、布里斯托尔、约克、达勒姆——也都与中国研究小组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1],页337])。
2. 中国申办第16届国际晶体学大会
加入IUCr后,每三年要参加一次大会。1984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三届大会上,唐有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则每年都要去欧洲(多半是英国)参加执委会年会([27],页10)。随着中国晶体学研究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国申请举办国际晶体学大会也提上了日程。但是中国在举办国际性会议方面还没有经验,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当时美国也在为举办大会做准备。唐有祺设想先举办一个小型国际会议作为尝试,因而在1986年举办了小分子结构会议。之所以选择小分子作为会议主题而不包括蛋白质等大分子,唐有祺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大分子研究当时在国际上并不突出,而小分子领域则更接近国际水平,于是先选择小分子试水,看看外国人的反应([28],页200—201)。1986年,首届“分子结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顺利举行,霍奇金参会。
1987年在澳大利亚珀斯召开的第14届大会上,唐有祺当选为IUCr副主席,在这届大会上,中国代表团与美国竞争1993年第16届大会的主办权([27],页10),这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科研工作尚处于恢复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挑战,但最终中国以压倒性票数胜出。这份胜利主要得益于英国在国际晶体学界的主导地位以及霍奇金在这一领域的权力与号召力。以下是唐有祺在访谈中谈到的内容:
反对派,国际上也有。那时要到某一个国家召开国际会议,没有美国的政治性同意是办不到的。而中国要得到美国的同意是很困难的,卡得很厉害。幸亏的是什么呢?学会活动的主要力量在欧洲。美国也是一个庞大力量,说话起很大作用,可是晶体学会在人数、学会数目、学科数目上,英国还是比美国强一点。第一、第二任的晶体学联合会主席都是英国人,晶体学会由英国主管,霍奇金在其中很有权力。要是没有这种关系,中国还是很难申请到主办权。特别是美国,不会让中国主办。([28],页204)
当时中国物理学会、化学学会尚且没有申请到过国际会议主办权,晶体学率先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再次陷入紧张。1989年7月在英国召开的年度执委会上,美国执委要求重议第16届大会主办权,唐有祺当时因签证问题,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与会执委最终通过决议,改由美国代替中国主办第16届大会。由于这一决定改变了第14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须经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才能生效。为此IUCr总部安排在1989年12月于伦敦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这次唐有祺一行人得以赴英国参会,在会上,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并努力做外国友人的工作,霍奇金在此时再次给予帮助,最终中国以22∶15的票数夺回主办权([28],页205—206)。
1993年5月,道森致电梁栋材,表示霍奇金希望来北京参加第16届国际晶体学大会。此时的霍奇金己83岁高龄,身体虚弱,卧床不起,中方非常担心炎热气候和长途跋涉对她身体的影响[17],但她坚持要来中国参会。在女儿的陪同下,她坐在轮椅上听报告、做采访,说话声音已十分细弱,但仍有着出色的记忆力。这是霍奇金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994年7月29日霍奇金在家中离世,结束了其奉献于科学的一生。
四 结语:英国左翼科学家与中国
霍奇金与中国结缘,她的左翼倾向起到很大作用,但并不是决定因素,跟进中国胰岛素研究进展是她的主要目的。根据布伦德尔的描述,“霍奇金将政治视为个体的个性,而非群体的信条或政治信念”[29]。这种认识在她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具体表现为人道主义同情和国际主义支持,而非为某个党派背书,包括她在国际科学界积极宣传中国成就,以及在帕格沃什会议上为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做出努力。她为人处事低调内敛,拒绝为自己贴上某种政治派别或社会运动的标签,使得她相对于贝尔纳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不仅能在西方科学界有一席之地,和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流关系,在苏联科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1982年被授予罗蒙诺索夫金奖章,1987年被授予列宁和平奖,是少数能够沟通东西方科学界的科学家之一。
放在中英科技交流的背景下,霍奇金也是一位重要人物,而不仅限于晶体学领域。霍奇金与中国的交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冷战为总体氛围,中间穿插了中国“文革”、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她和中国的交往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1972年,作为“文革”爆发后恢复中英科技交流的先行者,英国左翼对于重续中英友谊有着重要作用。“文革”不仅破坏中英关系,对英国左翼群体的态度也产生一定冲击,许多在中国的英国左翼分子都曾被处以某种形式的监禁,而英国左翼又缺少直接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渠道。但总的来说“文革”对英国“老”左派的态度影响较小[9],霍奇金和丈夫共同拥有的社会主义同情使他们对共产主义专政的缺点表示出某种程度的理解,左翼来华访问所获得的直观印象有助于打消神秘和外界的猜测。1978年以后,随着冷战氛围、政治思维的淡化,霍奇金与中国交往的作用则有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体现。
进一步将视角放大为中国对外科技交流的总体背景,仍然可以看到霍奇金个人在中国恢复参与国际科学事务上发挥的作用,具体体现为在中国自我封闭的时期扮演了传声器的角色,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科研工作的成绩;在中国恢复正常科研工作之初,帮助中国重新参与国际科学事务,这些主要得益于她在国际科学界享有的地位,英国晶体学在国际上也有话语权与美国抗衡。总的来说,霍奇金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始终给予了一种朴实的关切,中国蛋白质研究也得益于其附带的政治价值而成为“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为数不多取得成就的基础研究,内部、外部双重因素使得中国蛋白质研究虽历经数次政治运动,但在此期间仍能保持零星的国际交流,获得一定的国际前沿信息,1978年后中国蛋白质研究也顺利、迅速地重返国际舞台,与国际科学界没有出现过大的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