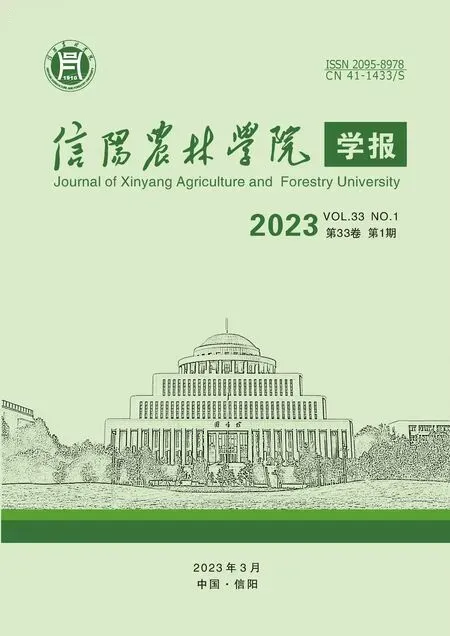“双重意识”下的困境与超越
——文化身份视域下《尼克尔男孩》的解读
乔昊阳
(新疆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1969-),当代美国文坛新贵,自1999年初涉文坛以来佳作迭出,获奖无数,备受赞誉。先后凭借《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和《尼克尔男孩》(The Nickel Boys,2019)两度摘得普利策文学奖桂冠。本文聚焦的正是怀特黑德继《地下铁道》后重探种族主义的历史之作——《尼克尔男孩》。该作延续了作家对非裔群体的政治关切,聚焦美国吉姆·克劳时期一所存在真实原型的工读学校——尼克尔学校,将矛头指向了伪善且充满隐性暴力的吉姆·克劳法。小说中主要人物心灵所遭受的“双重意识”的拉扯与撕裂,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张力,不仅促进了主角身份的流动与动态建构,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还构成了对美国非裔群体文化身份认同困惑的恰当隐喻。
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1]37,它关涉“我是谁?”“我与什么认同?”等问题,是某一个体乃至族群界定自身文化的标志与安身立命之根本。对该议题的哲学思考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从笛卡尔、黑格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纯思自我到马克思、阿尔都塞等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存在起决定作用的个人与社会交互下的自我认同,再到德里达、拉康、褔柯等去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身份认同[1]38-40:对身份认同的思索可谓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特别是在当今文化多元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对身份的探寻愈显意义重大。恰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言,此时“人类可能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我们是谁?”[2]。
然而目前对该小说的研究多集中于主旨意蕴与叙事特点,如,Kpohoue等(2020)对其所揭露美国制度化种族主义的批判,对“后种族主义”语境下面对种族问题的乐观与悲观态度的辨析(梁会莹,2022),以及黄子夜(2022)、Martín-Salván(2021)等对小说监禁叙事的研究等。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说人物的内心体验,特别是美国非裔群体特有的身份焦虑。本文拟从文化身份视角切入,探究《尼克尔男孩》中主角受“双重意识”影响下的身份危机与重建过程,旨在窥见在所谓后种族主义时代的当下美国非裔人民的真实生存体验,进而为多元文化冲击下的身份建构提供启示。
1 《尼克尔男孩》与“双重意识”
小说《尼克尔男孩》由两条平行而又不时交叉的叙事线索交替推进,聚焦两位非裔主角埃尔伍德·柯提斯与杰克·特纳的人生经历,在时空交错之中为读者呈现了种族主义肆虐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美国社会图景。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腹地——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某黑人聚居区生活着一名黑人少年——埃尔伍德·柯提斯。他聪慧勤勉、乐观正直,高中毕业之际,以优异成绩获保送高校的宝贵机会。然而报到途中,他因误乘一辆被盗赃车,被诬为犯罪同伙,遂被判入臭名昭著的尼克尔学校(Nickel Academy)劳教,自此沦为一个卑贱如镍币的尼克尔男孩(the Nickel boys)。所幸,他在学校与另一黑人少年杰克·特纳结识,为其惨淡人生注入一丝微光。恰与埃尔伍德相反,特纳悲观厌世、得过且过。然而,看似差之千里的两人却能心意相通,成为不可割舍的命运共同体。在细腻生动又直击心灵的描写中,男孩们的命运牵动着读者的心,然而作者却忽然顿笔,尼克尔的艰辛劳教生涯在看似轻松温馨实则暗藏危机的圣诞之夜戛然而止。是夜,节日的灯火勾勒出“火箭”形状,而笼罩在漆黑夜色中的火箭却要“发往另一个看不见的黑暗星球”[3]106,预示着男孩们晦暗不明的前途……此时,笔锋突转,场景蓦地来到20年后的纽约,“埃尔伍德”化身“黑人精英”再度出场,出乎意外的转变令读者始料未及,不禁发问:另一男孩现在何处?命运又如何?随后,时空不断流转,视角不断切换,隐藏故事在“揭幕”式结构[4]中被逐渐披露,埋藏数十年的辛酸秘密与痛苦往事才缓缓暴露在阳光之下。
怀特黑德运用现实主义笔触,融合悬疑、惊悚、黑色幽默等元素,揭露了美国积重难返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化种族主义之下黑人的生存境遇。其中,黑人主角在“双重意识”作用下所遭受的身份认同危机正是美国万千黑人的真实写照,最终超越“双重意识”后的身份重建更可为当下文化夹缝中挣扎的人们提供借鉴、注入勇气。
“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起源于后殖民批评先驱、美国泛非运动创始人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他在1897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文章中率先提出该概念,并在其著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20)中做出进一步阐释:
黑人……在这个美洲世界上,生来就带着一幅帷幕,并且天赋着一种渗透的能力——这个世界不让他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永远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另外一个始终带有鄙薄和怜悯的感情观望着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奇特的。它是一个人老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双重的——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两种并存……的敌对意识,这身躯只是靠百折不挠的毅力,才没有分裂。[5]
杜波依斯所思考的“双重意识”被认为是对美国黑人尴尬身份最原初的认知。数字“七”和“两”生动表征出黑人盼望平等的外在渴望、与内心“黑—白”二元对立的对抗与碰撞[6]129。在他看来,黑人生来便是白人世界中无声无形的低劣他者,他们仅仅充当着白人身份建构的隐形参照系,也因此全然丧失了自主认同的机会与能力,只能通过白人的眼光被动地看待自己。这其中蕴含着承袭自黑格尔主奴辩证哲学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逻辑。深陷残酷的生存法则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型认同模式中的他们,只得被迫抛弃本民族属性,祈求白人世界的接纳,企图藉此摆脱被动的客体与他者身份。于是,他们一方面不得不与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主流文化相认同,另一方面,隐藏在他们意识深处或无意识中的黑人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其所接受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可以说黑人置身于美国社会之内但同时又被排斥在美国以WASP 为主流的社会之外,构成了西方白人世界中“他者”的奇异景观。
2 迎合、取悦与疏离、自憎——双重意识下的畸形心理
小说中,“双重意识”在两位主人公——埃尔伍德和特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们渴望尊严、平等,不满“白人至上”的社会秩序,希望能够作为黑人堂堂正正地存活于世;另一方面,受到白人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他们又无意识地顺从、取悦白人,排斥、疏远黑人同胞,表现出迎合、取悦与疏离、自憎交织的病态心理。
一反大众对非裔群体“野蛮”“愚笨”“懒惰”[7]的刻板印象,埃尔伍德勤恳能干、聪敏好学、锐意进取,尽管生长在保守的南方腹地,他始终与先进思想为伍,视种族崛起为己之责任。他将偶得的唱片《马丁·路德·金在锡安山》(Martin Luther King at Zion Hill)视作毕生珍宝。透过这张小小的唱片,他开启了启蒙之旅:认识到“黑人被白人犯下的奴隶制罪恶所毒害,又因隔离而饱受屈辱与压迫”[3]13,了解到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浪潮,同万千黑人同胞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自此,他成为金博士的忠实追随者,将其当做精神领袖,始终用其箴言作为最高行为准则来约束、激励自己。像金博士一样,他始终怀揣平权之梦并为之斗争:他盼望有朝一日黑人孩子能进入游乐场玩耍,“每当餐厅旋转门开启时,他就打赌里面坐着黑人顾客”[3]19,他会将二手课本上白人学生写下的恶毒咒骂之词个个抹除,也曾连续三年孜孜不倦地在解放日演出中扮演托马斯·杰克逊(解放塔拉哈西黑奴的美国内战南军名将),甚至积极投身于镇上的民权抗议浪潮中。
然而,另一重意识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似乎在双重意识的争夺中更占上风。首先,两位主人公都有长期为白人雇主(主顾)服务的经历。埃尔伍德曾先后为白人开办的里士满酒店和马可尼烟草商店效劳,特纳亦曾在保龄球馆向白人顾客献媚,而在尼克尔,二人又一同为校董事会成员(白人)做“社区服务”。进入尼克尔前,埃尔伍德便是白人雇主眼中的模范黑人员工代表。他自小随外祖母在里士满酒店帮工,是后厨的得力助手。经理帕克先生早早相中了他“不同于同龄黑人孩子”的“勤奋天性与沉稳性格”[3]19,想尽快将其纳入麾下。然而,就在其即将成为家族第四代里士满酒店员工之际,另一白人雇主马可尼先生捷足先登,雇佣其为烟草商店店员。在新岗位上,埃尔伍德愈发兢兢业业,甚至潜移默化了白人的利益与立场。例如,黑人孩子会在商店偷拿糖果,马可尼先生出于经营策略,一直持默许态度。尽管往常埃尔伍德亦司空见惯,然而成为店员的他却对昔日同伴不依不饶、咄咄相逼。甚至入校劳教期间,在首次遭受毒打虐待后,虽然对学校非人的制度深感不满,却决心加倍努力工作,顺从白人意志、规则,用优异的成绩和快速的晋升证明自己,甚至以此表达“抗争”:
我被困在这里,但我会拼尽全力……我要缩短劳教时间。家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平和、可靠之人——尼克尔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他要问戴斯蒙德要多少分才能突破“初学者”(尼克尔为学生设置的最低等级),多数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升级、毕业。然后他会以两倍的速度完成。这就是他的抗争。[3]19
特纳早期在坦帕市“假日球馆”保龄球俱乐部作球童的经历更加凸显了白人意识的压倒性影响。在这里,他要做的只有两件事:“像打猎的狗一样”[3]77蹲伏在一旁等待为客人捡球;和白人主顾插科打诨(shucking and jiving),博人欢心以赚取小费。他整日嘻皮涎脸地周旋于白人顾客之间,“当他们犯规时,他开开玩笑,当他们投出洗沟球或技术球时,他就扮个鬼脸”[3]78。他这般有辱尊严的行为,甚至引起一位老年员工的鄙夷,老年员工曾经嫌恶地质问:“难道没人教你自尊吗?”[3]78然而,彼时一心谋生的他对此毫无感觉,甚至一无所知。可见,在白人意识和生存法则的双重压迫下,为求获得一丝微弱的怜悯与施舍,特纳或有意或无意地矮化、物化自己,使自己成为供白人顾客取笑、玩乐的“玩物”,这正是自我憎恨、自我抛弃的病态心理之行为表征。
这种畸形心理恰恰是黑人所内化的白人目光、白人意志作祟的结果。正如褔柯所说,“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权力的效应”[8],即对白人权力的服从和对黑人自我的否定。以白人为权力中心的美国早已沦为一座巨型“全景敞视监狱”,在充满规训力量的视觉暴力下,“卑贱和屈辱感被白人的眼光刻写进黑人的身体,内化到黑人的自我意识中”[9]。于是,黑人不断通过内化的白人视角看待自我,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对种族和个人的自我仇恨、自我抛弃以及罪恶感、羞辱感等不良心理[10],彻底堕为白人整体化规训力量的俘虏。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定义“自我憎恨”(self-hatred)为:“一个人为自己有所属群体中为人鄙夷的特质而感到耻辱——无论这些特质是真实存在还是无稽之谈。……(也)用于对自己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憎恶,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质。”[11]托马斯·斯劳特(Thomas Slaughter)生动描述了这种感觉:“在种族专制的压迫下,我经历着一种熟悉的双重过程,即外部强加的低劣化和对这种低劣的内化……我把白人对我的仇恨带入内心,仿佛自己的属性一样。”[12]
身为跨入中上阶级的“黑人精英”,发迹后的特纳对底层黑人鄙夷又排斥的心理,既是这种自我憎恨的具象化,又体现出同黑人同胞心灵上的疏离。这点在其与前“尼克尔男孩”奇奇·皮特互动时的所作所思中可见一斑。在纽约打拼的数十年里,特纳离群索居,极力避免与昔日同学碰面,一方面是由于回忆带来的创伤之深切,使他不堪面对过往的人与事;另一方面是因为立志(或已然)成为精英阶层一员的他有意无意与种族内部的底层群体划清界限。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一个冬日的傍晚,特纳在观看完马拉松比赛后与奇奇偶遇——这是他离校后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尼克尔男孩”之一。奇奇是个落魄潦倒的苦命黑人,在特纳看来,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穿着滑稽邋遢,言行粗野低俗,更有为瘾君子之嫌,这让他“怒火中烧,甚至想着这般蠢货尚苟活于世,为何他的朋友却已不再”[3]132。基于此般成见,他难掩身为精英阶层的优越之感和对底层群体的厌恶鄙弃。在被邀请小酌时,万般不情愿的他不得不自我安慰道,“或许在马拉松比赛后,要接受一场对同胞的‘善意考验’”[3]128,这种施舍般的态度将特纳的高傲体现得淋漓尽致,无形中加深了二者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群体心灵间的沟壑。在奇奇向其索要名片,期待谋得一份工作时,出于对他的不信任,特纳虽下意识“伸手掏钱包找名片——‘顶尖搬家公司总裁·XX先生’”[3]132,却谎称“没带”而婉拒。最终,虽勉强收下写有其联系方式的餐巾,却在分别后依然不停嘲讽并“将那方红色餐巾撕碎,扔到窗外”[3]133。这一小小举动不仅斩断了奇奇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封堵了他难得的改善生活的路径,也割裂了身为黑人精英的特纳与黑人社区的联结。更有甚者,特纳居然用一句“没人会喜欢一只垃圾虫”[4]133为自己开脱,认为他不过顺应了一场成功的“城市生活质量提高运动”[3]133。这句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的话语,从侧面表明他已深深融入了白人价值体系。
特纳此般心理和行为在美国黑人精英群体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民权运动后,获得良好教育和体面职业的新一代“黑人精英”纷纷由黑人区迁入白人区,努力表现为主流“美国人”而非“美国黑人”。他们已然实现“美国梦”,认同美国精神,思想上彻底转型为美国“国家精英”,更被形象地戏称为“黑皮白心”。其中不少人与黑人底层社区保持距离,避免被看作“黑人代表人物”,甚至抱有对其种族的负面刻板印象。调查表明,认为“黑人富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的比例在白人被访者中占52%,而在黑人被访者中则达59%;认为“黑人生性懒惰”者在白人中占比为34%,而持此观点的黑人为 39%[13]。可见,“当问题涉及黑人整体是否具有讨厌的社会特性时”,黑人“总是表现出比白人更为负面的评价”[14]。可知,像特纳一般的黑人精英人士,受白人意识影响,不但在地理空间上脱离了黑人社区,而且在情感上也与他们渐行渐远。
3 破除对立,合二为一——身份的回归与超越
小说正文在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中结束:深夜的草场上,两个黑人男孩在万分惊恐中狂奔——正是埃尔伍德与特纳。寂静的黑夜里,喘息声格外清晰,突然,枪声响起,埃尔伍德双臂大张,踉跄着栽进草丛。在状似百余年前“逃奴猎手”追击逃亡黑奴的场景中,故事达到高潮也进入尾声——在最为紧张、刺激的时刻一切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待解的谜团与依稀可见的答案。埃尔伍德是否不幸丧生?既然特纳侥幸逃脱,又为何“消失不见”?
小说后记拨开了萦绕读者心头的迷雾,也揭开了特纳长达50年的“替身(Doppelgänger)”生涯所造成的身份窘境。如学者于雷所言,(当下)“替身”形象旨在揭示独特语境下“人物所面临的伦理焦虑与混沌”与“包藏于作品本身的潜在政治意识”,特别是对“性别、种族等政治问题”进行“寓言式解构”[15]。特纳个人身份的“双重性”及错位、割裂之感亦构成了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困境的恰如其分的隐喻。
原来,在逃出生天后,为纪念亡友,又为掩人耳目,特纳“盗用”埃尔伍德的身份,辗转各地、打拼生计,“为他而活”[4]162。在长达50年的时间(1964—2014)里,他一直戴着“埃尔伍德·柯蒂斯”的假面生活,始终用好友高尚的道德标准引导、约束自己,最终如愿地“成长为他认为埃尔伍德会为之骄傲的人”[3]162;甚至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复述、演绎埃尔伍德的故事,将自己由内而外塑造成了他的完美替身。然而,长期的身份错位与内在割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特纳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恐慌。特纳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埃尔伍德的亡者面具之下,甚至当他“在日头底下走过百老汇大街时,在漫漫长夜的尽头伏案读书时”[3]162,亡友的声音都会不时在脑海中回荡。
然而一切却在几十年后的2014年,开始全面崩塌。2014年作为尼克尔学校暴行的亲历者及受害者亲友,特纳不顾其通缉犯身份,毅然重返塔拉哈西、重返尼克尔学校,为官方调查举证。在此,特纳故地重游,来到尼克尔的校园,但当他翻过围墙、穿过草场、来到那片熟悉的树林时,不禁发现“两个男孩都已消失不见”[3]162。曾几何时,他利用埃尔伍德的身份重获新生,而此时此刻,当他真真切切地站在此处,才恍然发现这一身份早已和他的肉体一同被埋葬、消亡——他的面具脱落了。此时,双重身份的撕裂与拉扯骤然转化为“丧失”身份的不安与迷茫,一种虚无感充斥着内心,他不得不在妻子的一声声“杰克、杰克”的呼唤中,在相互蜷缩、依偎中捕捉一抹真实的余晖。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特纳看似丢失了身份面具,却实则摆脱了替身关系中傀儡般的客体处境,而这种尴尬处境正是造成他数十年身份困窘的祸首之一。在经历了面具剥脱的短暂阵痛后,特纳以“杰克·特纳”的身份重生、崛起,以最为本真的面貌,堂堂正正地站在世人面前。也就是说,特纳恰恰于身份的打破中,实现了身份的重建,这其中所蕴含的微妙的悖论式逻辑可谓耐人寻味。此刻,他不再徘徊、摇摆于他与埃尔伍德所形成的“双重意识”之间,而是在吸纳了亡友宝贵品质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个人身份的超越式回归。这也象征着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黑人文化身份于“混杂”中的复归。
重获“杰克·特纳”之名的特纳亦不再消极受制于(白人与他者)“双重意识”的控制,而是选择跨越种族主义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主动实现个人身份的“混杂性”重建与回归。他选择重返黑人群体,再一次与黑人同胞建立联结,直面、悦纳内心深处的黑人意识的同时,利用所谓白人意识而获得的话语权为广大黑人同胞争取权利——于“混杂”的“第三空间”为全体黑人发出正义之声。此时,怀揣着埃尔伍德与枉死同胞们的希望、信念的特纳,重返塔拉哈西,将“尼克尔男孩们”终其一生未能完成的夙愿付诸实现,向种族主义笼罩下的茫茫黑暗照入了一丝曦光。
特纳的行为恰恰是对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双重意识”认同思想的实践。吉尔罗伊认为,所谓“双重意识”间的对立关系,不过是种族主义话语的“精心安排”,使“这些身份认同貌似相互独立,占据彼此空间”,“试图呈现它们的连续性,被看成是一种政治反抗、挑衅甚至是对抗的行为”[16]1。他主张打破种族主义主奴二元对立的底层逻辑,颠覆人类学传统中的本质主义,推崇以运动性、相互关联性和混合参考性为特点且更具内在颠覆力与能动性的“混杂”模式。相较杜波依斯,他倾向从更为全面、辩证的积极意义上阐释“双重意识”认同模式之内核,突显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未完成性、开放性和包容性”[6]131。他把“双重意识”建构成“黑色大西洋”时空意识中的一种跨民族、跨文明的认知之旅,“蕴含在多重杂交混合而成的多元文化之中”[6]131,在无限的“第三空间”中充满着张力。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混杂”与“第三空间”理论。巴巴认为“在东方与西方、他者与白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地带——混杂的居中(第三)空间”[17]114,而“混杂”恰恰构成了使不同立场得以发声的“第三空间”。特纳于“第三空间”混杂中的身份重塑,蕴含着对白人中心话语建构性与虚假性的嘲弄,可谓颠覆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即如巴巴所言“逆转了殖民者的否认,”使“‘被否认的’知识进入了主宰话语并疏离了其权威基础”[17]112。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应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18]222。特纳一直行走在身份认同的旅途中,从抵触抗拒到深情相拥,从被动盲从到积极重建,终其半生,这场坎坷的认同之旅才告一段落。他终得在文化交汇、碰撞的浪潮中寻到恰当的文化定位,完成人格的健全和自我的重塑。他的文化身份重塑历程,何其艰辛又何其振奋,可为当下文化夹缝中挣扎的人们提供借鉴、注入勇气,进而在文明愈发多元化的现实语境中产生重要意义。
4 结语
故事的结尾,在塔拉哈西,特纳命运般巧合地下榻了埃尔伍德幼年时打工过的里士满酒店。在装潢一新的酒店中,虽然早已不见那个喜欢在后厨阅读冒险故事的男孩的身影,但此时此刻,特纳的身形与光影中的幼年埃尔伍德交叠在一起,这既是埃尔伍德信念与希望的重生,也是特纳丢掉面具、摆脱“双重意识”后个人身份的重生与个体生命的升华。这一刻,特纳怀抱着对所有“尼克尔男孩”、乃至所有黑人同胞未来命运的憧憬,恰如他所热爱的马拉松比赛那样,人们不分种族、不论贵贱,庆祝着漫长忍耐和痛苦后的胜利。这一结局留下无限遐想空间,无疑是小说最为高光的一笔,这其中饱含着对黑人心灵解放、重塑的美好祈愿,彰显了怀特黑德用文学关怀现实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