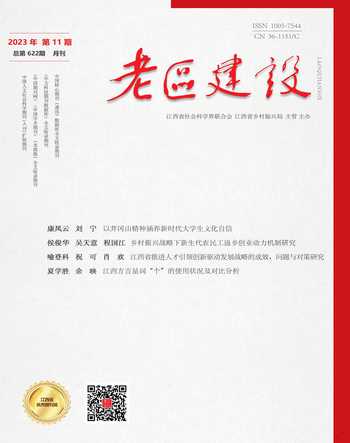江西方言量词“个”的使用状况及对比分析
夏学胜 余映



[摘 要]调查发现,江西方言中的量词“个”与其他个体量词存在混用及功能分化现象。“个”与“只”功能相近,在各地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其使用差异形成了各个区县、甚至各个乡镇的方言特色。“个”“根”“颗”“口”等可以统称为“个”系量词。它们在称量不同类型物品时混用,形成了一定的功能分化,同时,它们在各地方言的不同词音构成一个原型范畴,其各自的边缘成员存在重合。
[关键词]江西方言;“个”系量词;量词混用;演变分化
[中图分类号]H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544(2023)11-0063-11
[作者简介]夏学胜,江西农业大学讲师;
余映,江西农业大学讲师。
[基金项目]江西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袁州话词汇接触混用及其功能分化研究”(21YY06)
刘丹青认为汉语量词最本质的作用是个体化。[1]个体量词是量词研究关注的重点,其中“个”使用范围最广,以至于研究界曾出现了“个化”问题的讨论。戴婉莹认为“个化”是表量的个体量词发展的必然趋势,语言发展的趋势要求表量的个体量词趋向“个化”。[2]孙汝建提出“量词的所谓‘个化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存在的”,认为“个”在特定语体中使用时出现的高频率只能说明“个”的使用范围之广,而不能说明量词“个”能取代其他量词的地位。[3]这些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个”在量词中的重要地位。
量词“个化”是指现代汉语量词中具有相当强的量名组合功能的特殊量词“个”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泛化现象。[4]由此定义来看,“个化”问题研究需要历时较长的语言对比,但这个对比存在较大困难,因为仅依据现有文献很难全面反映汉语个体量词先前的使用状况。不过,如果对“个”进行大范围调查和共时对比分析,可以为量词各方面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本研究选用了100种日常物品,分出类别,调查它们在江西各地的量词使用状况,进而分析“个”在江西各地的使用状况。
一、江西方言量词“个”的使用状况
(一)量词“个”的地域分布
调查表明,同一物品在不同方言中使用的量詞会有不同;同一量词在不同方言中所称量的物品会有不同。量词“个”在江西各地方言中都存在,因地域不同,“个”所称量的物品种类的数量会有不同。比如,在宜春袁州竹亭镇所调查的100种物品中,使用“个”称量的只有4种,而使用“只”称量的有37种,其他物品则由近15个其他量词称量;赣州龙南汶龙镇调查到用“只”“个”称量的物品分别为19种、22种;九江彭泽棉船镇调查到41种物品使用“个”,而只有6种物品用“只”。本文将类似竹亭的“只”、棉船的“个”的量词称为强势个体量词。
江西西部、南部为“只”的强势区,东部、北部为“个”的强势区。其界线大约在抚州市与吉安市的交界及其延长线上,即在石城、宁都、永丰、新干、樟树、上高、高安、奉新、铜鼓所在地域及其以西以南的区域基本上是“只”强于“个”。在江西西部和南部“只”强于“个”的区域,仍然存在一些“个”强势的局部区域,包括以赣县区、信丰县、安远县、全南县、龙南县、定南等部分乡镇为中心地的辐射区。与之对应的是广昌、南丰、宜黄、乐安、丰城、高安、奉新、修水等地及其以东以北区域。在这些“个”强于“只”的区域,仍然存在一些“只”强势的局部区域,包括以南昌市、武宁县、都昌县、浮梁县、婺源县等地的部分乡镇为中心地的辐射区。总之,江西方言基本上呈现出“‘个中有‘只,‘只中有‘个,‘个‘只混用,相互间此消彼长”的态势。
在上图中,各区县在强势量词上总体存在差异,要么是“个”“只”的差异,要么是“个”或“只”不同词音的差异。一个量词的强势就意味着另一个量词的弱势。强弱更替间,地域方言的特点也就显现出来。图中的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域方言总是存在一些与临近地域不同的语言特点,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方言,从而具有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身份表征功能。图中的很多区域都与外省靠近,这些区域是否因与外省的情况相似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只”或“个”的强势使用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初步的调查表明,靠近赣东北的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也存在类似的“只”和“个”的强势区域。比如,福州话是典型的“隻”类方言,它兼有“隻”与“個”。[5]
(二)量词“个”在称量物品上的分布
由于量词“个”在江西西部、南部使用频率相对较低,本部分研究对象主要为赣北的九江市、南昌市和赣东北的上饶市、景德镇市、鹰潭市的方言。在所选用的100种物品中,两地五市所调查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使用“个”称量的较多是颗粒状物品、容器类物品,其次是条线状物品、编织类物品,最少的是块片状物品、动植物类。通过整理赣北232份、赣东北217份、赣西258份调查表,本研究发现两地不同物品在用“个”称量的频率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具体如图2所示。
以赣东北为参照系,依据所调查的特定物品使用“个”称量次数的高低进行排序,除篮球、药丸等少数物品在数量上有较大变化外,赣北所调查到的结果与前者基本一致。总体来看,在江西方言中,“个”更多用于称量篮球、包子、鸡蛋、南瓜、粽子、桔子、红薯、柚子、石头、茄子、枣子,有超过一半的调查表记录了“个”对这些物品的称量。“个”较少用于称量扣子、牙齿、豆子、药丸,用于称量棉花、泥巴、沙子、米的次数最少。赣西使用“个”的物品数量虽然相对更少,但图中曲线变化的弧度总体与赣北、赣东北保持一致。此外,赣西的“只”线与“个”线形成高低对称状况,即当包子、粽子、茄子等用“只”称量的物品数量较多时,用“个”称量的数量就会相应较少;当鸡蛋、篮球等用“个”称量的物品数量较多时,用“只”称量的就相应较少。赣西“只”的弧度也与其他三条“个”线保持大体一致。
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容器类物品的称量中。除碗、衣橱、棺材等少数物品外,赣北、赣东北两地用“个”称量容器类物品的频率总体一致。总体来看,“个”多用于称量衣橱、瓶子、箱子、酒壶、罐子、盆子、桶子、杯子、房子、盘碟、勺子、水缸、铁锅、碗,较少用于称量塘、车子、棺材、船、田、井等,具体如图3所示。
与赣东北、赣北相比,除碗、盘碟、船等少数物品外,赣西“只”的使用状况与赣北、赣东北基本相同。统计发现,在赣东北收集到的调查表中,有85份记录了“只”称量船、60份用“只”称量碗、35份用“只”称量盘碟。如果将“只”换用为“个”,那么赣东北的“个”与赣西的“只”就会更具有一致性。此外,在该地还有用“块”称量碗、盘碟的,用“张”“把”称量船、盘碟的。这些例子表明,方言量词并不都具有范畴化功能,并不都对被称量物品进行形状等方面的描述或分类。
在赣北、赣东北的调查表中,条线状物品大都可以使用“个”称量。钉子用“个”称量的在赣北调查到137次,在赣东北调查到136次。梯子用“个”称量的在赣北、赣东北分别为91、72次。锄头分别为84次、69次。秤分别为71次、71次。锯子分别为67次、62次。蜡烛分别为49次、54次。铲子分别为49次、52次。钥匙分别为43次、46次。木头分别为42次、47次。带子分别为42次、31次。剪子分别为39次、33次。卷烟分别为27、21次。针分别为25次、43次。筷子分别为20次、20次。尺分别为19次、30次。笔分别为17次、10次。伞分别为6次、7次。绳子分别为6次、7次。毛发分别为4次、4次。线分别为0次、3次。条线状物品中,除钉子外,其他物品用“个”称量的频率并非很高。这种情况在使用“只”更多的地域也是如此,以吉安市为例,在该地收集到的102份调查表中,有36份记录了用“只”称量梯子,其次是钉子、秤、蜡烛、锄头、桔子、钥匙、铲子、尺子、剪子、笔、卷烟,其他如针、筷子、伞、木头等则不超过10份,而线、毛发则为0份。相比于颗粒状物品、容器类物品,“个”“只”对条线状物品的称量都更少。
块片状物品更少用“个”称量。在赣北,只有鼓调查到40次用“个”称量,梳子调查到38次,凳子调查到36次,其他物品则大都只有十几次或几次。其中,布、瓦、床均只调查到1次,而皮、墙、纸没有调查到用“个”称量的情况。在“只”强势的吉安市,情况也大致相似。“只”称量最多的是鼓、凳子、梳子、桌子等,其他都不足10次,其中布、皮没有调查到。相比其他物品,块片状物品混用的量词数量最多。调查表明,属于衣物类的帽子、袋子、蚊帐等在赣北、赣东北调查到的数据都超过90次,属于高频使用“个”称量的物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强调容积的颗粒状物品。
在有生命的物体中,除人、白菜高频使用“个”称量,其他则很少。但王志芳引用的实例中有用“个”称量鹅、牛、驴等动物的[6];王彤伟列举了唐代用“個”称量竹、树的用例[7];王绍新举例证明了“个”在唐朝以前可称量蝼蛄、树、河神等动物,在唐时可称量马、猿、猫、狗、泥牛、白鹤、蛤蟆、蝉、蜣螂、鱼、蝴蝶等[8]。古代文献和作品对各地方言的记录不十分全面,现代的文献和作品也难说全部记录了各地方言量词的使用,因此大概率存在用“个”称量全部或绝大部分动植物的可能性。相对于“个”,“只”对动植物类的称量频率则高得多,以吉安吉水文峰镇为例,在10种动植物中,用“只”称量的就有8种。动植物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強调体积的颗粒状物品的次类。
在100类物品中,用“个”称量的次数在30次以下的有米、沙子、泥巴、棉花、衣服、裤子、裙子、猪、鸡、虫、牛、狗、蛇、线、绳子、笔、卷烟、尺、伞、毛发、筷子、船、井、田、叶子、布、皮、被子、镜子、墙、饼、砖、桌子、纸、毛巾、瓦、席子、扇子、门、书本、床等41种物品,其中线、叶子、布、皮、墙、纸、瓦在不足5份的调查表中被记录为用“个”称量。如果以上物品在今后的调查研究中可以被确证用“个”称量,那就意味着“个”有可能曾被用于称量所有物品,只是后来被其他量词在部分物品上取代,从而形成现今多量词混用的状况。“只”的情况也类似。
周芍认为,具象越清楚、外表特征越明显的,越倾向于使用特性量词;反之,越抽象越不具备外表特征的,就越倾向于与中性量词 “个”组合。[9]这个判断或结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在汉语个体量词出现的早期,其数量极少甚至只有一个(如“个”),它们的功能只是为了与其他非个体量词(如“双”、“斤”等)相区分,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出于诸如文学描写等各种可能的需要,量词开始获得功能的分化,出现用不同量词区分称量不同形状物品的状况。
二、量词“个”与其他量词的混用
(一)量词“个”与“颗”的混用
调查表明,量词“颗”“粒”“个”“只”等在江西各地方言中混用并发生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量词“颗”与“粒”主要用于称量较小的颗粒状物品,如米、沙子、药丸、豆子、扣子、牙齿、石头、枣子等;“个”与“只”主要用于称量较大的颗粒状物品,如篮球、包子、鸡蛋、南瓜、粽子、桔子、红薯、柚子等。
某些地域方言有“个”或“只”等,但无“颗”和“粒”,如上饶玉山六都、抚州临川上顿渡、赣州石城丰山等地的少数调查表没有调查到“颗”“粒”被使用的状况。有的地域方言有“粒”无“颗”,例如宜春袁州竹亭话、吉安青原富滩话、赣州上犹双溪话等。有的地域方言有“颗”无“粒”,例如赣州信丰的正平、嘉定、安西等地的调查表都没有记录到“粒”的使用。从目前的调查看,信丰县是江西境内“颗”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也是为数不多的“颗”使用频率高于“粒”的地方。在称量颗粒状物品时,江西方言总体状况是“个”“只”使用频率高于“颗”“粒”,“粒”的使用频率高于“颗”,具体如表1所示。
在称量物品上,“粒”更多称量米、沙等极小物品。物品越小,各地方言中用“粒”称量的可能性就越高,“粒”的使用频率与物品的体型大小总体呈反比。相比而言,“颗”则更少用于称量米、沙等物品,称量更多的是豆子、石头等物品,其称量的规律性远没有“粒”强,由于词音上它更接近“个”,因此有可能是“个”的一种演变形式。
(二)量词“个”与“口”的混用
量词“口”主要用于器皿类物品的称量,有少数用于动植物,还有极少数用于其他物品的称量。例如,在江西宜春袁州竹亭话中,“口”可以用于称量砖、瓦、镜子、钉子、针等,这些物品不是器皿,没有开口,其用“口”称量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江西方言中,量词“口”主要用于称量井、塘、棺材、水缸、铁锅、田等6种物品。这六种物品调查所得数据如表2所示。
以赣东北为例,调查表中记录了用“口”称量井、塘、棺材的最多,超过百份,其次为水缸、铁锅、田等超过50份,称量其他物品的则都不超过10份,其中碗有7份,桶子、船为6份,罐子、酒壶为5份,杯子为4份,盘碟为3份,衣橱、盆子、箱子、房屋为2份,瓶子为1份,勺子、车子为0份。具体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个”是容器类物品称量的主体,“口”在一定范围内对“个”形成使用上的补充,以至于可以看作是“个”的一种演变形式。相比来看,更多用“口”称量的井、塘、棺材、铁锅、水缸、田等一般是开口显著的大容器。
(三)量词“个”与“根”的混用
与颗粒状物品不同,条线状物品在江西方言中主要由“根”“把”等量词称量。量词“根”主要用于称量毛发、针、线等11种物品,其他物品则一般不超过10份。这11种物品调查所得的数据如表3所示。
以赣北为例,调查表中记录了用根称量毛发、针、线、绳子、木头、蜡烛、筷子的超百份,称量带子、卷烟、笔、针的超60份,称量其他物品的则都不超过10份,其中锄头有10份,秤有8份,尺为7份,钥匙为4份,剪子、锯子为2份,伞、铲子、梯子为1。量词“把”主要用于称量伞、剪子、尺等9种物品,其他物品则一般不超过10份。这9种物品调查所得得数据如表4所示。
从表4基本可以推断,江西方言在“把”的使用上整体上保持一致,不同地区在频率的高低上存在细微的差异。除了用“根”“把”称量,部分条线状物品在各地方言中还有用其他量词称量的记录,比如“条”“支”等,但这些总体占比不高,占比最高的主要是“根”“把”“个(只)”,具体情况如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在赣北方言中,条线状物品的称量主要呈现“‘根‘把分化对立,‘个分散称量全部”的态势。相比“根”“把”而言,“个”称量物品的面更广,几乎涵盖绝大多数条线状物品,虽然其出现频率比前两者要低。这些物品原本有可能都是用“个”称量,只是到后来,其中部分物品在有些地域方言中的称量演化为“根”“把”或被其替代,并且形成功能的分化。“根”一般用于称量毛发、针、线、绳子、木头、蜡烛、筷子、带子、卷烟、笔、钉子等形状规则、均匀细长的长条形物品;而“把”更多用于称量伞、剪子、尺、钥匙、铲子、锯子、锄头、梯子、秤等形状不规则、一般带有把手的、多用手进行操作的长条形工具。
三、量词“个”与其他量词的词音比较
(一)“个”与“根”“件”的比较分析
总结前文可以发现,“块”“颗”“口”在江西各地都存在相同词音的状况,且词音都与“个”保持强烈的对应性。具体如表5所示。
总体来看,在大多数江西方言中,“颗”“口”“块”一般都可视为量词“个”声母送气化的结果,其中“颗”与“个”关系最近,“口”“块”关系更远。与之相对应的是“根”“件”,在大多数江西方言中,它们的声母与“个”基本相同;除少数方言外,它们大多数带的是鼻音韵母,基本可以视为“个”的韵母鼻音化的结果。其中“根”与“个”关系更为接近,“件”可以视为“根”的进一步演化。“个”“颗”“口”“块”“根”“件”等可以统称为“个”系量词。
四、结语
本调查采用调查对象自主选择方言量词用字的做法,有的方言量词与普通话量词词音接近,所称量的物品相近,汉字选择相对容易,但在有些方言中,量词的词音变化较大,或者出现数个相近的音变形式,以至于无法参照普通话进行汉字选择。本调查采用调查对象自主记录词音的做法,但因为其没有经过系统的国际音标记音训练,其准确性存在一定问题,但基本能够反映出方言间的词音差异,拼音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汉字行使了量词书写功能。
刘丹青提出方言中的量词尚缺系统的调查研究。[11]系统研究需要大量的数据,本研究试图通过大量数据从宏观上获得方言量词的相关认识。
任何一个语言词汇系统都是从简单向复杂发展,汉语复杂的量词系统也大致如此。崔健把量词看作从集合中分离出个体或激活个体的手段。[12]这应该是个体量词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在汉语量词形成之初,汉语个体量词的数量应该是极少的,因为事实上只要一个这样的量词,汉语就能实现将个体与集合相区分的目的。如果从词音演变的角度去理解当今汉语方言复杂的量词使用状况,结合人口迁移、聚居等因素去分析,同时考虑汉字对方言量词的记录和推广功能,以及汉字字义对被称量物品的范畴化影响和汉字对语言更大范围的历时传播的影响,方言量词混用状况或许可以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刘丹青.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J].中国语文,2008,(1).
[2]戴婉莹.量词“个化”新议[J].汉语学习,1984,(1).
[3]孙汝建.关于量词“个化”论的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1).
[4]薛健.量词“个化”问题管见[J].汉语学报,2006,(5).
[5]陈泽平,秋谷裕幸.福州话的通用量词“隻”与“個”[J].方言,2008,(4).
[6]王志芳.量词“个”的使用泛化管见[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2).
[7]王彤偉.量词“个”及其字形“个、箇、個”的历时演变[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8]王绍新.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2).
[9]周芍.量词“个”与名词的组合倾向及中性选择机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1).
[10]余跃龙.山西晋语量词“个/块”的地理分布特征[J].汉语学报,2014,(4).
[11]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12]崔健.量词的功能差异和词类地位[J].汉语学习,2010,(6).
The Usag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Quantifier "ge" and Its Variants in Jiangxi Dialect
Xia Xuesheng Yu Ying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 quantifie“ge”(个) in Jiangxi dialects is mixed with its other variants in use and has a phenomenon of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 The functions of “ge”(个)and“zhi”(只)are similar, showing a trend of ups and down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use formed the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districts, counties, and even townships. “ge”(個), “gen”(根), “ke”(颗), “kou”(口), and other quantifiers, can b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ge” quantifiers. They are mixed when weighing different types of items, forming a certain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form a prototype category with different word sounds in different dialects, and their respective marginal members overlap.
Key words: Jiangxi dialects; Variants of “ge”(个); Mixture of quantifiers; Evol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责任编辑:严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