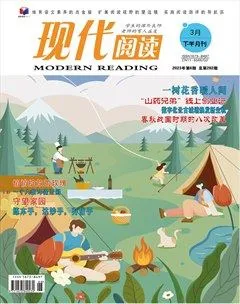烙馍与鏊子


在苏北,有一种美食叫烙馍,它是在鏊子上烙成的。小时候,家里主食以杂粮为主,只有客人来时才能吃上心仪的烙馍。奶奶是烙馍的一把好手,只见她先舀出一瓢面,倒入面盆,左手搅拌面粉,右手注水,不一会儿,一大块面团就成形了。水与面两种特性的事物,竟悄然融合了。面团和好后要醒一醒,然后用手掐出一个个小的面团,反复揉捏,团成球状,按成扁圆形,到这个时候,奶奶才会拿出跟随了她几十年的擀面杖。只见她左手揪着面饼的一边,右手搓着擀面杖,面饼在案板上匀速地转动起来,如同我用鞭子抽打几下后的陀螺有趣地舞动起来。就这样,烙馍有了最初的模样。木棍与面团,本来毫不相属的物品,成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有奶奶在,妈妈只有烧鏊子的份儿了。母亲早已架好了鏊子,它是用生铁铸成的,圆形,中间略鼓,呈锣状,有三足,这露天的锅灶,简单而有意蕴。母亲添上一堆柴火,烟呼地腾上来,小小的庭院里烟罩了一切。这也许是最原始、最朴素的埋锅造饭吧!我想炊烟袅袅也就是这时走进了旅人的诗句里,有了漂泊游子思乡曲的唱响。
奶奶用擀面杖将烙馍在鏊子上摊开来,待烙馍一面起了馍花儿和热气形成的鼓泡,再用一根扁竹坯子把它翻个个儿,继续煎烤另一面,这样一反一正,反复几次,很快一张烙馍就做好了。竹坯子一挑,一张烙馍优雅地落在竹筐里。我实在忍不住了,冒着被烫伤的危险,在烙馍上铺开炒好的辣椒,折叠上一端,卷起,大口嚼了起来。烙馍软柔劲道,薄而有韧性,妙不可言。这时候家中来客是从来不会介意的,我也只顾自己傻傻地笑,现在想来,那时的情境,真是其乐融融,美美与共!这铁与火,面与水,彼此包容,演变着大自然千古不变的规律,展示着它们的慈悯与宽厚,让世间万物得以延续,生生不息。
是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朝丞相李斯的千古名句,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因子。它向我们昭示,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跨越现实和虚拟,跨越地域和文化,才能产生智慧的碰撞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