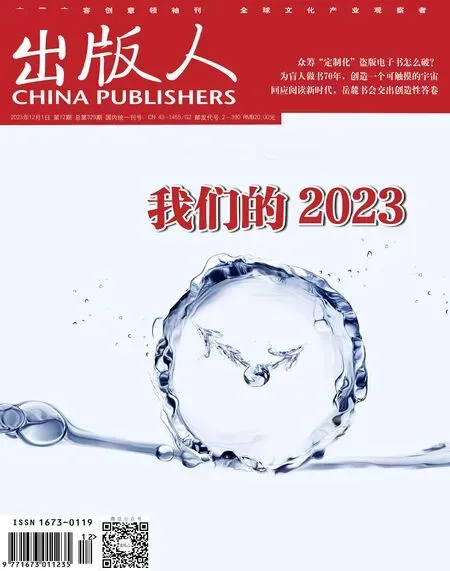“神仙译者”有了,编辑为什么找不到
记者 | 李晶 为什么“神仙译者”百年一遇,编辑要被“烂稿”折磨。
在图书市场上,那些被“糟糕的翻译”毁掉的经典好书经常被拿出来盘点,一本书的译者有时候与原创作者同等重要。与编辑一样,译者的工作也同样具备“幕后”“隐匿”的特点,不过他们的能力同样决定了图书的质量。
正所谓“好译者是笨蛋编辑的救星”,编辑眼中的“神仙译者”,既要有优秀的语言能力,又要有深耕垂类领域的专业背景;既要有与编辑详尽、靠谱、亲切、体贴的沟通能力,又最好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为图书的营销宣传提供助益……都说编辑是一个高门槛的职业,现在看来图书翻译的门槛一点也不比编辑低。
既然在图书出版工作中,译者的身份如此重要、对译者的要求如此之高,那么图书译者能否在这个行业获得合理的报酬以及相应的职业荣誉感呢?编辑找到心目中的“神仙译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出版人》采访了6 位图书译者,他们都是从编辑到翻译的跨界译者,希望通过双重视角重新看看图书译者在出版行业中的真实情况。

翻译点什么不好,干吗要去翻译书啊!
首先跳出出版行业,看看其他行业的译者收入。以英语语种为例,市面上正规翻译公司的旅游、展会、解说口译报价为每天1000 ~4500 元;电影字幕笔译报价为每分钟30 ~300 元,按平均7 分钟千字算,价格为每千字210~2100元。而图书翻译报价一般在每千字60~120元。这相当于做几天口译就能赚到一本书的翻译稿酬,而电影字幕翻译的价格竟然是图书翻译的十几倍!
一位稿酬在行业平均范围内的全职图书译者,按照一年一百万字的翻译量来算,全年收入也只有10 万元左右,这个收入真的能养活自己吗?
身为给译者开稿费的外国文学编辑,黄建树自己也觉得图书译者的付出与回报比并不合理:“报酬提高了一些,但跟CPI 相比,感觉增长幅度很小。”2000 年前后,译者就能拿到千字80 元的稿酬,如今绝大多数图书译者还是拿这个数。去年“天才译者”金晓宇被爆出稿酬千字仅五六十元,引发了不少争议,而像金晓宇这样拿“入门级”稿费的译者在行业内比比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物价翻了近两倍,期间图书译者稿酬被拿出来反复争论过,也产生了小幅增长,不过“稿费涨一倍到千字160元才是合理的”,译者何啸风认为。
国内按版税计费与译者签约的出版方不多,大多数情况下译者获得的图书翻译稿酬不会因为图书销量而产生变化,然而一本书的销量真的与译本质量毫无关系吗?大多数拿一次性稿酬的译者看到自己翻译的书畅销了,内心多少都会掺杂着骄傲和失落并存的复杂情绪。
据黄建树观察,翻译行业内能拿版税的条件比较苛刻,只有少数知名译者能拿到版税,而且一般只有在译公版书的时候才会给版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译者早一步进入图书翻译领域,自然会先成为“站在塔尖上的人”。然而在一些编辑眼中,现在的年轻译者可以通过网络或出国留学等方式与最新学术文化动态接轨,所以年轻一辈译者的翻译水平整体不仅在提高,甚至可以超越老一辈译者。但他们并没有获得与同样的知名度以及水平相当的报酬。
另外公版书也在考验着年轻译者的定力。由于首译版权书面临着未知市场的风险,一次性稿酬对出版方和译者来说都更加保险,也成为普遍的稿酬结算方式。然而引进版权书的首译往往比公版书难度更高,需要译者付出更多与编辑的沟通成本,而获得的回报比公版书低,这自然会折损做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社科等艰深领域图书译者的信心。
刚入行没多久的译者董纾含告诉《出版人》,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成长型菜鸡”,很多事情都还在学习阶段。在与出版方签订合同时,除了稿费结算方式、千字多少人民币,她还会重点看看出版方是否要买断版权。如果出版方买断版权后不再出书,译者也不能把译稿授权给其他出版单位出书,这对译者来说是很麻烦的事。在与出版方合作的过程中,年轻译者还有可能遇到一些类似买断版权、拖欠稿费的“坑”,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从行业内部来看,不对等的收入回报和职业荣誉感使图书译者的从业信心降低,图书译者在出版环节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也给翻译工作造成了重重阻碍。从行业外部来看,新技术的出现、竞争者的涌入也让有志于在这个行业深耕的年轻译者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
GPT-4Turbo都出来了,书还要你来翻译?
从业八年的出版公司编辑小墨之所以会产生做图书译者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生气和愤怒。不少编辑都与他深有同感,任职于浦睿文化的编辑何啸风说:“纯粹是因为翻译的稿子太烂了!我职业生涯中第一部稿子就译得很差,当时心里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译!”
村上春树《第一人称单数》的译者烨伊就从编辑转行成为全职译者。曾在某知名民营图书公司做编辑的几年里,烨伊译书几乎没有间断过,那时候所有的译作都是她利用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做,但两样工作一起干,时间久了身体就不太能吃得消,于是只好忍痛割爱做全职译者。
在图书出版这个小圈子里,“今天你是译者我是编辑,明天我是译者你是编辑”,编辑兼职译者的现象很常见。不过这些编辑之所以会遇到令他们“怀疑人生”的译稿,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些译稿的背后是大量的兼职译者。
在烨伊看来,这些兼职译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老师、文艺爱好者,他们有的为了丰富履历而接下图书翻译的任务,有的就是为了尝试而接触图书翻译,翻译水准不一。虽然也有真正爱好翻译、用心做事的译者,但整体上不可避免地缺乏对行业的了解,进而也导致行业整体缺乏规范性,成了恶性循环……
兼职译者大量涌入图书翻译行业的现象,和机器翻译的出现密切相关。当被问到编辑如何处理自己并不熟悉的语种文本时,编辑小墨的答案是“借助机翻平台”,他认为懂得怎么使用机翻平台是现在引进书编辑的必备技能。机器翻译的出现方便了编辑的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图书翻译的门槛,让那些编辑眼中“很烂”的译者能够乘虚而入。
不过在机器翻译向AI 翻译的方向不断发展并进化的过程中,译者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AI 翻译的出现对认真负责的好译者是有好处的,当然有些不认真、不负责的译者在AI 的帮助下可以变得更不认真、不负责。”小墨说。接受采访的大多数译者也认为AI 翻译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取代他们的工作,而是随着AI 翻译水平的提高,他们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帮助。
在本次调查中,“目前来看图书译者最大的竞争者是什么?”这一问题得到了意料之外并且相对一致的答案:
董纾含:“是自己吧(啊,好中二的回答)。”
康海源:“可能还是自己——如何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法、逻辑、语文水平。”
黄建树:“也有可能是译者自己。我个人觉得,自己和自己‘竞争’、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经验、时刻端正自己的态度,也是一件要紧事。”
何啸风:“最大的竞争者就是彼此吧。总是能遇到一些很厉害的译者,觉得——哇,这个句子我怎么想不到这样译呢?”
在对人本身抱有信心的年轻译者眼中,AI 不是竞争者,最大的竞争者是自己。“有些老社编辑,一句外语不会,也能做引进书,主要就是相信译者吧。”小墨补充道。也许现在不认真负责的译者做的翻译工作,从机器辅助变成辅助机器,直到有一天被机器取代后,最终这些相信自己也值得编辑相信的译者会留下来。
因为这是很好玩的事,会尽力把这件事做好!
虽然图书译者在工作上面临重重阻碍和复杂的环境,不过仍有不少年轻译者都把这样一项超高难度的工作当作“好玩儿”或者激励自我成长的事情,愿意在各自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和语种上钻研,敢于挑战更具创造性的引进版新书的翻译工作,并在不同类型的图书翻译市场上生发出自己的见解。
在图书译者圈里,大家公认文学翻译对译者的语言和文学功底要求最高,文学翻译中的顶级译者可以说是翻译界的天花板。编辑黄建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英语,硕士具体方向是英美文学。在他看来,英美文学翻译“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语言来说,已经非常‘卷’了。当然也有一些空白地带,但相对较少”。
2014 年硕士毕业以后,黄建树先做了3 年的出国留学咨询相关工作,然后转行做编辑一直到现在。他说自己之所以兼职做译者,是因为喜欢文学、喜欢英语、喜欢翻译。他翻译的书有《成为母亲》《超凡脱俗的鸟》《早春》《四面风》《承诺》等,其中不乏获布克奖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译稿质量高,被同行称为“树师”。
因为本职就是历史社科类图书编辑,小墨翻译的图书也以历史社科为主。以他的经验来看,历史社科类引进版图书以前市场翻译需求很大,现在似乎在萎缩。不过主攻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康海源却发现:“从版权贸易的情况看,历史社科类中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方向的选题竞争却越来越激烈了,国外有些新书事实上还没正式出版,版权就被国内机构买下了,有时令人吃惊。”
上学的时候,康海源所读的专业几乎人手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套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他没想到毕业后会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成为这套丛书的编辑。进入学术翻译的领域让他体验到不少乐趣:“它让你‘跳出椰壳碗’,与更大的世界(包括古代的世界)发生联系;让你像闯关一样,去破解一个个长难句;让你用语言还原前后句、前后段的逻辑关系,感受思维的乐趣。作为译者,我会尽力把这件有趣的事做好。”
关注法语翻译的何啸风认为:“法语图书和英语图书一样已经和国际接轨了。虽然有些书出版时会宣传‘被遗忘的法国大师’,但是至少就社科领域而言,基本上口碑不错的新书,很快都会引进到国内。”他主要关心的是社科领域中的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我认为二者是有关联的,它们都关心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同时他也发现社科书的翻译需求近几年明显增加了,“看这类书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人们更关心社会了”。
专业是戏剧的董纾含读书期间兼职做戏剧相关的活动,比如写剧本、参加戏剧节的制作和翻译。毕业后短暂做过一段时间图书编辑,在做编辑期间找到了译书的乐趣,于是开始了“非专业翻译”的生活。转行成为全职图书译者后,她喜欢和编辑们聊天、学行业知识,在各种出版行业聚会的场合,她都会拿出精致的名片,向大家郑重地推荐自己的译者身份。今年9 月,她翻译的上野千鹤子和水无田气流的对谈集《结婚由我》正式出版,新书上市后,她开心地给业内女性友人赠送这本书。
为什么“神仙译者”百年一遇,编辑屡受“烂稿”折磨?
“神仙译者”百年一遇,编辑屡受“烂稿”折磨,原因到底是什么?
小墨曾经遇到一本一度难产的书。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编辑着急催稿,两年过去了翻译费却迟迟不给支付。他有些生气了,比较严厉地发邮件向负责的编辑“发飙”,后来接手的编辑抱着同情与理解妥善解决了问题。最后他和编辑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正所谓不“骂”不成交。编辑对“神仙译者”的第一个诉求就是不拖稿,那么出版方至少也要做到不拖欠稿费。
黄建树回忆,翻译《早春》时,编辑和改稿过程都很愉快,编辑郭歌将两人关于译文的商讨整理成了一个四万多字的文档,专门请朋友设计做成了一册“小书”,在后来见面时送给了作为译者的黄建树。这才叫专业编辑与“神仙译者”的双向奔赴。
烨伊认为,目前两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译者稿酬不容易提高:假如出版机构对文本质量要求很高,要求编辑具备非常优秀的改稿能力,并给编辑大量时间打磨内文,那么他们没必要买那么好的译稿,因为他们可以“屎上雕花”;假如出版机构对文本质量根本不在乎,只追求效率和码洋转化,30 分的译稿和70 分的译稿对他们来说区别不大,在既定下限的基础上不愿花钱买质量,只追求利益最大化。
将翻译成本转移给编辑,或者主动降低文本标准,这些压缩图书成本的倾向都会让优质译者很难出头。近年来,从电商崛起到直播卖书,掌握新渠道似乎成为出版机构的制胜法宝,但在“渠道为王”的观念驱使下,图书破价等乱象层出不穷,退让的是价格,压缩的是成本,钱省在了文本上,花在了流量上。留给好书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优质图书译者的空间自然也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