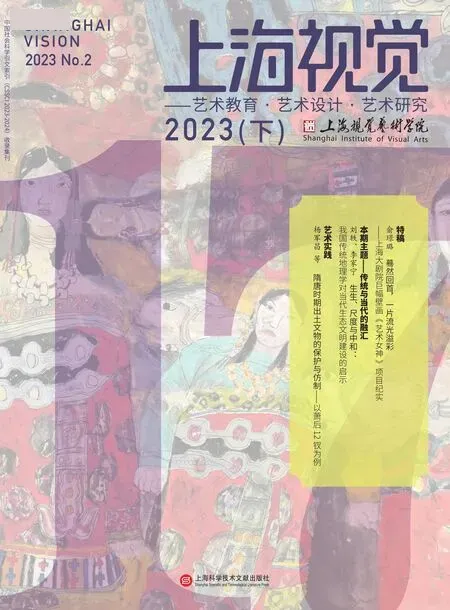电影《美丽人生》的创伤叙事与国际争议
田爽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 201620)
一、电影介绍
电影《美丽人生》(英文名Life is Beautifu,又名La Vita è bella,1997)是由意大利著名导演罗伯托·贝尼尼①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Remigio Benigni),1952年10月27日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区,意大利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在电影《美丽人生》中,贝尼尼既是本片导演,也是男主角圭多的饰演者。贝尼尼现实生活中的妻子Nicoletta Braschi饰演了本片的女主角多拉。执导的电影,1997 年在意大利上映。1999 年,该电影获得了第71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配乐奖三项奖项。该片的4K修复版于2020 年在中国内地上映。电影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笼罩下的意大利。
电影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在前半部分,生活是美好的:热情善良的犹太青年圭多(Guido,由Roberto Benigni 饰演)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镇,邂逅了美丽的贵族姑娘多拉(Dora,由Nicoletta Braschi 饰演)。圭多坚持不懈地追求多拉,多拉终于被打动,两人走进了婚姻殿堂。前半部分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圭多话痨式浮夸表现与各种巧合桥段为观众带来不少笑料。
随后故事进入了后半部分。圭多与多拉结了婚,有了乖巧可爱的儿子乔舒亚(Josue,由Giorgio Cantarini 饰演)。圭多与儿子乔舒亚有犹太血统,因此被纳粹分子抓走并关押至犹太人集中营。多拉主动前往集中营和家人团聚。圭多在集中营中一边千方百计与女牢中的多拉联系,一边哄骗乔舒亚:集中营的生活是一场游戏,胜利的人能获得坦克。年仅五岁的乔舒亚相信了父亲的谎言。为了赢得坦克,乔舒亚忍受了集中营里孤独、饥饿、恐惧和苦难。解放前夕,圭多惨死于纳粹分子的枪口下。战争结束,多拉与儿子乔舒亚重逢。美国军队开着坦克经过,乔舒亚欢呼自己终于赢得了游戏,赢得了坦克。
《美丽人生》歌颂了一个父亲用谎言保护儿子的壮举,电影充满了温情和人性光辉。电影的部分灵感来自于贝尼尼的父亲路易吉·贝尼尼(Luigi Benigni)在德国埃弗尔特纳粹劳改营(Nazi work camp in Erfurt)的经历。路易吉向他的孩子们讲述过往经历时,用幽默和充满人文主义的角度讲述奇闻逸事,极力避免让孩子们感到沮丧和恐惧。这种呵护童心的讲述方式对贝尼尼产生了深远影响,电影里圭多乐天派的形象和对父爱的宣扬,都反映了贝尼尼对父亲的审视与记忆。
二、电影的创伤叙事
(一)创伤展示的方式
谢菲尔德大学人文学院高级讲师哈丽特·厄尔(Harriet Earle)在2016 年将创伤定义为“没有伤口的伤口”,她认为创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创伤经历最难表述、也最难克服②Harriet Earle在2016年在Film International杂志14卷1期发表的文章《Creating The Traumatic Body》中写道:“Trauma is a wound without wound”,“The rupture of experiences by the victim of trauma is not physical but remains within the psyche。It is for this reason,among others,that the experience of trauma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o describe,to catalog to overcome.”(35-43页)。因此,不同于肉眼可见的物理伤口,创伤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创伤电影常常讲述创伤事件、受害者的创伤经历或创伤事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持续影响。犹太人大屠杀(外文名为Holocaust 或Shoah,以下简称为大屠杀)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群体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伤事件。因此,以该事件为历史背景的《美丽人生》属于创伤电影的范畴。
以大屠杀为背景的电影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展示创伤:一是打造虚拟的历史空间,通过画面与声音还原和重现历史事件,故事片多采用此方式叙事;二是展现创伤证据(纪录片多采用这种方式),如公布详细数据、历史文件、受害者的声音图像等,以证明事件的真实性和残酷性。
《美丽人生》采取了第一种方式,即用声音和画面营造二战的历史场景,在搭建的虚拟历史空间内讲故事。有人明确反对用电影技术还原大屠杀历史。例如,法国犹太导演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1925-2018)认为电影的虚构和再现会招致窥淫癖与幸灾乐祸祸。他奔走采访,拍摄了纪录片《浩劫》(外文名为《Shoah》,于1985 年4月在法国上映),长达544 分钟的《浩劫》记录了经历过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对纳粹分子暴行的控诉。
(二)电影的时间叙事
无论电影采取哪种方式展示创伤,都会涉及到时间。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连贯的,单向地向前流逝。电影有时长限制和叙事需要,因此不必如实反映时间。电影中的时间通常有三种形态,一是故事展示的时间;二是电影的放映时间;三是观众的心理时间。例如,电影镜头用三秒钟的慢镜头展示杯子掉落,杯子掉落的过程是故事展示的时间,放映的三秒钟是放映时间,观众感觉到杯子掉落用了很久则是观众的心理时间。在这个例子中,故事的展示时间远远超过了杯子掉落的实际时间,这种把叙事时间故意延长的手法为“时间的膨胀”。
《美丽人生》采用时间顺序叙事方式,按照时间的自然流动进行叙事,不使用闪回和倒叙,故事有清晰的发展脉络。电影用到了“时间的省略”,和上一段提到的“时间的膨胀”相反,“时间的省略”则是把叙事时间故意缩短。最显著的一处是:多拉进入小屋,圭多也跟着进入(图1)。随着圭多的呼唤声,儿子乔舒亚蹦蹦跳跳地从小屋里出来,扑向多拉,说“我的坦克丢了”(图2),圭多回答“我们会找到的”。这段对话为之后圭多用坦克鼓励乔舒亚战胜困难、战争胜利后乔舒亚等到坦克等情节埋下伏笔。

图1 圭多进入小屋

图2 儿子从小屋里出来扑向多拉
该片段的叙事省略了圭多夫妇生子、儿子成长的过程。故事的展示时间为圭多夫妇结婚生子、孩子长大,电影放映时间大约为一分钟,观众感觉到时间飞逝则是观众的心理时间。这个片段也是电影由爱情喜剧转变为战争悲剧的分水岭。
(三)电影的空间叙事
在电影中,空间叙事和时间叙事几乎同等重要。二者平衡才能使电影的情节完整,令人信服。与叙事时间一样,叙事空间也不同于真实空间,它是电影的制作者用声音和图像创造的特定的、虚拟的、理想化的空间。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中,电影的主要叙事空间是热闹开阔的街道(图3),影片后半段的主要叙事空间则是筑有高大墙体的集中营(图4)。集中营戒备森严的高墙与热闹开阔的街道构成空间上的对比关系。

图3 热闹开阔的街道

图4 戒备森严的集中营
叙事空间与观众的记忆有很强的关联,正如纽卡斯尔大学现当代文学教授安妮·怀特黑德(Anne Whitehead)所说:“景观是一个以历史为模型的场所。我们对周围景观的解读总是伴随着传承的记忆、事实信息、个人和国家政治。”③原文出自Anne Whitehead写的《Trauma fiction》:“Landscape is a site that has been modeled by history.Our readings of the landscapes by which we can surrounded always combine inherited memory,factual information,and personal and national politics.”在与二战有关的电影中,作为叙事空间的集中营不再是普通地方,而是承载着人们创伤记忆的空间,是灾难的象征,能唤起人们的创伤记忆。
除集中营这个封闭的场所,《美丽人生》还有其他密闭空间的取景,例如去往集中营的拥挤车厢(图5)、集中营的狭小床位(图6)、乔舒亚藏身的邮筒(图7)……这些拍摄地使观众产生恐惧、紧张和呼吸困难等焦虑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创伤。观众的焦虑感可能与幽闭恐惧有关:一方面,封闭空间是让人逃离周遭环境的容身之所;另一方面,封闭空间可能成为创伤的载体,因为灾难降临时人们被困其中无处可逃。

图5 去往集中营的车厢

图6 集中营的狭小床位

图7 乔舒亚藏身的邮筒
(四)其他大屠杀元素
电影中的其他大屠杀元素还包括苦力劳动、毒气室、带有名字的条纹衣服、州长办公室的法西斯领袖肖像等。但是,电影并未刻画暴力和非人化的真实场景:纳粹的恐怖只限于语言暴力,并没有直接呈现谋杀和酷刑;对于毒气室,电影仅展现了受害者在前厅脱衣服的场景;圭多在镜头外被枪杀,观众只能听到枪响。
最接近残酷史实的场景是圭多抱着乔舒亚在烟雾弥漫中行走(图8),圭多一边哄乔舒亚入睡,一边安慰自己这可能是一场梦。烟雾中,圭多看到一堆雕塑般的遇难者尸体(图9)。昏暗的色调、迷蒙的烟雾、其他布景的缺失,使得这串镜头如梦如幻,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作为一部大屠杀电影,电影的叙事似乎游走于现实与虚构之间,将大屠杀元素和艺术技巧做了结合。对苦难和残酷的刻画点到为止,而非直面暴力和恐怖,它的处理是艺术化、符号化的。

图8 圭多抱着乔舒亚在烟雾弥漫中行走

图9 圭多看到的雕塑般的尸体
(五)电影的叙事者
前面提到,从大屠杀的元素来看,电影的叙事游走于现实和虚拟之间。而叙事者的不一致更加剧了二者界限的模糊性。
电影开场,第三者的画外音告诉观众,他们接下来要听的故事“像寓言”。像寓言而非是寓言,暗示故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然而,电影结束时,画外音揭示讲故事的人是已成年的乔舒亚,即集中营的经历是他的童年记忆。若将开场画外音视为叙事者,电影似乎反映历史事件,呈现大屠杀集体记忆;若将电影结束的画外音视为叙事者,电影则讲述成年后的乔舒亚对童年和父母的回忆。我们很难界定这部电影是真实历史还是童年印象。
三、国际争议
国内相关论文对该影片的探讨多集中于歌颂父爱与信念、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圭多的乐观精神和人性光辉、分析电影里的音乐等主题。不同于国内的赞誉之声,在国际电影研究领域,这部电影自放映以来受到了诸多争议。
(一)反对者意见
1、对大屠杀历史的呈现不客观
1999 年,美国电影评论家大卫·邓比(David Denby,1943-)在《纽约客》发表了文章,指责该电影“不可信(unconvincing)”和“沾沾自喜(self-congratulatory)。文中强调,贝尼尼清楚地知道,二战中98%的儿童在抵达集中营后立即被杀害,因此父母通过游戏拯救儿童的阴谋是不可能的④原文出自David Denby的文章《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Another Look at Roberto Benigni’s Holocaust Fantasy》: “Surely he[Benigni]knows that a young child entering Auschwitz would be immediately put to death,and that at every camp people were beaten and humiliated at random.He shows us nothing like that.”。邓比认为贝尼尼否定了大屠杀史实。
认为该电影违背历史史实、旨在否定大屠杀的学者不在少数。以色利作家特拉维夫大学电影学院科比·尼夫教授(Kobi Niv,1947-)也认为《美丽人生》中,父子所在的集中营环境太好了,充满欢笑,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像一个不那么恐怖的劳动营。他指出,这部电影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天真、迷人,它是西方抹去大屠杀污点的一种方式,传播种族主义偏见。⑤观点出自Kobi Niv的文章《Life is Beautiful,But Not for Jews: Another View of the Film by Benigni》。
2、欢笑与游戏是对大屠杀的淡化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在《人能在奥斯威辛之后生活吗?:一位哲学读者》⑥书籍英文题名为《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A philosophical reader》。一书中,通过奥斯威辛的大屠杀证明西方批判哲学的死亡。阿多诺广为人知的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⑦原文出自阿多诺1949年的著作《文化批判与社会》。旨在说明文学作品可能会对创伤事件异化,把灾难变成表演和修辞。他呼吁艺术作品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灾难。
科比·尼夫教授还分享了他第一次观影《美丽人生》的感受:观影的第一个小时里,平庸的喜剧和不合时宜的笑声让他感到越来越愤怒⑧观点出自Kobi Niv的著作《Life is Beautiful,But Not for Jews: Another View of the Film by Benigni》。。埃坦亚学术学院的伊亚·赞伯(Eyal Zandberg)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欢笑做了剖析:“很多评论家对使用幽默的修辞来表现大屠杀表示担忧,甚至愤怒,尤其是对罗伯托·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这些评论家认为,在大屠杀面前,这种风格是不协调、矛盾且有颠覆性的。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喜剧表现形式更能有效地反抗恐怖,因为与悲剧不同,喜剧表示不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⑨原文出自Eyal Zandberg的文章《Critical laughter:humor,popular culture and Israeli Holocaust commemoration》:“many critics have expressed concern,and even outrage,over works that use the rhetoric of humor to represent the Holocaust,mainly as a reaction to Roberto Benigny’s film Life is Beautiful (Gilman,2000;Niv,2000).These critics argued that the incongruous,ambivalent and disrup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enre are inadequate to deal with the Holocaust.On the other hand,some argue that comic representations are more effectively in revolt against horror because,unlike tragedy,they do not accept what has come to pass (Des Pres,1988).”
不少学者认为《美丽人生》用喜剧与游戏降低了大屠杀规模和恐怖性,快乐的结局违背了大屠杀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的本质。尽管它歌颂赞美了人性,但是与人类极端的苦难显得不严肃且浅薄。把集中营的生活视作游戏,就是通过自我欺骗故意忽视集中营的苦难、折磨和生存危机,用闹剧淡化大屠杀,剥夺人们的判断力和道德敏锐力。
3、主角的设定存在偏见
贝尼尼并没有赋予电影的主角圭多过多的犹太人特质。作为犹太人,圭多的外貌特征、信仰、习俗等特质并没有在电影中展现,相反,他与非犹太人恋爱结婚,只想开一家小书店和家人幸福生活。只有书店审批不通过、被纳粹抓走才让观众意识到他是犹太人。因此有人认为,模糊犹太人特征迎合了天主教会将温顺犹太人同化的理想。
电影中圭多不仅被模糊了犹太特质,他的形象甚至是矮化的。他滑稽笨拙,肢体喜欢抽搐躁动,爱讲无聊的笑话,这样的形象扭曲了犹太人群体的形象。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在当代国际话语场域下呈现出中心性:大屠杀是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被迫害的犹太人是受压迫的象征。因此,在反映大屠杀历史的电影中,冲突的双方通常是残暴的纳粹分子和无辜的犹太受害者。如果电影丑化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不仅伤害了犹太观众对祖先的情感认同,也有篡改历史、歪曲集体记忆的嫌疑。
(二)支持者意见
1、喜剧形式可以传达悲剧无法传达的观点
韦尔斯利学院教授毛里齐奥·维亚诺(Maurizio Viano)在其文章《美丽人生:接受、寓言和大屠杀的笑声》(1999)中写到,尽管很多评论家难以原谅这部电影,但它仍是一部广受欢迎的成功之作。他在文中为饱受批评的贝尼尼辩解:“与其说贝尼尼雄心勃勃渴望更高的地位,不如说他真诚地希望他对喜剧和笑声的看法得到认真对待。”⑩原文出自Maurizio Viano的文章《Life Is Beautiful:Reception,Allegory,and Holocaust Laughter》:“Benigni's desire for a higher status is less a symptom of ambition than of a genuine wish that his ideas on comedy and laughter be taken.”毛里齐奥认为,贝尼尼的喜剧方式是尊重大屠杀,同时可以传达悲剧无法传达的观点。“美丽人生”这个题名体现了贝尼尼的创作目的,即使人振作起来,在压迫的环境下赞美生活之美,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绝望。他认为该电影的批评者只关注了电影快乐的一半,实际上,这部电影在精神上(而非表面上)忠于现实—也就是说,贝尼尼非但没有贬低大屠杀,反而将大屠杀这场历史的噩梦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重新载入集体记忆。他认为,《美丽人生》能让人们从大屠杀中解脱出来,并不是因为大屠杀被贬低,而是因为精神的力量被放大。
2、寓言与欢笑是人类应对苦难的有力武器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教授史蒂夫·西波林(Steve Siporin)在其1999 年发表的文章《美丽人生:四个谜语,三个答案》⑪文章原英文题名为《Life Is Beautiful : four riddles,three answers》。中分析了电影中谜语的使用,他认为电影中充满隐喻的谜语和民间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欣赏其艺术性;圭多在集中营创造的“儿童游戏”有意义且震撼人心。他的主要观点有:电影告诉我们爱(电影中是父亲对儿子和家庭的爱)是生存技巧的来源和具体力量;当人类精神遭到可怕的精神攻击,卑微的艺术(谜语、儿童游戏)是与之对抗的有力武器。他认为,圭多从游戏的角度解释集中营规则,是用意志对抗纳粹暴行,将无意义的劳动变得有意义,从而中断纳粹的非人化过程。
3、电影反对种族主义
对于《美丽人生》否认大屠杀、传播种族主义偏见的观点,支持者做出驳斥。支持者认为,恰恰相反,电影对种族主义是批判态度。例如,圭多冒充一个视学官客人去多拉任教的学校,被校长要求向孩子们讲述他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种族,圭多胡说八道的内容和自身的犹太身份暗示了种族主义的荒谬;圭多的叔叔(犹太人)最心爱的马被涂成绿色,上面写着“ACHTUNG!!CAVALLO EBREO(小心!!犹太马)”,象征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图10);圭多在宴会上骑着这匹马带走多拉,是对种族主义的讽刺和反抗;把纳粹集中营的苦难比做一场游戏,也是对法西斯的轻视和鄙夷。
4、电影无法呈现真实历史
美国大屠杀文学学者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1929-)在其1975年的著作《大屠杀与文学想象》⑫原文出自 《The Holocaust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There are two forces at work...in the literature of atrocity: historical fact and imaginative truth.The literature of atrocity is never wholly invented;the memory of the literal Holocaust seethes endlessly in its subterranean depths.But such literature is never wholly factual either.”中指出:“暴行文学中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即历史事实和想象中的事实。暴行文学不是完全虚构出来的;大屠杀的记忆在其底层深处永无止境地翻腾。然而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并非完全真实”。《美丽人生》在历史层面受到的批评,在于想象中的事实对历史事实的违背。然而,大屠杀历史的残酷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理解范围。用电影来呈现真实是不可能的,再高超的电影技巧也难以复现集中营历史的邪恶;如果真按照史实复原毒气室、焚尸炉等场景仍是不道德的,这些画面对于幸存者及其后代是二次伤害,还会变成视觉奇观满足观众的窥视癖。
(三)争论的实质
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议,都回归到一个基本问题: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的?它是文学创意的产物,还是对创伤性历史事件的大胆处理?我们前面提到,《美丽人生》围绕叙事的前半部分(包含主要的喜剧情节)和后半部分(主要为集中营场景)之间的紧张关系展开。电影以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片中有悲伤,也有惊喜和幸福。它既不是一部历史纪录片,也不是对真实事件的重构,而是一部虚构的寓言式的电影。
电影是否违背再现大屠杀的道德问题,涉及到艺术作品的美学和伦理问题。支持者多从艺术与审美方面赞扬该电影是充满希望且振奋人心的救赎,反对者则从道德方面引导大众正视历史事实,双方的争议的实质是强烈的道德主义和审美化艺术观的分歧。
四、创伤与集体记忆
在第二章的空间叙事部分,我们提到集中营是承载集体记忆的空间,那么如何理解“集体记忆”呢?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在他的著作《集体记忆》(原题名《La mémoire collective》)中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可以拥有集体记忆,个人对过去的理解与集体记忆密切相关。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杰夫莱·奥利克(Jeffrey K.Olick,1964-)认为集体记忆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社会框架下的个体记忆的集合,另一个指独特的群体现象。”⑬原文出自Jeffrey K.Olick写的《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One refers to the aggregation of socially framed individual memories and one refers to collective phenomena.”在他的表述中,前者强调个体的记忆和认知,后者则关注社会和文化现象,而非个体记忆。
电影中,乔舒亚向父亲圭多的致敬,也是贝尼尼本人对父亲路易吉的致敬,圭多这个在集中营中幽默乐观、保护孩子的角色带有贝尼尼对路易吉的审视和记忆。但是事实上,路易吉并不是犹太人(贝尼尼也不是),而是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成员,轴心国同盟的一员。元帅彼得罗·巴多利奥向同盟国投降后,路易吉和其他意大利士兵被驱逐到德国,在德国的劳动集中营里沦为战俘。尽管在德国集中营里遭到残酷对待,但这样的经历是被排除在意大利标准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为什么呢?
数以万计的非犹太意大利士兵受训于法西斯政权,在国外和纳粹并肩作战,最后成为战俘,这样的历史承载着意大利的集体创伤:二战中的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更是战败国。意大利在公共领域通常强调其二战受害者身份以缓解创伤并提升凝聚力,因为苦难的集体记忆是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源泉。意大利关于二战的文学和新闻报道中,德国通常是种族灭绝、邪恶力量的象征,意大利人的形象则是勇敢而善良的。
路易吉这样的经历在公众领域是沉默的,只在家庭成员间口口相传。语言的无力和对主流的顺从使得创伤难以传播。随着幸存者的衰老和死亡,反犹太主义和白人至上等观念逐渐抬头,一部分人试图否认篡改残酷的大屠杀历史。所以,确保大屠杀被重述、被后代铭记变得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讲,这部颇具争议的《美丽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它将个体记忆和家庭记忆带入集体记忆中,让公众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五、结论
大屠杀的恐怖与残暴很难用文字来呈现。电影作为一种“通过视觉的形式再现过去,展示历史主题、历史记忆与历史问题的强有力媒介”⑭原文出自Ib Bondebjerg的文章《Confronting the Past.Trauma,History and Memory in Wajda’s film》:“(Film is a) powerful medium for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and for putting historical themes and questions of memory and history.”,和传统媒介相比,在描述创伤事件、刻画个体创伤经历方面存在天然的优势。当电影讲述历史事件时,难免会对公众的记忆和群体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用电影刻画大屠杀仍有一些难点:出于道义,最残酷的画面无法通过电影技术呈现给观众,无论是借助蒙太奇手法,还是像《美丽人生》一样回避残酷,都无法让观众直面最黑暗的历史;在悲剧的框架下,电影发挥创造力方面受限,尤其对于故事片来说,虚构容易招致批评。
有学者认为应当禁止以大屠杀为题材的故事片,只允许拍摄纪录片作为大屠杀证词;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大屠杀不该被搬上荧屏,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这两种观点均是强烈的道德主义对艺术审美的约束。
《美丽人生》是否值得赞扬,大屠杀故事片是否应该被禁止,国际学界至今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历史需要被铭记,如果电影作品违背历史史实,人们对于大屠杀的关注从历史转向了艺术性和创造性是非常危险的。我个人认为,电影应该展现大屠杀,让观众在叙事中感受过去的时间、整合历史碎片。电影创作者应保持道德正义和伦理尺度,再现历史场域的真实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