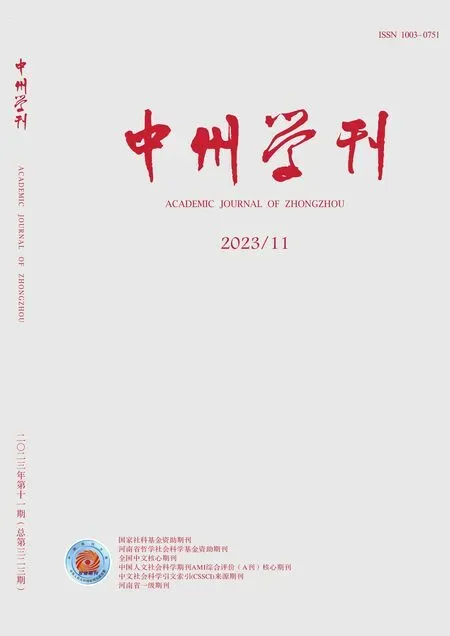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邵炳军
笔者所谓的“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所谓的“讽谏诗”是指居于下位者运用委婉曲折的诗歌言语,对居于上位者尤其是天子、国君的失误进行讽喻劝诫与批评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本文拟以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为历史文化背景,来讨论这一时期讽谏诗对西周时期讽谏诗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探讨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轨迹与基本特征。
一、春秋时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基本状况
时贤已有研究成果认为,《诗经》中的讽谏诗大约有70余篇①。据笔者初步考订,这些讽谏诗,创作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53年)的大致有19篇。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邶风·式微》《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将仲子》《魏风·葛屦》《小雅·节南山》及传世文献所存逸诗《琴歌》《原田诵》《优孟歌》《慷慨歌》《吴为无道歌》《凤兮歌》11首②。这些讽谏诗的创作年代在周平王元年至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89年)之间,基本上分布于春秋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③。
(一)春秋前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前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682年)的讽谏诗主要有3首,分别是周大夫家父(家伯父)的《节南山》、郑大夫的《将仲子》、卫人(国人)的《君子偕老》,具体分析如下。
《节南山》见于今《诗·小雅》,为周大夫家伯父刺幽王乱政亡国以谏平王中兴王室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左右④。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王师为以幽王废天子宜臼(平王)的母舅西申侯(姜姓国,在今陕西省眉县附近)为首的军事联盟所败,幽王在骊山戏水(水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为犬戎所杀,西周覆亡⑤。这表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二是幽王十一年至平王十年(公元前771年—公元前760年),王室嫡庶相争,出现了平王宜臼与其庶弟携王余臣“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这说明嫡长子王位承袭制与王权观念已经发生重要变化。
《将仲子》见于今《诗·郑风》, 为郑大夫刺庄公纵容其弟公子段(公叔段)失君臣长幼之道而致公室内乱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郑庄公二十二年。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克公叔段于鄢(郑邑,即鄢陵,地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公叔段出奔共(卫别邑,即今河南省卫辉市)。这表明诸侯公室宗子与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终于引发庶孽之乱,嫡长子君位承袭制受到严重挑战。二是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桓王率王师与卫、陈、蔡之师伐郑,郑师与王师战于繻葛(郑邑,又称“长葛”,在今长葛市治东北二十余里),王师大败,郑大夫祝聃射王中肩。这说明王室与公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诸侯不再“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左传·昭公九年》)⑥,竟然“敢陵天子”(《左传·桓公五年》)了。
《君子偕老》见于今《诗·鄘风》,为卫人借宣公夫人宣姜淫乱失道以讽谏公室上层贵族之作,当作于周桓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99年)以后,即卫惠公元年以后。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桓王元年(公元前719年),卫宣公晋即位后始纳太子伋(急子)之妻(宣姜),生公子寿及公子朔(惠公);二是周桓王二十年(公元前700年),卫宣公薨后,齐僖公强迫公子顽(昭伯)烝宣姜,生齐子、戴公申、文公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五人⑦。尽管这种“烝”“报”婚姻现象是一种氏族社会母权制时期群婚制或亚群婚制的文化遗存,但当周代贵族阶层已普遍实行父权制一夫一妻多妾婚制后,这种现象自然属于违背婚姻礼仪的乱伦“非礼”之行。
(二)春秋中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中期(公元前681年—公元前547年)的讽谏诗主要有6首,分别是黎大夫的《式微》、魏缝衣女的《葛屦》与秦百里奚之妻的《琴歌》、晋舆人(攻木之工)的《原田诵》和楚优孟的《优孟歌》《慷慨歌》,具体分析如下。
《式微》见于今《诗·邶风》,为黎大夫劝黎侯自卫归于黎(帝尧之后,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西南三十里)之作,当作于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狄灭卫之前,即卫懿公八年之前。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齐邑,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逐步实现了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这表明,霸主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后形成的政治权力真空,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二是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赤狄伐邢灭卫,兵锋直逼中原。这说明,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面依然严峻,黎君去国居卫而望助己,然卫君却无救其属国危难之志。
《葛屦》见于今《诗·魏风》,为魏公室缝裳女刺贵族妇人心胸狭窄而不体恤贫贱者之作,当作于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之后,即晋献公十六年之后。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曲沃(即今山西省曲沃县)武公并晋,僖王以一军命武公为晋侯。这表明在王权式微之后,周王室不得不认可公室小宗吞并大宗君权这一既成事实。二是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率上军灭魏(姬姓国,都邑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北七里之河北城,即故魏城),以之为晋县。这说明由于诸侯内部矛盾不断加剧,促使晋国加快了武力兼并其他诸侯的步伐。
《琴歌》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为秦百里奚(五羖大夫)之妻讽谏百里奚勿忘糟糠之妻之作,当作于周襄王六年(公元前647年)左右,即秦穆公十三年左右。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姬姓国,都邑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五十里张家店之北),年已七十余岁的虞大夫百里奚仕于秦,穆公授之国政。这表明秦穆公开始重用贤臣以图霸业。二是周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21年)期间,百里奚辅佐秦穆公,广地益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襄王贺其以“金鼓”。这说明秦穆公继晋文公之后获得霸主地位,逐步实现了西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原田诵》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为晋舆人谏文公应率诸侯之师谋立新功以伐楚师之作,作于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1年),即晋文公五年。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王室发生内乱,晋文公独自出面安定王室。这表明晋文公奉行“勤王”以“求诸侯”之策,开始图谋霸业。二是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1年),晋会齐、宋、秦之师及楚师战于城濮(卫地,即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之故临濮城),楚师大败,文公乃会诸侯盟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这说明晋文公继齐桓公成为诸侯霸主,维护了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
《优孟歌》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慷慨歌》见于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的《楚相孙叔敖碑》,二者皆为楚优孟讽谏庄王勿忘孙叔敖相楚功勋之作,作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即楚庄王二十二年。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定王九年至十五年(公元前598年—公元前592年)期间,即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期间,孙叔敖仕庄王为令尹,庄王以师事之。这表明楚庄王重用贤臣以富国强兵,开始北向中原图霸。二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晋邲(即汴河,亦曰汴渠,其上游为荥渎,又曰南济,首受黄河,在河南省荥阳市曰蒗荡渠)之战,晋师败绩。这说明楚庄王获取了霸主地位,逐步实现了南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三)春秋后期、晚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后期(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06年)的讽谏诗,仅存《吴为无道歌》1首。《吴为无道歌》见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为楚大夫申包胥(申勃苏)赴秦谏哀公以师救楚之作,作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即吴王阖闾九年。与此诗创作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自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之后,楚王室内部大宗与小宗之间、小宗与小宗之间的王位之争使国家长期陷入内乱。这表明楚国君权渐次式微而霸业中衰。二是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楚邑,在今湖北省麻城市东北)之战,楚师败绩,吴入郢。这说明吴王阖闾终于继楚庄王成为一代霸主,维护了南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春秋晚期(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53年)的讽谏诗,仅存《凤兮歌》1首。《凤兮歌》见于《论语·微子篇》,为楚陆通(楚狂接舆)讥讽孔子不能隐为德衰之作,当作于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即楚昭王二十七年。与此诗创作直接相关的政治历史事件有二:一是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即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因执政卿季孙斯(桓子)受齐女乐,遂去鲁适卫,开始了其周游列国(卫、曹、宋、齐、郑、晋、陈、蔡、楚)十四年的人生经历。这表明孔子试图通过游学以入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二是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故孔子自蔡(即负函之蔡,本楚邑,地即今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楚王城)赴楚之叶邑(即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之故叶城),后因楚令尹公子申(子西)的反对而未封。这说明孔子的政治主张难以迎合统治者的胃口,因此孔子四处碰壁,国君敬其人而不用其言。
二、春秋时期讽谏艺术演化的基本特征
春秋时期的诗人对西周时期的讽谏艺术,具有创造性传承与发展之功。这一时期讽谏诗的具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
春秋时期讽谏诗的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像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讽幽王以谏平王,郑大夫的《将仲子》讽谏庄公,卫人的《君子偕老》讽谏宣公夫人宣姜,黎大夫的《式微》讽谏黎侯,晋舆人的《原田诵》讽谏文公,楚优孟的《优孟歌》与《慷慨歌》讽谏庄王,等等。
《节南山》全诗十章,前八章的批判锋芒主要集中在太师皇父尹氏身上,第九章始以“我王不宁”带出幽王,卒章方以“以究王讻”将讽谏笔触直指幽王。至此,诗人国破家亡之孤独、无处远循之忧虑、匡时补天之清醒,达到了三位一体之境界,实现了叙宗周覆亡之事、抒自己离乱感伤之情、刺幽王亡国祸民之讻的创作目的,将讽谏艺术推向极致。因此,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评之曰:“[九章]‘王’字轻轻带出,诗人忠君爱国之心,含蓄无限。立辞之妙,可以为法。[十章]结出作诗原由。”[1]389
《优孟歌》全诗十八句,前十四句主要对“贪吏”与“廉吏”进行比较,后四句始点明创作缘由:“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2]2413-2414《慷慨歌》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亦主要对“贪吏”与“廉吏”进行比较,后二句始点明创作缘由:“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3]此二诗言辞多辩,于谈笑嬉戏之中,陈述孙叔敖生前为令尹,尽忠为廉,筐箧橐简,但卒后其子却穷困负薪,以讽谏楚庄王勿忘孙叔敖相楚之功。
如果说周大夫家父作为王室宰夫(下大夫)讽谏在位天子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是其职责所在的话,那么楚优孟作为楚乐人之长(相当于周王室的中大夫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贵族子弟乃其职责所在,讽谏在位国君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则是一种自觉行为,体现了一种政治担当。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中下层贵族诗人群体,利用讽谏诗对天子与国君进行政治批判,完全是一种自觉意识。这相较于西周王室的祭公谋父、召伯虎、芮良夫等公卿类上层贵族讽谏诗人群体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性进步。
(二)“赋”“比”“兴”三体综合运用
毫无疑问,讽谏的本质特征是抒情的。但春秋时期讽谏诗人的抒情,大多不是直白式表述与口号式呐喊,而主要是通过运用“赋”体叙事艺术与“比”体和“兴”体形象感知来实现的。
1.以“赋”体叙事艺术来强化讽谏诗的社会功能
所谓“赋”体,就是敷陈其事的艺术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化讽谏诗社会功能的叙事艺术。比如,《节南山》全诗十章,前三章采用“赋”体叙事艺术来直陈时弊,揭露尹氏的黑暗政治;中间三章采用“赋”体叙事艺术来说明事理,指出缘由;末四章以感叹抒发愤懑之情。可见,全诗以大量篇幅来进行叙事,敷陈太师皇父尹氏为政之失。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结尾“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的抒情,具有了更为厚实的事理基础,使叙事主题更为深刻,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自然强化了讽谏的社会功能。因此,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评之曰:“唯家父,周朝世臣,义与国同休戚。故不惮诛罚,直刺其非,无或稍隐。”[1]388
又如,《葛屦》全诗两章,首章六句与卒章前三句皆用“赋”体来展开叙事,完整地涵盖了时间(“履霜”之季)、地点(寒冷的“缝裳”处所与温暖的宫室)、人物(“缝裳女”与“好人”)与事件(缝制衣裳与试穿新衣)四要素;卒章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方点出正题。特別是随着叙事空间由“缝裳”之所向“试衣”之室的转换,显示出叙事时间的前后推移;人物描写则将贫贱之女的任劳任怨与贵族夫人的心胸狭窄前后对照,褒贬分明。因此,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五评之曰:“仪容服饰虽为大人,而中心偏急,不称其外也。盖表里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4]卷5
可见,这一时期讽谏诗人的生活感知由以集体情绪为主向以个人感受为主变迁,叙事意识由自发阶段向自为阶段转变;其所创作的讽谏诗的情节结构由断面式空间描写向线性式时间描写发展,人物描写由扁平式符号化向立体式形象化转变。
2.以“比”体与“兴”体形象感知来增强讽谏诗的抒情功能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往往选取客观物象与事象作为喻体或兴象,采用“比”体或“兴”体以强化讽谏的形象感知,以增强讽谏的艺术感染力。比如,《吴为无道歌》凡七句,开篇以“封豕长蛇”比喻吴国对诸侯造成的严重危害;结句则以“草泽”比喻吴师入郢(楚都邑,即今湖北省江陵市荆州镇北五里故纪南城)后,昭王涉睢济江入云中(云梦泽)奔随(楚邑,当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南)的艰难处境[5]。足见此歌连用两个借喻,一喻吴害之大,二喻楚境之险,从而凸显“告急”之迫,足以打动秦哀公以师救楚之心。
又如,《原田诵》凡两句,首句以稠密茂盛之“原田”这一客观物象作为喻体,比喻晋、宋、齐、秦之师威武强大;又以“原田每每”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象,引出“舍其旧而新是谋”之旨,鼓励晋文公应毫不犹豫地与楚师展开决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此诵将“比”体与“兴”体合二为一,从而增强了讽谏的形象感知,强化了抒情的艺术效果。
(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春秋时期讽谏诗运用最典型的是呼告、设问与夸张等三种修辞手法。
1.以呼告强化讽谏诗的情感效果
春秋时期讽谏诗中的“呼告”,往往与“比拟”“示现”结合使用,带有“比拟”或“示现”性质,通常可以分为“比拟呼告”与“示现呼告”两大类。比如,在《节南山》中,诗人以比拟呼告手法,五言昊天:“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我王不宁”。这种把事物人格化的修辞手法,就是直接与想象之物说话——或呼唤,或倾诉,或沟通,或指责,或怒吼,诗人将自己的悲愤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是由于“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2]1900,因而这种表达方式更能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与深度思考。当然,“怨天”只是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尤王”才是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即《诗大序》所谓的“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又如,《将仲子》全诗三章,每章八句,首句皆以“将仲子兮”这一声示现呼告开篇,十分亲密,以透露“爱”仲子的真情实感;然后却要求仲子不要再来会面,并解释心里“爱”但又不敢“爱”的客观原因;在直接袒露了自己“仲可怀也”的心迹之后,又揭示“畏”而不能“爱”的外界压力,即“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当然,如果我们将“我”想象中与“仲子”面对面的情话与“爱”与“畏”错综交织的矛盾心理,结合诗歌创作背景与诗人的创作动机而论的话,郑大夫此诗乃借民间男女之情喻公室君臣、嫡庶、长幼之道,即刺庄公纵容其弟公叔段导致公室庶孽之乱。因此,明代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七十八《洪子问疑录》评之曰:“(《将仲子》)后世君子亦有取焉,以为畏心生而善念存矣!”[6]
2.以设问增强讽谏诗的艺术效果
所谓“设问”,即心中早有定见却在语中故意提出问题的修辞方式。比如,《式微》两章,起句全用设问——“胡不归”,结句则自问自答:“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诗人采用明知故问的修辞手法,比直接的叙述显得更加婉转而有情志。因此,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二评之曰:“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故当不惮淹恤。今言我若无君,何为处此?自言己劳,以劝君归,是极谏之辞。”
又如,《凤兮歌》全诗凡八句,以“凤兮!凤兮”连续两个比拟呼告开篇,紧接着即以“何德之衰”设问,谓凤有道则见而无道则隐,来讥讽孔子不能隐为德衰;故下文自问自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劝谏孔子既然无圣明之君,尚可避乱自隐而不晚;结句又以“今之从政者殆而”来劝谏孔子,谓乱世不可复治,告诫其务必归隐。因此,宋代张栻《癸巳论语解》卷九评之曰:“接舆之意,盖欲夫子隐居以避世耳!观其知凤德之衰,且辞气舒而不迫,其人天资亦高矣!”[7]
3.以夸张增强讽谏诗的表达效果
所谓“夸张”,即一种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的需要而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着意扩大或缩小的修辞方式。比如,《节南山》七章本写寻思避乱之所而无可去之地,然诗人却别出心裁,妙用夸张修辞手法,说“项领”之“四牡”竟是“蹙蹙靡所骋”,以揭示出土地日削、四方昏乱、无处逃遁之政治危局。因此,宋代朱熹《诗集传》卷十一评之曰:“言驾四牡而四牡项领,可以骋矣。而视四方则皆昏乱,蹙蹙然无可往之所,亦将何所骋哉?”[8]146
(四)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强化讽谏诗的审美内涵
“美”与“丑”,既是一对客观存在,更是一对主观认知。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往往运用以“美”为“丑”手法以强化讽谏的审美内涵。正所谓“讽刺之诗,直诘易尽,婉道无穷”[9]者。比如,《节南山》首章“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两句,三章“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六句,皆赞美三公之首太师摄司马皇父尹氏上辅翼天子,下教化万民,秉国政之平,居权衡之正;下文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四句,三章“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两句,却笔锋突兀逆转,揭露其罪责深重而徒有其名。诗人在这里正是运用以“美”为“丑”的反比艺术手法,强化了讽谏的艺术效果,拓展了诗歌的审美内涵。因此,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古诗之意》引苏东坡语评之曰:“诗者,不可言语求而得,必将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10]
又如,《君子偕老》首章“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次章开篇“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七句,皆先极力状写其服饰仪容之美——衣服盛,容貌庄,具有天仙、帝女之貌,可惊鬼神而感天帝。首章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两句作结,次章以“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两句作结,则皆言其行为品德之丑——贵为小君,然无“淑德”,无天仙、帝女之尊,极其卑贱而可鄙!卒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八句,则直言其具有国色天香之姣、倾国倾城之貌,为整个邦国之大美女。诗人先美其形,后丑其质,美丑相对,更显其丑,笔法绝佳,达到了“广揽遐观,惊心动魄,传神写意,有非言辞可释之妙”[11]之艺术境界。
(五)以“卒章显志”结构模式点明讽谏诗的缘由主旨
所谓“卒章显志”,即叙事主体(narrative subject)采用篇末点题方式,为受述者(narratee)表达叙事动机与创作主旨的一种叙事结构模式。比如,《葛屦》二章,前面皆用“赋”体来展开叙事,但在卒章篇末却直接点明“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的创作宗旨。诗人谋篇布局采用以铺陈手法张本而示末之章法,即“卒章显志”结构模式,极富艺术表现力。这种“卒章显志”的结构模式,为其他“风诗”所罕见。因此,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六评之曰:“明点作意,又是一法。”[1]242
又如,《琴歌》三首,前面皆以“赋”体追忆当年出嫁时之贫困、临别时之体恤、离别后之窘境与今日之富贵,然后篇末分别以“今日富贵忘我为”“今适富贵忘我为”“今日富贵捐我为”[12]点明创作主旨,告诫百里奚为秦相后,应富贵不淫而糟糠不易。因此,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六论之曰:“(《秦风·晨风》)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与《扊扅之歌》(《琴歌》)同意,盖秦俗也。”[4]卷6
要之,这一时期的讽谏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较西周时期有了质的飞跃。
三、春秋时期讽谏诗演化的动因及诗学传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及诗歌创作艺术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则是其最根本、最主要的因素。这种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政治生态变迁是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在新兴封建势力的斗争下,内部的矛盾增加,天子威权一落千丈,各诸侯国的独立性急剧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依次出现了“天子守在四夷”“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的政治格局,分别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政治生态。当时孔子所产生的“有道”与“无道”的感叹与困惑,实际上道出了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民政治依次演变的历程。
比如,春秋前期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刺幽王之主旨与戒平王的动机,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王权以中兴王室;而像郑大夫的《将仲子》刺庄公纵容其弟公叔段失君臣长幼之道以致公室庶孽之乱,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维护君权以稳定公室,进而强化王权的社会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王室的讽谏诗人,还是公室的讽谏诗人,他们的创作动机依然是以王权为中心的,诗歌主旨依然是弘扬“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一君民关系。
又如,春秋中期黎大夫的《式微》谏黎侯自卫归于黎,讽谏对象为诸侯国君;而像秦百里奚之妻的《琴歌》讽谏其夫百里奚为秦相后应贫贱不移、不忘糟糠之妻,则是通过维护“上下”“夫妇”人伦关系,来维护“君臣”人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创作动机依然是以君权为中心的,诗歌主旨依然是弘扬“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左传·文公十八年》)这一君臣关系。
又如,像春秋后期楚大夫申包胥的《吴为无道歌》,其主旨为谏秦哀公以师救楚。然从申包胥谓伍子胥(伍员)“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左传·定公四年》)与昭王返国后“辞不受(封邑),遂退隐,终身不见”[13]之言行观之,其所突显者为“我”,而非其“君”;“复国”是为“庇家族”,而非“祐宗子”⑧。可见其创作动机名义上是以君权为中心,实际上是以族权为中心;诗歌主旨自然不再是弘扬君臣关系,而是凸显“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一家族关系。春秋晚期楚陆通的《凤兮歌》讥讽孔子不能隐为德衰⑨,在这位耕隐之士心里,自然不再去关心王权、君权与族权,而是对孔丘落魄境遇的惺惺相惜之情。
由此可见,讽谏诗实际上是“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创作缘由是“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创作动机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大序》)。因此,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的巨大变迁,便成为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社会基础与讽谏诗创作本质性变革的主要动因。
(二)天道观念嬗变是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思想根源
政治思想是政治生态诸元素中最直接、最本质的元素,政治思想巨变的前提则是哲学思想尤其是天道观念的嬗变。
西周时期,由先周时期的“神意政治”进而转变为“天意政治”,“天界”中的上帝神与祖先神开始分离,人王以“天”之子而“受命”治理人世。正由于周人眼里的“天”是一种有意识的人格神,他们便在王权观念基础上,将“明德”与“上帝”结合,形成了“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观念。
降及厉幽之际,人们对于“天”不再寅畏虔恭,而是持怀疑甚至是不满的态度了。如宣王大夫仍叔《云汉》中的“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慧其星”“瞻卬昊天,曷惠其宁”,幽王卿士凡伯《召旻》中的“旻天疾威,天笃降丧”“天降罪罟,蟊贼内讧”,都表达出对天降灾祸的强烈不满。
至春秋时期,“天”之权威开始衰微,天意之尊严已所剩无几。如平王大夫家父《节南山》中的“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平王卿士凡伯《瞻卬》中的“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天何以刺?何神不富”“天之降罔,维其优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藐藐昊天,无不克巩”,秦人《黄鸟》中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不仅表现出诗人对“天”的怀疑与怨恨,而且表现出诗人对“天”的蔑视与谴责——“天”已成为不仁不义、不惠不德、昏庸残虐的暴君,天国大厦的思想根基已逐步为新思想因子所摇撼。
这一时期诗人们之所以仰首向天,怨叹天道无情、降下灾难,展现出天命观念从周初之兴到周末之衰的演变轨迹,这正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念开始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尤王”转变的一种表现。于是,朴素的民本意识逐渐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本思想,诗人们的政治批判意识得以强化,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更加自觉,铁肩担道义的政治责任愈加强烈,他们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8]2便油然而生,自然会把政治批判的锋芒直指现实生活中的最高统治者——周王与国君。故诗谏的历史传统,逐渐转化为一种诗谏的政教制度。
(三)讽谏诗歌创作模式的建立与讽寓诗学批评传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艺术的演化,除了政治生态变迁、天道观念嬗变这些外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诗歌创作艺术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即讽谏创作模式的建立与讽寓诗学传统的形成。
1.讽谏诗歌创作模式的建立
讽谏诗是以诤谏时事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作品。故现实生活中违反传统之事愈多,其创作数量自然愈多。就讽谏诗出现的年代而言,目前明确可考的最早诗篇为《祈招》,为穆王卿士祭公谋父谏止穆王肆心周游之作。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昭公十二年》)由此可知,讽谏诗至迟在周穆王时期开始出现了。
当然,此类诗篇的大量产生,则在厉王之世(约公元前857年—公元前842年)。就诗人的创作动机与诗歌的社会功能而言,讽谏诗与传统颂美诗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批判与歌功颂德。讽谏诗篇政治批判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朝廷谋议缺失、国君亲佞远贤、执政者虐民害人、酗酒败德、妇人干政诸方面。如《诗·大雅》中召伯虎(召穆公)的《荡》《民劳》,芮良夫(芮伯)的《桑柔》,凡伯的《召旻》《板》,等等。甚至有不少诗篇采用“卒章显志”的篇章结构安排方式来明确讽谏对象,以强化讽谏效果,如《诗·小雅》中的《民劳》《板》《何人斯》等。由此可见,“讽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在周厉王时期已初步形成了。
入春秋以后,讽谏诗人的政治批判目的更明确,态度更坚决,方法更直截,语言更犀利,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之类。同时,讽谏诗人群体,不仅仅是王室的贵族诗人,而且包括公室的贵族诗人、平民诗人甚至奴隶诗人。于是,讽谏艺术为社会不同阶层的诗人们所广泛运用,讽谏成为全社会各阶层人们实现政治批判创作动机与社会功能的主要手段。可见,讽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亦即文本写作层面的讽寓(allegory)——采用道德化、寓意化方式进行诗歌创作的基本模式,在春秋时期已完全建立起来。因此,清代吴大受《诗筏》云:“有隐讽者,《君子偕老》一篇,但述其象翟之盛,鬒发之美,眉额之皙,至于‘胡天胡帝’,而犹未已;且缀以‘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则并其亵衣之纤媚而形容之,而以‘邦之媛也’四字结之。羡美中有怜惜慨叹,爱莫能助之意,略无一语及其淫乱。”[14]
2.讽寓诗学批评传统的形成
随着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讽寓模式的出现,理论批评层面的讽寓文学批评模式,即采用道德化、寓意化方式进行诗学批评的基本模式,也应运而生。当然,前者属于作诗范畴,后者属于解诗范畴。此两者虽然互为因果关系,但毕竟不属于同一范畴。就作诗而言,这种道德化、寓意化的创作模式,是以历史性——再现历史语境为基本前提的,其所诉求的是艺术真实;而就解诗而论,这种道德化、寓意化的批评模式,是以情感性——回归情感语境为基本前提的,其所诉求的是审美意识。
就讽寓诗歌创作模式而言,这种影响在西周晚期讽谏诗出现后就已经产生;就讽寓诗学批评模式而论,这种传统至迟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只是因为文献不足,我们一时难以验证而已。就现有文献来看,起码像春秋中期晋公子重耳夫人齐姜引《将仲子》、鲁季孙行父(季文子)《节南山》、荣栾赋《式微》,或直接引述诗句为文,或间接化用诗意为文,或汲取思想营养,或借鉴艺术手法,已经初步具备讽寓诗学批评的特征。至春秋后期孔子采取讽寓方式来引《诗》、论《诗》、释《诗》以论道,其根本目的就是把对《诗》的解读看作对人自身与社会的一种理解,以作为君子人格培养与社会礼仪教化的一种手段,足见当时“讽寓”诗学批评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后经汉儒对《诗》文本的讽寓性解读,讽寓诗学批评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要之,这种解诗范畴的讽谏,不仅来源于作诗范畴的讽谏,而且作用于作诗范畴的讽谏。两者相互作用,对后世讽谏诗的创作与讽谏诗学理论范畴的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批判对象、艺术手法与结构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创造性发展。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注释
①详见:杨简、李清文:《论“大雅”讽谏诗的文化意蕴》,《学术交流》2005年第12期;王慧:《“变雅”中政治讽谏诗生成原因解析》,《华夏文化论坛》2007年;王长华、赵棚鸽:《〈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夏保国:《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祝秀权:《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祝秀权:《“主文谲谏”的周代献诗》,《山西师大学报》2016年第1期;王齐洲:《周代言谏制度与文学发展》,《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②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③笔者将春秋时期划分为前、中、后、晚四个历史阶段。详参: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页。④本文所涉及诗歌作品的创作年代,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及其相关论文,不再逐一标注。⑤本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凡见于《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管子》《战国策》《韩诗外传》《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者,概不逐一标注。⑥本文所引《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毛诗正义》《论语注疏》《尚书正义》,皆据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概不逐一标注。⑦宣姜为齐僖公禄父之女,卫宣公夫人;公子顽为宣公庶子,惠公朔庶兄。⑧包氏出于霄敖熊坎长子蚡冒熊眴,昭王熊轸为霄敖熊坎次子武王熊通七世孙,虽皆属“霄敖”之族,然血缘关系早出“五服”之亲。⑨就出身而言,陆通为楚公族,孔丘为宋公族,皆属贵族;然就其当时的处境而论,陆通自刑身体而避世不仕,孔丘则辞官去鲁而周游列国,皆属“庶人”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