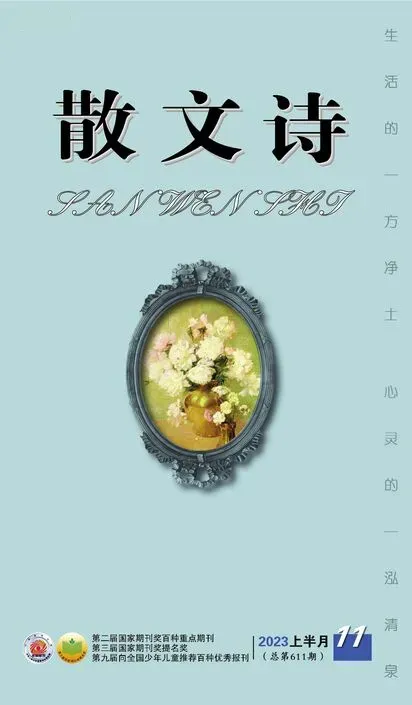大地帖
◎南苡
秋收记
伤疤撕裂,耕种的土地,在秋天又一次被缝合。
铁锨与锄头的用法,没有技巧。
挥动的臂膀,时高时低,一亩要走几行,都有规矩。
庄稼的种与果,在一个人的手上,不做挣扎,不作更改。蚂蚁,翻过土蛋,寻找从前的痕迹。
很多脚印,深深浅浅,留在时光执笔的深处,根深蒂固。丰收的路途,欢笑再一次随风播洒。
由近及远,由低到高,在村庄之外,在屋顶之上。
耕种的晚霞
在玉米地的西边,种一片晚霞,与抽出的须一个颜色。
没有路,通向那里。
借助农具,借用野草的一生,将迟暮的真相,像重提的旧事一般挂在天上。
庄稼人,站在玉米地垄上,最后一次守望。
如此,在晚霞的演绎下,眼前的阡陌,似乎更为漫长。
秋天没有推迟,那些未完成的笔画,跟着风的姿态,穿过土地,穿过天空。
在空旷的人间,章法有度。
葡萄架下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村庄。
葡萄架下,是比村庄更小的一个村庄。
蛐蛐儿的鸣唱,如此悦耳,它的音浪却永远走不出村庄,抵达不了远方。
乡愁,就这样被困在夜晚,夜阑人静,月光如水。
残存的墙体,斑驳如旧,阻挡着太多难以安放的词语。
在词语连接的尽头,是时常赶不回去的故乡。
长路,一段又一段,曲曲折折,铺向秋天,铺向时光的终点。
摘一串葡萄,在不同的时辰。
如此,才不怕旷远的村庄,在一瞬之间,消失不见。
风的长短句
说一句话,被风吹走。
说了三十年的话,被风吹去了哪里?
路上有人回来,相同的身影,要在送葬亲人之时,走回故乡。
村庄的风,在大人的眼中,吹了一辈子,这么长的风,似乎一辈子都吹不完。
可是,风与风之间,却又大相径庭。
风再短,都不会去走人走的路。
它们时而温柔,时而冰冷。它们在人间的路,无比艰难。
高贵,贫穷,喧闹,荒凉。
一片叶落了,是风;一个季节走了,是风;一个人走了,会是风吗?
风的一生或长或短,都在人间发生,也都在人间散场。
草木书
时令已过立秋,草木的样子依旧热烈。
站在山坡上,草木饱满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幅遗失千年的画,落款无从考证。
周围的留白,在人与牲口的生活下,纹理粗糙,注解着世事沧桑。
叶还在树上,草还在地上。
昆虫与植物,作为原野之上的主人,它们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承载着秋在自然法则上的规律。
螳螂,蟋蟀,花生,玉米。
高低错落,在适当的位置,随性而为。
等一场雨,颂一场风,草木的故事,事到如今,已成定局。
故乡帖
时光加载,一些人流经那条河,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人记录一个人的出走,也没有人记录一个人的归来。
再大的尘埃,也不会将一座村庄隐藏,生命落在人间,越往前走,越难回头。
故乡的符号,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也会在一个人身上消失,无法以笔记载。
在路上,转过身再回望故乡,只是大地上的一个点。
恰恰是这些点,才会让更多人的一生,灵魂上都有一扇门,永远无法关闭。
月光,在秋风吹起的夜晚,等相思落下,等笔上路,等心——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