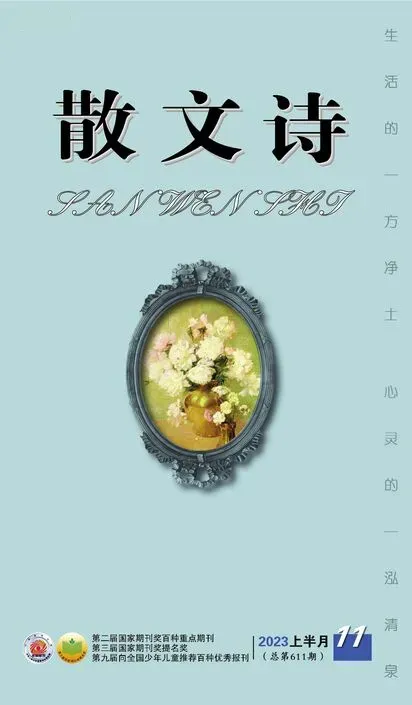袁家渡
◎王业旺
消失的渡口
先是高滔浊浪,斩断退路;再是涓涓细流,烟火萦绕。
尔后是高滔浊浪,又替代涓涓细流。
风在风里,水在水里。
交替,大喜大悲交替,大起大落交替。
在渡口,春与秋交替,生与死交替。
在渡口,谁能举起一滴水的重量?
它从不游戏人间,却一直在动荡与不安中行走。它从不停顿,只是如实地记录人间来来去去的生老病死。在哭与笑中,在乐与悲中,记录生活中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记录生命路程上的坎坷与颠簸。
它记录了人间,却没有记录自己。使命完成,默默消失——这,就是曾经的袁家渡,现在叫毛畈。
仿佛山水的空白处,它的历史一片空白。仿佛一缕云烟飘过,没有痕迹。它没有舞台,也就没有谢幕:它,只是进了另一道门。
渡
一滩沙涂,一滩杂草,一湾细水。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袁家渡。
已经习惯了赤足站在河里,洗涤碎花的裙裙和绣着大红牡丹的被套,并且晾晒在河滩的石头上,然后在夜里暗自神伤。
已经习惯了用柴火编织的火苗,炒一盘豆角,炒一碟扁豆,再炒一碗腊肉,并端上桌。然后,倚门张望。
袁家渡,像一根晾衣绳,牵系着一茬人又一茬人的思念,牵系着大山深处的烟火。
现在,它只是隐藏了往日的喧嚣,它只是洗尽了岁月的浮华。
素颜向天。
滞留在时间之上的船工号子隐隐约约,依然在季节的渡轮上回旋。曾经的大水,只在记忆里流淌。
它不是穿梭的鱼,有自己的远方。
它只是捆绑在这堤河岸上一个永久的纤夫。
有缘的,渡;无缘的,渡。渡走了该渡的,渡走了不该渡的。
渡不走的是自己。
慰藉
前方,是水,后方,也是水;
左岸,是山,右岸,也是山。
袁家渡,水托起的婴儿;
袁家渡,山养大的孩子。
溪水涨了,便是渡口,便是排,便是船。摇到外婆家的小木船,摇过潜水,摇过皖水,也在长江摇过。
一方渡口,一席方言,有古老的残留,走到哪里,都像是替家乡代言。
洪水去了,竹篙便是扁担,一头插在屋里,一头插在山里。山路和水路一样,压弯了腰。
脚印又深又沉。一个脚印紧挨着一个脚印,一个脚印搀扶着一个脚印。一队队,一群群,在风中颤颤巍巍;在山涧蜿蜒辗转。
摇摆着,山路,悬在悬崖上。摇摆着,陡峭,险峻。
摇摆着,抬着轿。摇摆着,抬着棺。
锣鼓敲起来,鞭炮响起来,迎亲。
锣鼓敲起来,鞭炮响起来,出殡。
生也是,死也是,喜也是,悲也是。
锣鼓敲起来。鞭炮响起来。
在孩子们眼里
渡口荒废了,滩涂还在。大水退了,野草肥美。
——孩子们的乐园。
河边,孩子们放着折叠的小纸船,这是他们眼里的星辰大海。
孩子们是善良的。追逐蝴蝶的时候,他们也是飞舞的蝶。他们追的只是快乐,却不赋予任何含义。
在孩子们眼里,即使一平方的草地,也是心里的大草原。他们会用柳枝编织的帽子,戴在头上加冕。他们采下狗尾巴草,放在手心里,捻呀捻,旋转的尾巴,一粒粒草籽飞在手心。抛向空中,又落在河滩上,寻不见了。
快乐,一直都在孩子们眼里。
一个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株蒲公英,像摘下一朵纯真的梦,一朵白色或黄色的小绒花,放在唇边,轻轻一吹。一朵朵蒲公英飘了起来。于是,嬉戏的孩子们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这是孩子们一颗颗飞翔的心。如此令人怦然心动。
花絮漫天飞舞——世界,只剩下纯美与纯净。